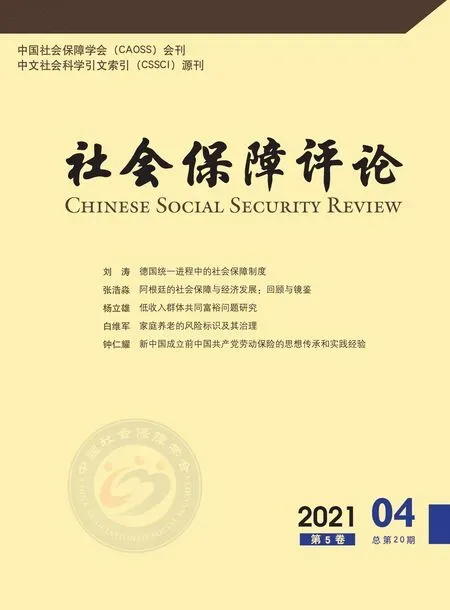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問題研究
楊立雄
一、引言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遠景目標,要求“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2021年5月20日)提出建設“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為此,需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升“低收入群體增收能力和社會福利水平”。如果說“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那么,“提升低收入群體增收能力和社會福利水平”則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難點。低收入群體實現共同富裕面臨什么挑戰?共同富裕要達致什么目標?以及如何實現低收入群體的共同富裕,這是本文要解決的幾個關鍵問題。
在討論上述問題前,需要對低收入群體這一概念做出界定。目前,學術界對低收入存在兩種理解:一是將低收入與貧困等同起來,認為低收入是收入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種狀態。①厲以寧:《論共同富裕的經濟發展道路》,《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5 期。二是將貧困與低收入區分開來,要么貧困包含了低收入,②楊云善:《著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6年第6 期。要么低收入包含了貧困。③楊云善:《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基本途徑》,《社會主義研究》2006年第3 期。在政府發布的政策文件中,對于低收入存在兩種理解:一是社會政策定義,即實施社會政策時所界定的人群范圍,通常將低收入界定為人均收入高于低保標準、低于低保標準的一定倍數(通常為1.5 倍)的群體,或者將低收入界定為低保標準的一定倍數以下的所有群體;二是統計調查定義,即將所有家庭收入按五等份劃分,處于底層20%的家庭即為低收入戶。本文所說的低收入群體是指家庭人均收入在低收入線以下的人口。需要說明的是,目前我國尚未建立低收入線。因此本文所說的低收入群體并不基于特定的低收入線測算而得,而是指收入處于社會較低層次的人群,通常指按五等份劃分的低收入戶(20%)。在這些低收入戶中,兜底保障人群(如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供養、其他社會救助對象)、臨時救助對象、支出型貧困以及貧困風險等人群組成是低收入戶重點關注對象。
二、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的實踐與探索
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實現共同富裕一直是黨和政府高度關注的問題,由此采取了多項措施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包括實施扶貧開發和脫貧攻堅戰略、建立兜底保障體系、實施收入倍增計劃等。這些措施收到顯著成效,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存得到有效保障,但是也存在需要改進的方面。
(一)共同富裕思想與低收入群體的脫貧之路
改革開放以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成為黨和國家的根本發展戰略,但是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目的和根本目標并沒有改變。歷屆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均把共同富裕提升到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和黨執政的必然要求。鄧小平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就是實現共同富裕”,①《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5 頁。鄧小平將共同富裕提升為社會主義的本質,他說,“社會主義最大的成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②《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 頁。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所提倡的共同富裕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提出來的,目的在于打破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解放生產力。為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應首先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些先富起來的地區上繳更多的稅收,國家將其向不發達地區傾斜,改善基礎設施,實施扶貧開發,帶動落后地區和貧困人群走向共同富裕。江澤民堅持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原則,強調“從根本上說, 高效率、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質決定的。”③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37 頁。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加快分配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江澤民要求“正確處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關系,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形成一個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數、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數的“兩頭小、中間大”的分配格局,使人民共享經濟繁榮成果。”④《江澤民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0-541 頁。進入新世紀后,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是收入差距也快速拉開。為此,胡錦濤多次強調要妥善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要更加關注社會公平,并把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內容,要求“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712 頁。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發表講話時談到,“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2021年1月28日,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又強調“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目標。”這些論述豐富了共同富裕的內涵,提升了共同富裕的地位。
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過程,黨和政府始終把貧困問題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將其納入國家發展戰略,采取一系列措施解決農村低收入群體的發展問題;同時,自20 世紀90年代開始逐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起覆蓋全民的社會安全網,解決了低收入群體的生存之憂。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的探索和實踐,其措施主要有:一是農村扶貧開發。自1986年起,我國政府開始在農村實施大規模扶貧開發戰略,先后制定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等減貧規劃,走開發式扶貧的道路,通過多種方式和途徑,采取綜合配套措施,幫助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經過20 多年不懈艱苦奮斗,中國的扶貧開發取得了巨大成就:解決了兩億多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農村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貧困人口由1978年的2.5 億人減少到2000年的3000 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從30.7%下降到3%左右。②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農村扶貧開發白皮書》,國務院新聞辦官網: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1/Document/307929/307929.htm,2001年10月15日。進入新世紀后,國家把扶貧開發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加大公共財政預算,堅持開發式扶貧和社會保障相結合,農村扶貧開發取得新成就:以新標準衡量的農村貧困人口數量從2000年底的9422 萬人減少到2010年底的2688 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2.8%。③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新進展白皮書》,國務院新聞辦官網:http://www.scio.gov.cn/zxbd/nd/2011/Document/1048657/1048657.htm,2011年11月16日。二是建立全民兜底保障體系。1993年上海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拉開了城鎮兜底保障體制改革的序幕。1997年,在全國層面正式開始建立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在全國層面正式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圍繞最低生活保障,政府逐步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社會救助體系,改革五保供養制度和臨時救助制度,完善災害救助制度,建立醫療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制度,切實保障了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截至 2020年底,全國共有城市低保對象488.9 萬戶、805.1 萬人,農村低保對象1985.0 萬戶、3620.8 萬人,城鄉特困人員447.5 萬人,全年共實施臨時救助1380.6 萬人次。④民政部:《2020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民政部官網: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2109/20210900036577.shtml,2021年9月10日。三是實施收入倍增計劃和農村脫貧攻堅戰略。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首次將居民收入倍增納入黨的報告,提出“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13年3月,《國務院批轉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通知》(國發〔2013〕6 號)下發,進一步明確了城鄉居民收入實現倍增的目標,要求力爭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長更快一些。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意見還強調,要集中更多財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十二五”時期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提高兩個百分點左右;加強對困難群體救助和幫扶,健全城鄉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逐步提高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湖南湘西,首次提出“精準扶貧”的戰略構想。隨后,國務院扶貧辦多次下發文件,加快了精準扶貧工作機制的建立,加強了建檔立卡工作。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標志著農村反貧困進入新的階段。經過多年的持續奮斗,到2020年底,如期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貧困人口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大幅提高,“兩不愁三保障”全面實現。
(二)經驗與不足
我國對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的探索取得顯著成效,到2020年底,我國消除了絕對貧困現象,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探索歷程,有經驗也有不足。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經驗與不足:
一是重視區域差距,忽視群體差距。20 世紀80年代,農村貧困問題主要集中于老、少、邊等地區。為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降低貧困發生率,1986年,國務院成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1993年后改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核定了592 個貧困縣,并將其作為基本扶貧單位;劃定18 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實施連片開發。進入新世紀后,國家將扶貧開發重點從瞄準貧困縣轉向貧困村和貧困戶;2013年以后,瞄準對象重點轉向貧困戶(即建檔立卡貧困戶),但是促進貧困縣脫貧摘帽、促進深度貧困地區發展仍然是精準脫貧的重點任務。經過多年奮斗,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得到明顯改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明顯提升,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徹底解決。①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國務院新聞辦官網:http://www.scio.gov.cn/ztk/dtzt/44689/ 45216/45224/Document/1701692/1701692.htm ,2021年4月6日。除扶貧開發外,國家針對地區發展差距,還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中部崛起計劃、東北振興戰略。上述措施收到一定效果,2002—2013年,不同地區的人均收入差距呈現下降趨勢,東部與中部的收入比從1.69 下降到1.40,東部與西部的收入比從1.70 下降到1.51。②吳彬彬、李實:《中國地區之間收入差距變化:2002—2013年》,《經濟與管理研究》2018年第10 期。但是在區域差距有所下降的同時,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卻在持續上升。200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為0.479,到2008年達到0.491,③參見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中國住戶調查年鑒(2020)》,中國統計出版社,2020年。此后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從總體上看基尼系數仍然保持較高水平。此外,我國財富的不平等程度超過收入不平等程度。研究數據表明,1995—2015年,中國最富10%人群的財產占全部財產的比重從40%上升到65%。①Thomas Piketty, et al.,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23368, 2017.
二是重視生存兜底,忽視生計發展。為適應市場經濟轉型的需要,自20 世紀90年代開始,政府改革社會救濟制度,建立包括低保、特困人員供養、受災人員救助、醫療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就業救助、臨時救助在內的“兜底”保障體系。近些年來,在農村脫貧攻堅的要求下,各地進一步豐富了兜底保障項目,較大幅度地提升了兜底保障標準,進一步筑牢了社會安全網。但是重視“兜底”保障的同時,忽視低收入群體的生計發展,低收入群體易陷入“貧困陷阱”之中,出現貧困代際傳遞發生率高于絕對貧困發生率的現象。②吳繼煜等:《多維因素視域下貧困人口代際傳遞特征研究》,《人口學刊》2021年第4 期。而日漸提升的“兜底”水平和日趨豐富的保障內容對受助者的就業激勵產生負面影響,獲得低保救助后勞動供給傾向下降;③文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兼有消費改善與勞動供給激勵效應嗎?》,《上海經濟研究》2021年第2 期。而且,隨著兜底保障時間的延長和轉移支付水平的提升,兜底保障對象尋找到工作的概率顯著降低。④慈勤英、蘭劍:《“福利”與“反福利依賴”——基于城市低保群體的失業與再就業行為分析》,《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 期。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兜底保障制度的設計缺陷(如100%的收入邊際稅率、福利疊加、連帶利益等)和人力資源開發不足是兩個主要原因。兜底保障對象普遍存在缺乏勞動技能、學歷層次低、市場競爭力弱、就業穩定性差等問題,各地對其人力資源開發存在畏難情緒,往往采取簡單的“一兜了之”做法,而在職業介紹、就業培訓、崗位開發等方面缺乏相應的配套制度,再加上現金轉移支付產生的收入效應,從而造成福利依賴和就業陷阱。
三是重視收入提升,忽視公共服務。進入21 世紀,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收入型貧困大大減輕,但是受教育產業化、醫療費用和房價快速上漲的影響,居民貧困形態從收入型貧困轉向支出型貧困,快速增加的剛性支出擠占了居民基本生活支出,導致部分家庭陷入生活困境。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我國居民的居住支出和醫療保健支出分別只占消費支出的14.39%和5.94%,到2019年,上述支出占消費支出的比例上升到23.45%和8.82%,其中:城鎮居民的兩項支出占消費支出的比例分別從13.52%和6.38%上升到24.16%和8.13%,農村居民從15.83%和5.21%上升到21.54%和10.66%。⑤參見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中國住戶調查年鑒(2020)》,中國統計出版社,2020年。研究表明,支出型貧困已成為致貧的主要原因。如:武漢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因病致貧的比例達到61.1%,因殘疾致貧達到23%,因學致貧占比4.8%,其他致貧的接近4.9%。⑥張明麗、范艷玲:《因病支出型貧困家庭的社會救助問題研究——以武漢市為例》,《經濟研究參考》2020年第24 期。造成支出型貧困的重要原因在于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不完善或服務水平偏低,如:醫療報銷水平低,個人自負過高;養老托殘服務體系不健全,通過市場獲得的照料服務導致家庭負擔過重;住房保障受益面窄,夾心層家庭住房問題凸顯。
四是關注絕對貧困,忽視相對貧困。長期以來,反貧困政策主要聚焦于解決由收入不足引起的絕對貧困問題,由此導致反貧困政策的目標聚焦于赤貧群體。在制定保障標準時,以解決絕對問題為目標,因而長期維持一個較低的標準。與發達國家以中位收入的60%的標準相比,我國低保標準仍然偏低,尤其是城鎮低保標準偏低的問題較為突出。2020年,各省市農村平均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與農村民居人均收入的比例最低為27%(吉林和黑龍江),最高值為47%(北京),中位值為36%;各省市城鎮平均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與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最低只有16%(湖南省),最高只有25%(天津、廣西、西藏),中位值為20%。隨著絕對貧困的逐步緩解,并受低保過低標準的影響,導致社會救助受益面逐步收窄。全國城鄉最低生活保障人數高峰時期保障人數超過7000 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超過5%,但到2021年第2 季度,全國最低生活保障受助人數下降到4311.3 萬人,受助率下降到3%左右,北京、上海、江蘇和浙江的低保受助率已低于1%。
五是重視行政主導,忽視社會參與。在探索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政府發揮主導性作用,成立了專門機構,制定了各項計劃,加大了財政投入,取得了顯著成效;同時在政府主導下,發動社會力量對貧困地區和低收入群體進行幫扶,采取定點扶貧、東西扶貧協作等方式進行扶貧。但是這種基于“父愛主義”的扶貧理念和“命令-控制”型的行政管理模式,導致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探索過程中社會力量參與激勵不足。①楊立雄、魏珍:《相對貧困治理機制研究——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視角》,《社會政策研究》2021年第2 期。在扶貧開發和精準脫貧過程中,定點扶貧和東西扶貧協作呈現行政主導特征,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仍然處于初步發展階段;《社會救助暫行辦法》第十章專章規定社會力量參與,民政部在其下發的《關于做好當前困難群眾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也再次強調社會力量參與,但是從總體上看,社會力量參與低收入群體的共同富裕實踐中,存在社會力量參與面窄(主要集中于醫療救助領域)、資金規模小等問題,社會力量救助對政府救助的補充作用有待進一步提高。
三、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面臨的挑戰
經過多年的持續奮斗和不懈努力,我國從一個底子薄、基礎弱、國情復雜的發展中國家邁入全面小康社會,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同時,建立了低收入群體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機制,兜底保障制度逐步健全,保障內容和保障水平逐步提高。但是也應該看到,我國仍然存在數量較為龐大的低收入群體,他們與社會平均收入存在較大差距,實現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面臨較大的挑戰。
(一)低收入群體實現共同富裕任務艱巨
首先,我國低收入群體數量龐大。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國家整體經濟實力升至世界第2 位,人均GDP 突破1 萬美元大關,整體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吃不飽”“穿不暖”的現象基本消滅。但是,我國仍然存在規模龐大的低收入群體。處于第一圈層的為社會救助對象(包括特困人員、低保對象、住房救助對象、醫療救助對象、教育救助對象等),通常由老弱病殘等人群組成,具有貧困程度深、脫貧難度大等特點。2020年底,全國特困人員和城鄉低保對象社會救助對象超過4556 萬人,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對象1214.0 萬人,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對象1475.1 萬人。①上述各類社會救助對象有重合。參見民政部2021年9月10日發布的《2020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處于第二層次的為貧困邊緣戶及臨時困難家庭,這些家庭收入處于社會救助之上,不符合社會救助條件,但是處于脫貧不脫困的狀態,包括:低保邊緣戶、支出型貧困家庭以及建檔立卡脫貧戶中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易致貧戶。目前,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易致貧戶近500 萬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達到5954.16 萬人;②參見民政部2021年9月10日發布的《2020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教育部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2021年9月16日發布的《2020年中國學生資助發展報告》。自疫情發生以來,農民工、個體經商戶、靈活就業等群體受到較為嚴重的沖擊,這些邊緣群體因疫陷入貧困的概率大幅度上升。據估計,全國失業人數至少在1000 萬人以上,另有上億農民工滯留家中。而據學者的計算,處于低保之上、低收入標準之下的人口數量至少達到1 億人。③高強、曾恒源:《中國農村低收入人口衡量標準、規模估算及思考建議》,《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 期;李瑩等:《中國相對貧困標準界定與規模測算》,《中國農村經濟》2021年第1 期。處于第三層次的為工作貧困、中低收入群體。對工作貧困問題的研究表明,我國工作貧困主要集中于靈活就業者、勞動密集型行業從業者、低學歷者、農民工等人群,工作貧困發生比例呈現逐年上升的態勢,到2010年,四成以上的工作者其家庭收入低于貧困線。④姚建平:《中國城市工作貧困化問題研究——基于CGSS 數據的分析》,《社會科學》2016年第2 期。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收入五等份劃分,2019年的低收入組和中間偏下收入組共40%家庭戶對應的人口為6.1 億人。而根據李實的測算,2019年我國低收入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60%以上。⑤李實等:《縮小收入差距 推進共同富裕社會建設》,《中國經濟報告》2021年第4 期。
其次,低收入群體離“富裕”存在較大差距。雖然低收入群體的家庭收入呈現穩步增長趨勢,但是從總體上看,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存仍然較為艱難。2021年第2 季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標準只有693.5 元/月,占2021年上半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比僅為19.34%;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6150.4 元/年,占2021年上半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比為38.65%。上述兩個指標與國際通用的相對貧困標準(通常為中位收入的40%、50%、60%)仍然存在差距。多數地區殘疾人“兩項補貼”現金補貼標準處于每人每月100—200 元之間,甚至還有部分地區只有50 元左右,難以起到緩解殘疾人生活和護理支出壓力的作用。城鄉居民養老金水平也不高,中央政府負責的基礎養老金每人每月只有93 元,多數地區平均養老金低于2000 元/年。再看最低工資,2021年上半年多數地區的最低工資低于2000 元/月,最高(上海)為2590 元,最低(安徽最低檔)只有1180 元。再看低收入戶(20%)的家庭人均收入,2019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380.4 元,僅相當于中間偏下收入戶(20%)的家庭人均收入的46.78%。①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0)》相關數據整理計算所得。除此之外,低收入家庭成員中失能、殘疾、患病等情況較為常見,其康復、醫療、照料等支出較大,導致其生活質量大幅度下降。
最后,低收入群體與社會平均收入的差距較大。我國貧困形態自20 世紀90年代逐步轉型,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絕對貧困現象已基本消滅。但是,由于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在居民收入不斷增長的情況下,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速度仍然低于平均速度,導致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世界銀行的計算表明,1990年中國基尼系數為0.322,隨后持續上升,到2010年達到0.437,2015年下降到0.386,在159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在第68 位;②IndexMundi, China-GINI Index (World Bank Estimate), https://www.indexmundi.com/facts/china/indicator/SI.POV.GINI.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數據顯示,2004年,基尼系數為0.473,隨后持續上升,到2008年達到0.491,隨后逐年下降,但是目前仍然超過0.4,居民收入保持較高的不平均狀態。按照收入五等份劃分,發現低入戶與其他收入戶的絕對差距與相對差距均在持續拉大。2000—2019年,農村低收入戶(20%)人均純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的差距從1451.4 元擴大到2019年的11758.1 元,收入差距(即人均純收入/低收入戶(20%))從2.8 倍上升到3.8 倍;城鎮低收入戶(20%)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從3148 元擴大到2019年的26809.4 元,收入差距從2 倍上升到2.7 倍以上。分組比較來看,2000年至2019年,城鎮低收入戶(20%)與中等偏下戶(20%)、中等收入戶(20%)、中等偏上戶(20%)和高收入戶(20%)的收入差距分別從1.5 倍、1.9 倍、2.4 倍和3.6 倍上升到1.7 倍、2.4 倍、3.4 倍和5.9 倍;農村低收入戶(20%)與其他四組的收入差距從1.8 倍、2.5倍、3.5 倍和6.5 倍上升到2.3 倍、3.3 倍、4.6 倍和8.5 倍(見圖1、圖2)。

圖1 城鎮居民低收入戶與其他收入戶收入差距發展趨勢

圖2 農村低收入戶與其他收入戶收入差距發展趨勢
(二)低收入群體的分配弱勢
造成低收入群體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低收入群體在分配中處于弱勢地位。主要表現在:
首先,低收入群體在第一次分配中處于弱勢地位。低收入群體以年老失能者、重度殘疾人、健康欠佳者等人員為主;無業人員、靈活就業人員和失業人員所占比例長期處于較高水平;一戶多殘家庭、老殘一體家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受教育程度低,綜合素質不高,職業技能不足,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甚至有較高比例的低收入群體是市場競爭的失敗者。現行反貧困制度安排重在保障生存權,通過建立和完善社會安全網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這種保障方式簡單易行,保障效果立竿見影,但是單一的現金救助方式忽視了被救助者及其家庭的能力建設,無法幫助他們實現自立自助。對山區貧困問題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低、勞動參與能力弱等因素導致了低收入群體市場參與率低,并由此形成長期貧困和貧困代際傳遞;而貧困又進一步降低低收入群體的市場參與率,形成貧困陷阱。①郭志儀、祝偉:《我國山區少數民族貧困成因的框架分析——基于市場參與率的視角》,《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 期。
其次,國家再分配力度有待加強。低收入群體收入來源單一,尤其是最貧困階層,他們多數沒有勞動能力,在第一次分配中處于弱勢地位,作為一種轉移支付,社會救助直接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有效彌補第一次分配的不足;另外,部分低收入群體致貧原因是剛性支出超出家庭的承受范圍,社會救助對災難性支出家庭予以補償,緩解家庭貧困程度,也增加了低收入群體的收入。社會救助制度是政府對低收入群體的財政轉移支付,它通過貨幣或實物的形式,直接或間接地增加了受助者的收入,因而對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會產生影響。從總體上看,我國社會救助(包括城鄉低保、醫療救助和其他救助)支出呈現穩步增長的態勢。2001年,社會救助支出90.6 億元,到2019年增加到2281.4 億元,①根據《中國民政統計年鑒(2020)》相關數據整理計算所得。增長了25 倍。社會救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從0.48%上升到0.9%;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與就業、住房保障及扶貧等方面的財政支出水平占GDP 的比重從2003年的5.23%上升到2015年的9.37%,加上社會保險基金支出,其比例為15.37%。②關信平:《當前我國社會政策的目標及總體福利水平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6 期。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轉移支付的力度較弱,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2019年,OECD 國家的平均社會支出水平達到20%③OECD, Social Expenditure—Aggregated Data,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SOCX_AGG.)。
最后,第三次分配作用有待提升。雖然第三次分配并不能讓低收入群體實現共同富裕,但是它在促進收入分配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些年來,我國慈善事業穩步發展。《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20)》顯示,到2019年,我國社會公益資源總量為3374 億元,彩票公益金募集量為1140.46 億元,互聯網公開募捐、“99 公益日”募捐等約43 億元。④楊團、朱健剛:《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2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3-7 頁。這些捐贈資金主要用于扶貧。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有4.1 萬個社會組織開展了6.2 萬個扶貧項目,投入資金超過600 億元。⑤楊團、朱健剛:《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2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12 頁。中國慈善聯合會發布的《2019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顯示,2019年全年接收境內外款物捐贈只有1701.44 億元人民幣,慈善捐贈投向教育、扶貧和醫療三個領域的資金分別為440.31 億元、379.02 億元、272.23 億元。⑥中國慈善聯合會:《2019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官網:http://www.cncf.org.cn/storage/ueditor/fi le/2020/09/19/39c9155e41612e431eb076253d1777ec.pdf。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第三次分配的規模偏小,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很小。如:美國Giving USA Foundation 出版的慈善捐贈報告《Giving USA 2021: The Annual Report on Philanthropy for the Year 2020》的數據顯示,2020年度,美國慈善機構收到各類捐贈約4714.4 億美元,其中個人捐贈3241 億美元、基金會捐贈885.5 億美元、遺贈411.9 億美元、公司捐贈168.8 億美元。⑦Giving USA 2021: In a Year of Unprecedented Events and Challenges, Charitable Giving Reached a Record $471.44 Billion in 2020, https://philanthropy.iupui.edu/news-events/news-item/giving-usa-2021:-in-a-year-of-unprecedentedevents-and-challenges,-charitable-giving-reached-a-record-$471.44-billion-in-2020.html?id=361, 2021-6-15.根據統計,個人捐贈占GDP 的比排在前五的國家是:美國(1.44%)、新西蘭(0.79%)、加拿大(0.77%)、英國(0.54%)、韓國(0.5%),而中國僅只有0.03%,在24 個國家中排在最后一位。⑧這24 個國家分別是:美國、新西蘭、加拿大、英國、韓國、新加坡、印度、俄羅斯、意大利、荷蘭、澳大利亞、愛爾蘭、德國、瑞典、奧地利、芬蘭、日本、法國、挪威、瑞士、西班牙、捷克、墨西哥和中國。參見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Gross Domestic Philanthropy: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GDP, Tax and Giving, https://www.cafonline.org/docs/default-source/about-us-policy-and-campaigns/gross-domestic-philanthropy-feb-2016.pdf.
四、低收入群體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與路徑
實現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首先需要對共同富裕的內涵進行界定,由此才能確定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的目標。可以確定的是,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首要目標是達致富裕,然后才是縮小與平均收入的差距。基于此,需要采取適合低收入群體特征的措施,最終達致共同富裕的目標。
(一)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目標
早期學者在研究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①參見陳中玉:《論鄧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思想》,《理論探討》1994年第5 期;徐海茳:《鄧小平“先富后富共同富”思想的哲學思考》,《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4年第1 期;吳廣良、吳國柱:《論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南京政治學院學報》1994年第1 期。時,將共同富裕理解為群體之間收入差距縮小的過程,如:陳德華認為共同富裕是“富的越富”,“窮”與“富”縮小差距的過程;②陳德華:《社會生產力、市場經濟、共同富裕與公有制》,《經濟學動態》1998年第1 期。宋濤認為共同富裕是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增加社會產品的產量,逐步增加全國人民的收入的過程。③宋濤:《學習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經濟評論》1998年第1 期。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標之后,學者對共同富裕理解超越了收入范疇。如:張來明、李建偉認為共同富裕包括了收入分配公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機會均等、健康公平及資源普惠;④張來明、李建偉:《促進共同富裕的內涵、戰略目標與政策措施》,《改革》2021年第9 期。楊宜勇認為共同富裕包含了全民共富、共創共建、全面富裕、共同致富能力和逐步富裕;⑤楊宜勇、王明姬:《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的標準及實現路徑》,《人民論壇》2021年第23 期。劉培林等人進一步擴展了共同富裕的內涵,包括:政治內涵,即國強民共富的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經濟內涵,即人民共創共享日益豐富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成果;社會內涵,即中等收入階層在數量上占主體的和諧而穩定的社會結構;⑥劉培林等:《共同富裕的內涵、實現路徑與測度方法》,《管理世界》2021年第8 期。陳麗君等人認為共同富裕具有發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續性三大特征,并由此構建了包含3 項一級指標、14 項二級指標、81 項三級指標的共同富裕指數模型。⑦陳麗君等:《共同富裕指數模型的構建》,《治理研究》2021年第4 期。分析“富裕”詞義,是指財物充裕豐富或經濟寬裕,其核心詞義在于錢財充足,因此收入是衡量“富裕”的關鍵性指標。而上述越來越多的指標已經遠遠超越了“富裕”含義,涵蓋了公共服務、社會權利甚至政治權利,導致共同富裕的目標復雜化。為此,需要化繁為簡,回歸本意,即:解決了溫飽, 能夠維持簡單再生產,達到社會所公認的基本生活水平的一種狀態,且收入差距逐步縮小。基于上述理解,制定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的目標就變得簡單,即:一是讓低收入群體達到富裕;二是縮小低收入群體與社會平均收入的差距。
從某種意義上說,富裕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具有時空性。為簡便計,在此不去制定低收入群體富裕的絕對收入水平,而以相對標準為重點制定低收入群體的共同富裕目標。回顧2000—2019年收入發展趨勢,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從6280 元增長到42358.8 元,年均增長率10.60%;而城鎮低收入戶(20%)的人均收入從3132 元增長15549.4 元,年均增長率只有9.34%,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低收入戶(20%)的收入差距從2.01 倍上升到2.72 倍;農村人均純收入2253.4 元增加到16020.7 元,年均增長率接近11%,農村低收入戶(20%)人均純收入從802 元增加到3319.7 元,年均增長率不到9%,農村人均純收入與低收入戶(20%)的收入差距從2.81 倍上升到3.76 倍。而城鎮低收入戶(20%)與農村低收入戶(20%)的收入差距從3.9 倍上升到4.7 倍。因此制定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的最低收入標準,既要縮小低收入群體與社會平均收入的差距,也要縮小城鎮低收入群體與農村低收入群體的差距。為此設定三個目標:到2035年,城鎮低收入戶(20%)與城鎮平均收入的比降到2 倍以下,農村低收入戶(20%)與農村平均收入的比降到2.5 倍以下,城鎮低收入戶(20%)與農村低入戶(20%)的收入比降至3 倍以下。假設居民收入增長為5%,①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十四五’期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基本同步”。“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十四五’期間,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處于5%—5.5%之間”。則城鎮低收入戶(20%)的年均收入增長率應達到7%(即超過平均收入2 個百分點),農村低收入戶(20%)的年均收入增長率8.3%(即超過平均收入3 個百分點以上)。城鄉低收入戶(20%)收入增長目標預測如圖3 所示。

圖3 城鄉低收入戶(20%)收入增長目標預測
2019年,城鎮低收入戶(20%)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549 元,農村低收入戶(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263 元,按上述目標發展,到2035年,城鎮低收入戶(20%)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5562 元,農村低收入戶(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266 元,農村低收入群體與農村平均收入的差距降至2.3 倍,城鎮低收入戶(20%)與城鎮平均收入的差距降至2 倍,城鎮低收入戶(20%)與農村低收入戶(20%)的差距降到3 倍。
(二)低收入群體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
結合低收入群體特征,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促進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
一是幫低收入群體“掙錢”,通過勞動創造美好生活。通過市場獲得收入,通過勞動創造財富,是個人和家庭擺脫貧困、進入小康、邁向富裕最重要的途徑,是低收入群體實現富裕的主要途徑。首先,加大低收入群體人力資源開發,提升市場競爭能力。研究表明,家庭在教育方面的花費能顯著降低其貧困的脆弱性,而且對貧困家庭的降低程度大于非貧困家庭;①斯麗娟:《家庭教育支出降低了農戶的貧困脆弱性嗎?——基于CFPS 微觀數據的實證分析》,《財經研究》2019年第11 期。教育支出對農民增收的影響遠高于其他扶貧舉措。②彭妮婭:《教育經費投入對貧困地區農民收入影響的實證》,《統計與決策》2021年第3 期。因此,要把低收入群體人力資源開發放在實現共同富裕的第一位,政府要大幅度增加教育與職業培訓投入,尤其是對失業者和有勞動能力的無業者,要重點加強其職業技術培訓,提升勞動參與率。
其次,大力開發公益性就業崗位,創新就業形式。各地開發綠色生態類、社區服務類公益性崗位,實現一人就業、全家脫貧的目標。隨著生活質量的提升,公眾對對托幼養老助殘服務類需求快速增加,社會服務人才較為缺乏,為此,政府加大購買服務和公益性就業崗位開發力度,吸引低收入群體就業,達到一舉兩得的目標,既改變了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同時也增加了低收入群體的收入。
最后,改革福利制度,提升就業回報率。包括:針對勞動年齡段有就業能力的福利受益者,改無條件救助為有條件受益(受益與培訓掛鉤、限制受益時間、降低福利待遇);對有勞動能力的低收入群體強化就業救助成先原則,將主動就業、主動創業或積極履行就業培訓的義務作為接受救助的前提條件。③李成威、于雯杰:《激勵性就業扶貧機制構建:德國哈茨法案的啟示》,《財政科學》2019年第8 期。同時,構建正向的就業激勵機制,對主動就業、主動創業或積極接受就業培訓的受助者給予物質和精神雙重獎勵,即額外發放一定期限的救助金并報銷其找工作的開銷;對那些在安排專業社工做動員后仍拒不參加培訓、不主動就業、兩次以上拒絕職業介紹者,降低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甚至取消某些項目的救助資格。
二是替低收入群體“省錢”,減輕家庭剛性支出負擔。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減輕個人或家庭剛性支出負擔,不僅是降低貧困發生風險的主要措施,也是低收入群體實現富裕的主要渠道。目前,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減輕低收入群體支出負擔:首先,改革醫療保障制度,減輕自負醫療負擔。近些年來,針對因病致貧問題,上至中央、下至鄉鎮,采取了一些措施,收到較好效果。但是這些措施主要針對建檔立卡貧困戶、民政救助對象等特定群體實施的成惠性保障,難以解決貧困邊緣的因病致貧問題,并造成了群體之間的不公平。為此,一方面要加強城鄉居民醫療保險財政投入力度,擴大醫療保險報銷范圍,提升基本醫療保險報銷比例;另一方面要加大醫療救助力度,擴大醫療救助覆蓋面,成化針對低收入群體的醫療特惠政策,引導社會力量設立專項醫療救助基金,資助低收入群體參加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性醫療保險。
其次,加大住房保障力度,減輕家庭住房支出。目前,城鎮低收入家庭住房負擔占家庭支出的比例過高,現行具有“生產型社會政策”特征④王晶、江治強:《住房保障與城鎮困難家庭的住房負擔》,《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 期。的住房保障政策對最低收入家庭減輕住房負擔的效益并不顯著,同時也讓夾心層處于尷尬地位。⑤潘雨紅等:《重慶市公租房配租效率實證研究》,《重慶交通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4年第5 期。為此,需要改進現行住房保障政策,包括:出臺住房保障法,完善住房保障法律體系;大力發展政策性租賃住房以及共有產權房,探索多樣的保障性住房模式,形成多層次住房保障體系;完善收入調查機制,嚴格保障性住房申請、準入和退出機制,保障住房分配的公平性;建立多元化的住房保障供應體系,完善住房保障信息系統,加大住房保障資金保障力度。
最后,完善照料服務體系,減輕照料負擔。完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建立低收入群體參保補貼制度,提高低收入群體長期護理保險參保率;統一殘疾與失能認定及評級標準,整合評估體系,促進殘疾人托養照料、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與長期護理保險的政策銜接。遵循“基本公共服務+產業化”的思路,對特困供養人員、失獨老年人、低收入家庭中的失能(殘疾)老年人由政府承擔兜底養老服務責任;針對一般家庭中的殘疾、失能、高齡老年人的長期護理照料需求,建立以家庭照護為主、政府承擔基本養老服務責任、社會主體廣泛參與的社會化服務模式。全面建立適度普惠型兒童福利制度,將受助對象從孤殘兒童向困境兒童擴展,并最終覆蓋全體兒童;按照“分層推進、分類施保”的原則和要求,創建多層次兒童福利服務體系,包括孤兒福利服務、特殊困境兒童福利服務、困難家庭兒童福利服務和普惠性兒童福利服務。建立殘疾人全生命周期護理照料體系,以低收入、重度殘疾人為主要服務對象,為其提供托殘照料服務,實現“托養一個人,解放一群人,致富一家人”。
三是給低收入群體“發錢”,增加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收入。首先,改進低保制度,提高低保標準,擴大低保覆蓋面,包括:建立全國統一的低收入線制度,由國家統計局每年進行調整并發布;各省市參考全國低收入線制定本地區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但不得低于全國低收入線;改革“補差”制度,將資格線與救助標準分離,本地低收入線只做為低保資格線,根據家庭貧困等級確定領取的低保標準;改革低保財政體制,中央財政承擔至少80%以上的財政責任,上移管理權,由中央對地方低保項目進行考核。
其次,建立全國統一的最低養老金制度。2019年,全國城鄉居民養老金的平均水平為每人每年1942.56 元,合計每人每月162 元,遠低于當年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為此建議整合城鄉居民養老金、高齡老年津貼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最低養老金制度,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一發布,待遇標準應不低于全國統一的低收入線;各地根據全國最低養老金制定適合本地的最低養老金標準,但不得低于全國最低養老金。全國統一的最低養老金由中央財政負責,地方增加的部分由地方財政承擔。
最后,建立家庭津貼制度。福利國家普遍建立了家庭津貼制度,其中兒童津貼是家庭津貼中最為普遍的一種項目,國家通常會給所有養育兒童的家庭發放兒童津貼。①姚建平:《為什么要給予兒童現金補貼?》,《群言》2019年第12 期。目前,我國建立了高齡老年津貼、殘疾人護理補貼制度,少數地區開始發放育兒補貼金,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家庭津貼制度處于起步階段,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建議:針對困境老年人、困境兒童和重度殘疾人,建立家庭照顧津貼制度;在全國層面建立普惠性育兒津貼制度,減輕家庭育兒負擔;將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改為傷殘生活津貼,大幅度擴大津貼受益范圍。
(三)低收入群體實現共同富裕要處理好的幾對關系
一是個體與群體的關系。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是指整個群體而言的一種生活狀態,這個群體并沒有一個精準的范圍邊界。從扶貧的角度看,低收入群體指的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國家劃定的扶貧標準的個人或家庭,通過多年的精準脫貧,這一群體已擺脫了絕對貧困狀態;從社會救助的角度看,低收入群體包括了特困供養人員、低保對象、低保邊緣對象以及地方政府規定的其他困難群體;國家統計局在進行收入調查時則將所有調查戶按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從低到高順序排列,平均分為五個等份,處于最低20%的收入群體為低收入組。在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問題研究中,應以收入五等份為標準確定低收入群體的邊界范圍,以此為重點人群制定社會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群體共同富裕指標不能應用于每個個體,群體的共同富裕并不要求每個個體都達到“富裕”的標準,或者說,實現了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的目標,也仍然有部分人群生活在相對貧困狀態之中,而社會政策則要關注這些重點人群,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其基本生存。
二是權利與義務的關系。當代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責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但是政府對個人的生活保護應盡多大的責任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對人民所關心的問題積極做出回應,做好民生領域的保障工作,對社會救助工作做出一系列決策部署,取得了巨大成就,切實為老百姓織密、織大民生保障安全網。但是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其中國家與個人義務的不對等,使以低保為門檻的政策疊加效應逐漸顯現,造成“福利懸崖”“福利依賴”。為此,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首要任務是明確政府的責任邊界:一方面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愿望,逐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以維護社會公正為原則,促進分配正義,保障權利均等,逐步實現公民與日俱增的社會權利;在此基礎上,基于“成先規則”(priority rules),完善社會安全網,保護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尊重個人對消極公民權利的選擇自由。基于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殘補型的福利道路仍然是最佳選擇,或者說,只有當非個人原因或不可抗力陷入困境,政府才有責任提供基本生存保障。而對于個體來說,政府理應保障其自由選擇(積極公民權或消極公民權)的權利,但是個體也應該為自己的選擇結果負責,個人對自己及家庭應負起最主要的責任,個人權利的獲得需要先承擔起應負的責任與義務,尤其是經濟成功只能通過個體的努力和辛勤的汗水換來,而不能依靠政府的分配而獲得;個人理所應當享受的權利只限于基本生存保障權和機會均等權。
三是市場、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實現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需要三次分配共同發力。追求美好生活,并為此付出努力,理所當然是個人的首要責任;同時,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職能是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生存,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社會是一個連帶體,“先富”也有責任帶動“后富”。在實現低收入群體共同富裕的過程中,要處理好市場、國家和社會的關系。政府固然有保障個人及家庭基本生活的責任和義務,但是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建立起高水平的福利體制是不切實際的,因此第二次分配在實現低收入群體的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只能起到托底作用,或者說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政府只能讓公民維持基本的生存或有尊嚴有質量的生活。而第三次分配固然在調節收入分配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即使在慈善較為發達的美國,巨額的慈善捐贈也未能讓窮人擺脫困境,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固化和延續了不平等狀態,①Maclean Mairi, et al., "Elite Philanthrop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in the New Age of Inequa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21, 23(3).更談不上通過第三次分配實現低收入群體的“富裕”目標。因此,“富裕”的責任主體在個人,個人只有通過自己的付出才能過上美好生活;而“共同”的責任主體則在國家,包括:建立公平公正的初級分配市場,在關注效率的同時,兼顧公平性,打破資源壟斷局面,改變“親資本、疏勞工”政策,支持勞動致富;打破身份、戶籍界限,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確立公民權利,逐步縮小第二次分配差距。而社會在低收入群體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發揮補充作用,政府要引導慈善捐贈投向低收入群體,引導社會志愿力量幫扶低收入群體發展生計,增強其可持續發展能力。
五、結語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黨和國家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一直未變。改革開放以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成為黨和國家的根本發展戰略,國家采取“三步走”發展戰略和“先富”帶“后富”的發展策略探索共同富裕之路。通過開展大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扶貧開發,建立完善兜底保障制度,實施收入倍增計劃,實施精準脫貧戰略,全面消除了絕對貧困現象,實現了低收入群體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目標。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推動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但是低收入群體實現共同富裕面臨較大的挑戰,不僅表現在全面脫貧之后我國仍然存在數量龐大的低收入群體,更表現在他們與新時代富裕的目標存在較大差距。更加嚴峻的是,雖然不同收入群體的收入均得到較快增長,但是低收入群體與社會平均收入的差距總體上有拉大趨勢。因此,實現低收入群體的共同富裕,關鍵任務有兩個方面,即:實現低收入群體收入的快速增長,縮小低收入群體與其他群體的收入差距。要實現上述目標,一方面需要提升低收入群體的市場競爭力,提升勞動參與率,通過勞動實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減輕低收入群體在醫療、生活照料、住房等方面的剛性支出壓力;同時,需要進一步加強轉移支付力度,提高對特殊群體的保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