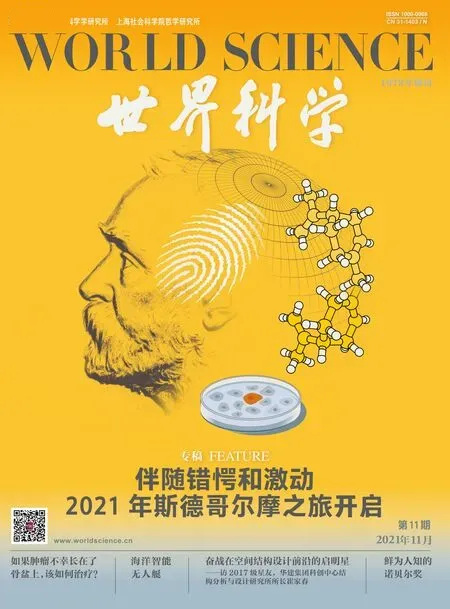物理學探索未來—拜拜,小蘇西
編譯 夏冰

早有諺語教導我們: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然而,在最近幾十年里,物理學家沒能遵此行事。對他們來說,20世紀——實際上還有之前的19世紀——是收獲偉大勝利的階段。他們改變了認識物質世界的方式,從而提升了人類操控周遭世界的能力。如果沒有物理學家在過去兩個世紀內獲取的知識,現代社會可能壓根不存在。
另一方面,物質世界也為物理學家提供了昂貴的玩具。舉一個近些年的項目,2008年,大型強子對撞機投入運行。這件耗資60億美元的“玩具”占據著日內瓦附近一條總長27千米的環形隧道。這件玩具不負眾望,很快就發現了一種物理學家早已預言存在的基本粒子:希格斯玻色子。早在20世紀60年代,物理學家就通過相關計算預言存在這種粒子。此后,大型強子對撞機就把重點放在了它真正的設計目標上,尋找一種叫作“超對稱”(supersymmetry)的現象。
超對稱理論問世于20世紀70年代,簡寫為“蘇西”(Susy),堪稱一個包羅萬象的籃子。不過,物理學家最近才把所有標著“基本粒子”的雞蛋放到這個籃子里。粒子物理學標準模型涉及大量隨意的數學假設,而超對稱理論就能消除它們。此外,超對稱理論還是更深層假說弦理論的先驅,后者旨在將標準模型同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結合在一起。愛因斯坦的理論解釋了引力問題,而標準模型則解釋了其他三種基本力——電磁力、弱核力和強核力——以及與這些力相關的粒子。這兩種理論都很好地描述了各自領域的物理現實,但它們之間并不互通。而弦理論就是連接這兩種理論的橋梁,因此也稱作“萬物理論”。
弦驅動的物質世界
弦理論認為,宇宙由一些極其微小的事物構成,這些東西的振動方式就類似于樂器中的弦。和我們熟悉的弦一樣,弦理論中的弦也具有共振頻率和諧波。這個理論認為,弦的各種振動模式就對應著各種基本粒子。這些粒子既包含了此前已觀測到的所有粒子(它們是標準模型的組成部分),又囊括了那些超對稱理論預言的粒子(有待發現)。按照超對稱理論的設想,如果標準模型中的每種粒子都有一種與之對應的“超對稱粒子”——這種所謂的“超粒子”質量更大,因而也叫作“引力子”,是將引力整合進統一理論的必需,但相對論本身并沒有預言引力子的存在——那么標準模型的數學弱點就會隨之消散。
然而,到目前為止,無論是超對稱理論,還是弦理論,都沒有得到有力證據的支持。大型強子對撞機已經運行13年,卻還未找到任何超粒子的蹤跡。即便是2021年早些時候公布的兩項有待解釋的實驗結果(一項來自大型強子對撞機,另一項來自一架規模小一些的類似機器),也沒有出現任何能夠直接支持超對稱理論的證據。因此,很多物理學家都擔心,他們的努力只是徒勞。
實際上,他們也完全有理由緊張起來。弦理論現在已經貼上了一個令人惴惴不安的概念標簽——我們熟悉的宇宙是四維的(三維空間再加上時間),而弦理論要在這個基礎上再增加6個維度(某個版本的弦理論要求增加7個維度)。此外,弦理論描述的宇宙有10500種可能,其中只有一種匹配我們人類生活的這個宇宙。光是接受這些概念就很有挑戰性。然而,如果沒有超對稱理論作基礎,弦理論還會變得更加瘋狂:宇宙的維度會急劇上升到26個。此外,缺少超對稱理論的弦理論還有諸多缺陷,無法描述標準模型中的大部分粒子;會預言一些奇怪物質的存在,比如“超光速粒子”(顧名思義,這種粒子的運動速度會超過光速),因而與相對論相抵觸。因此,如果沒有超對稱理論作基礎,以萬物理論為目標的弦理論看上去完全就是一條死胡同。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那么那些萬物的非弦理論就有了生存空間。
我們必須承認,在其他那些萬物理論中,有許多名字都很拗口,比如“因果動態三角化理論”“漸進安全引力理論”“圈量子引力理論”“量子理論的振幅多面體形式”。不過,就目前來說,學界偏愛的萬物理論(統一相對論和標準模型的理論)是所謂的“熵引力假說”。
這里有怪獸
熵是系統無序度的測度。我們大家都知道,熱力學第二定律是這么說的:熵只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也即,事物在發展的過程中總會有變得更加混亂的傾向。上述與引力理論(先不提更普遍的“萬物理論”)之間存在何種關系似乎不是很明顯。不過,黑洞把這兩者連接了起來。所謂“黑洞”,就是一些引力場強大到連光都無法逃脫的天體。廣義相對論的數學推演就預言了黑洞的存在。雖然愛因斯坦直到1955年去世都懷疑黑洞是否真的存在,但后來的觀測結果證明,這種天體的確存在,只不過并不是黑的。
1974年,劍橋大學的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證明,黑洞可以通過其邊界處的量子效應向外輻射粒子——尤其是光子。光子是與電磁輻射(包括光在內)相關的粒子。這個結論產生了一些特別的結果,光子可以攜帶輻射熱,所以釋放光子的事物必然具有溫度。于是,根據黑洞的溫度和質量就能計算出它的熵。這點很重要,因為把所有這些變量都放到熱力學第一定律中后——“熱力學第一定律”的內容是:能量既不會憑空產生,也不會憑空消失,只會從一個物體轉移到另一個物體,或者從一種形式(比如熱)轉變成另一種形式(比如機械功)——就能得到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方程組。
2010年,阿姆斯特丹大學埃里克·弗林德(Erik Verlinde)發現了熵與廣義相對論之間的這種聯系,這一發現意義重大。熱力學定律的基礎是統計力學,涉及以概率形式描述粒子行為的物理量(如溫度、熵等)。而支撐標準模型的數學理論:量子力學也同樣描述這些粒子。既然愛因斯坦方程組可以用熱力學形式重新表述,那就意味著,時間和空間同樣也是量子力學這種深層微觀圖景的外在屬性。那么,從原理上講,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現有形式似乎都可以從某些描述宇宙更本質性質的深層理論中推導得出。
而弦理論就不太容易推導出來,因為弦并不是足夠基本的物理實在。熵引力假說卻宣稱能夠描述空間和時間(用愛因斯坦的術語來說,就是“時空”)的真正本質。這個理論認為,時空由連接宇宙所有粒子的“量子糾纏”現象編織而成。
量子糾纏也是愛因斯坦嗤之以鼻但最后證明為真的現象,其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35年。這是一種兩個或兩個以上物體結合(也即所謂的“糾纏”)在一起的形式,處于量子糾纏狀態的物體無法分別獨立描述。這引出了不少怪異效應。其中最特別的是,假設有兩個粒子處于量子糾纏狀態,那么,無論它們相隔多遠,其中一個的狀態改變都會立刻影響到另一個的狀態。愛因斯坦稱其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因為這種現象似乎違反了相對論的基本前提:宇宙存在速度上限,也即光速。
就黑洞來說,愛因斯坦沒有活到見證自己的觀點被推翻。然而,實驗結果確實表明他錯了,量子糾纏也是如此。實驗表明,這種現象真實存在,并不違反相對論。雖然處于量子糾纏狀態的兩個粒子之間可以產生瞬時影響,但我們無法利用這種效應以快于光速的速度傳遞信息。此外,在過去5年中,哈佛大學布萊恩·斯溫格爾(Brian Swingle)和加州理工學院肖恩·卡羅爾(Sean Carroll)已經開始運用量子信息理論構建弗林德博士理論的實踐模型。他們在這一過程中用量子信息比特(也即所謂的“量子比特”)代替糾纏粒子。其結果是簡潔但信息豐富的時空模擬。

量子比特是經典比特(常規計算機的設計基礎,也就是0和1)在量子理論中的對應物。熟悉量子計算領域的人肯定很熟悉這個概念。量子比特是量子信息理論的基礎,它與經典比特之間的區別主要是兩點:其一,量子比特可以處于“疊加態”,即可以同時代表0和1;其二,量子比特與量子比特之間可以發生糾纏。量子計算機正是憑借這兩大特性完成了常規計算機很難(甚至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壯舉,比如一次執行多種計算任務、以相對較少的時間完成特殊類型的計算。
斯溫格爾博士和卡羅爾博士還表示,借助量子比特的糾纏特性,我們還可以利用它們來研究現實如何運作。糾纏作用更緊密的量子比特就代表時空中更接近的兩枚粒子。由于到目前為止,量子計算機仍處于發展階段,這個建模過程只能借助量子比特的數學表征方式完成。饒是如此,相關結果似乎也的確符合廣義相對論方程組,從而支持熵引力假說的相關論斷。
冒著顛覆因果關系的危險
在弦理論遲遲沒有突破的情況下,上述模型讓熵引力假說成了頭號備選方案。不過,“時空是宇宙外在屬性而非基本構件”的概念也帶來了一個令人困擾的后果:它模糊了因果關系的本質。
根據熵引力假說構建的理論圖景,時空是多種狀態的疊加。正是這一點讓因果關系變得模糊起來。就目前來說,描述時空的最佳數學分支是4條軸(而不是我們更為熟悉的3條軸)互成直角的幾何形式。額外增加的這第四條軸代表時間,因此,就像物體在時空中的位置一樣,事件在時空中的發生順序由幾何形式決定。現在既然熵引力假說要求不同的幾何構型可以疊加,那么有時就會出現“A導致B”以及“B導致A”這兩個命題都為真的情況。
這個結果并非只是猜測的產物。2016年,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朱莉亞·魯比諾(Giulia Rubino)使用偏振光子和棱鏡開展實驗,得到的結果與理論預測完全一致。這顯然給那些對因果關系本質持傳統觀點的老派學者造成了困擾。
不過,加拿大圓周理論物理研究所的路西安·哈代(Lucien Hardy)發現了一種重新表述量子力學定律的方式,它能解決上面提到的這個問題。在他看來,通常的因果關系可看作計算過程中的數據壓縮:這是一種能讓你花小錢辦大事的概念。有了因果關系,你就可以根據現時現刻的一小點信息推斷出未來會出現的諸多狀況——也就是將捕捉未來物理系統狀態所需的細節信息壓縮了。
然而,哈代博士認為,因果關系或許并不是唯一一種描述這類關聯的方法。相反,他從零開始發明了一種一般方法,用于描述各種關聯模式。他本人稱這個方法為“類因果框架”。這種方法的目的是重現因果關系,但它本身并不以因果關系為前提。哈代博士以類因果框架為基礎,重新表述了量子理論(2005年)和廣義相對論(2016年)。類因果框架的數學并不是萬物理論。不過,等我們真的發現了這種理論,很有可能需要類因果原理來描述它,就像廣義相對論需要四維幾何形式描述時空一樣。
振幅調制
的確有很多堅實的概念性工作支持熵引力假說,但這個理論并不是替代弦理論的唯一方案。在其他值得注意的理論中,有一個叫作“圈量子引力理論”的老對手。這個理論最初是由匹茲堡大學的卡洛·羅韋利(Carlo Rovelli)和加拿大圓周理論物理學研究所的李·斯莫林(Lee Smolin)在1994年提出。最近這些年則出現了一種類似的理論,叫作“因果動態三角化理論”。這兩個理論都認為,時空并不是廣義相對論認為的那種平滑結構,而是一種復雜結構。圈量子引力理論認為,時空的基本構型是圈;而因果動態三角化理論則認為,時空的基本構型是三角。
第三種備選方案則是“漸進安全引力理論”,其歷史要比圈量子引力理論更為悠久,可以追溯到1976年,由標準模型的主要構建者之一史蒂文·溫伯格(Steven Weinberg,2021年7月逝世)提出。在標準模型中引入引力子是提出量子引力理論的自然方法。遺憾的是,這種方法沒有任何作用,因為當我們在能量較高的背景下計算引力子這些假想粒子間的相互作用時,相應的數學內容似乎就變得毫無意義。然而,溫伯格認為,如果能有功能足夠強大的機器做相關計算,那么就能克服這種表面上的數學崩潰現象。(用數學語言來說,這種計算就是“漸進安全”。)近年來涌現的諸多超級計算機就擁有這樣的高超性能,并且,從它們得到的初期結果上看,溫伯格似乎是正確的。
不過,熵引力假說的最有力競爭者是“量子理論的振幅多面體形式”。這個理論由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尼瑪·阿爾卡尼-哈默德(Nima Arkani-Hamed)和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亞羅斯拉夫·特恩卡(Jaroslav Trnka)在2013年提出。他們發現了一類叫作“振幅多面體”的幾何結構,每一種多面體都編碼了一種可能出現的量子相互作用的細節。另一方面,這種振幅多面體的各個面包含了所有可能出現的物理過程。于是,我們就可能通過振幅多面體重新描述所有量子理論。
大多數以萬物理論為目標的理論都試圖將引力(愛因斯坦從幾何角度描述引力)引入量子理論(并不依賴幾何描述)。量子理論的振幅多面體形式則恰恰相反。這個理論認為,無論如何,量子理論在本質上仍舊是可以用幾何描述的。更巧妙的是,量子理論的振幅多面體形式不僅不以時空概念為基礎,甚至不以統計力學為基礎。相反,時空概念和統計力學都可以自然地從這個理論中推導出來。因此,雖然量子理論的振幅多面體形式尚未全面建立量子引力理論,但它確實開辟了一條極有可能實現這個目標的道路。

時間、空間甚至因果關系都只是宇宙的外在表現而非基本屬性,這種觀點相當激進且令人費解。不過,這極有可能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我們之所以認為,20世紀的兩大科學革命,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是極為深刻的物理學理論,就是因為它們推翻了常識。接受相對論,意味著放棄人類此前固有的時間和空間概念;而接受量子力學,則意味著坦然面對像糾纏和疊加這樣的古怪量子現象;接受熵引力假說,或者其他類似的理論,意味著你的想象力要完成類似的飛躍。
不過,如果沒有相關數據支撐,任何理論都不會有什么價值。畢竟,這正是超對稱性理論面對的問題。魯比諾博士的工作就明確地指出了這點。當然,粒子物理學實驗室之外的理論突破也是我們期望見到的。此外,雖然意義尚不明確,但在過去幾個月中,我們確實看到了兩項可能表明標準模型存在缺陷的實驗結果。
2021年3月23日,歐洲核子研究委員會(大型強子對撞機就是這個組織管理運行的)的一支研究團隊報告稱,他們發現,電子與其質量較大的“表親”渺子的性質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差異。由于電子和渺子之間除了質量不同之外,其他屬性完全一樣,標準模型便預言,當其他粒子衰變成這兩種粒子時,產生的電子數目應該與渺子數目完全一致。然而,事實可能并非如此。大型強子對撞機的中期實驗結果表明,有一種叫作“B介子”的粒子在衰變時往往會產生更多的電子。這意味著,標準模型可能還缺少了一種基本力。接著,2021年4月7日,美國最大的粒子物理學研究機構費米實驗室宣布了他們的渺子實驗中期結果,即渺子g-2實驗。
在量子世界中,不存在完美真空。相反,在時空的每一個角落,都會有粒子不斷冒出、消失。這些粒子是“虛”粒子,而非“實”粒子——也就是說,它們是肇始于量子不確定性的瞬時漲落。不過,雖然這些粒子的存在時間很短,但也足夠和更永久的物質發生作用,比如:霍金預言的黑洞輻射的來源。
標準模型預言了這些虛粒子與比黑洞更傳統的物質之間的相互作用的強度。為了檢驗這些預言,渺子g-2實驗讓發射出來的渺子沿著一根磁性強大的超導儲磁環排列。量子漲落會改變渺子晃動的方式,而探測器則會以不可思議的精確度捕捉到這種變化。渺子g-2實驗的結果表明,讓渺子產生這種晃動的相互作用要比標準模型的預言稍強一些。如果這個結果得到進一步證實的話,那就意味著標準模型至少缺失了一種基本粒子。
破曉時分
這些缺失的粒子是超粒子的可能性并不高。不過,如果最后證明缺失的粒子的確是超粒子,那就意味著笑到最后的是超對稱性理論。然而,目前沒有任何有利于這個方向的證據。此外,正是由于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出現支持超對稱理論的證據,這個理論的擁躉明智地保持沉默。
無論上述兩項實驗結果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有一點都是肯定的:它們確實表明,仍存在一些現有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實際上,量子理論和相對論的起點,也是一些類似的無法解釋的現象。因此,物理學的最黑暗階段之一似乎的確就要迎來黎明的曙光。
資料來源 The Econom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