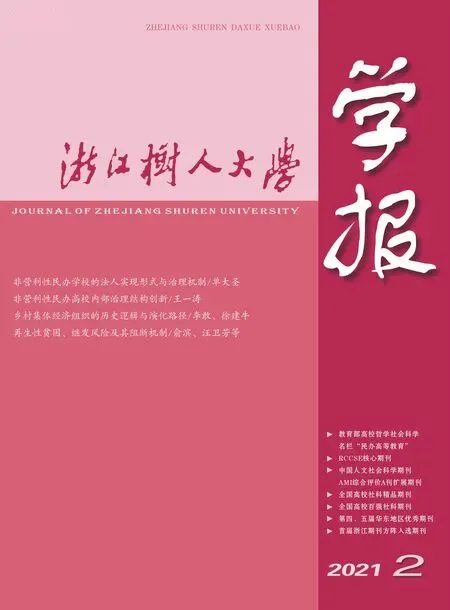有意味的形式:中國傳統繪畫審美意蘊下的中國詩電影
郄欣萌
(云南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院,云南 昆明 650091)
詩電影是源自西方的一種電影形態,其特點為電影修辭中隱喻、象征與節奏的運用。而中國的詩電影較之西方,具有鮮明的美學特色,創造性地繼承了中國傳統詩學、畫學的美學基礎,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中國傳統繪畫具有“以形寫神”“寓情于景”“虛實相生”等美學觀念,中國詩電影即基于此進行轉化發展。本文將中國詩電影與中國傳統繪畫藝術進行對比,從內容與形式角度分析兩者在審美意蘊上的相似之處,意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藝術,喚醒電影創作者的美學追求,提升大眾的視覺修養。
一、中國傳統繪畫的審美意蘊
(一)以形寫神
東晉顧愷之秉持“以形寫神”“遷想妙得”的繪畫理念(1)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中國美術史教研室編:《中國美術簡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92-93頁。,其中“以形寫神”是指在畫人物畫時,外在形似并非首要的追求目標,以形似而傳神才是成功。南朝謝赫提出的繪畫六法,排在首位的便是氣韻生動。可見,對人物精氣神的把握在中國傳統繪畫中非常重要。不同于西方繪畫的寫實,中國傳統繪畫審美注重“妙在似與不似之間”(2)周積寅、史金城編:《近代中國畫大師談藝錄》,吉林美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112頁。,不把畫得像作為評判作品的首要標準,而把傳遞的思想和情感看得更為重要。只有“遷想”的體驗,才能“妙得”(3)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中國美術史教研室編:《中國美術簡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92-93頁。。藝術家們傾向于先觀察、體會自然,形成個人的感悟后,再提筆作畫,在經歷了“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4)鄭燮:《鄭板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4頁。三個階段后,作品便融合了自然與藝術家的個人情思,實現了從“物竹”到“心竹”再到“意竹”的轉變,達到了形神兼備,從而突出作品的意境。
(二)寓情于景
王國維(2015)說“一切景語皆情語也”(5)王國維:《人間詞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24頁。,便是中國傳統藝術理念中寓情于景的境界,即意境,從詩到畫皆如此。“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包含六種意象,連在一起就有了孤獨、漂泊之感;“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中山、夕陽與飛鳥的意象,融合著悠然自在之感。中國傳統山水、花鳥畫更將情感融入景物之中,元末明初倪瓚的《漁莊秋霽圖》描繪秋天漁莊景色,畫面由山石、幾枝樹木、湖水和山巒等意象構成,簡約淡雅,清秀雋美,展現出畫者清高、不與世俗相爭的境界。明代徐渭是潑墨大寫意畫派的創始人,其所畫的《梅花蕉葉圖》將大片蕉葉位于畫幅中心偏左,梅花置于蕉葉上方,湖石位于下方點綴,不求形似,聊以自娛,寄寓豪邁個性、超凡脫俗之情。明末清初八大山人畫鳥禽類多以白眼示人,其《孤禽圖》僅用一水禽為描繪對象,抒悲憤、憂郁之情。故在中國大多藝術家筆下,景物不是單純的景物,多隱喻個人情感,呈現別樣韻味。
(三)虛實相生
笪重光(1982)言:“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6)笪重光:《畫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頁。計白當黑是中國傳統繪畫中常運用的構圖技巧之一,留白的方式不僅能夠體現畫家言有盡而意無窮之情境,更架起觀者與畫家的溝通橋梁,可謂“觀”與“悟”的結合。詩畫中的虛實將形象與想象合一,營造意象境界。南宋四家之一馬遠的《寒江獨釣圖》,畫浩渺江水中的一葉扁舟,一老翁獨自垂釣,此外畫面大幅留白。老翁是“實”,留白是“虛”,空白的畫面傳遞著情思與遐想的意味,是時空的巧妙融合。
中國傳統繪畫發展了幾千年,形成了以形寫神、寓情于景和虛實相生的審美觀念,奠定了中國藝術審美意蘊的基礎。而電影作為一門較年輕的藝術,發展時間僅百年,尤其是中國電影,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繪畫藝術的諸多手法。中國詩電影在畫面構圖上虛實相生,對人物外在與情緒的刻畫上以形寫神,在空鏡頭拍攝與敘事情節上寓情于景,這些都是吸收了中國傳統繪畫的審美意蘊而形成的新的藝術風格。
二、有意味的形式與中國詩電影
(一)有意味的形式
藝術家經過“寫實”“傳神”,再到“妙悟”之境,由于“妙悟”,他們透過鴻蒙之理,堪留百代之奇。然而藝術意境與作品,就是要通過秩序的網幕,使鴻蒙之理閃閃發光(7)宗白華:《藝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8頁。。“鴻蒙之理”即藝術家的情思,是內容;“秩序的網幕”,是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意在說明藝術家如何通過作品傳達出“意味”,把握形式。
英國的克萊夫·貝爾(2005)認為,藝術作品的基本性質在于它是“有意味的形式”,即“在每件作品中,以某種獨特的方式組合起來的線條和色彩、特定的形式和形式關系激發了我們的審美情感。我們把線條和顏色的這些組合、關系以及這些在審美上打動人的形式稱為‘有意味的形式’”(8)克萊夫·貝爾著,薛華譯:《藝術》,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這一觀點在西方新古典主義與立體主義流派中得到印證:安格爾運用柔和的線條與色彩畫出《泉》的人體美;畢加索利用拼貼的手法,注重繪畫作品外在的色彩、線條,給予作品一種新的表現方式,這是由外在形式所構成的“有意味的形式”。中國學者李澤厚(2009)則認為,“有意味的形式”是經過歷史沉淀的美,如秦代用以祭祀的青銅器上所繪饕餮紋飾,在當時的人們看來是獰厲可畏、難以欣賞的,但放至現今,青銅器不再實用,紋樣也有了獰厲之美(9)李澤厚:《美的歷程》,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38、44頁。。此外,“有意味的形式”也可看作是一種意境美,如宗白華(1981)所述:“美與美術的特點在‘形式’,在‘節奏’,而它所表現的是生命的內核,是生命內部最深的動,是至動而有條理的生命情調。”(10)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頁。世代諸多中國藝術家始終把追求意境作為藝術表現的最高標準,宗白華顯然將這“意味”看作“意境”,看作藝術家情思的構造。無論是中國文人畫中文同、鄭板橋的墨竹,還是米芾、元四家、吳門派、清初四僧的山水畫,均在寫景的同時寓個人情感于其中,升華了作品的境界。由此,“有意味的形式”即具有獨特外在形式的,經過了歷史沉淀與考驗的,具有豐富內涵的藝術作品。
(二)中國詩電影概念梳理
1.西方詩電影。“詩電影”是一種電影形態,其概念源自西方,以法國“詩性電影先鋒派”及蘇聯“詩性蒙太奇”學派為代表。1920年,“詩化先鋒派”創始人路易·德呂克拍攝電影《沉默》,被視為詩電影的開端,隨后讓·愛浦斯坦、讓·梯德斯科、萊昂·姆西納克等人提出了一系列詩電影的相關理論。蘇聯導演塔可夫斯基拍攝了大量詩電影,呈現在世人面前。然而,西方詩電影作品大多重視電影技巧的運用,弱化了抒情性。如法國“詩化先鋒派”的很多電影畫面前后拼貼,缺乏邏輯性,是無意義的抒情;蘇聯“詩性蒙太奇”學派則把詩與蒙太奇技法結合,如愛森斯坦拍攝《戰艦波將金號》,將雜耍蒙太奇應用于電影創作等。西方的詩電影與其傳統詩學中“重視對意象如何安排制作的技巧、重視人工安排”(11)⑤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3-34頁。的特點有著相似之處,對技巧的運用大于情感的抒發。
詩電影是一種從西方發展演變而來的電影形態,因此,其概念有時易與“詩意電影”混淆。傳統的電影類型包含喜劇片、愛情片、驚悚片、犯罪片以及科幻片等,詩電影不屬于傳統劃分的電影類型,是一種較新的電影形式。王國平(1985)評價道:“詩電影是一種電影風格。”(12)③王國平:《論詩電影》,《當代電影》1985年第6期,第38-45頁。此外,富于詩意的電影與詩電影是不能簡單地畫等號的。好萊塢大片里可能存在幾分鐘的詩意,驚悚片里也可能有詩意,但僅憑幾分鐘、幾個鏡頭的詩意,顯然無法判斷其整體屬于詩電影風格③。《現代漢語詞典》將“詩意”界定為:“像詩里表達的那樣給人以美感的意境。”(13)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172頁。法國詩意現實主義電影是在20世紀30年代后出現的電影創作傾向,能夠給觀眾帶來一種詩意的滿足。詩意更像是一種形容,可以說詩電影的追求目標是詩意,而具有詩意片段的電影不一定是詩電影。
2.中國詩電影。中西詩學本不相同,西方詩多為長篇敘事史詩與戲劇,而中國從《詩經》《楚辭》開始便注重抒情。“中國詩注重自然之感發,有興發感動之特質。”⑤西方詩重視技巧,忽略了詩歌最寶貴的感發特質。基于詩學本質的不同,西方詩電影多注重運用詩的隱喻、象征與節奏性等技巧,中國的詩電影則是結合傳統詩學和一定藝術美學的基礎進行轉化發展的。《電影藝術詞典》將“中國詩電影”的概念界定為:蓋源于創造性地繼承了中國豐厚的詩學傳統,精粹在于情與景的交融,以有限的在場景物升華出無限高遠空靈的境界(14)許南明編:《電影藝術詞典》,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頁。。與中國繪畫之審美意蘊一致,中國詩電影更多重視意境的表達,借鑒傳統繪畫中詩畫一體、外師造化、虛實相生、計白當黑和以形寫神等美學觀念;吸收了傳統繪畫構圖、光影(用墨)、色彩等表達要素,很好地將藝術表達形式進行轉化,發展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詩電影。
中國詩電影即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它融合了克萊夫·貝爾之“形式”、李澤厚之“歷史”和宗白華之“意境”。在形式上,中國詩電影運用長鏡頭、空鏡頭以及留白構圖等藝術表現形式;在內容上,中國詩電影敘事緩慢、貼近生活,營造情景交融之意境。此外,《小城之春》《早春二月》《巴山夜雨》《城南舊事》等早期詩電影更是經過歷史的沉淀,成為寶貴的代表民族文化的藝術作品。
三、傳統繪畫審美意蘊下的中國詩電影
(一)內容:敘事
美學史可以充分證實,各種藝術技巧的相互借鑒是必要的,至少在藝術演進的特定階段上是如此(15)安德烈·巴贊著,崔君衍譯:《電影是什么?》,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頁。。電影作為“第七藝術”,吸收了其他藝術門類的諸多特點。在內容上,它的敘事比文學更快,電影的敘事除了線性、非線性外,可以任意跳躍和壓縮時空。電影比繪畫更清晰明了,它不像《清明上河圖》那樣的長卷畫講述,也不單純是題詩句于畫上進行解釋說明。電影既可以運用長鏡頭視角,也可以通過剪輯拼貼構成邏輯,它比雕塑更全面,不像《拉奧孔》一般展示瞬間的痛苦。電影通常是故事性的,是一種有頭有尾的講述。傳統繪畫審美意蘊影響下的中國詩電影,在敘事上更多是線性敘事,表現為慢節奏、極少跳躍,有時也以獨白和字幕的方式為敘事添彩,營造詩般的意境。
1.剪輯。如果說西方的蒙太奇詩電影是單純的技巧性拼貼、無意義的抒情,那么中國的詩電影剪輯更有利于意境的營造,更有意味。中國詩電影的剪輯手法節奏緩慢,每個畫面停留時間較長,前后鏡頭銜接多有隱喻作用,空鏡頭與人物的銜接也往往是情與景的融合。
影片《我的父親母親》可以看作是一部詩電影風格的作品,敘事手法為回憶與現實插敘講述,父親和母親的故事是全片的主線。導演很好地運用剪輯方法令影片敘事自然不跳脫,娓娓道來又意味深長。影片開頭是兒子的獨白,令觀眾開場便了解故事的前提。在13分26秒,獨白再次響起,此時鏡頭中兒子手拿父親、母親的黑白照片,用此道具進行轉場。在13分45秒,畫面從黑白照片轉到金黃色田野,此時獨白的內容為:“是一輛馬車把父親拉到了三合屯。”隨后馬蹄聲響起,遠處馬車越來越接近畫中央。第一次回憶與現實的轉場利用黑白照片這一物象,剪輯運用疊化手法,將黑白照片慢慢淡出,金黃麥田逐漸顯現。第二次轉場出現在69分49秒,鏡頭依舊停留在那條路,金黃變成了白雪,兒子的獨白再次響起:“這就是父親和母親的故事。”此時剪輯手法依舊運用疊化,現實情境中兒子走在那條路上。最后的轉場是在86分30秒,年邁的母親望著念課文的兒子,鏡頭疊化至年輕時母親望著念同一篇課文的父親。影片三次轉場都運用疊化手法,前后場景的安排設置更是用心。照片、小路,以看似簡單的意象,營造出溫情的意境。剪輯在回憶與現實敘事邏輯符合的情況下,給人以自然流暢之感。疊化這種剪輯轉場手法,多運用于節奏緩慢的敘事情節中,詩電影中的疊化運用較為常見,就像我國傳統水墨繪畫里的用墨,流暢且富有層次感。
除疊化手法外,鏡頭前后的銜接也能夠營造詩一般情景交融的意境。在詩電影作品里,情節的講述過程中往往插入空鏡頭,如利用天氣的變化暗示人物的心情;利用某種意象暗示人物的品格;增加具有代表性和隱喻意味的場景鏡頭的時長等。影片《童年往事》講述了主人公阿孝牯的成長軌跡,全片敘事節奏溫和,用一段段細節和事件來刻畫人生,畫面唯美,是詩電影風格的代表。電影在刻畫某些場景時拉長了時間,如阿孝牯在小學時的升學考試,那時父親還未去世。老師說考上的同學桌子上會打鉤,阿孝牯望向自己的桌子,此時鏡頭對準用粉筆打著對勾的桌子,持續時間長達7秒,隨后才轉到阿孝對父親傳達考上了的場景。場景暗示著人物的心理,單個場景持續時間長,也構成了全片節奏緩慢的基調。此外,微風、下雨是全片最常出現的天氣,且多用空鏡頭穿插其中。在影片前半小時,阿孝牯還貪玩地在街上跑來跑去,玩彈珠、陀螺……在23分插入的鏡頭為隨微風搖晃的樹,是無憂無慮童年的象征。父親生病后,家庭收入不足,隨即在29分29秒插入下著大雨、樹木搖晃的空鏡頭;母親去世后,阿孝牯哭泣后銜接大樹隨風搖晃的空鏡頭,是悲傷與無助的象征。合理安排空鏡頭插入的位置,能夠更好地反映現實、烘托情感。
2.字幕。字幕在日常影視作品中起到解釋、說明的作用,位于影片下方,多是演員臺詞的體現。在詩電影中,字幕常在電影情節中畫面的某一位置出現,或以單鏡頭黑底白字的形式出現。這與中國傳統繪畫在作畫后題上幾句詩詞,講求詩畫一體的意味相似。影片《悲情城市》講述林氏家族四人的遭遇。片中的林文清是聾啞人,常用筆寫字與人交流。在9分45秒,他與友人互相寫字交流墻上的照片。此時字幕出現,內容是對于二哥、三哥情況的說明。字幕用繁體字,以從左至右、從上至下的閱讀順序出現在黑屏正中,顏色偏淺藍,別有新意。在13分17秒,友人告知林文清小川校長發病的情況,寫道“靜子甚憂傷”,用詞詩意而非大白話,增添了影片的詩意氛圍。
影片名稱通常也以字幕的方式出現,不同影片字幕樣式不同,但均與影片風格相符。影片《路邊野餐》以緩慢的敘事、真實的場景構成詩電影風格。該片敘事時空相互交叉,既有現實,又有夢境和回憶。在1分53秒出現“‘金剛經’第十八品:‘一體同觀分’”的內容字幕,意在為全片整體基調作鋪墊,與影片交錯的時空形成呼應,指明過去、現在、未來三心皆不可得,應活在當下。該字幕采用從左至右、從上至下的閱讀順序,中間予以部分留白,排列有序,烘托了影片整體的詩意氛圍。此外,不同于大部分影片片名的出現時間,該片的片名在播放半小時后才出現,不僅暗示了影片的慢節奏,更說明了其整體的詩意氛圍。
(二)形式:視聽
歌德說:“題材人人看得見,內容經過努力可以把握,而形式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秘密。”(16)轉引自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心理學新論》,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75頁。形式可以說是藝術表現的關鍵,能給觀者留下第一印象。作為視聽藝術的電影更是如此,如何將電影語言和要講述的內容完美結合起來,是導演需要深思的問題,也是構成影片整體風格的關鍵。
1.鏡頭與畫面。電影以鏡頭為視角講述故事。鏡頭語言圍繞攝影機拍攝手法,可劃分為不同景別、不同拍攝方式和不同角度等。不同的鏡頭語言構成了不同的畫面語言,單個場景中的畫面語言又涉及不同的場面調度、布景造型設置、光影和色彩等元素的設計。中國詩電影在鏡頭語言上多用長鏡頭和搖鏡頭,這與中國傳統繪畫中長卷畫的觀看視點相似;在畫面語言方面,構圖多留白、色彩搭配溫和不艷麗、光影運用層次感十足,這與中國傳統繪畫的審美意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影片《路邊野餐》的開頭是長鏡頭敘事,第一個畫面為閃爍的燈光,隨后鏡頭向左搖:穿白大褂的大夫、墻上破舊的人體圖、輸液瓶……鏡頭隨談話內容逐漸移動,在女大夫提到狗時,鏡頭繼續左搖至門口:點燃的火、潮濕的地面、站在天臺邊的人、“診所”牌子……隨后鏡頭向前慢推,狗入鏡。整個開頭通過一分半鐘的長鏡頭對影片的大致場景進行交代,這便是詩電影與中國傳統長卷畫在視點、講述方式上的相似之處。
構圖一詞源于西方美術,指在視覺藝術中對畫面中所描繪物體的位置安排。影視構圖則是指在畫幅中,將鏡頭前的表現對象及各種造型元素有機地組織、分布在畫面中,形成一定的畫面形式(17)張菁、關玲:《影視視聽語言》,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頁。。在中國傳統繪畫藝術中,構圖被稱為“經營位置”,畫面中不同物體位置的安排需要畫家用心經營。北宋郭熙提出描繪山的“三遠法”視點——平遠、高遠、深遠,分別對應平視、仰視和俯視。影片《長江圖》講述了高淳駕駛貨船沿著長江送貨時,反復遇見同一個女人的奇幻故事。該片無論從構圖、色彩還是光線構造的虛實層次,都極富中國傳統水墨畫的美學韻味。影片的空鏡頭以展現長江、船、山川為主。在展現全景的江面與山川時,多運用“平遠”“深遠”視角構圖,在展現沿岸的寺廟和佛像時運用“高遠”俯拍,增強敬畏感。在構圖上,影片通過留白刻畫人物心理。在52分,安陸跑向江邊,對著江上的一艘船向高淳喊話。此時鏡頭是水平視角的全景,人物位于畫幅偏右,顯得渺小;畫面一半以上被江占據,江面上的船朦朧不清。這種位置安排將人物遠離熒幕中央,江水和天空大幅留白,是人物無助心理的隱喻。另外,片中許多山水的空鏡頭也與中國水墨畫有異曲同工之處,除去可以利用陰天環境拍攝的客觀條件外,這種相似更多是通過對色調和光線的把握來實現的。《長江圖》全片以冷色調為主,畫面色彩偏藍,充滿神秘、憂郁氛圍;在利用光線刻畫人物時以暖色自然光為主,江面上的強光則為冷色調。船行駛至鄂州時,在字幕后接了一個由下至上隨后平視的搖鏡頭,畫面以江水為界限加以分割,上方山川的遠近用虛實展現。左右的山更近,如水墨畫一般用墨較深,中間的山更遠則更淡。冷色調加上偏暗的光線,讓鏡頭看起來像一幅黑白水墨畫。
2.人聲與音樂。波德維爾等(2013)詳列了電影中“聲音的力量”:構塑觀者對影像的詮釋,引導觀者對特定影像的注意力,營造期待心理,賦予靜音新的價值(18)Bordwell D, Thompson K,Film Art, McGraw-Hill, 2013, pp.267-268.。電影進入有聲時代后,聲音成為電影塑造藝術性的重要一環。按照聲源不同,電影聲音可分為人聲、自然音響和音樂。聲音與畫面也存在著統一、對位與措置的不同關系,用以營造不同效果。中國傳統繪畫雖然是二維平面的視覺藝術,但有著“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和“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意味。在詩電影中,人聲的對話和獨白是自然流暢的;音樂是緩慢悠揚的,大多與畫面相匹配,以營造情景交融的意境。
影片《童年往事》的開頭是一段第一人稱視角的獨白:“這部電影,是我童年的一些記憶,尤其是對父親的印象……”畫面配以鄉下住所內部的細節,獨白語氣親切平和,是口音不那么標準的普通話;內容對電影的故事起到解釋說明作用,對故事背景作了大致交代。《長江圖》《小城之春》等詩電影也在開頭運用獨白的方式,挖掘人物心理,拉近了觀眾與熒幕的距離,為故事講述提供方便。除獨白外,人物對白也是聲音的一種。對話意味著信息,在相對靜態的畫面里,人物對白往往更加吸引觀眾。影片《長江圖》中,安陸的臺詞充滿詩意,偏離了生活中的日常用語。片中高淳在江邊仿佛看到了安陸,這時的安陸說:“可是我看得見他們的善良/那么小/但是那么美/告訴我/未來是什么樣的……”這時的臺詞暗示著兩人的心理變化,且用詩意的、非口語化的方式表達。相比之下,船員武勝說話更為真實日常,在被高淳問及“那要是你高興了,人家不理你了呢?”時,他回:“再換一個唄。”可見,電影中人物的臺詞、說話語氣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導演向觀眾傳遞信息的一種手段。
“音樂的情緒調子決定了電影畫面的氣氛、神韻、情緒。”(19)張菁、關玲:《影視視聽語言》,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頁。影片《童年往事》的同名主題曲以鋼琴為主,配以弦樂,緩緩流淌,是專為電影主題而創作的。此配樂在片中多次出現,出現時多單純以音樂配畫面,沒有人聲。在12分44秒,主題曲響起,伴隨阿孝牯洗碗的場景,音樂漸強,鏡頭展示幾個孩子在外面看工人修電線,賣廢品,在街上跑,玩彈珠、陀螺……31分42秒至34分,主題曲配以父親寫字、微風的街道、電線桿、剪斷電線的阿孝牯、忙碌的家人。該主題曲在影片中出現不下六次,且往往伴隨著童年往事的日常片段。戈達爾認為:“電影是瑣碎片段拼湊起來的人生。”(20)轉引自陳旭光:《電影藝術講稿》,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頁。這種專為電影創作的主題曲與電影所傳遞的意味相似,不僅能渲染影片情緒,更能讓觀眾在單獨聽主題曲時反復想起影片的場景。
中國詩電影是借鑒和吸收了中國傳統繪畫審美意蘊的獨有形式,無論是畫面還是講述方式,均有著鮮明的美學特色。如今的電影市場商業片泛濫,創作者急功近利,觀眾追求刺激性的視覺體驗,有時忽視了藝術片的存在,這種情況令人擔憂。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詩電影是經過了歷史積淀的,能夠喚起審美情感的,韻味無窮的“有意味的形式”。中國電影市場需要將傳統藝術與現代社會結合的詩電影,它可以提升大眾的視覺修養和構建具有中國傳統審美觀念的電影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