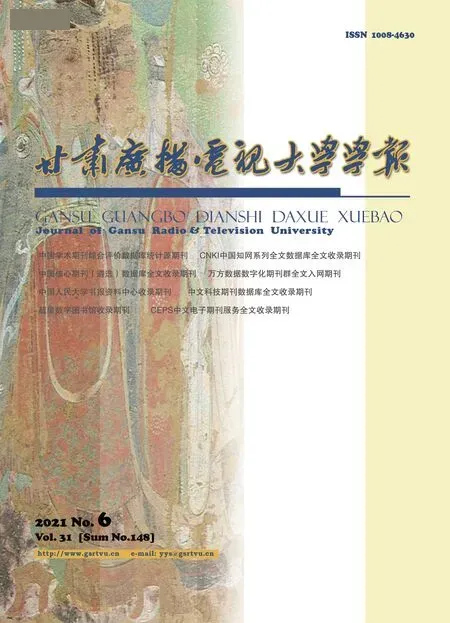論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的原因
李尚靜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由于傳主本人身份的多元性、文章體例的特殊性等原因,歷來受到學者的重視和討論,但仍有很多疑點亟須辨析。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的原因,目前學界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其一,“心折長卿”說,持此論者認為因人載文;其二,“愛其文賦”說,持此論者認為人以文傳;其三,“諷諫”說,此說本于司馬遷的賦論;其四,“以文傳人”說,章學誠首倡此說,啟發(fā)后學;其五,多元原因說,近代學者大多認為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的原因是多元的。但是,關于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并錄文的原因的研究,如果不立足于文本,很容易流入臆測。本文擬對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的原因,以及司馬遷選錄司馬相如文章的標準兩大問題進行研究,兼及司馬遷對《難蜀父老》和《大人賦》主旨的認識。
一、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的原則
關于司馬遷在本傳中對司馬相如所持的態(tài)度,學界存在兩種極端的觀點:一是持肯定態(tài)度。牛運震稱:“(《史記》)獨于司馬之文采錄最多,連篇累牘,極繁不厭,可謂心折長卿之至。”[1]696二是持否定態(tài)度。金錫齡指出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的原因在于“推原”武帝“窮兵黷武,敝中國以事四夷”之“禍本”,“歸咎于相如”[2]690。其實,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秉持“實錄”的原則,至于諸家從司馬遷的序事中得出或臧或否的不同結論,不是因為司馬遷持肯定或否定的一家之見,而是傳主作為個體的復雜性使然。
《史記》史料的來源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以“史記石室金匱之書”[3]4001為代表的文字史料;以金石、圖像、建筑為代表的文物史料;以游歷訪問、實地調查、取訪故舊、詢問交游為代表的口傳史料[4]。司馬遷對這些原始資料廣征互證,作了一番考信的工作,以求其真,以傳其真,是謂“實錄”。至于司馬遷之“愛奇”,也是以實錄為基礎的“實中求奇”,是在眾多可靠真實的歷史材料中選擇具有個性和特異性的事件予以記錄的偏向。
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秉持“實錄”原則。首先,“琴挑文君”“文君當壚”一事。司馬遷載此事意在“實錄”,至于后人以此貶譏相如“竊妻”“竊貲”①,則是出于個人的是非判斷。這件“異聞”的來源,與司馬遷的游歷訪問有關。司馬遷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3]3999,大概就是在此次出使中,他來到了司馬相如的故鄉(xiāng),從耆老故舊口中得聞此事。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于世”[5]1645,且曾為中郎將,出使巴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3]3692,其在蜀人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加之司馬遷與司馬相如所處時代相去不遠,蜀父老尚記憶猶新、津津樂道,故這則材料可信度較高。
其次,出使西南夷一事。對于這件事功,本傳中著重記錄的是相如的兩篇檄文,肯定其“除邊關,關益斥”[3]3692的成績。但在《平準書》中直言其弊曰:“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余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3]1715司馬遷使用互文法,雖在本傳中“多婉辭,為才人諱”[2]689,但亦不失“實錄”,稱美而不隱惡,“善惡必書”[6]。
再次,受金失官一事。此事可以說是相如一生的轉折點,之前相如仕宦是很積極的,但是“復召為郎”[3]3699后,司馬遷便稱他“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閑居,不慕官爵”[3]3699。受金一事,疑點頗多,司馬遷記述相如受金失官之后,緊接著說其“與卓氏婚,饒于財”[3]3699,此事前文已經言明,司馬遷的語言風格以“峻潔”稱,何必重復?且受金后“歲余”便“復召為郎”,未免過于輕率。總之,歷史上確有“其后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3]3699一事,司馬遷如是書,此即“實錄”。至于此事疑點,沒有史料佐證,不敢妄言,故于序事中微文傳疑,亦不失為“實錄”。
可見,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秉持“實錄”原則,這個原則貫穿《史記》全書。“實錄”是就史家對史實掌握及記述的真實性和可靠性而言,至于史家對史實的評價則屬于“義”的范疇[7]。司馬遷對司馬相如的褒貶皆以史實為基礎,有斯事故有斯褒貶,其事不同,故褒貶不一。后人對司馬相如的評價不同,也是因為個體的價值判斷不同,取“義”不同而已,不妨礙司馬遷之“實錄”。
二、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的原因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提及作列傳緣由時說:“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3]4027這是司馬遷在選擇人物進入列傳時所持的總體標準。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的原因是多元的,主要包括以下三點:
其一,司馬相如用文學的方式多方面推動了漢武帝的政策。據劉躍進考證,《子虛上林賦》定稿于元光元年(前134)[8]。此時,竇太后已死,漢武帝開始真正執(zhí)掌大權,實行了元光改元、崇尚儒術、設立太學、察舉孝廉等一系列政策。正當漢武帝準備將大一統理論在地理、政治制度、思想意識形態(tài)等各個方面推行時,司馬相如的《天子游獵賦》產生了。在這篇大賦中,司馬相如在地理方面禮贊了統一中國的遼闊疆域之美;在政治方面,退諸侯而進天子,加強皇權和中央集權,宣揚了以天子為政治中心的大一統理念;在思想方面,勾畫出以“游乎六藝之囿,騖乎仁義之涂,覽觀《春秋》之林”[3]3686為理想的禮樂中國、文化中國,突出了儒家思想作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地位。司馬相如作為時代的寫手,用“文”的方式開啟了漢代的儒學政治,在文學文化層面推行了當時國家行政層面的各項政策,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和價值。
其二,司馬相如的事功。司馬遷將《司馬相如列傳》編次于《西南夷列傳》之后,可見太史公對司馬相如開通西南夷的政治功績的推重。司馬相如的事功還體現在以下四篇政論文中:《喻巴蜀檄》集糾責、曉喻、安撫于一體,檄文一下,不費兵卒,平息動亂,“深得告諭之體”[9];《難蜀父老》為武帝開疆拓土的軍事政策加上了文明傳播的色彩,以超凡的政治遠見為武帝的地理擴張與文明傳播提供了支持;《諫獵疏》語含雙關,表面說身危,實際隱含著政荒國亡之深憂;《封禪書》為經國之巨制,這篇遺文以“大司馬”之口奏封禪之禮,言國之大事,從中可見司馬相如一生之所求與失意。以上四篇文章都與政治聯系密切,同屬應用性文體②。《西京雜記》說:“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10]可知,司馬相如的歷史貢獻絕不僅限于文學,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首先著眼的是其事功,其政治家的身份是第一位的。
其三,司馬相如在文學方面的貢獻。司馬遷用錄文的方式肯定了傳主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司馬相如的大賦是新的文學形式,是漢代特有的文化現象,是大漢盛世時代精神的產物,漢代文學繁榮的局面離不開司馬相如的功績,出于“實錄”原則和良史之“識”,司馬相如其人其文也有載于史冊的必要。司馬遷對相如賦的文學美感的體認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想象和虛構。司馬遷在記述《天子游獵賦》本事時稱:“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3]3640“空藉”一詞直接點出了相如辭賦想象和虛構的特點。二是巨麗之美。司馬遷評價相如賦“侈靡過其實”[3]3689、“多虛詞濫說”[3]3722、“靡麗多夸”[3]4025,雖持否定態(tài)度,但也從另一個側面表現出司馬遷感知到司馬相如賦夸張、麗藻和虛構的特點。
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固然有對其文學成就的考量,但更多還是從“事功”的角度,去衡量司馬相如的政治功績,更重要的是,考察司馬相如的作品對當時國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政策所起的作用及其歷史意義。總之,司馬遷之所以為司馬相如立傳,是因為司馬相如及其作品確有傳之不朽的價值和地位,是基于實事求是的“實錄”原則。
三、司馬遷選錄司馬相如文章的標準
“以文存人”是一種重要的立傳方式,《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體例的特殊性在于其大量載錄了傳主本人的文章。研究司馬遷選錄司馬相如文章的標準,有助于我們深入把握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的原因。《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選錄七篇文章,賦三篇,分別為《天子游獵賦》《哀二世賦》《大人賦》;散文四篇,分別為《喻巴蜀檄》《難蜀父老》《諫獵疏》《封禪書》③。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共有三處,司馬遷明確提出自己的選錄標準,茲分別討論之。
(一)“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錄《天子游獵賦》后,寫道:“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云夢所有甚眾,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3]3689此處,司馬遷明確提出自己的選錄標準為“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其言“刪取”,但此賦并未經過刪削,“刪取”一詞為偏義復詞,“刪”的意義已經淡化,主要強調“取”的意義。《史記索引》引小顏云:“刪要,非所謂削除其詞,而說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剟,失之也。”[3]3689既已收錄全賦,猶謂“刪取其要”,乃是司馬遷言自己對于所錄之賦,有所去取。
司馬遷收錄《天子游獵賦》,所去者為何?所取者又為何?《史記索引》引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于正道耳。”[3]3689蓋去其“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之處,取其“歸于正道”之處,即“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以下。
可見,太史公錄賦之意,不在司馬相如大賦的閎侈巨衍、靡麗之詞,而在其曲終奏雅的諷諫部分——“明天子之義”[3]3640。
(二)“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錄《封禪書》后,在全文結尾指出:“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3]3722可見,司馬遷的另一個選錄標準為“尤著公卿”,即重視作品在官員和政治方面的影響。
“西漢官僚體系中除了祿秩系統以外,還存在著以‘公卿大夫士’形式排列的‘爵位’系統”[11],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中職官與“位”的對應關系,“公卿”代表了整個官僚體系的上層。“尤著公卿”即重視作品在上層官僚中的影響力,或者說,對朝廷及政治的影響力。
“尤著公卿”點明了司馬相如文章的讀者及受眾,司馬相如大部分作品在創(chuàng)作中的預設讀者和實際的首席讀者都是天子,故其文具有“代天子立言”[12]48-57的性質。《天子游獵賦》宣揚了皇權、大一統和以儒學化洽天下的思想;《喻巴蜀檄》《難蜀父老》力排眾議,闡發(fā)了漢武帝開邊政策的意義;《封禪書》昭示了封禪儀式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以一種勸天子封禪的積極姿態(tài),力促漢武帝舉行泰山封禪。可知,司馬相如的作品與天子之心和時代意志的契合,其文在“公卿”之間的傳播,“使咸知陛下之意”[3]3692,為漢武帝各項政策的推行起到了輿論造勢的作用。
司馬相如自己雖官職不高,僅為“言語侍從之臣”[13]21,“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3]3699,但其文章卻“尤著公卿”,通過文學的方式在政治方面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影響力,其鴻文直接與時代精神和天子意志建立起深微的聯系,這也從側面體現出司馬相如的政治功績。
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只提及篇名,并未錄文,三篇已佚,以篇名觀之,似乎更偏向于私人性和學術性,與國家政治和帝王生活關系不大。此外,與司馬相如同時且有作品傳世的文人還有很多,如鄒陽、羊勝、枚乘等,但是司馬遷或者沒有為他們立傳,或者沒有錄文,其原因大概就在于“尤著公卿”這個標準。由此可見司馬遷在立傳和錄文時對傳主本人及其文章的政治影響力的重視。
(三)“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記載太史公曰: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jié)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wèi)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3]3722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楊雄”此下28字,為“后人以《漢書贊》附益之”[14]非司馬遷原文,故不論此句。“太史公曰”是司馬遷在史傳中抒發(fā)己見的重要形式,其在此指明自己的選錄標準為——“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司馬遷所謂“可論者”,即“太史公曰”指出的相如文章與儒家經典的“合德”之處——“節(jié)儉”和“諷諫”。統觀本傳及《太史公自序》中與本傳有關之語,共有三處談及“歸引”,分別為“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3]3689、“然其要歸引之節(jié)儉”[3]3722、“然其指風諫,歸于無為”[3]4025。可見,司馬遷在選錄司馬相如文章時,自覺地以儒家傳統詩教為準,表現出重視文章現實功用的思想傾向。
這種思想傾向也存在于《屈原賈生列傳》中,司馬遷贊《離騷》為“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3]4022、“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3]3010。不為宋玉之徒立傳的原因則是雖有“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3]3020。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表達了司馬遷對相如文章諷諫性的肯定,表現出司馬遷對文學作品現實功用的重視。
總之,司馬遷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對司馬相如文章的選錄,雖然客觀上可能會讓讀者產生太史公尚文辭、重詞章、“特愛其文賦”[15]的感受,即重視相如作品的文學特質。但是從司馬遷的主觀意圖,或者說從司馬遷明確表示出來的標準而言,他更看重的是文章與現實政治的聯系,推重那些具有現實作用、諷諫作用、教化作用,在當時有政治影響力的文學作品。可見,司馬遷對司馬相如文章的選錄標準與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的原因是一脈相承的。
四、司馬遷對《難蜀父老》和《大人賦》主旨的認識
(一)司馬遷對《難蜀父老》主旨的認識
關于《難蜀父老》的主旨,文人學者的觀點不一,或認為其文質兼美、合于禮法,東晉文學家李充稱其為“德音”[16];或認為其助君之惡、阿諛媚上,蘇軾言:“(相如)創(chuàng)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17]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相如作《難蜀父老》的緣由為:“相如欲諫,業(yè)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3]3694可見,司馬遷指出此文有兩層主旨:一為“風”,司馬相如“建節(jié)往使”[3]3692,“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3]3694,此時相如或已認識到了通西南夷之弊,故借蜀父老之言諷諫天子。對比司馬相如出使前后所做的《喻巴蜀檄》和《難蜀父老》兩文,可見其態(tài)度之變化。《喻巴蜀檄》作于出使前,一味訓誡蜀民急國家之難,其責甚切;《難蜀父老》作于出使后,反復言及“百姓之勞”,其意甚憐。一為“宣”,通西南夷又確有其必要性,是“天子之急務”,功在千秋,澤流萬邦,可見相如開闊的政治眼光。司馬相如具陳利弊,以示天子。司馬遷已將其意明言,蓋真知己也,奈何后人以“導諛”度之。其“不敢諫”的原因蓋如張耒所說的“夫既以開其利于前也,徐覺其害,又不忍默然”[18],司馬相如自悔前言,對此事頗有微詞,又怕違逆帝意,故不敢直諫。
在客觀效果上,這篇作品對“天子之意”的宣揚之義遠超諷喻之義,但是不能據此評價相如是“逢君之惡”。一方面是因為司馬相如確實反對“蜀父老”只重眼前利益的一隅之見,表現出與天子相合的政治眼光;另一方面是因為漢大賦的言說方式就是推而隆之、欲諷反勸、欲抑反揚,這就是賦家與天子和諧溝通的途徑。武帝開邊之舉牽涉甚廣,公孫弘以相位之尊尚且“不肯面折庭爭”[3]3574,何況司馬相如身居文學侍從之下位。
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言,自己之身份為“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所畜,流俗之所輕”,即使“伏法受誅”,世也不能“與能死節(jié)者比”,“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13]579。對于司馬相如被誤解貶毀的遭遇,司馬遷豈無惺惺相惜之痛?即使司馬遷確有借相如之文貶刺武帝之意,也恐怕沒有譏諷相如不能諫止之意。
(二)司馬遷對《大人賦》主旨的認識
關于《大人賦》的主旨,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此賦針對“上好仙”而作,“大人”指帝王,目的在于諷諫武帝,但客觀效果是“勸而不止”。揚雄、顏師古、姚鼐都力主此說。顏師古評:“昔之談者咸以西王母為仙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娛游之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羨慕也。”[5]2598二是認為“大人”指得道之人。萬光治指出,此賦寫的是由求仙而至得道的精神歷程,是文人之思而非帝王之思,這是一篇從傳統“悲士不遇”的主題中游離出來的游仙兼思玄作品[19]。
司馬遷曰:“《子虛》④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夸,然其指風諫,歸于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3]4025太史公將《大人賦》的主旨歸于兩點:“風諫”和“無為”。
一方面是“風諫”的主旨。據司馬遷對《大人賦》本事的記載,相如獻賦的原因是見“上好仙道”,又“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3]3703。“帝王之仙意”豈非長享富貴之奢欲哉?故賦中以“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風之,“長卿則謂帝若果能為仙人,即居此‘無聞’‘無見’‘無友’之地,亦胡樂乎此耶?”[20]表現出司馬相如對武帝求仙活動的冷靜審視和對“生”的本質要義的追求。
另一方面是“無為”的主旨。“無為”是老子思想的重要命題,他提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21],“無為”不是“不為”,而是順應自然、不妄為,這樣才能以超功利達到大功利,實現“無不為”。司馬遷將這個道家哲學的核心概念引入對相如賦的批評中,顯然與他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有關。如果說“《子虛》之事”“歸于無為”,“無為”還與儒家“節(jié)儉愛民”的思想相通,那么“《大人》賦說”“歸于無為”,“無為”則更多地指向道家思想。
“無為”首先是司馬相如晚年對漢武帝多欲政治的反思。司馬相如用“文”的方式在政治、文化、思想等多個領域推動了漢武帝的各項政策,但仍然身居底位,與自己出將入相、位列眾卿之長的大志相差遠矣。失望之余,司馬相如對漢武帝治理天下的方式進行了深刻反思,既肯定武帝的雄才偉略,也看到了漢武帝的種種弊病——各方面追求有為,故以“無為”止之,“先行代言出漢武‘罪己詔’的本質內容”[12]48-57。
更重要的是,“無為”也是司馬相如對自我的反思。《大人賦》開頭曰:“悲時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游。”這是典型的屈原式的文人之思,是司馬相如對自己精神出路的思索和探求。高光復指出:“這種情緒之中包含著對世俗的厭棄,在他(相如)的其他作品中似乎不曾流露過。或許是到了晚年,歷世既久,對于現實有所體會,通過本篇有所寄托罷。”[22]這種思索的最終結果便指向無為、無物我、無死生的道境。
嵇康發(fā)現了司馬相如的道家思想傾向,他在《圣賢高士傳贊》中為司馬相如立傳并作贊,稱相如“越禮自放”[23],將其視為隱逸遁世之人。聞一多指出了《大人賦》與道家思想的聯系,他認為《大人賦》寫的是“無積的大,《莊子》的大,為想象空間的大”[24]。后世對《大人賦》“勸而不止”的批評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因為在這篇更富有主觀抒情性的騷體賦中,司馬相如并不是為國家、宗族的命運而游,而是為個人的解脫而游。
許結曾經這樣評價漢賦的思想內涵,他說:“正因為漢賦藝術本身形成兼容南北文化的態(tài)勢,所以其表現儒道哲學思想有時涇渭分明,有時交叉模糊。”[25]深受儒道哲學影響的司馬遷在司馬相如的賦中,自然地發(fā)現了這兩家思想的并存。如果說,司馬遷對《大人賦》“風諫”主旨的揭示,更多體現了儒家思想。那么,司馬遷對《大人賦》“無為”主旨的揭示,更多的則是文人以道家思想為寄托,對現實政治的反思,對人生困境的超越和對絕對精神自由的追求。
司馬遷為司馬相如立傳并錄文的作法具有重要的史學意義和文學意義。就史學意義而言,此舉既是對先秦史傳傳統的繼承,也是對后代史傳體例的開創(chuàng)。一方面,其源流可以追溯至先秦史書的記事與記言;另一方面,又為《漢書·藝文志》《后漢書·文苑傳》等篇提供了史傳采文的體例和范式。就文學意義而言,此舉既提高了《史記》自身的文學價值和文獻學價值,也對文學總集的產生和漢賦經典地位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影響。
注釋:
①揚雄曾說:“司馬長卿竊貲于卓氏。”劉勰亦云:“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
②劉躍進《〈獨斷〉與秦漢文體研究》(《文學遺產》2002年第5期,第13-25頁)稱:“就秦漢時代而言,文體的觀念還沒有后世那么明確,大多數的文體還是以應用為主……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說,那些應用性文體更能得到時人的重視。”
③依據蕭統《文選》對文體的劃分,《喻巴蜀檄》和《難蜀父老》同屬“檄”類(卷四四),《諫獵疏》屬“上書”類(卷三九),《封禪書》屬“符命”類(卷四八)。
④此處依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所注標點,但“《子虛》之事”指代不明,這里筆者姑且將“《子虛》之事”看作是對《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全文收錄的《天子游獵賦》的代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