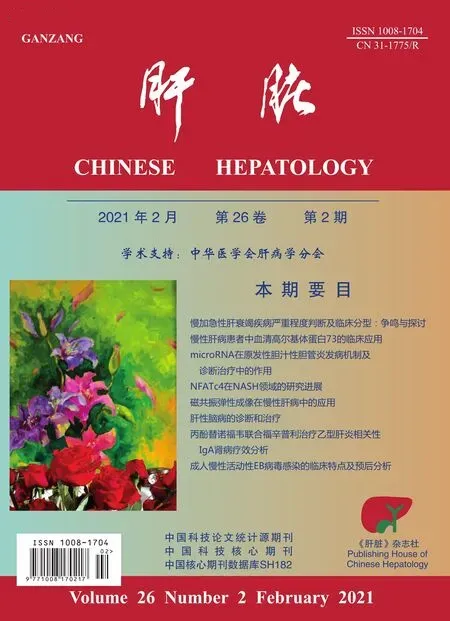肝性腦病的診斷和治療
朱姝 王璐 張燁瓊 彭亮 高志良
肝性腦病(HE)是慢性肝病和急性肝衰竭常見且嚴重的并發癥。一直以來,HE被認為是一種代謝性疾病,在肝移植后可以逆轉,這一認識正隨著大量研究而改變。從病理生理學的角度來看,氨在HE的發病機制中仍發揮著中心作用。血腦屏障的通透性/功能、腦脊液成分、類淋巴回流、腦能量代謝、神經傳遞、細胞間通訊紊亂,均能導致神經功能障礙。本文就慢性肝病相關的HE分類和分級、機制以及治療和預防等進行綜述。
一、HE的分級、分類和診斷
HE廣泛定義為由肝功能不全和(或)門靜脈系統分流引起的腦功能障礙,表現為從亞臨床改變到昏迷的廣譜神經精神異常[1]。廣泛應用的West-Haven標準根據臨床表現將HE分為0~4級[2]。近年來,ISHEN提出的肝硬化神經認知功能變化譜(SONIC)標準將無明顯認知功能異常表現的輕微型肝性腦病(MHE)和West-Haven標準0、1級HE統稱為隱匿型HE(CHE);出現明顯神經精神異常的2~4級HE統稱為顯性HE(OHE)。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臨床標準定義的HE分級不可重復,不適用于臨床試驗。目前應用于臨床試驗的分類方法有HE評分算法、臨床HE分級量表、HE分級工具等[3 4]。
HE的診斷具有挑戰性,主要依據急性肝功能衰竭、肝硬化和(或)廣泛門體分流病史、神經精神異常的表現以及特殊輔助檢查,并排除其他神經精神異常。OHE的診斷相對直接,在復雜的情況或沒有明顯誘因時,診斷可能變得困難。對于診斷不明確,特別是出現局部神經表現的患者,應進行腦的影像學檢查。當癥狀輕微且診斷工具有限時,診斷性治療可有助于確診。CHE的診斷則需要患者陪護人員的仔細觀察,MHE的診斷還需要數字連接試驗、數字符號試驗等神經心理學測試。
在HE的診斷中,正常濃度的血氨陰性預測值很高(0.81),可用于診斷排除[5]。無論肝性腦病程度如何,80 μmol/L的血氨界值與高死亡風險相關[6]。這表明,氨不僅僅是一種神經毒素,而且可以作為肝硬化和急性肝功能失代償患者預后的生物標志物。同時,氨的檢測很不容易,需要仔細的樣本處理、快速檢測和可靠的分析設備來獲得準確的結果。理想的血氨抽取條件如下:最好在患者空腹時抽取靜脈血,放置于帶有穩定劑的試管中,立即在冰上冷藏,送到實驗室迅速(30~60 min內)分析。如果是采用動脈或毛細血管檢測血氨,應獲得并使用相應的參考值[7]。
對于肝硬化HE患者群體,血氨水平隨HE分級的嚴重程度而升高[6],但HE分級之間存在大量重疊,沒有絕對數值來區分嚴重程度。所以在HE的診斷和分期中,血氨水平不應優先于臨床檢查。
二、發病機制及病理生理學
(一)全身性因素 氨中毒學說仍是HE的核心發病機制。有意思的是,在高級別的HE人群中,肝硬化患者與急性肝衰竭患者相比,血氨濃度更低[6]。這可能提示肝硬化引起的肝性腦病可能存在除氨以外的重要的病理生理機制。系統性氧化應激和炎癥反應自身以及與高氨血癥的相互作用促進HE發生、發展。近期的研究表明,低鈉血癥與HE風險之間存在線性關系[8],未并發HE的肝硬化患者通過改善低鈉血癥可增強其對復雜信息的處理[9]。另外有研究發現,在膽管結扎誘導的肝性腦病大鼠腦內檢測到膽汁酸,從而引起神經炎癥[10]。
(二)神經病理生理學 血腦屏障的存在使得除了氨之外,發生在血液中的變化不一定發生在大腦中,反之亦然。神經系統本身的病理生理變化值得關注。腦內有缺陷的類淋巴系統(用于清除大腦中堆積的各種物質)可能參與HE的進展[11]。神經體液途徑通過上調神經甾體濃度正向調節GABA-A受體復合物,增加GABA能張力也是潛在機制[12]。能量代謝相關的產物濃度變化在HE患者腦脊液樣本中的顯著差異表明神經細胞能量代謝受損存在[13]。嚙齒動物HE模型還發現,神經退行性變是HE的可能機制[14]。
在肝性腦病中,神經元死亡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肝移植后神經系統并發癥的出現、以及氨可通過誘導星形細胞衰老導致神經元死亡被證實,神經元死亡、永久性腦損傷也許應納入HE的發病機制[15-16]。這將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對HE是一種可逆的綜合征的認識。神經元死亡機制尚未明確,將成為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而現代迅速發展的多功能核磁共振檢查手段也為肝性腦病的神經病理生理研究提供了更加先進的方法。
(三)肝腸軸和微生物組的作用 隨著測序技術的快速發展,對肝臟-腸道甚至遠離肝腸軸位置的微生物的進一步了解為HE提供了新的機制思考方向。腸道環境對HE患者的大腦功能有重大影響,藥物能改變腸道環境,進而改變大腦功能。腸道微生物無論在種類組成還是功能方面都與HE相關[17]。例如,變形桿菌門(腸桿菌科,包括大腸桿菌、肺炎克雷伯菌等)因為產生各種破壞性的內毒素,是潛在的“有害菌”。某些革蘭陽性梭菌(毛螺菌科、疣微菌科)家族因為產生短鏈脂肪酸并具有膽汁酸轉換的能力被認為是定植且潛在有益的[18]。肝硬化的病因改變了患病和發炎的肝臟產生膽汁酸的能力,清除來自腸道的細菌抗原的能力也受到損害,導致潛在致病變形菌的增加。由受損腸道環境產生的毒素,如氨和炎性細胞因子進入循環,使肝性腦病加重或爆發[19]。肝硬化的細菌類群在糞便、大小腸黏膜、腹水和肝臟本身的組成受損(更多的潛在致病菌和更少的定植菌)[20-23]。然而,類似的微生物變化也發生在遠離腸道-肝臟的地方,如唾液和血清,這可能歸咎于潛在的免疫抑制狀態[24-25]。細菌譜可以預測肝硬化患者的住院、死亡和器官衰竭,并可能具有臨床相關性[22]。最近的證據表明,真菌失衡也可能在肝硬化進展中發揮作用[26]。因此,調節肝性腦病中微生物群的組成和功能可能影響臨床病程、腦功能,甚至依此制定有效的治療干預。
(四)營養不良和肌肉減少 營養不良是慢性肝病的常見癥狀,肌肉減少癥在肝硬化患者中幾乎是普遍的。肌肉中的谷氨酰胺合成酶在肝臟疾病期間行使氨解毒的重要代償功能,伴隨肌肉減少癥的肝硬化患者有更高的氨水平和更高的肝性腦病風險[27]。
三、HE對肝移植術后神經系統預后的影響
過去,HE被定義為一種代謝性疾病,能在肝移植后被完全解決。然而,肝移植后持續的神經系統并發癥仍然影響著可能高達47%的肝移植患者[28]。研究記錄了有HE病史的患者在肝移植術后出現神經恢復受損,提示反復發作的HE導致永久性細胞損傷[29]。不可逆的腦損傷可能無法通過肝移植來解決。在肝移植受者中觀察到的神經系統并發癥是肝移植前的殘留癥狀還是新近發生的圍手術期癥狀(肝移植影響),或與共病有關,目前難以準確定義。
四、HE的治療和預防
慢性肝病患者OHE發作的一般治療包括生命體征的監護及維持、去除誘因和營養支持。需要強調的是,營養支持應避免限制蛋白質的攝入。應達到基于指南的目標卡路里攝取量,充足的蛋白質攝入量,減少空腹時間,注意給予夜間和清晨含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加餐等。
大多數HE的治療方案都是針對氨,即減少氨的產生和重吸收。當前HE 的治療主要為不可吸收雙糖(乳果糖和乳糖醇)和口服吸收極少的抗生素(利福昔明)、支鏈氨基酸、益生菌和L-鳥氨酸-L-天冬氨酸。白蛋白和白蛋白體外透析(ECAD)治療發揮了白蛋白對抗炎癥和清除毒素的能力;除ECAD外,血液濾過降低血氨也非常有效。
處于臨床階段的新興療法包括苯乙酸鳥氨酸酯、苯丁酸甘油酯和糞便微生物移植[30-31]。處于臨床前階段的新興療法包括脂質體支持的腹膜透析(LSPD)、工程細菌、活性炭微球、γ-氨基丁酸A型受體調節類固醇拮抗劑(GAMSA)和谷氨酰胺合成酶替代療法[32-35]。
近年來,得益于醫學生物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們對HE病理生理學的理解有了相當大的提高。在此基礎上,更多靶向治療方案將會被提出。隨著生活質量要求的提高,HE患者的家庭管理和監測手段亟待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