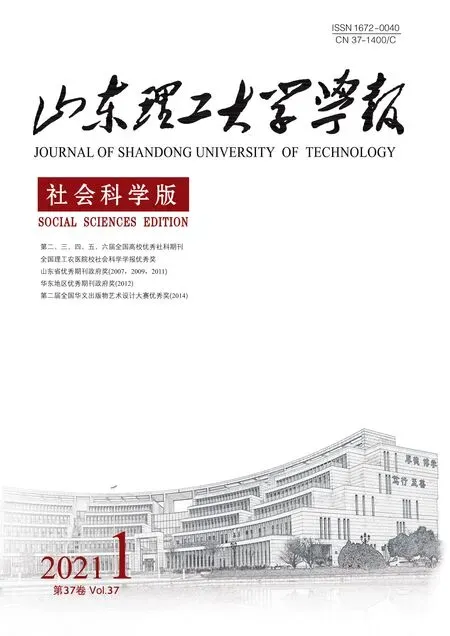董事的破產申請義務研究
朱翔宇,于永寧
一、問題的提出
立法層面,我國《企業破產法》第7條規定,針對未解散的企業,有法定情形時,債務人、債權人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產清算申請。針對已解散的企業,依法負清算責任的人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破產清算申請。質言之,在公司瀕臨破產時,只要其還未解散,則不存在破產申請義務人,僅存在破產申請權利人。同時,雖然我國《公司法》第147、148條規定了公司董事的信義義務,第148條更是通過禁止性事項列舉的方式對信義義務的范圍作出界定,但其中也并未涉及董事的破產申請義務。此外,公司制度中的信義義務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自我道德與良心的約束來加以實現[1],法律難以作出精細規制,這為我們通過構建解釋論來彌補漏洞留下了充足的空間。
實踐層面,由于董事破產申請義務的缺失,很多本該進入破產程序的危機企業往往會鋌而走險,選擇繼續經營以求起死回生,但大多不會成功并可能走向如下兩種極端:一者,大部分企業成為僵而不死的“僵尸企業”。截至2016年,在《企業破產法》頒布的十年內,法院每年受理的破產案件數量只有兩三千件,通過司法程序退出市場的“死亡企業”占比不足1%,與“僵尸企業”龐大的體量相去甚遠[2]。央行2018年數據顯示,我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約為三年,成立三年后的正常經營比率僅為三分之一左右[3]。照此數據粗略計算,同年我國無法維持正常經營的中小企業數量至少以百萬計,但全國審結公司清算、企業破產等案件的數量僅在1.6萬件左右[4],大量“僵尸企業”仍無法迅速退出市場。二者,小部分企業通過司法程序進行破產清算。但在此之前,公司的資產往往會被利益相關者轉移,或因為企圖挽救公司而進行的冒險商業行為虧損殆盡,最終進入破產程序的企業幾乎沒有資產或僅有極少資產,使得債權人的利益難以得到保障[5]。
梳理我國既往研究成果,為了避免陷入經營危機的公司不主動向法院申請破產而產生種種問題的現象,學界對于在法律中明確董事破產申請義務的呼聲較高[6-7]。但科以董事破產申請義務也可能存在其為避免承擔個人責任而過早地向法院申請破產,導致公司錯失被拯救機會的可能。因此,在引進破產申請義務時,不應持“人有我有”的心態,而應立足我國現狀,探究有效可行的路徑。且法律的修改或制定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我國正處于后新冠疫情背景下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關鍵時期,大量企業面臨市場退出問題。為了切實解決我國當前的現實問題,應在解釋論與立法論兩個進路上“雙管齊下”。在解釋論進路上,應明確作為董事信義義務的破產申請義務,為當下董事的履職行為提供指引;在立法論進路上,應對董事違反破產申請義務的責任作出特別規定,在法律層面明確責任性質、賠償對象、賠償范圍以及免責條款。
二、解釋論進路:明確董事的破產申請義務
(一)義務主體:董事而非股東
如前所述,對已解散公司,清算義務人即為破產申請義務人(《企業破產法》第7條)。依據《民法典》第70條的規定,清算義務人主體是法人的董事、理事執行機構或者決策機構的成員。我們認為,之所以立法者將股東排除在外,而著重強調已解散公司的董事等實際經營參與者的清算義務人兼破產申請義務人地位,是因為董事直接參與公司的經營與管理,更清楚地了解公司內部狀況;而股東作為公司的剩余索取權人,在公司瀕臨破產時會產生與公司債權人不可調和的矛盾。依據上述立法邏輯,角色的定位決定了瀕危企業的破產申請義務主體應是董事而非股東。
1.股東不宜成為破產申請義務人
公司內部存在三大沖突,分別為經營者與股東之間的沖突、股東之間的沖突、股東與包含債權人和職工在內的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沖突[8]。在公司瀕臨破產的語境之下,股東的機會主義行為會加劇其與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沖突,使二者處于對立地位的兩端。對股東來說,破產清算時公司財產會按順位先行償付給各類債權人,到達股東時往往已無財產可分或僅剩“殘羹冷炙”,這是股東不愿意看到的結果。因此,他們往往在企業瀕臨破產時提升風險偏好,進行“高風險、高收益”的商業活動,冒險地進行自我拯救,希望能夠避免企業進入破產清算程序。若冒險成功,企業起死回生后可以繼續給股東帶來收益;若冒險失敗,股東依然會受到有限責任的保護,僅在自身出資范圍內承擔責任,在這一意義上,股東具有天然的高風險偏好。但對債權人而言,若公司的冒險行為失敗則可能造成極大的利益損害,因此他們更希望瀕臨破產的公司避免風險過高的商業決策,維持資本以實現對債務最大比率的清償。因此,若將破產申請義務賦予股東,顯然不利于保護債權人,也是缺乏期待可能的。
2.董事宜成為破產申請義務人
在當今世界政壇上,以獲得多數選票取得的政治權力具有顯性的合法地位。而通過革命獲取的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卻少有人加以研究。
第一,如前所述,股東一般并不直接承擔公司的經營與管理義務,普遍認為有限責任制之下,股東出資義務是其全部義務,除此之外不再承擔任何法定義務[9]。而董事直接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全面掌握公司各類經營信息、財務狀況,再加之專業的商業判斷,更能夠確定對陷入危機的企業提出破產申請的最佳時機。第二,存在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兼任董事的情況,此時股東與董事身份統一,既是公司的剩余索取權人,又是公司的實際經營管理者,則又會出現發生在董事身上的機會主義傾向。且即便董事并非由股東兼任,公司破產也會導致董事失去在公司中的工作以及相應獲得薪水的機會,還會造成業內對董事經營能力的負面評價,這些都是使董事作出違背債權人初衷和利益的商業決策的“不當激勵”(Perverse Incentive)[10]。因此,為了保護債權人利益,規制股東兼任董事與董事受到“不當激勵”而進行的機會主義行為,明確董事的破產申請義務人地位是必要的。
(二)公司瀕臨破產時董事信義義務的間接指向:股東到債權人
企業破產并非一天形成的,而是日積月累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原有公司權力分配格局下的信義義務結構會造成較高的代理成本,因而需要作出一定的調整[11]。若允許董事只服務于股東利益,那么一定會產生具有“僵尸企業”特征的風險經營行為,僅使股東獲得收益,而債權人承擔風險[12]。因此,董事信義義務的調整取決于公司財務狀況,公司資不抵債的程度越高或導致資不抵債結果的可能性越大,就應有越多的信義義務從股東轉向債權人[13]。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說信義義務的轉變并非直接指向的轉變而是間接指向的轉變。《公司法》第147條規定董事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也就是說,以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為基礎的董事信義義務履行的直接指向始終為“公司”這一主體,而非其股東或債權人。因此,雖然董事由股東會或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但其并不當然成為股東的利益代表人,而應作為公司的利益代表人,對整個公司負責。既然是對公司整體負責,那么董事就應當將公司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納入履職時的綜合考慮范圍,平衡股東、債權人在內的各方利益。此時,股東、債權人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對董事履行信義義務的受益都通過公司的間接傳導而獲得。因此,股東、債權人均為董事履行信義義務的間接受益主體,是董事信義義務的間接指向;公司是董事信義義務履行的直接受益主體,是董事信義義務的直接指向。
公司正常經營時,股東享有資產收益并參與重大決策的權利(《公司法》第4條),董事會執行股東會的決議并對股東會負責(《公司法》第46條)。但股東的資產收益是以公司資產收益為基礎的,法院處理盈余分配時,仍應當首先考慮公司的利益,此后才考慮股東收益權的實現[14]369。董事亦應當依照上述利益位階履行職責,因為其信義義務的直接指向為公司,間接指向為股東與債權人,所以必須先向公司負責,通過經營管理使公司持續盈利,而后股東才能夠通過分紅的方式獲得資產收益。這個過程中,董事是股東的代理人,更關注如何高效履行股東會決策,為股東實現公司的營收目標,其信義義務的間接指向也偏向于股東而非債權人。
但在公司破產時,《企業破產法》具有傾斜保護債權人的特征,規定債權人對公司的債權法定優先于股東對公司的剩余索取權(《企業破產法》第113條)。既然法律賦予了破產時債權人較股東對公司剩余財產的優先索取權,那么在公司瀕臨破產的處境下,債權人利益就占據了公司整體利益的更大部分。并且,企業進入破產程序后,和解、重整、清算分配等重大事項都是由債權人會議決議通過的而非股東會或股東大會(《企業破產法》第61條),也就是說,破產企業的命運由債權人實際控制而非股東。因此,為了更好地保護債權人,公司瀕臨破產時,董事信義義務的間接指向也應當更偏重于債權人而非股東,否則就無法保障企業破產時財產不會大幅減少,難以實現破產法所期待的債權人保護效果,違背我國《企業破產法》之立法本意。
公司由正常經營到破產的過程也是一個自身資產狀況不斷惡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中,經營狀況的惡化往往不是“斷崖式”的,而是日漸加深的。董事信義義務的間接指向亦是如此,在公司由正常經營到破產的過程中,由偏重股東轉化為偏重債權人,且程度隨著公司經營狀況的惡化而提高。
(三)破產申請義務:公司瀕臨破產時董事信義義務的內容
在某種意義上講,董事信義義務不過是民法帝王條款“誠實信用原則”在公司法上的延伸[14]438。其中,勤勉義務起到克服董事懶惰和無責任心的作用,忠實義務起到克服董事貪婪和自私行為的作用[15]。但是,《公司法》中有關董事信義義務的條款過于偏向原則性規定,需要解釋論進行彌補[16]。而對于偏原則性的義務內容變化該如何進行解釋?我們可以從民法中尋找答案。
在民法中,合同法上的附隨義務同樣以誠實信用原則為依據,并隨著合同關系發展而產生,旨在使債權人的給付利益獲得最大可能滿足(輔助功能)或維護對方人身財產利益(保護功能)[17]。比如,買賣合同中出賣人交付標的物之前的保管義務,簽訂合同雙方對所知悉商業秘密的保密義務,其他當事人以誠實信用原則為基礎而應當履行的附隨義務,違反附隨義務則可能承擔包括固有利益在內的損害賠償責任[18]。雖然附隨義務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從目的上看,很多具有保障債權人利益最大化以及相對方人身財產權益的行為都被解釋進了附隨義務中,所以附隨義務才在合同關系中的義務群內占據了重要地位,對實現債權人利益最大化有重要作用。
再回歸到董事信義義務,同樣作為誠實信用原則在部門法中的具體體現,在公司瀕臨破產語境下,也具有保障債權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如前所述,公司由正常經營走向破產的過程中,董事信義義務的間接指向由股東轉為債權人。為滿足間接受益人的利益需求,信義義務的內容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當公司無拯救可能時,董事向人民法院提出破產申請更能滿足債權人利益需要,也最符合公司整體的利益要求,因此,從客觀目的解釋的視角,將破產申請義務納入董事信義義務是合理且必要的。首先,對外來說,公司應當承擔社會責任(《公司法》第6條),明確破產申請義務作為董事信義義務有助于“僵尸企業”的清退,減少無效供給,優化存量,提升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培育企業家精神。其次,對內來說,有效防范股東的機會主義行為,保障公司與債權人利益。董事破產申請義務的空白導致了公司瀕臨破產時內部治理的混亂,使利益主體各方“野蠻競爭”,難以達成利益的平衡,且股東總把公司看作財產而非組織,更難以緩解其與債權人之間的矛盾。最后,明確破產申請義務作為董事信義義務的解釋論構建彌補了法律漏洞,即能夠為當前公司治理實踐提供依據,也能夠為立法論的構建奠定理論基礎。
三、立法論進路:明確董事違反破產申請義務的責任邊界與免責事由
(一)現行法律規范缺乏解釋空間
違反義務造成損害后果的,應承擔相應的責任,《企業破產法》有關董事責任的條款集中于第125條與第128條。第125條規定,董事因違反忠實義務、勤勉義務致使所在企業破產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該條款的主要問題在于責任對象不明確,若將責任對象解釋為公司,則僅強調了董事違反信義義務導致企業破產的嚴重后果,是《公司法》中董事違反信義義務責任承擔條款在破產法上的體現,有重復立法之嫌[19]。若因《企業破產法》在立法目的上具有保護債權人的傾向性,而將責任對象解釋為債權人,則又缺少責任范圍與追責方式的規定,不具有實踐可操作性。且申請破產并非董事違反信義義務導致的企業破產,反而是對信義義務的恪守,難以通過該條款明確董事違反破產申請義務的責任。
《企業破產法》第128條規定,債務人存在本法第31、32、33條所規定的減損企業財產、個別清償、藏匿財產的行為,侵害債權人利益的,債務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他直接責任人應承擔賠償責任。該條款將董事對債權人責任行為劃定在了一個較小的范圍,董事破產申請義務顯然無法在此范圍內解釋,造成了董事對債權人責任立法層面的“掛一漏萬”現象。現行法律框架下,既沒有關于董事不履行破產申請義務的責任承擔規定,也無法通過解釋學構建將其明確,為彌補制度漏洞,只能通過立法論的構建以進行特別規定。
(二)對董事違反破產申請義務的責任承擔進行立法論構建
1.原告資格
德國法明確規定董事違反破產申請義務的責任承擔對象為債權人,《德國民法典》第42條第2款規定,在債務超過情況下,董事會應立即申請開始破產程序。因過失對申請延遲負有責任的董事會成員,對債權人因此而受到的損害承擔責任;他們作為連帶責任人負其責任。作為判例法國家的美國在1991年的“Credit Lyonnais Bank Nederland,N.V.v.Pathe Communications Corp”案中明確了董事在公司瀕臨破產時對債權人也負有受托義務,又于2001年“Oficial Committe of Unsecured Creditors v.R.F.Lafferty & Co.,Inc.”案中明確了公司瀕臨破產時,若董事不及時申請破產反而進行不當的繼續經營決策,則可能會被債權人追究責任[20]。
不管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主流國家,均認可違反破產申請義務的董事應當對債權人承擔直接的責任。具體到我國,雖然董事信義義務的直接指向是公司,但在立法上,《公司法》第152條賦予了股東因董事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導致其權益受損時直接針對董事的訴訟權利。這說明雖然信義關系是相對的,但追索違背信義義務責任的請求權突破了此種相對性,公司的直接利益相關者對董事的侵權行為也能夠直接提起訴訟。依照此邏輯,也應當確定債權人為責任承擔的直接對象,賦予單個債權人或債權人集體直接提起訴訟的權利;但勝訴后的賠償仍應當納入公司破產財產,按照清算順序統一分配,不得個別清償。
2.責任性質與范圍
在責任性質方面,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普遍將董事違反破產申請義務認定為侵權行為。以我國臺灣地區為例,其移植了德國的立法模式,臺灣地區“民法典”第35條規定“法人之財產,不能清償債務時,董事應即向法院聲請破產。不為前項聲請,致法人之債權人受損害時,有過失之董事,應負賠償責任。”第184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于他人者亦同”。1967年臺上1353號判決認定“民法典”第35條屬于保護他人之法律,旨在保護法人之債權人,違反此條法律應當由董事承擔的責任性質為侵權責任[21]。
在責任賠償范圍方面,德國法以董事有義務提出破產申請的時間點為界,區分新舊債權人。對舊債權人,賠償范圍是董事應提出但未提出破產申請時債權人預計可以分配到的數額與實際分配給他們的數額之間的差額,包括偏頗性清償給債權人帶來的損失;對新債權人,賠償范圍是與未進入破產程序的公司進行交易而導致的所有信賴損失(《德國支付不能法》第15條、《德國民法典》第823條)。英國法未作上述區分,但在賠償責任范圍的確定上賦予了法院極大的自由裁量權。英國1986年《破產法》第214條規定,董事違反破產申請義務有責任對公司財產作出法院認為合適的補償,數額由法院根據董事不當經營給公司帶來的財產凈損失與自由裁量判斷[22]180。
具體到我國,責任性質方面,董事違反破產申請義務的責任性質也宜確定為侵權責任。因為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法院通常將董事違反忠實勤勉義務侵害股東權益的行為認定為商事侵權行為,在《侵權責任法》框架內對董事違反忠實勤勉義務對股東造成損害進行司法上的評價(1)參見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粵03民終14642號民事判決書;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蘇商外終字第0050號民事判決書。。在立法論構建時,將董事違反破產申請義務損害債權人權益的責任性質確定為侵權責任,更有利于保持責任性質體系上的統一。責任范圍方面,雖然我國目前針對此類董事特殊侵權賠償責任的范圍沒有明確規定;但是《侵權責任法》中針對財產損失賠償的填平規則值得借鑒,賠償范圍可以規定為包括債權人的既有利益和信賴利益在內的可得利益的全部損失。并且,不宜采取德國法區分新舊債權人的立法模式,因為在董事需要承擔違反破產申請義務責任的案件中,債權債務關系往往錯綜復雜,難以區分新舊債權人,為達到商事審判效率性的需要,就董事對債權人直接承擔的特殊侵權責任作明確規定,以覆蓋全部新舊債權人是有必要的[23]。
3.義務的觸發與免責
在董事破產申請義務何時觸發這一問題上,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認為義務產生的時間為臨近破產期間[24]。而臨近破產是一個很難客觀界定的模糊時間段,英國標準是公司無避免進入破產清算的“合理希望”;歐盟標準是“可預見,但尚未真正逼近破產”[22]167-168;德國標準是“公司具備破產原因”,即支付不能或債務超過(《德國支付不能法》第15條)。
具體到我國立法論構建,有學者建議將“破產界限”界定為“僵尸企業”的狀態,認為此時的企業就屬于“事實破產”狀態[25]。但事實上,在瞬息萬變的商事活動中,企業的資產狀況也是時刻變化且具有會計裁量空間的,很難通過“劃線”的方式對不同的企業作出瀕臨破產的認定,這可能也是為何我國一直不存在“僵尸企業”統一認定標準的原因。基于此,要判斷從哪個具體的時間點開始董事具有破產申請義務是缺乏必要性與可行性的,因此可借鑒德國模式,明確企業具有破產原因后,董事也就具有了破產申請的義務。我國《企業破產法》第2條規定的破產事由“當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明顯缺乏清償能力”,也應當作為觸發董事破產申請義務的原則性判斷標準;但并不是只要滿足此條件,董事未申請破產則一定承擔侵權責任,具體到個案裁判,還需交由法院根據董事是否具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以及公司資不抵債程度等證據來進行衡量。
除此之外,為了保障董事正常履職,避免其為了規避自身責任過早提出破產申請的情況,規定相應的免責事由是必要的。英美法系往往通過商業判斷規則來判定董事是否能夠在個案中免責,依商業判斷規則,董事善意、小心地行使職權,不存在其他利害關系,出于公司利益最佳的考慮作出了業務決策,即使給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損失,也可以獲得司法豁免[14]521-524。包括我國在內的大陸法系國家并沒有將董事基于商業判斷規則的豁免在法律中作出明文規定,但是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已經能夠看到商業判斷規則適用的影子。如泰琪公司訴其董事邁克違反忠實勤勉義務損害公司利益一案中,法院就認為邁克缺乏侵害泰琪公司利益的主觀目的,也無侵權過錯,其向興業銀行發函、提起訴訟要求恢復預留印鑒和保全賬戶等行為屬于特定情形下采取的救濟措施,是基于董事長職務在職權范圍內作出的商業判斷行為(2)參見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9)滬02民終字11661號民事判決書。。這足以表現出商事判斷規則在司法實踐中的重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適用商業判斷規則時,應作出舉證責任倒置的特別規定,因為債權人對董事履職狀況、公司經營狀況、財務狀況等信息獲取成本高且難度大;而董事獲取上述證據成本低,應承擔證明自己無故意或重大過失的責任,對自己謹慎決策、謀求公司利益最大化、咨詢專家意見等行為進行舉證證明,最終由法院作出裁判衡量董事是否善意,可否免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