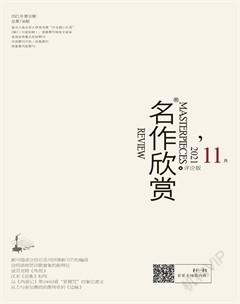中國畫創作中“留白”美學背后的意蘊
摘 要:“留白”作為中國傳統繪畫的藝術表現手法之一,不僅能夠襯托和凸顯畫面主體,拓展畫面想象空間,還能營造含蓄寧靜的意境美。本文以中國畫創作中“留白”應用的必要性作為分析基礎,嘗試探討了“留白”美學背后的意蘊以及中國畫創作中“留白”的應用切入點與思路等。
關鍵詞:中國畫創作 留白 意蘊
中國畫創作中的“留白”,并非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也不是“墻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而是老子所說的“知其雄,守其雌;知其黑,守其白”。“留白”帶來的意蘊是茫茫雪地中徒留的爪痕,是被藝術化的“空”“虛”“無”,是“白畫”,是讓齊白石的《蝦》、徐悲鴻的《馬》更具有張力的傳統藝術表現手法。“留白”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中華民族特殊的哲學思想、審美心理、社會歷史,作為中國畫營造畫面空間的手法之一,“留白”的內涵以及闡述的美學意蘊并不固定,可表示意境,可表示云霧,可表示山水,甚至表示虛無。
一、中國畫創作中“留白”應用的必要性
1.基于豐富構圖效果的需要
中國畫創作中使用的“留白”是畫家有意留出的,如夏圭和馬遠,夏圭的畫作多以半邊構圖為特色,其余的畫面大量留白;而馬遠在創作時,慣性選取最具有代表性的一角為著眼點,徐徐繪制龐大的展示對象,但畫面中除一角外,其余同樣是大量的空白。二人在創作中對空白巧妙的運用和重視,使中國傳統繪畫在經營位置、置陳布勢方面出現了新的表現方式,這也讓中國傳統繪畫形成了由遠觀畫勢、從近觀畫質的新的觀察方式及畫作表現技法。“留白”在中國畫形式與構圖中的應用,不僅能凈化畫面,擴展畫作的意境,還利于凸顯主體物象,為畫作帶來無窮生機。因此,無論是計白當黑,還是知白守黑與以實托虛,中國畫中“留白”的運用是利于豐富圖示的。
2.基于畫面層次與主體凸顯要求
中國傳統繪畫與西方繪畫側重焦點透視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國傳統繪畫以散點透視法為主,畫家為增加畫作的層次感和立體感,就需要巧妙運用留白,留白會明晰地分離畫面的層次與空間,讓畫面縱深性延伸。比如何家英的《落英》,畫作中人物形象位于視覺中心,背景色的白色與土地的褐色對比,讓畫面的層次感與空間感更為清晰。除畫面層次性外,“留白”的引入對突出畫面主體同樣具有輔助性。事實上,無論在西方繪畫還是中國繪畫中,主題形象的體現都是畫面層次、要素對比的結果。畫作中,畫家為了凸顯某部分,其他部分要舍棄處理或者弱化,“留白”恰恰可完成此項要求,且簡單便捷。如唐伯虎的《孟蜀宮妓圖》,為了突出人物形象,唐伯虎將畫作的背景部分使用大片空白的方式呈現,如此,賞畫者就會自然而然地將觀察點集中在人物上,如人物的衣著、表情等。空白的背景看似無用,實際卻能對人物起到襯托、突出的作用,空白的虛、無特性不會增加畫面的壓抑感,無形中自然能突出畫面中人物的主體形象,畫面不會因為太實太滿而影響意境呈現及賞畫者的聯想。
二、中國畫創作中“留白”美學的體現
1.刪繁就簡突出主體,提供審美思維空間
中國畫作中畫家為營造畫面氣氛,突出畫作主體,往往會使用“留白”的方式來表現水、氣、云等的不可捉摸及流動感,賞畫人在觀畫時,看云不是云,看水不是水,氣、霧交纏暈染,盡管什么具象化的東西都沒有看到,但是卻會因此心生幻想、聯想,雖然賞畫者所產生的想象并不一定與作畫者所期待的一致,但是借助留白誘發出的朦朧性意象,作畫人完成了造型的統一和確定,達到了水、氣、云等氣韻生動,畫面上下連貫、靈動、不壓抑的最高要求,“留白”對畫面流暢度、明暗過渡、畫面層次變化的彰顯,使觀畫者一眼看到的是經過高度濃縮概括的畫面主體,以及畫面中未曾提及的虛幻空間。
以清代《天地一沙鷗》為例,任立凡在此畫作中以沙鷗為畫面實處,除幾支蘆葦外,畫面空無一物,大量的留白展示了“虛”與“空”,大片大片的虛空高度概括了《天地一沙鷗》中的海面,虛實相襯,海天一色的縹緲、空曠、浩蕩之處又有著無盡的荒涼,虛空與實處的對比增加了《天地一沙鷗》畫面的鮮明生動感,正因為留白的存在,《天地一沙鷗》的沙鷗與蘆葦才顯得曠遠、清淡,“留白”作為《天地一沙鷗》的物象底色,概括式地展示出了天地之浩渺,任沙鷗自由飛翔的豪邁之意。
2.造景抒情襯托意境,豐富畫面形式
倪云林認為中國畫中的“留白”是“逸筆草草,不求形似”。中國畫中的“留白”方式形態各異,其凝聚的是畫家的個人格局、畫作的各種意趣。唐伯虎、蘇軾、八大山人、李可染等著名畫家,在創作中使用的“留白”方式不同,有的用“留白”表示野鶴閑云之隱逸,有的用“留白”展示冷清孤寂之感,有的用“留白”表達不知歸去的茫然無奈。但他們筆下的“留白”最大的共性是,“留白”是構圖的形式化處理,他們借虛實結合來豐富構圖形式,讓作品更為有趣靈動,無論是疏密、深遠、繁簡還是虛實、高遠,他們筆下“留白”的存在,讓畫面的形式感更強,構圖章法更為豐滿,畫面層次更為多樣。
“留白”在豐富畫面形式的同時,也具有造景抒情之意。比如范寬筆下的《溪山行旅圖》,畫作中一座雄奇巍峨的大山占據大幅畫面,讓賞畫者倏然有身在此山中之感。遠望,山中云霧不可捉摸,隱隱地籠罩著山峰,遙遠處有深不可測的樹木與水面,近觀地面處有可循的水流,《溪山行旅圖》意境天成,氣韻生動,無論遠望還是近觀,都會讓賞畫者有身臨其境的觀感。李苦禪在品評八大山人畫作時,提出八大山人構圖的巧妙在于“空白處補以意,無墨處似有畫,虛實之間,相生相發”,這句話明確地闡述出了中國畫借“留白”而體現出的意境。從“夏半邊”和“馬一角”的作品中,能明顯看到“留白”對畫面靈動性的強化。畫家在畫面中注入的思考與情感,主要通過其謹慎構思、大膽使用筆墨語言來體現,而“留白”正是畫家在構圖、立意之處心中有情、有乾坤的表現。
三、中國畫創作中“留白”美學的意蘊
1.彰顯畫家遷想妙得,黑白相稱豐富畫作形式美
中國畫作中的“留白”表現方式并不仙童,其遵循的是黑白相應、虛實相間的原則,主客相融、虛實相生的規律,畫家在畫作過程中靈活地處理實境與空白的關系,實際也是在處理虛實、黑白、聚散的關系。“留白”對畫面整體效果及意境的表現作用極為突出。作為中國畫作審美性和藝術性完美統一的輔助方式,中國畫作中的“留白”比例關系是否處理得當會直接影響到情感、意蘊、美學效果的表達和呈現。比如在山水畫中云、路、水、氣要融會貫通、相互連貫,就必須靈活應用黑白關系讓畫面渾然一體。
很多名家作品都是白與黑完美統一的結果,畫家通過巧妙使用“留白”的方式讓畫面的廣度和深度得以體現。在中國畫中,“留白”不僅用于表現視覺空間的拓展效果,如在山水畫中用“留白”表示云起于雨后的空渺感,在“留白”的襯托下,山川的俊秀、雄厚、奇峭躍然紙上,白云的縹緲和流動又增加了畫面的飄逸感,白與黑交錯自然而然地展示出了山水的平淡、開闊、簡潔,在拓展畫作世界空間的同時,也呈現出了山川與白色云氣相襯的朦朧美,以及云山戀所帶來的煙嵐繚繞的舒展的動態美。
2.黑白比例靈活配搭,虛實結合展示畫面氣韻
中國畫中的“留白”是畫家與賞畫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結果,畫作中的自我與自然是和諧統一的,“留白”在中國畫中的作用在于可在自我與自然間取得平衡,能營造出物我兩忘的境界等。比如《瀟湘奇觀圖》中米友仁以明顯的山巒疊嶂作為大面積云霧的實體襯托對象,山間樹峰相連,山上云霧彌漫、縹緲迷蒙,而《瀟湘圖卷》中董源同樣使用大面積的空白來展示水域之上的蒼茫感,遠處的長山、遠樹、茂林、復嶺均被隱藏在云煙中,水天一色,天與山相融,在清澈靈秀、悠遠空曠的畫面韻味影響下,畫家與賞畫人的情感與思想自然而然融入畫作中。華琳指出“畫中之白,即畫中之畫,亦即畫外之畫”,在創作中使用“留白”的畫家,會極為重視黑白比例的配搭,山水畫重視虛實關系,白少黑多,花鳥畫黑少白多,更重視構圖的疏密性。
在靈活應用黑白比例對比后,畫家在創作中能充分體現出中國傳統哲學所強調的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的審美境界。此審美境界所延伸出的和諧平淡、淡雅寧靜、悠然自樂的氣韻美,以形態各異、大小不等的空白作為載體,在畫家的創作中借助畫面的時與聯想的虛相襯,從虛無處彰顯氣韻。以《淺塘渡牛圖》為例,李可染使用大量的“留白”來展示晴空一碧、水波蕩漾的畫面意境,但此意境并非是寫實的而是需要借助賞花人的聯想來形成的。淺塘、渡牛、“留白”,畫面的含蓄、內在氣韻躍然紙上。
四、結語
中國畫創作中的“留白”并不是完全的虛無,而是通過與畫作中實物的對比所形成的虛空間。“虛而入萬景”,畫家在繪畫創作中借助虛與實的對比,完成了現實空間與虛擬現實的延伸,塑造出了靜謐、空靈、生動的境界,達成了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最高審美標準。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書畫論中多次強調“留白”的價值,但這并不意味著“留白”的創作方式只能繼承而不能創新。
參考文獻:
[1]喬麒麟.論中國畫創作中留白的運用[J].牡丹,2019(33).
[2] 屈劼.虛實結合——論中國畫的留白藝術[J].藝術品鑒,2019(8).
[3] 金樂樂. 無畫處皆成妙境——中國畫創作中“留白”的體驗與思考[D].濟南大學,2018.
[4] 劉穎. 接受美學視角下中國畫留白的審美研究[D].湘潭大學,2018.
[5] 張玥忞.“留白”在中國畫創作中的應用[D].南京藝術學院,2018.
作 者: 黃霖清,福建藝術職業學院講師。
編 輯: 杜碧媛 E-mail: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