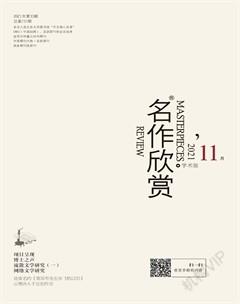關漢卿的《竇娥冤》:清氣長留天地間
摘 要:關漢卿雜劇《竇娥冤》中的竇娥是一個非常苦命的平民女子,但她的身上卻閃耀著高貴的人性光輝。然而部分現代學子并不認同竇娥舍己為人的善良,說她是“白蓮花”,這是對竇娥的誤解和不恭。《竇娥冤》具有極強的悲劇價值,它突破了中國古典戲劇“先離后合,始困終享”的大團圓模式,表現了出于“主人翁之意志”的“蹈湯赴火”的抗爭精神,它的審美效應是悲壯而不是悲慘。《竇娥冤》是關漢卿區別于傳統文人士大夫的平民意識和人文情懷的產物。
關鍵詞:《竇娥冤》 竇娥 悲劇價值 人文情懷
關漢卿的《竇娥冤》是元雜劇社會問題劇中思想深度和情感強度都極為突出的作品,因此它才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關漢卿的《竇娥冤》也是中國戲曲史上被京劇及豫劇、秦腔、河北梆子等多個地方劇種改編演出,舞臺生命力極其強大的作品,因而它在普通的中國民眾中的影響非常廣泛,以至于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可能因為被人誤解而感嘆:“我比竇娥還冤!”
一、竇娥:柔弱、善良與剛強的和諧統一
關漢卿《竇娥冤》中的竇娥是一個普通的非常苦命的平民女子,但她的身上卻閃耀著高貴的人性光輝。
首先,竇娥是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民女子。竇娥七歲以前,她的父親是一個窮書生,生存無計,靠借貸度日,借了貸還不起,連上京應試的盤費都拿不出,只好以竇娥抵債。竇娥后來生活了十三年的蔡家,雖然衣食無憂,但人丁稀少,竇娥丈夫不幸去世后,只剩下婆媳二人相依為命,連一個撐門戶的男人都沒有。
其次,竇娥是一個非常苦命的女子。她三歲喪母,七歲離父,在蔡家做了十年的童養媳,剛與丈夫成親,丈夫又去世了,從此開始了孤單清冷的守寡生活。不料,她又被無賴張驢兒欺負陷害,在公堂上被貪婪酷虐的梼杌太守嚴刑逼供,最后蒙冤而死。一個人本應享受的人間溫情,竇娥一點也沒享受到,連最基本的生命權利也被剝奪。這里有天災,也有人禍,但天災人禍傾盆而下,降臨到一個人的身上,讓一個弱女子如何承受得起?
再次,竇娥的性格非常善良。竇娥的善良有恪守孝道的成分,但更多是出于一種人性的美好。竇娥對年邁的婆婆非常體貼,看到討債回來的婆婆面帶淚痕,她趕忙上前問候;婆婆被逼無奈把張驢兒父子帶回家中,竇娥雖然沒有聽命于婆婆,但并沒有埋怨;她為生病的婆婆做羊肚湯喝,怕婆婆受不了拷打,自己違心接受“藥死公公”的罪名;赴法場路上,她怕婆婆看見自己傷心,央求解差不走前街走后街;與婆婆最后分別的時刻,她叮嚀婆婆不要為自己難過;冤情昭雪后,她請求父親照顧婆婆的余生。
在和現代的年輕學子交流的過程中,有部分學子并不認同竇娥舍己為人的善良,說她是“白蓮花”,我認為這是對竇娥的誤解和不恭。對于網絡名詞“白蓮花”,360百科是這樣解釋的:“又被稱為‘圣母白蓮花,諷刺形容為以瓊瑤小說以及現代偶像劇中為代表的女主角,她們有嬌弱柔媚的外表,一顆善良、脆弱的玻璃心,像圣母一樣的博愛情懷及好到逆天的運氣。”竇娥弱小但并不柔媚,善良卻并不脆弱,仁愛卻有“逆天”的壞運氣,根本與現代影視劇中的“白蓮花”不像。
在竇娥的善良行為中,最難得的是“怕婆婆受拷打,違心承認是自己藥死公公”,最后致使自己命喪黃泉。這樣的犧牲,一般人做不到,因此才非常可貴。現代社會不應該強求、鼓勵別人去“犧牲”,去“舍己為人”,但如果有人心甘情愿地或者不得已地“舍己為人”,我們應該向他(她)表示崇敬,所以我們應該向竇娥表達崇敬之情。
第四,竇娥的性格非常剛強。竇娥的剛強里有恪守“貞節”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一種抗擊邪惡的英勇。在對待是否接納張驢兒父子的問題上,竇娥和蔡婆是有非常明顯的不同的。在荒郊野外,面對張驢兒父子對自己性命的威逼,蔡婆選擇妥協情有可原;但到了自己家中,蔡婆再去勸竇娥屈從于張驢兒,便是一種糊涂、軟弱、無原則的行為。竇娥對張驢兒的反抗,一方面是替自己死去的丈夫守節的倫理行為,另一方面是對張驢兒恃強凌弱的霸道的反抗。面對霸凌,蔡婆選擇妥協、忍受,竇娥選擇奮起反擊。梼杌太守貪贓枉法,也是一種邪惡。竇娥被打得“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肉都飛,血淋漓”,但絕不屈從。性格剛強的竇娥自然不會無聲無息地死去,于是她站在天地之間,高聲喊冤:“沒來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憲,叫聲屈動地驚天。”性格剛強的竇娥,也不會對使她蒙冤受屈的“天地日月鬼神”及官府忍氣吞聲,她憤而質問:“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她憤而譴責:“這都是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性格剛強的竇娥,即便身死法場,她的鬼魂也不愿放過賽盧醫、張驢兒、梼杌太守等社會邪惡勢力。
第五,竇娥的人格非常清正。“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自私是一種正常的人性,憐貧惜弱、舍己為人的善良是一種高貴的人性,而巧取豪奪、恃強凌弱的霸凌是一種邪惡的人性。面對強大的邪惡勢力,逃避、屈從、難得糊涂是一般人的選擇;而以剛強去抗擊,雖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是強者的選擇。無賴的張驢兒、貪贓枉法的梼杌太守是人世間的一種邪氣、一種濁氣,竇娥的善良、剛強是人世間的一種正氣、一種清氣。一般情況下,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兩不相干。但在兩者交集相遇、難分難解的時候,正者、清者的氣場若不夠強大,便會被污濁淹沒。比如蔡婆,本來十分善良,但遇到張驢兒父子,只有被動接受屈辱,時間一長,恐怕連屈辱的感覺也喪失了。但竇娥不一樣,她性格上的極度善良與剛強是植根于人格深處的。一個普通的平民女子卻表現出中國士大夫階層所推崇的“出淤泥而不染”的正氣與清氣,這是多么難能可貴。竇娥維護的不是倫理上的“清白無瑕”,而是人格上的“清白無瑕”。所以在身赴黃泉之際,竇娥要發出“三樁誓愿”,讓血濺白練、六月飛雪、大旱三年的異象來向世人昭示自己的清白與冤屈。“若果有一腔怨氣噴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滾似綿,免著我尸骸現;要什么素車白馬,斷送出古陌荒阡!”她要讓滿天飛雪遮住她的尸體,絕不讓這個世界的邪惡與污濁淹沒了自己。
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苦命的平民女子,除了和婆婆相依為命的平靜生活和“服孝守節”的內心安寧,她沒有更多可以依仗的東西。當邪惡不期而至地打破了她生活的平靜和內心的安寧的時候,植根于人格深處的清正使她選擇了“爭到頭,競到底”的抗爭。雖然由于社會邪惡勢力的強大,她被毀滅了,但那種“善良”與“剛強”的高貴人性卻永放光芒,照亮后人精神世界的荒蕪。“清氣長留天地間”的竇娥是關漢卿留給后人的一份精神資源,《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與《我不是潘金蓮》中的李雪蓮身上都有竇娥的精神基因。
二、《竇娥冤》的悲劇價值
“悲劇”是源自西方的戲劇審美形態,在西方形成了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一整套的悲劇理論。但中國古代戲曲的起源和形成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在中國古代的戲曲理論著作中,是沒有“悲劇”的概念的,是王國維首次以“悲劇”的標尺來衡量元代北曲雜劇的價值。他在《宋元戲曲史》中以贊賞的口吻說:“明以后,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梧桐雨》《西蜀夢》《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妻》等,初無所謂‘先離后合,始困終享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
王國維說“明以后,傳奇無非喜劇”不合文學史事實,有點偏頗,但他指出元雜劇中悲劇作品較多,卻是實際情況。由王季思先生首先提出并得到認可的“中國十大古典悲劇”是:元代的《竇娥冤》《漢宮秋》《趙氏孤兒》《琵琶記》,明代的《精忠旗》《嬌紅記》,清代的《清忠譜》《長生殿》《桃花扇》《雷峰塔》。可以說,關漢卿的《竇娥冤》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最具有悲劇審美效應的作品。
首先,《竇娥冤》的結局不是“先離后合,始困終享”的大團圓模式。在關漢卿的筆下,竇娥的人生結局是屈死法場,盡管最后冤案被昭雪,但竇娥的現實人生終究是被污濁而強大的社會邪惡勢力毀滅了。關漢卿的《竇娥冤》是不符合中國人“善有善報”“好人一生平安”的社會心理期待的,它告訴人們,只要這個社會存在“巧取豪奪”“恃強凌弱”的霸凌心理和行為,只要這個社會存在“視人命若草芥”“視金錢為上帝”的貪腐心理和行為,這個世界就不可能是“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好人就不可能平安。準確地講,從題材上把《竇娥冤》分屬“公案劇”是不確當的,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竇娥所生存的社會環境的不美好,無比清晰地展示了一個好人被欺凌、被冤屈、被殺死的事實,因此,《竇娥冤》是一部典型的社會問題劇,是一部寫實性很強的作品。它昭示我們:“悲劇是沉重的現實人生,不是美好的夢里幻象。”
第二,關漢卿的《竇娥冤》表現了出于“主人翁之意志”的“蹈湯赴火”的抗爭精神,它的審美效應是悲壯而不是悲慘。在關漢卿的筆下,竇娥的年少孤苦、青春守寡是一種悲慘,竇娥的被欺凌、被陷害、蒙冤受屈是一種不幸,但這都不是表現的重點。關漢卿著重表現的是竇娥這樣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女子面對不幸命運的態度。命運的悲慘沒有消弭竇娥的善良,無賴的欺凌陷害、官府的為虎作倀并沒有讓竇娥俯首聽命,她“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地去抗爭地痞無賴、抗爭貪官污吏、抗爭不公正的“天地日月鬼神”,維護自己清正的人格。如果深入閱讀關漢卿的《竇娥冤》,你會認識到它以“法場問斬”為高潮的情節結構的設置、“反大團圓”的結尾模式的設置、寫實與浪漫結合的創作方法、第三折慷慨激昂的感情的抒發,都是竇娥“蹈湯赴火”的“剛強”性格與抗爭精神決定的。關漢卿并沒有“主題先行”,而是遵從人物性格的邏輯來進行他的戲劇創作。所以,關漢卿的《竇娥冤》帶給我們的審美體驗是“悲壯”而不是“悲慘”,“悲慘”只能讓人產生“憐憫”,“悲壯”卻能使人體會人性的高貴與莊嚴。
三、“浪子班頭”關漢卿的人文情懷
在元代,文人的社會地位是很低的,關漢卿的社會地位尤其低,他是典型的“偶倡優而不辭”的“書會才人”,是典型的為正統文人不屑的市井文人,是他的《南呂·一枝花·不伏老》套曲里自豪宣稱的“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作為一個被“仕宦”世界疏離的書會才人作家,他只能通過為市民社會編演雜劇來獲取生活資源,實現人生價值。
讀關漢卿的《南呂·一枝花·不伏老》,我們能感受到一種與“仕宦”世界的價值觀念相對抗的情緒:“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珰珰一粒銅豌豆。”正是這種混跡于社會底層的“眠花臥柳”的生活,使關漢卿形成了一種正統文人所不具有的對底層百姓苦難的體驗與同情,對他們或剛強或軟弱但不失善良的性格的審視,從而使他的雜劇具有一種難得的平民意識和人文情懷。
在他現存的十多部雜劇作品中,沒有典型的倫理劇,他從不生硬地去宣揚“忠孝節義”等倫理觀念。在他看來,倫理不應該作為外在的強迫人們去踐行的規范而存在,倫理只有和人們內在的人情人性相結合才具有價值。因此,《竇娥冤》里竇娥因愿意“守節”而美好;《望江亭》里譚記兒因不愿過“孤鸞單鳳”的生活而選擇再婚同樣美好;《魯齋郞》里銀匠李四、小吏張珪都因為權豪勢要的霸凌而妻離子散,最后兩對夫妻破鏡重圓,做丈夫的李四及張珪皆沒有因妻子的失節而心存芥蒂,他們也一樣美好。
關漢卿的《竇娥冤》《魯齋郞》《蝴蝶夢》也不是典型的公案劇。《竇娥冤》的表現重心是竇娥善良、剛強的性格及“爭到頭,競到底”的意志及抗爭精神,最后的“冤案昭雪”是為了表現竇娥的性格服務的,而竇娥的蒙冤而死恰恰是由于官員貪腐、無賴橫行等社會問題造成的。《魯齋郞》與《蝴蝶夢》都出現了“包待制斷獄”的情節,但兩部作品都不是為了表現“包待制”品行的廉明及“勘案”的智慧,案情皆由權豪勢要的橫行無忌而生,根本不需要費心思勘察,“包待制”需要應對的是如何施展智謀去應對權貴階層。其實更本質的是,權貴階層的橫行無忌恰恰是當時的律法給他們的特權,包待制不能光明正大地替弱者伸張正義恰恰顯示了清官在現實環境中的無奈。所以,這三部劇都應劃歸為社會問題劇,它們顯示了關漢卿對底層百姓命運的深刻觀察。
在關漢卿現存的劇作中,有七部婚戀劇。其中只有一部比較接近“才子佳人劇”,即和王實甫的《西廂記》、白樸的《墻頭馬上》、鄭光祖的《倩女離魂》一起被列入元雜劇“四大愛情劇”的《拜月亭》。其他六部劇作中,《救風塵》里的趙盼兒、宋引章,《謝天香》里的謝天香,《金線池》里的杜蕊娘都是妓女,她們“倚門賣笑”,周旋于狡猾的無賴、狠毒的老鴇之間,善良軟弱的被欺騙、被打罵,只有頭腦清醒、有膽有識的才能存活。《調風月》里的燕燕是位大戶人家的婢女,被“小千戶”引誘失身,費盡心機才做上了“小夫人”,但等待她的能有什么好的命運呢?還有這些劇作里的書生,沒有功名便沒有社會地位,追求妓女都需要別人的成全。這些劇作都顯示了關漢卿對處于被侮辱、被損害地位的社會邊緣人物命運的關注與悲憫。
關漢卿區別于傳統文人士大夫的平民意識和人文情懷,使他的劇作具有深刻的思想底蘊,使《竇娥冤》具有了“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的悲劇價值。
參考文獻:
[1] 王學奇等.關漢卿全集校注[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2]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 王季思主編.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基金項目: 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項目“ 文化傳承背景下河南高校戲曲鑒賞教學探究”,項目編號:2019-ZZJH-720
作 者: 張冬云,文學碩士,南陽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
編 輯:趙斌?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