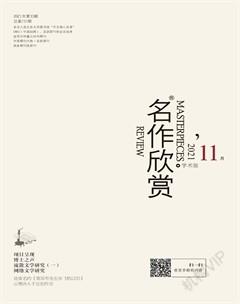楊逵對郁達夫的譯介
摘 要: 楊逵雖然從未到過中國大陸,但他有著很深的傳統文化情結。楊逵與郁達夫曾有過一面之交。1948年8月臺北東華書局出版了楊逵對郁達夫小說的譯介本《微雪的早晨》,其中不僅有《微雪的早晨》《出奔》兩篇小說,還收錄有楊逵的介紹性短文《郁達夫先生》。本論文通過分析楊逵選譯郁達夫作品的原因,呈現楊逵的創作主張及楊逵展開此譯介活動時臺灣的社會情況。同時指出由于諸種局限,《郁達夫先生》中出現的錯誤與表述不清之處。
關鍵詞:楊逵 郁達夫 譯介
一、楊逵的中國情結
盡管楊逵(1906—1985)有生之年未曾到過中國大陸,但對中國大陸始終保持著密切的關注。他曾將《水滸傳》視為理解中國政治、社會、風俗、習慣的鑰匙,希望能透過這部小說接觸中國社會的真實面。在文學創作中,楊逵也不時地將筆觸指向中國社會。如作品《泥娃娃》中,他描寫了以“我”的校友富岡為代表的在戰亂的南京趁火打劫、大發國難財之惡劣行徑。此外,不論何時楊逵都自覺地承擔起傳播中華文化的使命,他曾明確表示要做中日文化交流的中間人:“如果這樣的我們能做中間人,把中國文化介紹到日本,也把日本文化介紹到中國,那真是再好不過的事了。”楊逵曾自覺地擔當起作為“溝通本省及外省人民”的橋梁:與大陸赴臺人士交好,比如與曾經執教于東海大學的徐復觀惺惺相惜、與軍營作家朱西寧“一見如故”;他還向“認識或不認識的友人及全臺灣的大眾推薦”大陸電影《人道》、蕭軍的小說《第三代》。在《〈第三代〉及其他》中楊逵說:“《第三代》是有趣的好小說,我期待著有一天能把它介紹給各位讀者。”
1947年11月至1948年8月間,因應時代變化,受臺北東華書局之邀,楊逵先后出版了中日文對照本“中國文藝叢書”三輯:《阿Q正傳》《大鼻子的故事》《微雪的早晨》。 以上三輯叢書所收錄的分別是楊逵對中國現代著名作家魯迅、茅盾、郁達夫的部分作品的譯介。楊逵曾在《臺灣新文學停頓的檢討》中說過:“由于日本極力阻礙內地和島內的文化交流,而且是長期如此,所以導致我們現在必須苦于多重隔閡。為了彌補這個鴻溝,我們必須付出過人的努力。具體的做法如下:作家的交流、刊物的交換,以及作品的交換等,形形色色,但我們必須一一切實實行,克服這個困難。” 毫無疑問,楊逵向本地民眾譯介現代名家作品正是“為了彌補這個鴻溝”,加強兩岸文化交流所付諸的實踐。
二、楊逵與郁達夫的交集
1948年8月楊逵版郁達夫小說的中日文對照本《微雪的早晨》由臺北東華書局出版,其中不僅有《微雪的早晨》《出奔》兩篇小說,還收錄有楊逵的介紹性短文《郁達夫先生》。
楊逵與郁達夫雖然年齡相差了近十歲,但是他們有著些許相似的經歷,比如二人都曾經先后東渡日本求學;兩人在文學上都是多面手,在詩歌、雜文、文論等領域都有所建樹,二人又都主要以小說稱譽文壇;二人都曾做過編輯,都曾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而且楊逵與郁達夫還曾經有過一面之緣。
郁達夫曾于1936年到過中國臺灣,郁達夫赴臺一事在臺灣文學界曾引起極大的反響。臺灣作家尚未央在《會郁達夫記》中對此有過記錄:“‘會郁達夫這念頭,從幾個月前島內新聞一齊把這極有魅力的消息報道出來以來,就已經深刻地印在一般素常關心文學的人們的腦上了。有時偶然在路上相逢,書信的往來,或定期聚合,屢次都把他當為中心話題提出來議論,這么一來,更使這念頭越深刻、越熱烈地盼望其來臨。”尚未央的《會郁達夫記》中還頗為詳細地寫及了郁達夫在臺灣期間與當地的作家們,尤其是與《臺灣新文學》的尚未央、櫪馬、廢人、林占鰲、高祥端等九位作家,以及佳里的吳新榮、郭水潭、徐清吉三位作家的見面經過。尚未央的《會郁達夫記》雖沒有提及楊逵,但這篇《會郁達夫記》就刊載于《臺灣新文學》的第二卷第二號中,作為當時《臺灣新文學》主編的楊逵是不可能不了解郁達夫在臺灣的動態的。 楊逵曾經多次談及自己與郁達夫的交集,比如在《〈第三代〉及其他》中:“去年(1936),郁達夫氏來日本,從東京繞道臺灣回去。那時,我在臺中見到他。他說,東京的知識分子非常熱情地款待他。”在就柳映隄關于與20世紀30年代大陸左翼作家之間關系的問詢時,楊逵曾做過如下答復:“其實,我和三十年代大陸作家是素不相識,只是民國二十五年底,郁達夫來臺時,曾以招待者身份見過一面。”
三、楊逵選譯郁達夫作品的原因
《微雪的早晨》是郁達夫創作于1927年的作品,此作是以知識分子為題材的小說。小說中寫的是忠厚正直的大學生朱雅儒,在貧困艱辛的大學生活中,因為自己青梅竹馬的戀人被軍閥奪去,因而在激憤郁恨中發瘋至死的故事。《出奔》則是郁達夫創作于1935年的作品,這篇小說向來被視為郁達夫小說創作的結筆之作,它是一篇直接表現大革命時代風云的作品。小說中對投機革命者的奸詐狡賴,對不擇手段的悍婦的兇殘狠毒,對革命青年的搖擺軟弱,都有繪聲繪色的刻畫。其實《出奔》《微雪的早晨》這兩篇小說都并非郁達夫的代表作品,但是楊逵沒有選擇其在《郁達夫先生》一文中著重介紹的《沉淪》進行譯介,或是選擇同為郁達夫代表作品的《銀灰色的死》《南遷》等進行譯介,而是選譯了《出奔》《微雪的早晨》這兩篇作品。在筆者看來,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出奔》《微雪的早晨》與楊逵歷來的創作主張更為接近。楊逵一貫主張并踐行著“文學反映現實,表現著生活”的創作理念,而郁達夫的這兩篇作品都是以客觀現實為描寫對象,偏重于對社會生活的剖析,客觀性、社會性和寫實性較強的社會小說,而并非《沉淪》《銀灰色的死》《南遷》這樣側重于自我表現、自我體驗,抒寫內心世界的苦悶、憂煩、感傷,偏重描寫性苦悶和靈肉沖突,反映著頹廢情緒的自我小說。
其次,楊逵對《出奔》《微雪的早晨》的翻譯是在1948年左右完成的。盡管據蘇維熊“中日對照中國文藝叢刊發刊詞”中所述,楊逵這時期對于中國現代名家名作的譯介旨在“全國普及國語運動”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理解祖國文化,而且要哺育它,使它更為高尚,更為燦爛,使其真正的精華宣揚全世界”,但是楊逵在譯介郁達夫這兩篇小說時,也正介于如何建設臺灣新文學的論爭期。這場論爭討論的是臺灣文學的大眾性、文學的指導思想(即歷史唯物論)、新現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等問題。在此期間楊逵多次強調指出:臺灣新文學需要的是能切實地表現人民真實的心聲,促使人民奮起,弘揚民族解放與國家建設的偉大力量的作品;而非滯留于“藝術的王國”中,書寫或關注主人公意識的流動,心緒的弛張、情感的起伏,帶有濃郁的主觀性、抒情性,以及厚重的感情深度而充斥著靈與肉的沖突的自我小說。
再者,楊逵對郁達夫的《出奔》《微雪的早晨》的翻譯是于“二二八事件”發生后的1948年前后進行的。結合《出奔》與《微雪的早晨》的內容,在筆者看來,楊逵之所以選譯此兩部作品是有其用意的:即楊逵正是通過選譯此兩篇小說,委婉間接地表達他對光復初期國民黨在臺灣所實施的政策的不滿與批判。《出奔》中所反映的正是國民革命不徹底,國民黨內部弊病百出的現象,而《微雪的早晨》則反映的是軍閥暴行。
四、楊逵《郁達夫先生》中存在的問題
誠然,楊逵出版中日文對照本《微雪的早晨》是在光復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推行“中國化”(去日本化)而“普及國語運動”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同時楊逵出版中日文對照本《微雪的早晨》也是在被視為“現代臺灣文學史上唯一的,臺灣文學界與中國大陸文學界最直接密切交流的四年”的歷史時期進行的。即楊逵在光復初期對中國現代作家的關注譯介并非其獨有行為。據下村作次郎統計,戰后初期臺灣出版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的中日對照本有:
一九四七年
魯迅著、楊逵譯《阿Q正傳》,東華書局,一月
魯迅著、王禹農譯《狂人日記》,標準國語通信學會,一月
郁達夫著、楊逵譯《微雪的早晨》,東華書局,八月
魯迅著,藍明谷譯《故鄉》,現代文學研究會,八月
茅盾著、楊逵譯《大鼻子的故事》,東華書局,十一月
一九四八年
魯迅著、王禹農譯《孔乙己?頭發的故事》,東方出版社,一月
魯迅著、王禹農譯《藥》,東方出版社,一月
一九四九年
?沈從文著,黃燕譯《龍朱》,東華書局,一月
從以上列舉的篇目可見,楊逵是臺灣光復初期最早譯介出版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的人。而且從涉及面上言,在光復初期當臺灣文化場域掀起“魯迅熱”,多數臺灣譯介者將目光集中于魯迅作品時,楊逵則在譯介魯迅作品的同時將目光投向包括郁達夫在內的更多中國現代作家。從數量上看,光復初期四年間,臺灣出版了對現代作家作品中日對照本共計八種,楊逵的譯作即占三種,幾近半數,為此也足見楊逵為“普及國語運動”,促進臺灣民眾正確地理解認識祖國文化所付出的努力與良苦用心。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楊逵用日語寫作的約五百字介紹性短文《郁達夫先生》中存在著不少錯誤或表述不清的問題。比如“先生于1911年留學日本,就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后,由東京帝國大學經濟科畢業。1922年回國后,立即與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共組創造社,展開文藝工作”,“他的處女作《沉淪》是大學畢業后不久寫的”,“1926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轉換時期,他沉醉在與王映霞之間的甜蜜戀愛生活中,僅出版了描寫這種生活的日記體作品”。
首先,郁達夫留學日本時間實為1913—1922年,即開始于1913年而非1911年,而且郁達夫是于1914年7月才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其次,創造社是于1921年6月在日本正式成立,而非“1922年回國后”才成立;再次,郁達夫的小說處女作是其于1920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寫成的《銀灰色的死》而并非《沉淪》,只是1921年10月郁達夫將《銀灰色的死》《沉淪》《南遷》等三篇小說集結為《沉淪》出版。小說集《沉淪》是郁達夫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集子,因此楊逵將郁達夫的處女作寫為《沉淪》實是有誤或者至少是表述不清的。第四,1926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時期,郁達夫除了出版所謂的描寫戀愛生活的日記體作品外,還出版有《達夫全集》第一卷《寒灰集》、第二卷《雞肋集》及第三卷《過去集》;同時還發表有政論文《廣州事情》,公開揭露作為大革命根據地的廣州的黑暗。因此,楊逵說“郁達夫1926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時期,僅出版了描寫這種生活的日記體作品”并不正確。
上述所列出的錯誤或表述不清之處是如何造成的確切原因不得而知,但是在某種層面上可見在臺灣光復初期,在兩岸尚未能正常交流的情況下,完全缺乏漢文素養,后來“才正式開始學習中國語和北平語”的楊逵的譯介過程是極為不易的。然而,1998年6月由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出版的《楊逵全集》(第三卷)中收有黃英哲教授對《郁達夫先生》一文的漢語直譯,而此譯文對以上這些問題卻未給予任何修正說明,則不免有些令人遺憾了。
參考文獻:
[1] 王曉波.冰山下的臺灣良心——我所知道的楊逵先生[A].被顛倒的臺灣歷史[M].臺北:帕米爾書店,1986.
[2] 宋田水.楊逵·胡風·左翼文學(下)[J].臺灣日報,1998年1月8日.
[3] 楊逵.談水滸傳[A].涂翠花譯//彭小妍.楊逵全集(第十卷)[M].臺南: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
[4] 楊逵.《第三代》及其他[A].涂翠花譯//彭小妍.楊逵全集(第九卷)[M].臺南: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5] 楊逵.二二八事件前后[A]//黃惠禎.楊逵[M].臺南:臺灣文學館,2011.
[6]林梵.楊逵畫像[M].臺北:筆架山出版社,1978.
[7] 楊逵.推薦中國的杰出電影《人道》[A].陳培豐譯//彭小妍.楊逵全集(第九卷)[M].臺南: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8] 楊逵.“臺灣文學”問答[A]//彭小妍.楊逵全集(第十卷)[M].臺南: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9] 黃萬華.去殖民性進程中的戰后初期臺灣文學[A]//楊彥杰.光復初期臺灣的社會與文化[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
[10] 楊逵.臺灣新文學停頓的檢討[A].涂翠花譯//彭小妍.楊逵全集(第十卷)[M].臺南: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
[11] 尚未央.會郁達夫記[A].臺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二號)[M].昭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12] 楊逵.論文學與生活[A]//彭小妍.楊逵全集(第十卷)[M].臺南: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13] 樂齊.精讀郁達夫[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8.
[14] 下村作次郎.戰后初期臺灣文壇與魯迅[A].邱振瑞譯//中島利郎.臺灣新文學與魯迅[M].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
[15] 藍博洲.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序)[A].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M].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
[16] 楊逵.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A]//彭小妍.楊逵全集(第十卷)[M].臺南: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17]方忠.郁達夫傳[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18] 楊逵.郁達夫先生[A].黃英哲譯//彭小妍.楊逵全集(第三卷)[M].臺南: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
[19] 楊逵.一個臺灣作家的七十七年[A].葉石濤譯//彭小妍.楊逵全集(第十四卷)[M].臺南: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基金項目: 福建省中青年教師教育科研項目“光復初期兩岸文化交流——以楊逵譯介活動為觀察點”(JZ180423)階段性成果
作 者:?蔡榕濱,文學博士,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
編 輯:曹曉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