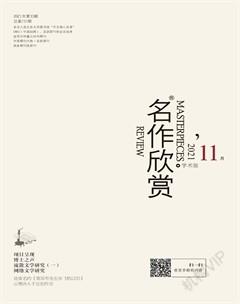出走與歸來,抗?fàn)幣c犧牲
摘 要: 曹禺的筆下活躍著一個個形象飽滿、個性鮮明、極富感染力的女性,如周蘩漪、花金子、愫芳、陳白露、丁大夫等人。以1938年為分界線,曹禺前期戲劇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洋溢著生命激情,充滿了抗?fàn)幍囊庵竞蜌庀ⅲ诓茇?938年之后的戲劇作品中,女性形象則基本趨于傳統(tǒng)化,反而呈現(xiàn)出一種古典美,曹禺戲劇作品中這種女性形象前后期的變化主要與他審美追求的轉(zhuǎn)變有關(guān)。
關(guān)鍵詞:曹禺 女性人物 戲劇作品
曹禺可以說是刻畫女性形象的大師,在他的筆下活躍著一個個形象飽滿、個性鮮明、極富感染力的女性,如《雷雨》中的周蘩漪、《黑字二十八》中的韋明、《原野》中的花金子、《家》中的瑞玨、《北京人》中的愫方、《日出》中的陳白露、《蛻變》中的丁大夫,等等。她們或者性情剛烈、張揚自我,或者溫柔賢淑、恪守傳統(tǒng),她們雖然身份、地位、身處的環(huán)境各不相同,但是曹禺把她們作為一個個鮮活而真正的“人”去描寫刻畫,凸顯她們的人性,把她們的命運與整個時代和社會緊密聯(lián)系,賦予這些女性以人格美與人性美。
有研究認(rèn)為,以1938年為分界線,曹禺筆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可以明顯地分為兩類。1938年以前,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洋溢著生命的激情、充滿了現(xiàn)代氣息,而在他1938年之后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則基本趨于傳統(tǒng)化,具有一種古典美。具體到作品中的人物,曹禺前期戲劇中的女性周蘩漪、陳白露和花金子等人,她們敢作敢為,勇于追求自我,處在被禁錮、被毀滅的迷途之中,不甘心被欺凌、被侮辱,拼盡全力掙扎著向前,最終沒有逃脫悲慘的命運。她們的命運既顯示出飛蛾撲火般的悲壯,又充滿了雷雨般的力量。1938年之后,在《黑字二十八》(1938年)、《蛻變》(1939年)、《北京人》(1941年)、《家》(1942年)等作品中,與《日出》《原野》等作品中的女性大為不同,這一時期曹禺筆下的女性形象多以溫柔賢惠、無私奉獻(xiàn)為主要特征。這一時期的丁大夫、瑞玨、愫芳等人,與蘩漪、陳白露和花金子等人剛烈的性情所不同,她們習(xí)慣了默默承受,為愛人、為家庭、為社會承受著苦難,她們溫柔賢淑、善解人意、任勞任怨、恪守傳統(tǒng),在他人價值的實現(xiàn)過程中實現(xiàn)著自己的幸福,體現(xiàn)出一種甘于奉獻(xiàn)的質(zhì)樸美。
曹禺戲劇作品中這種女性形象前后期的變化主要與其審美追求的轉(zhuǎn)變有關(guān)。以《原野》為分界線,此前,曹禺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時追求一種張揚自我、充滿反抗精神、渴望突破禁錮走出牢籠的個性美,表現(xiàn)出一種理想主義色彩。而后期的戲劇作品中,曹禺的審美觀念逐漸發(fā)生變化,他開始關(guān)注女性身上所具有的那種甘于奉獻(xiàn)、恪守傳統(tǒng)的美德,體現(xiàn)出一種現(xiàn)實主義。前期的女性人物可歸為出走一類,她們以各自的方式去抗?fàn)幧鐣⑻与x家庭、抗?fàn)幟\的不公、試圖打破世俗的無形枷鎖,不惜以毀滅自己為代價追求自我理想的實現(xiàn);后期的女性人物則走在了回歸的道路上,她們甘于為愛人奉獻(xiàn)自己,為家庭默默奉獻(xiàn),為國家貢獻(xiàn)力量,可以說,自1938年之后,曹禺正在逐漸收拾起“反傳統(tǒng)的旗子”,“反身向傳統(tǒng)回歸”。在曹禺的筆下,包括陳白露、花金子、周繁漪在內(nèi)的出走者、抗?fàn)幷撸憩F(xiàn)出強有力的生命力和欲望,富有抗?fàn)幘瘢欢笃诘亩〈蠓颉悍降热藙t回歸傳統(tǒng),富有自我犧牲精神,反映出作者不同的人生階段的不同體驗以及藝術(shù)想象。
一
“五四”之后,中國的現(xiàn)代戲劇逐漸發(fā)展成熟,受西方現(xiàn)代戲劇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各種新的戲劇思潮、戲劇觀念十分活躍,追求個性解放、掙脫舊社會的枷鎖是戲劇創(chuàng)作的重要命題,其中,尤其是女性意識的覺醒與解放格外閃耀。曹禺前期的話劇《日出》《原野》《北京人》中,有不少女性試圖掙脫婚姻的枷鎖,勇于改變自我以逃離現(xiàn)實的壓迫與困境。這種覺醒的女性意識類似于易卜生筆下出走的娜拉,她們深陷于熱烈、瘋狂而迷茫的抗?fàn)幹校w現(xiàn)出更為強烈的抗?fàn)幘瘛?/p>
《雷雨》的創(chuàng)作,曹禺把控訴的焦點集中在一個沒落而腐朽的封建大家庭中,這個家里的女性,各自經(jīng)歷著不同的人生悲劇,她們的悲劇生動地揭示了封建制度對女性的璀璨與扼殺,話劇中幾乎所有的女性都走向了毀滅的道路。
周繁漪出生在一個書香世家,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與善良的本性。她在17歲時被周樸園騙婚,至此開始了深受侮辱的生活,富足的物質(zhì)生活與極度貧困的精神生活撕裂著、折磨著她,最終在后悔與自責(zé)中發(fā)瘋。在《雷雨》中,繁漪可以說是一個極具抗?fàn)幮缘慕巧哂欣子臧愕膹娏倚愿瘛2茇沁@樣描寫繁漪的第一次出場的:“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壓抑的蠻勁,使她能夠做出不顧一切的決定。她愛起人來像一團(tuán)火那樣熱烈,恨起人也會像團(tuán)火,把人毀滅。”作者在這里交代與揭示了繁漪的性格特質(zhì)和情愛復(fù)仇的深層潛因。在與周樸園的逼迫與掙扎、摧殘與抗?fàn)幍膶α㈥P(guān)系中,她始終保持著生的希望,努力追尋著那一線微弱的希望。周繁漪是一個求生欲很強的女人,“郁積的火燃燒著她”,一方面她輾轉(zhuǎn)于周樸園的情感冷漠、精神摧殘和情愛禁錮中,保持著隱性抗?fàn)幍木駹顟B(tài);另一方面又周旋于周萍的熱戀與遺棄、逃避與阻攔中,當(dāng)事情發(fā)展到不能挽回的時候,周繁漪索性豁出一切,如雷電般怒吼爆發(fā),不惜付出一切代價,甚至采用自毀的方式,向?qū)V贫鵁o情的丈夫、冷酷而柔弱的周萍展開報復(fù)。在整個《雷雨》中,周繁漪暴烈而狂熱、執(zhí)著而偏執(zhí)、倔強而沖動的“雷雨”式性格,體現(xiàn)出女性生命底層蘊藏的求生欲與抗?fàn)幮浴?/p>
與周繁漪的“瘋狂與執(zhí)迷”不同,《日出》中的陳白露承受著更多的“清醒”的痛苦。陳白露原本是一個向往自由、向往愛情的進(jìn)步女性,最后卻可悲地淪落為供他人玩弄的金絲籠里的鳥兒。魯迅曾說過:“人生最大的苦痛,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陳白露的人生悲劇就是這樣一種清醒卻無路可走的路。
陳白露是大都市中的一個交際花,她一方面追求著奢華的物質(zhì)生活,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又極度厭惡這種紙醉金迷的生活。陳白露曾受到過新思潮的洗禮,擁有過活潑而純真的“竹均”時代,和大多數(shù)人一樣渴望有一個意中人一起組建一個幸福的家庭。她獨自一人到上海闖蕩,原本以為憑借著自己的年輕美貌和聰明才智,能闖出一條路來,卻不幸落入各種陷阱,淪落為一個交際花,過著一種寄人籬下的生活。然而雖身處困境,陳白露卻沒有自甘墮落,不愿意接受命運的安排,她認(rèn)為憑借著自己的美貌和聰慧,即便是潘月亭破產(chǎn)了,也許會有“李月亭”“王月亭”之類有錢有權(quán)的人來供養(yǎng)自己。可陳白露始終是清醒的,每每夜深人靜時她就感到空虛與迷茫,“她愛生活,又厭惡生活”。她厭倦了上流社會紙醉金迷、鉤心斗角、爾虞我詐的糜爛生活,卻無法抵抗與拒絕享受這種生活。這樣的生活方式一面在肉體上滿足著她,一面在精神上摧殘著她;她想要逃離這個地方,卻又舍不得這個地方。陳白露對于自身的困境保持著十足的清醒,她同情和自己命運一樣的人,一心想著救人,當(dāng)她目睹了“小東西”被摧殘蹂虐的境況,從這個女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向“小東西”伸出了援助之手。陳白露在痛苦的泥淖中掙扎著,想要反抗卻力量不足,陳白露承認(rèn)太陽快要出來了,但是太陽并不屬于她,她只能沉沒在黑暗中,所以,當(dāng)她賴以寄生的銀行家潘月亭破產(chǎn)時,她選擇了在日出前服毒自殺,永久地沉沒在了黑夜之中。“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后面,但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曹禺把《日出》的結(jié)局安排在了日出的時刻,其反諷意義不言而喻。
周繁漪的悲烈、陳白露的絕望,她們?yōu)閻矍椤榛橐觥榧彝嗨土俗约旱那啻耗耆A甚至寶貴的性命。曹禺前期所創(chuàng)作的戲劇中,《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基本上都是屬于現(xiàn)實主義作品,這些作品中女性的悲劇包含了曹禺對中國社會的初步反思和新舊社會交替中女性的悲劇處境。周繁漪、花金子、陳白露等女性歷經(jīng)千辛萬苦勇敢地邁出了突破枷鎖與禁錮的腳步,她們雖沒有突出重圍,卻為之而努力過、抗?fàn)庍^。周繁漪曾說:“我是個人,一個真正活著的女人。”她深陷變態(tài)的情欲中無法自拔,在瘋狂的報復(fù)中自我毀滅。陳白露在出走后走向了墮落,但又不甘心墮落下去,最后發(fā)現(xiàn)走不出一條新生的道路,在清醒中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這些女性的抗?fàn)幖仁菍鹘y(tǒng)價值體系的背離,也是對男性專制制度的反抗。曹禺賦予這些女性以一種“娜拉式”的出走儀式,為當(dāng)時的女性解放帶來了無限的可能。
二
1938年之后,尤其是20世紀(jì)40年代初期,《北京人》《家》的創(chuàng)作,標(biāo)志著曹禺的戲劇創(chuàng)作進(jìn)入了另一個階段。學(xué)界稱呼這一時期曹禺的戲劇創(chuàng)作進(jìn)入了“秋陽階段”,這一時期,曹禺的心境逐漸從“郁熱”轉(zhuǎn)入一種“沉靜”。體現(xiàn)在戲劇作品中,就是從《雷雨》《原野》時期的躁動向《北京人》階段的沉靜心理轉(zhuǎn)化,曹禺開始轉(zhuǎn)向塑造一些堅韌而賢淑、善良而淳樸的女性形象,表現(xiàn)出另外一種審美追求。如《北京人》中的愫方、《蛻變》中的丁大夫、《家》中的瑞鈺等人,她們具有強烈的犧牲精神,對生活表現(xiàn)出寬容和忍耐,走向了回歸傳統(tǒng)和本性的道路。
《北京人》中的愫方是一個真、善、美的女性。她出生在江南的一個名門世家,江南的秀麗山水與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愫方養(yǎng)成了端莊恬靜、溫柔體貼的性格。“蒼白的臉上恍若一片明凈的秋水,里面瑩然可見情深藻麗的河床,她的心靈是深深埋著豐富的寶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豐富的寶藏也坦白無余地流露出來,從不加一點修飾。”愫方的父母早亡,年幼時被送到了姨母家中去生活。正是這種孤苦無依而寄人籬下的生活,童年的不幸使得愫方習(xí)慣了忍受各種痛苦、歧視和侮辱。愫方不愛說話,“誰也猜不著她心底壓抑著多少苦痛與哀愁”,然而她的性格是溫厚而慷慨的,經(jīng)常會忘卻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撫愛著和她同樣不幸的人們”。與繁漪、陳白露一樣,愫方也熱烈地憧憬著愛情,她把自己的幸福與快樂完全地放在愛人曾文清的身上,無怨無悔地為曾家奉獻(xiàn)著自己的一生。愫方是哀靜的,她總是忍耐著,把世間所有的悲苦都埋藏在心里。愫方的一生幾乎是都是為了曾文清活著的,“他走了,他的父親我可以替他伺候, 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愛的字畫我管,他愛的鴿子我喂”,甚至是曾對她惡言相向的曾思懿,愫方也能溫柔地去愛護(hù)。愫方沉默地接受了命運的不公,用她的溫柔善良包容了所有苦難,只愿曾文清能夠逃出這封閉壓抑的樊籠。然而當(dāng)懦弱無能的曾文清狼狽地回到家里,愫方突然覺得絕望了,她的犧牲、她的忍受都不再有任何意義。此刻,愫方徹底打消了對曾文清保有的最后希望,意識到了自己之前的幼稚與無知,認(rèn)識到她所愛的人是一個懦弱不堪的人。所以她決定逃離這個環(huán)境,在曾、杜兩家爭搶棺材時,而后面曾文清吞煙自盡的時候,愫方對于這個家的希望終于徹底幻滅了,她決定與這個封建家庭脫離,毅然決然地去開始新的生活了。
愫方的離家出走,既是對丈夫曾文清的絕望,也是對封建家庭的絕望。她有著自己的理想, 她的離開是必然的,曹禺在結(jié)尾處表現(xiàn)出一種理想主義精神,愫方在認(rèn)清生活的本質(zhì)、認(rèn)清自己的悲劇命運時,重新選擇人生道路,到廣闊的“天涯”去尋找真正的“知己”。愫方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更貼近生活實際, 曹禺曾坦露塑造愫方這個人物形象的原因:“愫方是《北京人》里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部的力量,也可以說是用我的心靈塑造成的。我是根據(jù)我死去的愛人方瑞來寫愫方的。”可以說這是曹禺對一種理想人物及理想生活的期望與努力。正是因為經(jīng)過了這樣一種由死而生的“蛻變”,愫方才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她身上的傳統(tǒng)美德才獲得了一種新的生命。
1940年,曹禺完成了抗戰(zhàn)爆發(fā)后的第一個劇本《蛻變》。《蛻變》中的丁大夫是一位抗日戰(zhàn)爭時期支援后方的醫(yī)生。在劇作中,她只有姓而沒有名,曾在海外留學(xué),她在祖國危難之際,放棄了優(yōu)越的生活條件,投身于抗戰(zhàn)之中。她具有強烈的使命感與責(zé)任感,對待病人像是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丁大夫深明大義,舍小家為大家,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線去,在小家庭與國家之間,丁大夫選擇了報效國家,她曾說:“有一種人活在世上,并不是為的委委屈屈,整天打算著迎合長官,怕馬吹牛,營私舞弊,這種人生下來,就預(yù)備當(dāng)主人,愛真理,愛國家,言行一致,說到做到,把公事看得比私事重。”可以說丁大夫是一個“英雄”,曹禺在時代的召喚下,一改以往那些以揭露“黑暗”為題材的創(chuàng)作,轉(zhuǎn)向去歌頌光明,歌頌英雄,歌頌奉獻(xiàn),這一時期劇作中的女性人物代表了作家本人對時代的觀察與理解,體現(xiàn)了曹禺試圖回歸自我,恢復(fù)生命的本真狀態(tài)。
結(jié)語
曹禺說:“我對自己作品里所寫到的人和事,是非常熟悉的。我出生在一個官僚家庭里,看到過許多高級惡棍、高級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現(xiàn)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時間甚至可以說是和他們朝夕相處。”曹禺的戲劇創(chuàng)作始終離不開對人的觀察、體驗、探索與研究,《北京人》中的曾皓就有著曹禺父親的影子,同時曹禺的哥哥就是一個鮮活的曾文清的影子,而愫方則是依據(jù)曹禺的愛人方瑞的性格而塑造的。曹禺筆下一個個鮮活的女性的人物,不論是出走還是歸來,是抗?fàn)庍€是犧牲,都能代表那個時代的某一類女性,寫盡了她們的愛恨情仇。曹禺曾說:“我喜歡寫人,我愛人,我寫出我認(rèn)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寫過卑微、瑣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難于理解。沒有一個文學(xué)家敢講這句話:我把人說清楚了。”
是的,曹禺把這些女性都寫清楚了。
參考文獻(xiàn):
[1] 錢谷融.《雷雨》人物談[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2] 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4.
[3] 吳宏聰,范伯群.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M].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9.
[4] 朱棟霖.論曹禺的戲劇創(chuàng)作[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1986.
[5] 華芝.曹禺創(chuàng)作藝術(shù)探索[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
[6] 胡叔和.曹禺研究資料[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1.
[7] 李爽.曹禺劇作《北京人》中的“反傳統(tǒng)”與“傳統(tǒng)”[D].中央民族大學(xué),2009.
[8] 曹禺.曹禺自述[M]. 北京:京華出版社 , 2005.
[9] 王育生. 曹禺談《雷雨》[J]. 人民戲劇,1979 (3).
[10] 曹禺.論戲劇[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 , 1985.
作 者:?常誠,山西傳媒學(xué)院表演學(xué)院講師,研究方向:表演理論研究與教學(xué)。???????????
編 輯: 曹曉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