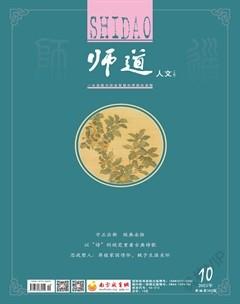屏幕育兒,忌憚還是享受?
方棠
“你拿起這本書是因為好奇,說得更直白些,你對孩子和屏幕之間的關系感到焦慮。”——這是《兒童電子屏幕指南》一書的第一句話,作者如同吉卜賽算命女人一般幽幽道來的口吻一下子吸引了我。花了一周時間讀完全書,腦海中竟浮現出醫學界的那句名言來:“有時治愈,常常幫助,總是安慰。”是的,這便是這本書帶給我的感受。它化解了我對屏幕的矛盾和糾結,讓我拋開了心中若隱若現、縈繞不休的內疚和焦慮,從而可以更加坦然地面對屏幕和孩子,也更加堅定自己一直以來的做法。
作者安雅·卡梅內茲采訪了教育、科技、心理等領域的諸多專家,對500個家庭展開了調查,在書中列舉了兒童與屏幕、父母與屏幕之間的種種爭議、問題和困惑,“引導我們一起度過充滿恐懼和夸張宣傳的暗礁區”,厘清數字媒體在我們自身、家庭生活以及所處時代中所扮演的角色,幫助我們尋找適合自己家庭的屏幕使用策略。
書中顯示,目前許多研究往往聚焦于技術所帶來的傷害,科學界對兒童和屏幕的關系存在一種系統性的偏見。肥胖、低質量睡眠、攻擊性、注意力渙散、認知能力障礙……這些觸目驚心的后果只能說與屏幕的使用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卻并沒有堅實可靠、不容置疑的因果關系。當然,過度使用屏幕造成的成癮性是不容忽視的,屏幕時間取代其他活動的“擠出效應”也應當引起我們的警惕。然而,屏幕本身并非毒藥,單純的限制和監控是遠遠不夠的。如果父母能主動地、有意識地塑造孩子對屏幕的使用,鼓勵溝通、學習和創造,它也可以幫助兒童克服自身缺陷,進行學習,建立人際聯系,成為交流與創新的工具,甚至與孩子的好奇心碰撞,產生神奇的成果……使用得當的話,其“潛力之燦爛不亞于危險之黑暗”。
正如書中歷史學家梅爾文·克蘭茲伯格的那句名言:“技術不是好的,也不是壞的,但也不是中立的。”屏幕和孩子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其基調是由我們自己奠定的。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時常聯想自身,反躬自問。回首往事,可以說,女兒是伴隨著屏幕長大的,她接觸屏幕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兩歲以前。我找到了自己曾發過的一條朋友圈,照片上,大約兩歲的她如同小青蛙一樣趴在床上,面前放著iPad,大概在聽兒歌。而書中提到,我國臺灣地區立法禁止兩歲以下的兒童使用電子設備,所以,某種程度上說,我竟然是個違法的母親;但好在美國兒科學會于2016年刪掉了“兩歲以前不準看屏幕”的專家建議,看到此處我不禁又松了口氣……
那時候,屏幕是帶給她快樂的工具,也能讓我在一整天的育兒中稍作喘息。雖然自己有意識地控制了時間,每次不超過20分鐘,每天也控制了次數,但仍免不了內心隱隱的負罪感。在這個崇尚密集育兒的時代,各種類型的“超人媽媽”樹立了育兒的最佳范本;在優秀媽媽的陰影之下,身為母親,既無法避免外界的評價,也無法逃脫內心的自我審判。好在除了在平板和電視上聽歌、看動畫之外,我們還有大量的親子閱讀時光,也有充足的戶外玩耍。女兒和屏幕的關系是正常而和諧的。
很快,到了四五歲,女兒不再只滿足于被動地觀看兒歌和動畫了,開始進入和屏幕互動的階段。我發現,她迷上了“寶寶巴士”app,而且似乎過于迷戀了,對它的興趣超過了其他一切活動。按書中的標準來看,她開始上癮了。曾經擔憂、恐懼的事情似乎變成了現實。經過一番爭論與商量(以及一些互相指責),我們終于狠下心來,決心減少甚至切斷她和屏幕的關聯。我們騙她說,iPad壞掉了,沒法修好了。這個突如其來的“噩耗”給女兒帶來了怎樣的痛苦可想而知,幸好,還可以到少兒圖書館的平板借閱區借著玩,那里的規定是每次只能玩一小時。就這樣,女兒玩iPad的頻率降至每周一次,而且每次都是在圖書館的環境下,玩過之后自然而然地開始閱讀……孩子的興趣總是多變的,慢慢地,iPad從她的生活中淡出了。
和作者安雅·卡梅內茲交談過的家長中,有些人認為盡早限制孩子對科技產品的使用很有好處也很重要,他們想讓家庭成為排除科技的避風港;另一些人則注重給孩子“搭腳手架”,主動向孩子介紹技術,幫助他們學會自我設限。作為一個熱愛科技產品的人,我始終想成為第二種媽媽,帶著孩子遨游在科技帶給我們的新奇和美妙之中,而不是被焦慮裹挾,費盡心思打造一個“網絡真空”。孩子總有脫離父母控制的一天,當電子產品對他而言從絕對禁止變成完全自由時,那種“報復式”的自我放縱無疑更令人擔憂。我想在孩子還小的時候,就讓她從他律中學會自律,在享受科技、娛樂和遵守規則、掌控自我之間達到某種平衡。
于是,有一天,我開始帶著女兒玩游戲,在她讀一年級的時候。
我介紹給她的第一個游戲是“紀念碑谷”。這款游戲的經典毋庸置疑:畫面簡潔、純粹、精美、奇幻;關卡的設置、視錯覺的設計精妙無比,每一關都是對空間想象力的極大考驗;情節、文案、配樂也令人贊嘆不已,充滿哲思和藝術美感,讓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當圖騰為了讓艾達繼續前行,用身體為她鋪路,不惜落入水中時,我們一起為圖騰的犧牲而感傷,也共同體會他再次出現時的意外之喜。女兒甚至還畫了一幅小畫來紀念艾達的圖騰朋友。當艾達經歷了一番冒險和波折后,終于和媽媽重聚、相擁時,我們也相視一笑,抱在了一起。經由這個游戲,我和女兒擁有了共同的屏幕時光和“數字回憶”,這回憶比任何私人化的記憶更持久、更牢固。因為它是一代人共同的記憶,已經作為一個符號,寫入了流行文化的歷史。
后來,我給女兒借閱了繪本《建筑師的大創造:錯位的建筑結構》和《顛倒國》,這兩本書就像紀念碑谷一樣,充滿了各種視錯覺畫面,我們的快樂從游戲延伸到了屏幕之外,拓展到了書本之中。
其實,類似這樣的拓展一直都有,很多媽媽都有意無意地做到了。比如女兒非常喜歡幾部動畫如《小豬佩奇》《米奇妙妙屋》《汪汪隊立大功》等,我都買過相關的玩具。家里有佩奇一家人,有米奇的朋友們,還有裝備精良的汪汪隊……看動畫之余,我們可以用玩具過家家,玩角色扮演游戲。有時是一起表演,有時女兒一個人就能自言自語玩很久。就這樣,屏幕內的時間延伸到了屏幕外的活動中,正如書中所說,“現實世界、故事世界和游戲混合在了一起”。
后來,我們還玩了手游“夢想小鎮”:我來一點點建造小鎮,她來打理動物園;我們一起種植麥子、玉米、蘿卜、甘蔗……然后收割。就這樣,我們的小鎮逐漸成形,一點點發展壯大。
再后來,女兒找到了自己最喜歡的游戲“我的世界”。這款游戲風靡全球,受到了教育界的追捧,許多人認為,它“以最純粹的形式展現了‘建構主義思想”,包含了“做中學”的教育觀。當女兒滿懷自豪地向我介紹她建造的醫院、小樓、漂亮寬敞的天臺、激光走廊以及陷阱時,我能夠發自內心地感受她的快樂,也樂于放手讓她獨自玩耍、自行探索了。因為對孩子來說,這是“無害”甚至有益的內容。
正如安雅·卡梅內茲告訴我們的,當孩子接觸屏幕時,控制時間不是最重要的,內容才是核心;共同的參與很重要。“凡是能夠支持親子積極互動的媒介都是有教育意義的。”慢慢地,我不再像以往一樣那么擔心上癮問題了,擺脫焦慮,拋開內疚,共同參與,享受和女兒的屏幕時光。
現在,我們最溫馨的互動除了親子共讀之外,便是看電影了。保證足夠的距離、合適的光線和正確的坐姿后,我們常常一口氣看完一整部電影,共同沉浸在迷人的光影變幻之中。每看一部電影,我們就擁有了更多的話題、更多的樂趣,以及更多的心照不宣、心有靈犀。
看完《麥兜》系列,我們重復著“魚丸粗面”的段子,在車流不息的路上一起快樂地哼唱《車車車車》;看完《機器人總動員》,女兒畫了瓦力和伊娃,我買了制作瓦力的一整套不織布,后來因太過復雜只好半途而廢,我們只縫好了瓦力的兩只眼睛;看完《冰雪奇緣》,我應女兒要求買了艾莎的裙子,她穿著閃閃發光的裙子在鏡子前臭美,我們還一起拼拼圖,用造雪粉做雪寶;看完宮崎駿的幾部電影,我們一起畫了千尋與白龍、波妞與宗介的數字油畫……
電影不光是我們游戲的內容,也可以單純只作為討論的話題。還記得女兒對《花木蘭》的評價:“電影挺好看的,就是人畫得有點丑。”我帶她比較二維動畫和三維動畫的不同以及各種畫風的區別,探討不同類型的美,試著向她展示審美的多元化;我們還談論了性別議題,木蘭雖然不如周圍的男性強壯,但她聰明、機靈、細心,以一己之力扭轉戰局,還救下了皇帝,她在性別不平等的時代創造了傳奇;后來,我給女兒講述了歷史上花木蘭的故事,還給她念了幾句《木蘭辭》:“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最近,我們又一起看了《瘋狂動物城》和《頭腦特工隊》,借閱了相關的繪本。女兒捧著《瘋狂動物城》的官方配套漫畫書細細品讀人物設定、故事細節,愛不釋手;繪本《情緒小怪獸》中有五個不同顏色的情緒怪獸,分別代表快樂、憂傷、憤怒、平靜、恐懼,正好可以和《頭腦特工隊》形成有趣的對照……
就這樣,女兒經常從屏幕跳進書頁,有時也會從紙質書溯回到屏幕。讀《三國》故事后,她把最喜歡的《草船借箭》那一集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完《西游記》連環畫,我們一起欣賞電影《大鬧天宮》。
除此之外,我還鼓勵女兒學習使用電腦。借來了《寶寶編程》,讓她在電腦上敲出一個個代碼,體驗小小程序員創造的快樂;鼓勵女兒學打字,有一天,她開始偷偷在電腦上編輯自己的文檔《我的未來計劃》。我想讓女兒感受到,電子產品除了有娛樂、社交的功能外,它也是我們學習、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
“技術無處不在,我們呼吸的空氣充滿了無線網絡信號。”智能手機在全世界攻城略地,仿佛整個人類都在參與一項不受控制、沒有對照組的實驗。無論成人還是兒童,我們都已無法逃離無處不在的屏幕。因此,我們不可能為孩子打造一個“無屏幕、無網絡”的烏托邦,也無法一廂情愿地把孩子拉回到玩玻璃球的時代,給他一個田園牧歌式的充滿懷舊氣息的童年。在不傷害視力和內容合適的前提下,我們不妨給孩子多一點自由;畢竟,每一代人都有屬于他們的童年。
安雅·卡梅內茲指出:“未來,每一個孩子都將會生活在數字創作、數字表達、數字交往比今天還要普及的環境中。”身為父母,我們需要認清形勢,放棄幻想,借助屏幕積極育兒,幫助孩子增強“數字免疫力”,提高數字素養……
當然,上癮問題仍是懸在所有父母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我們永遠不能掉以輕心。
責任編輯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