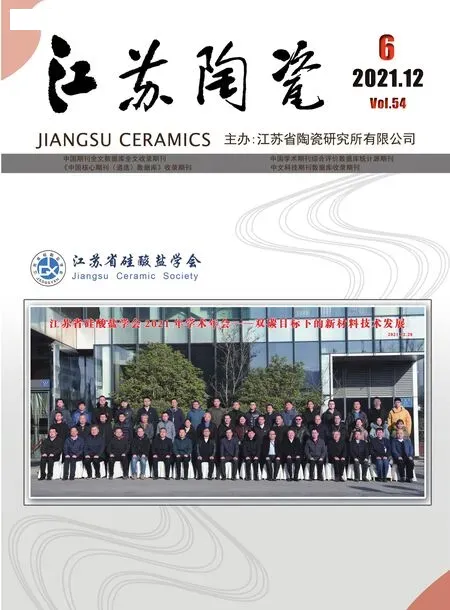試論原始墓葬文化功能影響下的彩陶藝術
孫圣國
(蘭州財經大學藝術學院,甘肅 蘭州 730020)
原始彩陶與巖畫藝術一樣為我們留下了遠古時代的形象記憶,與巖畫相對較直觀的形象不同,彩陶所表現的形式多數通過抽象隱喻和象征的裝飾方式來傳達,這也造成彩陶研究的諸多未解之謎。反觀彩陶墓藏出土的方式,作為隨葬物品無疑指向了原始的喪葬文化功能,除此,也間接反映了當時的生活特點、審美趣味及喪葬風俗,大量的墓葬彩陶則通過形態和紋飾傳達了對未知世界的某種風俗信仰,成為墓葬文化精神意識的視覺形象呈現。
1 墓葬出土彩陶的功能
從甘青地區辛店文化出土的多處彩陶內發現了粟類谷物的遺存,“蘭州白道溝坪M15內有隨葬10件陶器,其中三件內有谷灰遺存”,[1]“甘肅臨夏東鄉林家:F20內的陶罐內出土了碳化粟粒”[2],“甘肅青岡岔:F1內的陶罐內發現了糜子顆粒”[3],“青海樂都柳灣:墓葬中發現用容積較大的陶甕作為隨葬品。M339的4件陶甕內就存放有谷物”[4]。類似的碳化粟還出現在甘肅秦安大地灣、甘肅永昌的鴛鴦池等地,這表明彩陶作為容器不僅起著盛放糧食的功能,而且成為逝者的隨葬用品。在原始社會生產水平落后的情況下,食不果腹的不穩定生活決定了定居的人們必須儲存食物,才能渡過缺乏食物的冬春季節生存下去。溫飽和繁殖始終是氏族得以延續發展的關鍵問題,這種基本生存的需求在死后仍希望得到保障,以充足的食物伴隨逝者入葬便成為親人對死者的敬意和追思,也是對生者的心理慰籍與情感寄托。當然滿足溫飽問題僅僅是基本的功能,可以盛放糧食的素陶也同樣滿足這種需求。除此,而作為葬品的彩陶勢必蘊含另外的寓意和暗示——即生者對已逝親人超越現實的想象,通過想象為逝者創造了另外的一個理想世界,一個約定成俗的精神存在領域。從彩陶隨葬的數量多少和類型又暗示了墓主的經濟條件及在氏族中的地位尊卑優劣,或許在此階段開始出現了社會地位的區別,甚至出現了貧富分化現象。據考古發現,在半坡遺址中人面、魚、蛙等圖像的彩陶盆多數覆蓋在翁棺上,而成年人的翁棺和墓葬未發現類似的彩陶盆,這種彩繪陶盆可能是夭亡兒童的一種葬具,盆內的紋飾可能與舉行的兒童葬儀巫術活動有關[5]。
2 墓葬彩陶的文化指意
無獨有偶,在墓葬出土文物中,傳統的墓葬文化有引魂升天的戰國旌幡帛畫,彪炳功績、歌功頌德、張揚國力的秦始皇兵馬俑,事死如事生的西漢馬王堆帛畫及陶俑,從中國傳統墓葬文化的功能與經驗來看,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巫文化的影響下起到招魂引魄、超度亡靈的作用。從戰國、秦漢以來人們崇信玄學,崇信人去世后可以靈魂轉世、得道成仙。彩陶出現的鳥紋、水紋、太陽紋,甚至陰陽符號,許多的學者把這些認為是對自然現象的描寫,筆者卻認為這些元素可能是神話中的天界——即人死去靈魂居住的理想樂土,由神話傳說而演化而成墓葬信仰,水紋意指是西天王母的瑤池,而人面蛇身的圖像則與山海經故事的形象類似,這種高度程式化的抽象紋飾與后來殷商時期出現的青銅紋飾不能用直觀的自然現象來解釋,而是人們對自然、人對未知的主觀創造,墓葬藝術是最恰當的表現方式之一。龍紅也有類似的描述:“彩陶的設計與制作過程中,在器型與紋飾兩個方面都有著相當豐富的神話傳說的精神元素。”[6]第二,作為祭祀禮品事死如事生,厚葬逝者有重禮法、盡孝道之意。陪葬品越豐厚象征著逝者在冥界生活越富足。辛店文化彩陶內碳化粟類遺存揭示了其基本的用途。在魯南蘇北等地至今流傳著厚葬的長輩,或者給逝者穿著多層衣服,寓意著子孫后代能夠家資殷實。第三,取吉祥、鎮墓、辟邪之意,寓意后代人丁興旺、財源茂盛。黃河中下游流域的風俗仍把喪葬與后代相聯系,在殯葬的時候法師用松柏的枝葉拂掃靈堂或孝子,在下葬孝子將柳條的哭喪棒丟進墓穴,柳樹、松柏色澤翠綠易于成活、生命力頑強,寓意死者后代如松柏一樣萬古長青、子嗣興旺。國內外不少學者認為彩陶的蛙紋圖案象征原始的生殖崇拜,并且借助壯族民間蛙神崇拜進行類型研究[7]。而部分學者認為彩陶中出現的蟾蜍比較明顯,而蛙紋則多數比較抽象。金烏、蟾蜍在上古神話里寓意著日、月,蟾蜍指代蟾宮即月亮,在彩陶上繪有蟾蜍則有靈魂升天之意。另外,祭祀隨葬還有對墓主的墓志、旌表、褒揚、評價作用。早在殷商的墓葬青銅器、甲骨文上出現了文字信息,部分文字具有記載和旌表的作用,尤其在春秋戰國以后的貴族墓葬中比較突出,在遠古時代彩陶上出現的多是一些紋飾和符號,缺乏文字記載的相關信息,像柳灣、馬家窯等地的個別墓葬規格宏大,墓穴彩陶隨葬數量較多,墓主在部族中的身份地位明顯與眾不同,是否以此來表達對墓主生前的貢獻或敬意尚無可證明的依據。
3 彩陶藝術創造的根源解讀
從造物的演化過程看,陶器的素陶應當早于彩陶的燒造,從功能的角度看,陶器作為普通的生活用品出現應該不會晚于墓葬的使用,而原始彩陶是否唯一用于陪葬的目的而燒制至今尚無定論,但彩陶裝飾除了少量描摹客觀世界的形象外,所呈現的大量抽象形式,無論這種圖形是易于識別的具象形態,還是幾何紋飾為主體的抽象樣式,無疑這種方式不能視作簡單的個體行為而具有群體情感性的特定意義。至于彩陶紋飾產生的原因,學者們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一種認為來自于實踐經驗,原始人最初將泥巴貼在編制的器皿上燒制,經長期的生活積累創造了帶有細密肌理的紋飾;其次是運用工具在塑形的過程中拍打成型而留下的痕跡,在早期階段只有類似肌理的素陶紋飾,例如二里頭出土的陶器,是否在此基礎上進行二次創新燒制彩陶尚需要其它條件,因為在陶器的發展過程中,陶器上制作留下的弦紋、工具肌理而沒有演化成彩陶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作為工藝美術,彩陶的燒制與發展也并非簡單偶發因素,必要的制作工具、礦物顏色、黏土及燒造條件成為其必要的物質基礎。除此,在人類的早期階段推動彩陶發展的現實需要與心理需求則是維系發展的內在因素,而彩陶隨葬信仰則可能是推動彩陶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作為一種傳達意義的載體,其形態、紋飾表達的情感思維可能是多元的、不確定的意義,在原始社會由于繪畫技藝水平低下,運用直觀的繪畫手段未必能夠恰當地表現所需要的內容,對彩陶裝飾語言的選擇可能運用具有點、線、面形式感的平面形態——獨幅畫面或復合結構,從符號學的角度被研究者理解為符號。在《中國原始藝術精神》一書中,張曉凌認為“中國原始造型符號之所以被構造為一種獨特的形式,一種超越部族文化并具有獨特功用的造型體系,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決定符號形式的本質力量的生成。只有把原始人精神特征制作為符號形式的力量,才能成為原始藝術審美的本質力量,而這個力量正是由滲透于原始人思維、原始宇宙觀和生存方式各個方面的情感特征所形成的。原始人的這種情感原則使原始造型藝術從生成之日起,就以追求造型神韻的表現作為最終和最高目的——這是原始造型藝術觀念建構的核心部分。”[8]這是對原始藝術產生的本質力量提出的論斷,在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原始人對未知的自然現象不能用科學合理的方法來解釋,尤其是面對生存的威脅意圖借用圖騰、巫術等神秘的力量來團結部落尋找安全感,在難以預測的自然力面前追求安全心理的平衡。
介于生者與逝者的墓葬文化則具備形成這種本質力量的內在動力,這種動力必須具備幾個條件:第一,它屬于氏族成員共同認同的信仰和適用范圍;第二,在氏族內部形成并具有持續傳承的條件;第三,它必須寄托于某種儀式行為或視覺載體。它并不一定通過氏族權利來保障這種方式傳遞下去,可能通過民俗崇拜、圖騰或巫術信仰的力量使其延續。中國傳統的墓葬藝術所描繪的內容并不一定是現實生活的客觀再現,而是生者對死后未知世界的想象,把這些意識和想象通過借助于工具、材料、技藝轉化為紋飾、圖像等元素是藝術創作的基本路徑。戰國時期的“人物御龍帛畫”、“人物龍鳳帛畫”,人神同構的造型表現了虛幻的理想世界,實質是生者對死后未知世界的再造與精神寄托,而藝術創作是作者情感的感性顯現與精神追求,這或許是彩陶藝術產生與發展的本質動力。
4 結論
彩陶的母題至今在學術界存在著較大的爭議,有的學者從現存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角度去研究,有的學者從相近文化(如巖畫)的角度去探索。墓葬文化藝術表面上看是人從生到死,從人界到神界的視覺媒介與載體,實質上是人類現實世界面向未知世界的一種思維表現形式與認知方式。作為學術研究從神話傳說中去尋找依據的方法似乎并不可取,但商周時期的墓葬藝術卻又傳達了對鬼神的敬畏思想及天人合一理念,并先后出土了大量可考的證物。在此之前人類尚無明確的文字信息供人們研究,彩陶便成為人們認識原始社會的語言類型,彩陶的發展必定有其信仰的內在力量,正是這種動力造就了燦爛輝煌的彩陶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