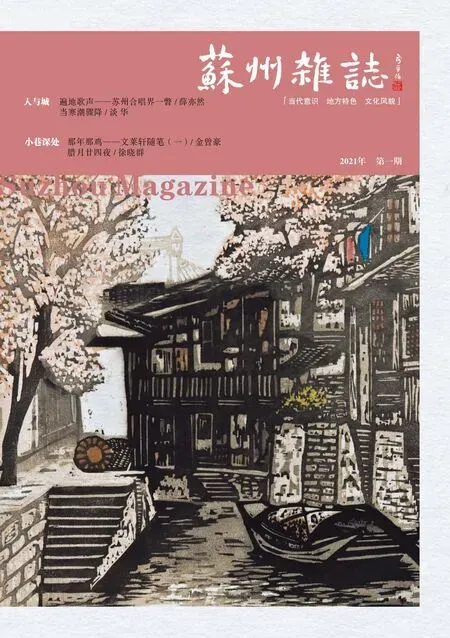我的書房
潘君明
藏書是我國的優良傳統,藏書之風深入民間,尤其在江南一帶,藏書風氣更盛。漢代,讀書人朱買臣、陸績就已藏書。清末學者葉昌熾所著《藏書紀事詩》,收錄私人藏書者一千一百余家,其中蘇州地區達二百余家。大凡一般文人學士,為讀書之需要,家中多有藏書,并出現了“汲古閣”“鐵琴銅劍樓”“百宋一廛”等藏書大家。我生活在吳地,不免受此影響,也開始藏書了。
說起我的藏書,由不自覺到自覺,由隨意購買到專門購買,由書籍雜陳到分類存放,有一段艱難曲折的過程。
我出身于農村,竹籬茅舍,家境貧困,經濟拮據,連讀書的學費都繳不上,更不用說藏書了。稍長,隨父親來到蘇州,幫助父親做工。我喜歡讀書,但家中無書可讀。怎么辦?有時,家中沒有早餐,父親給我零錢,要我自己去買來吃。我拿到零錢后,沒有去買早餐,而是把錢省下來,寧可餓著肚子,到樂橋那里書攤上去買書看。但所買之書僅是薄薄一本,不幾天就看完了,很不滿足。我父親有個朋友,家中藏有一大箱書,有《三國演義》《封神榜》《水滸》等,我就去借了看,大約看了一年有余,又沒有書看了。直到我參加了工作,有了工資,除絕大部分交給父母外,留下一點零用錢,可以進書店買書了。
那時,街上有家新華書店,我進去一看,哇,書架上全是書,厚的薄的,隨你挑著買。那時,口袋里錢不多,只能買一本。不過,那時的書很便宜,才幾角錢一本。我在藏書內找了一下,1979年出版的《辛棄疾》,0.17元;1980年出版的《龍川詞校箋》,0.32元;1982年出版的《唐詩小札》,厚達246頁,也只有0.66元。新華書店成了我的好友,每個星期日必去,每次購回一兩本,日積月累,書漸漸多了,開始形成了藏書。
書多了,放在哪里?放在紙箱內,放在肥皂箱內(用完肥皂的空箱)。但這不是辦法,看書很不方便。于是,購回了一只藤條書架,書多起來,又放不下了。再到舊貨市場購回一只較大的木制書櫥,但沒有多久,書櫥也放不下了。如再買書櫥,屋內也無處存放。無奈,只能將書捆扎起來,藏于床底下。哈哈,真的將書藏起來了。
那時,住房是租的,談不上有書房,僅在臥室窗口放一張書桌和一個書架,所謂“半是臥室半書房”。結婚后,有了孩子,隨著家庭人口的增多,工作單位照顧我,分配給我幾間老式住房,騰出一間做書房,做了兩只書櫥,這下放書可多了。但沒有幾年,書又放不下了。
幸好,隨著社會的繁榮,工資的增長,家庭經濟也有所好轉。我兒子靜洲購下了一層樓房,復合式,樓上的廳堂給我做書房,足有二十多平方米。這下我放開手腳,專門請來木匠,做了十五只書櫥一字排開,將我的藏書一一上架,看起來整齊美觀,真像個書房了。后來,我遷回到單位分配給我的新房,我寧可住小間,用大間做書房,將書櫥靠墻安置,環顧四周,滿目是書,這樣書房和藏書合在一起,總算遂了我的心愿。
我的書房樸素簡陋,布置淡雅。中間一張書桌,是大女兒靜珍孝敬我的,書桌上一臺電腦,是寫作的工具。墻上懸一副自撰聯:“歲月書中過,云煙筆底流。”掛一幅讀書照片,表示主人喜歡勤讀。
既然是書房,依據古人的傳統,得有個名稱。我生肖屬牛,成語有“牛角掛書”,講的是唐人李密騎牛看書、明人王冕放牛看書的故事,于是,取名為“角掛書屋”,其意是向古人學習,用功勤讀,還請書法家瓦翁、譚以文寫就。一幅字請桃花塢木刻年畫社做成匾額,懸于書房門楣;另一幅字做成鏡框,懸于書房內壁,也可說是一件雅事了。同時,我還請寒月老人篆刻“角掛書屋”印章,鈐于藏書扉頁,書亦生輝。
藏書,大多是逐一購回來的。有時出差去外地,也要去逛逛書店,或去舊書市場淘書。我有個習慣,凡是出門旅游,必先去書攤,買一本當地的旅游手冊。其原因是景點很多,看了不易記住,也不可能游遍全部。書買回來后,可以定心閱讀,也便于書寫游記之類的文章。所以收藏旅游之書,也成了我的最愛。
當然,有的書是有計劃買的,如《二十四史》。作為藏書者,這是必須有的。但那時工資很低,要全部買回來談何容易,只能一部一部買。于是,今年買幾部,明年再買幾部。后來,新版的《二十四史》定價上去了,價格貴了數倍以上。書店營業員認得我是老主顧,幫我與出版社聯系,去倉庫里找到了便宜點的舊版書。我前后大約花了五年多時間,才將《二十四史》全部購回。
藏書并不是裝點門面,也不是附庸風雅,主要是為了看書,增長見識,提高寫作能力。藏書者的理想不同,所藏的書目也不盡相同。我藏書是為了寫書,依據我的本職業務(在監獄工作)和業余愛好,偏重歷史古籍、地方文化和民間文學。為便于查閱書籍,我將藏書分為八大類:一是工具書,二是歷史古籍,三是地方文化,四是民間文學,五是民俗學,六是詩歌,七是野史,八是監獄學。書櫥內塞得滿滿的,放不下了,就堆放在地板上。自己曾想,不能再買書了,沒處放。但看到了中意的書,心里癢癢的,還是要買。
有些書一套多本,稱為“叢書”。在叢書之中,可以挑選幾本讀,有的則要系統性地讀。我對吳地文化特感興趣。小時候聆聽父親講蘇州山水、街巷、名人、民俗方面的故事,覺得好聽,影響極深。長大后,不知不覺中進入了研究吳地文化領域,很想讀這方面的書,以增加知識。但當時書籍很少,只能靠訪問年長的老者,了解歷史故事。1986年,在紀念蘇州建城兩千五百周年時,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江蘇地方文獻叢書》,其中有《吳越春秋》《吳地記》《吳郡圖經續記》《吳郡志》《吳門表隱》《清嘉錄》《宋平江城坊考》《吳郡歲華紀麗》《太湖備考》等十多本。要了解蘇州地方歷史文化,這些書是必讀的。我就一本一本地讀,這對于了解蘇州的歷史變遷、文物古跡、城池街巷、山水風光、社會民俗等,都是有益的。在我研究吳文化過程中,這些書是我的最愛,對我幫助極大。這一套書,有好多本經常翻讀,以致封面毀壞,邊頁磨損,真給我“讀爛”了。
有的書很厚,一部書有幾冊,有幾百頁、上千頁,甚至有上萬頁。說實話,這么厚的書確是很難讀完的,那就只能有重點地讀了。所謂“重點”,就是與自己的工作或寫作有關的。我研究中國監獄史,這就涉及每一部史書,依據監獄史方面需要的內容,有重點地讀。其方法是以朝代為主線,以監獄為重點,以人物為要點,一個朝代、一座監獄、一個人物地讀。如果這個人物是跨朝代的,那就聯系起來讀。將這座監獄的年代、地點、名稱由來、所關押的人物,以及用刑等,梳理清楚,最終寫成《中國歷代監獄大觀》一書,由法律出版社出版。這部書填補了我國監獄史學上的一個空白,在監獄系統受到好評。
讀書最花時間,經常有個感覺,好像未看幾頁書,一個小時已過去了。為了多讀書,讀到深更半夜是常有的事。我書房外有個小院,植有幾竿修竹,夜深,月色明亮,萬籟無聲,唯有竹影在窗前搖晃,好似我的知音故人,在陪我讀書呢。隨口吟道:“風清月白鳥歸林,欲覓蟲聲無處尋;唯有窗前數竿竹,伴我夜讀到天明。”
讀書不能死讀書,要讀以致用,增加知識,增長才干,邊讀邊摘錄是一個很好的讀法。書買回來后,不論是一冊、二冊或多冊,當時來不及看,但不能放在一旁,或藏入書櫥了事,而是要翻上一遍,看看目錄,記住書中的要點及大概內容,此后遇到問題,便于在書中尋找。
在工作或寫作中,經常會碰到難題,怎么辦?依靠讀書是個好辦法。書是長方形的,我稱之“長方先生”。遇到問題,就向“長方先生”請教,就能找到答案。
我堅持藏書與讀書、寫書相結合,學以致用,產生成果。無論是民間文學,還是文史散文、詩歌、楹聯等,均有著作問世。2014年榮獲江蘇省和全國首屆“書香之家”稱號。有書讀就是一種享受,就是一種幸福。我請友人刻了一方印章“角掛書屋主人拜讀”,鈐在書上,表示我對書籍非常珍惜,十分崇敬。
我出版了書籍,都要給我的子女,囑他們將書放好,利用空閑時間讀書。影響所及,有的買了書櫥,有的配了書房,也注意保存書籍了。
讀書是我的生活,生活需要讀書。一天不讀書,猶覺腦中饑。讀書是快樂的、幸福的。我的一生與書為伴,也是在讀書中度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