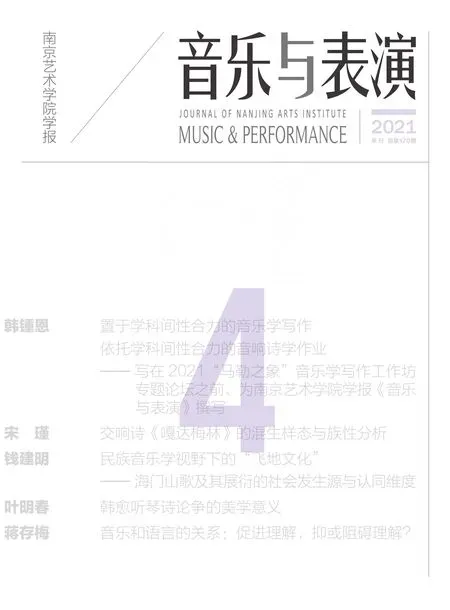論音樂的黏合性①
馮 亞(中國傳媒大學,北京 100024)
音樂的黏合性(adhesivity)是指音樂具有較強的活躍性、吸引力以及適應力,能夠同其他藝術形式或者藝術之外的社會實踐互為吸引并形成新的藝術門類或者新的社會實踐形式,也能夠迅速適應新的科學技術,借助不同的載體和媒介,創造出綜合的或新的藝術形態。
通常,我們把不能再進行剝離的獨立的藝術品種稱為元藝術,比如音樂、美術、文學;把兩種及以上的元藝術組合生成的新的藝術形式稱為綜合藝術,如:戲曲戲劇、舞劇、廣播、電影、電視、動畫、廣告、景觀、數字媒體(藝術)等。音樂與文學結合,形成了戲曲、戲劇;與形象性的畫面藝術結合,形成了聲畫藝術(電影、電視);與形體藝術結合,形成了舞蹈。不難發現,音樂是一個活躍分子,它幾乎可以和任何其他元藝術結合,形成綜合藝術。在綜合藝術中,音樂可以是主角,也可以是配角,身份地位靈活多樣。
音樂的黏合性也表現為它的活躍。幾乎任何一種新的技術的誕生或革新,促成了新的綜合藝術,音樂非但不會被淘汰,反而迅速融于其中,與時俱進。比如電的使用催生了電子樂器,相應的電子音樂迅速產生并且傳播開來。錄音、磁盤技術又推動了音樂的音響編輯;廣播、電視、網絡、電子游戲的普及則是擴充了音樂新的類型——廣播音樂、影視音樂、廣告音樂、游戲音樂,等等。音樂能夠迅速適應新的傳播媒介,產生相應的音樂品種。
現代社會,音樂與藝術以外的領域廣泛結合。音樂與體育結合,形成了花樣游泳、冰舞、藝術體操等,使得力量、速度、柔韌之美中增添了藝術的氣質;在重大的體育賽事比如奧運會中,主題歌成了必不可少的標志之一;音樂可以作為背景音樂存在于建筑環境、室外環境中,為構建環境和諧、優美氛圍的增添色彩;甚至,音樂還可以不拘泥人類的精神領域,在物質世界獲得追捧……音樂與宗教、音樂與勞動、音樂與商業無不千絲萬縷地聯系在一起。門鈴、智能洗衣機、手機等實用工具也引入了音樂作為鈴聲,音樂淪為美麗的信號。當然,被商業利用的音樂多是被動聽到,其美的特質因為過多的商品屬性而被掩蓋,甚至引起人的審美疲勞。
一、音樂的黏合性來自它的有聲性
音樂的聲音是從自然界中概括、升華后的有規律的聲音(樂音)和少部分沒有規律的聲音(噪音)。音樂首先具有聲音的屬性,即“聲音是人類聽覺系統對一定頻率范圍內振波的感受”[1]。其次,音樂是特殊的聲音形態,訴諸人的聽覺。聲音是構成音樂美的物質基礎,是音樂藝術存在的特殊方式。音樂的組成要素:音高、節奏、節拍、和聲、調式等都是依附于聲音而存在的。正因為音樂是有聲藝術,轉瞬即逝,所以,在電產生以前,音樂的傳播與傳承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口傳心授,人人傳播;一種是借助特殊的符號——樂譜這一物化形態進行音樂的記錄與傳播、傳承。這種模式在非有聲性藝術中是少有的。
音樂的聲音是有序的。音樂中樂音是有序的,樂音是有規律的震動的有固定音高的音;音階是有序的:從低到高排列的一組音;節拍是有序的:規定的強弱關系重復出現;調性是有序的:一個調只有一個主音;和聲是有序的:三度和弦關系的縱向疊加與排列;民族調式中的單樂段是有序的:起承轉合;奏鳴曲式是有序的:對立與統一的更迭……音樂因為有序而美,雜亂無章必然是不美的。相反,噪音是有震動沒有規律的音組成,因而不美,聽之令人煩躁,比如汽車喇叭的聲音、工廠機器的轟鳴、建筑工地的聲音等。當然音樂中也有噪音和噪音樂器,但那通常只是充當樂音的點綴。
音樂的聲音是豐富的。有序而不豐富的聲音,比如老式電報的嘀嘀聲、鐘表的嘀嗒聲、水車沖水的嘩嘩聲、重復的拍打籃球的聲音、電腦打字的聲音、甚至反復彈奏鋼琴上的“do”音,重復的聲音給人規則的感覺,但是機械的重復、過于單調統一的聲音令人乏味,是不美的。《國語?鄭語》里的觀點“聲一無聽,物一無文”[2]就是這個道理。豐富而有序是音樂聲音的特點,是音樂美的源泉。音樂聲音的豐富性表現為:在單部作品中,不論是橫向旋律線、樂段,還是縱向的和聲,或是兼具橫向與縱向的復調,無不體現著變化與統一;在個人風格方面:即使是同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在早期、中期、晚期也會存在風格的變化從微觀的音樂結構,到中觀的個人風格,再到宏觀的時代流派、國家、地方的音樂風格,等等,無不深刻體現著音樂的豐富性。
音樂的聲音是流動的。音聲在時間中流淌,音符間的連接成為時間的藝術。這種有序的音符流動形成節奏、音高的起伏(旋律)。人類對自身形體的審美有靜態的和動態的。靜態的人體的美、造型美,動態的技巧美、韻律美都是無聲的。肢體運動同樣強調節奏和起伏,這時流動的音符恰吻合了這些肢體運動的特性,融合為舞蹈、藝術體操、花樣滑冰等,形成特有的力量與形體美,更深刻地刻畫藝術形象。另外,音樂的流動也能彌合空間藝術如建筑、美術的視覺單調,可以作為背景與空間藝術同時呈現。電影的默片時代,人們明顯感到聽覺缺失嚴重影響了審美感受,電影為了給電影畫面增加聽覺美感嘗試了不少的辦法:請鋼琴師或小型樂隊在銀幕后伴奏;隨機播放鋼琴曲、交響樂片段;為電影編輯曲目匯編,等等。直到1927年《爵士歌王》上映,電影首次成了真正的聲畫藝術。
有聲性是音樂的物質基礎,有序、豐富、流動是音樂美的特點。如果音樂的聲音與畫面、語言及物質世界方方面面的有序“同構”了,美就產生了。這恰是音樂與其他藝術黏合的物質基礎。
二、音樂的黏合性來自音聲的不確定性
雖然音聲的文字符號——樂譜、音聲的表演、音響——音聲的物理形態記錄都已經是成熟的體系,但是從音樂的接受角度來看,音聲的表達并不直觀,對音聲的審美具有突出的不確定性。這恰是音樂與其他元藝術的差異之處。美國作曲家科普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言論:“音樂有意義嗎?——對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有的’。你能用一些文字來說明它的意義嗎?對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不能’。難題就在這里。”[3]美國電影音樂作曲家赫爾曼從電影音樂的角度分析,認為:“音樂實際上為觀眾提供了一系列無意識的支持。它不總是顯露,而且你也不必知道它,但是它卻起到了應有的作用。”[4]這里的“不必知道”既是指電影中聲音服務于畫面,也指由于音樂的不確定性,所以音樂的形象是模糊的。
這是由音樂存在方式的特殊性——音聲決定的。音聲(即音響形態、旋律)的由音高、節奏、時長等要素組成,它能夠準確地表現音高、音長、音量和速度,但卻不擅長刻畫直觀形象,也不具有概念性和邏輯性。音聲的非音畫、非語義特質決定了音樂體驗的不確定性。
黑格爾在《美學》第三卷的《音樂》一章,用了較多的篇幅討論了“音樂表現手段的特殊定性”,在討論音樂的旋律(音響形態)時,他認為:“音樂盡管要采取一種精神性的內容,并且以這種題材的內在實質或情感的內在運動作為它所表達的對象,這種內容畢竟是比較不明確的、朦朧的,正因為它是從內在方面(或精神方面)來掌握的,或是作為情感而反映于聲音的,——音樂的變化并不是每一次都恰恰代表某一情感、觀念、思想或個別形象的變化,而只是一種音樂的向前運動……”[5]可以看出,黑格爾雖然不是音樂家,但他對音樂的思考深刻,揭示了音樂的不確定性。
嵇康有“聲無哀樂”的觀點(這里的“聲”,指音聲,音樂的音響形態),音聲是沒有哀樂情感的。比如欣賞法國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鋼琴曲《月光》,如果他不標上“月光”這一標題,即便德彪西是真的是在用音符來表達他對月光的皎潔以及月夜下的和諧與恬淡的感受,但誰又會一定聯想得到呢?德彪西的鋼琴曲《亞麻色頭發的少女》,在音色與和聲方面的創新,捕捉并展現與傳統和聲迥異的色彩。這種音樂上的色彩創新與印象派畫家莫奈的創新相比,顯然后者的藝術形象更加直觀。
從受眾的角度考察,同一首音樂作品對不同的欣賞者來說,或者同一欣賞者在不同的時間里,人們的聯想、想象各不相同,音樂所引發的情感可能會有非常大的差異,對音樂的理解往往也是見仁見智。正所謂“理弦高堂而歡戚并用”(嵇康)。因為音聲具有不確定性,所以它就方便與各種具有概括性、形象化、邏輯性的藝術形式結合形成新的藝術形式。
(一)音聲與古典藝術的黏合
音聲的黏性首先反映在旋律與詩歌的結合,形成了音樂的重要體裁——多節歌(歌曲)。美學家蘇珊?朗格把綜合性藝術稱為各門藝術間的交叉。她分析認為:“適用于各門藝術之間的交叉關系的無所不在的原則就是:同化原則。例如在歌曲中,歌詞只能起到某種間接的作用,歌詞起的作用只是刺激作曲家的興奮,使作曲家為它譜曲。當歌詞進入歌曲之中并與音樂結合為一體時,作為一件獨立的藝術品的詩詞便瓦解了,它的詞句、聲音、意義、短語以及它描寫的形象也紛紛變成了音樂的元素。在一首千錘百煉的歌曲中,其歌詞是完全被音樂吞沒了的,在其中簡直就找不到任何有關歌詞的蛛絲馬跡。”[6]
蘇珊?朗格解釋中的“吞沒”了歌詞(詩歌)的是旋律,體現了音聲(旋律)強有力的黏合性。反過來,歌曲的有聲美,又加快了歌詞(詩歌)的傳播。中國的《詩經》《樂府新聲》在古代都是可以和樂而唱的歌曲,其在歷史上曾廣為流傳,在沒有音響記錄設備的時代,歌唱是文化傳播的重要渠道。
不同旋律可以與不同的詩歌融合為歌曲,甚至同一個旋律可以填上不同的詩歌,形成不同內容、不同風格的歌曲。比如童謠《兩只老虎》的旋律來于法國的宗教歌曲,土地革命時期,被填上“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的歌詞,成了廣為流傳的抗戰歌曲;《青春舞曲》的旋律來自王洛賓在維吾爾族地區的采風,旋律活潑歡快而歌詞是依據他本人失戀之后的感傷而重新創作的。詩、樂、舞結合形成了樂舞,樂舞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綜合藝術,東西方文明都有。樂舞消亡后,形成了新的變體:戲劇、戲曲、歌劇、舞劇。
(二)音聲與電的技術的黏合
工業社會的到來,電的發明改變了文明的進程,也改變了藝術發展的軌跡。有了電之后,音樂的聲響得以記錄、復制、編輯、傳播。音樂與有電的媒介結合,創新了音樂與其他藝術的綜合,電影、廣播、電視、網絡文藝、數字文藝中,音樂是不可或缺的有聲語言,無處不在。在聲畫藝術中,音樂更是成了非常活躍的組成要素,滲透在各個領域和環節。不管年齡、閱歷、身份、文化如何差異,人們在聽賞音樂時,豐富的、變換而細膩的情感世界總能與某一首音樂作品的美“同構”,從而產生心靈的凈化與升華,這正是音樂的魅力所在。音聲的不確定性成為音樂與其它藝術及技術綜合創新的重要優勢。
三、音樂的黏合性來自音樂藝術的抒情性
音樂不擅長表義,不擅長再現靜態的形象,那音樂的魅力何在呢?抒情!“聲無哀樂”,但是樂有哀樂。“音樂作為感染力的一種擴大或深化元素去對感覺發生作用”。[7]
在漫長的人類發展史中,是音樂展現人類豐富的情感世界,是音樂陪伴人們的情感生活。正如古人所云:“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序》)。中國人很早就總結了音樂與情感之間的關系,先秦時期,荀子在《樂論》中就提到“人之喜好音樂,為人情所必不免也”。漢代《樂記》中記載“情動于中,故形于聲”;《毛詩序》認為“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歐洲的音樂經歷了中世紀宗教音樂之后,世俗化的音樂崇尚情感的自由抒發與體驗,浪漫派時期是音樂抒情性發展的高峰。音樂理論家麗莎說:“在(音樂的)欣賞過程中,邏輯因素讓位于感情因素,居于次要地位。”[8]
音樂的音響形態以其特有的高高低低、快快慢慢、長長短短、強強弱弱、虛虛實實的運動形式傳達出不同的聲波,這些聲波傳遞被人的聽覺感知,引發聽者情緒(emotion)的變化。通過情緒,聲波喚起(引發)欣賞者對已有生活經驗的回憶,引發聯想、想象,從而獲得不同的審美體驗,產生情感(feeling)共鳴。情感是人類的高級心理活動,非常復雜,個性化的差異也很大。“情感主要由感覺、感情、激情以及情緒構成”。[9]人類的情感是一種高級、復雜的心理活動,情感豐富多彩、深邃微妙、無邊無際、神秘多變,甚至連自己都無法完全弄清楚自己的精神世界。縱然是無比高超的詩人、作家,誰又能絕對準確地把人類的復雜的情感表達得清清楚楚呢?語言的盡頭,即是音樂的開始。音樂的不確定性恰巧與人類的情感世界有冥冥之中的吻合。所以,音樂最擅長抒發各種情感。古今中外,抒情性的作品是音樂主要領域。音樂如何抒情呢?作曲可以通過音樂的藝術手段,表達自己的創作意圖,同時給欣賞者以引導,常見音響特點與心理反應模式有以下五種。
(一)暗示
暗示是一種思維方式,以不易覺察的手段對別人的心理活動或行為施加影響,使其自發地施授者的意愿思考或行動。音樂中的和聲、旋律線、節奏、速度等要素也都具有一定的色彩性,比如大三和弦明亮,小三和弦暗淡;大調式開闊明朗,小調式柔和暗淡;不同的音色、調式、音量具有不同的明暗、結構和飽和度等特性,暗示冷暖、善惡等不同心理活動。拉弦類樂器二胡、提琴擅長暗示惆悵、優美,而顆粒型比較強的樂器如琵琶、揚琴等則更擅長暗示輕松、歡快。軍隊進行曲多選用大調式,以暗示戰斗精神;人在憂傷、煩惱的時候常常更樂于接近暗淡的色彩,所以表現憂傷、悲痛的音樂常常選用小調式或下行旋律線、不協和音程、緩慢的節奏,等等。
小提協奏琴曲《梁祝》的“愛情主題”,四個樂句具有典型的起承轉合的性質,具有中國特色,暗示故事發生在中國;旋律素材取自越劇,進一步暗示故事發生在中國的南方;小提琴是最接近人聲尤其是女性音色的樂器,暗示故事的主人公是優雅的女性。小提琴流暢的技法拉出婉轉優美的旋律,展現飽滿、圓潤的音色,給人溫暖、美好的感覺,暗示愛情主題。這些瞬間完成的音符、音色不斷暗示,引發聽者美好的情緒感覺,進而結合已有社會經驗引起歌者情感共鳴。當然多數情況下,暗示是復合音樂技能與編排的效果。
(二)轉換
轉換是把聽覺的信息轉化為視覺、膚覺、嗅覺、味覺等感覺形式,進而產生情感共鳴。比如穆索爾斯基《圖畫展覽會》中的《兩個猶太人》,通過兩段對比性音樂塑造一胖一瘦、一富一窮兩個形象。富人的形象是緩慢平穩的旋律,比較低的音區,比較強的音量,加上銅管組的重量感音色,使人聯想到富人的肥胖身軀、沉重的步幅和優越的心態;窮人的形象是弦樂的一串高音區的斷奏,中弱,旋律性不強,刻畫了寒冷中的窮人瑟瑟發冷,聽賞時,細碎的音符轉換為一種寒冷的膚感,形象生動。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楊子榮“甘灑熱血寫春秋”唱一段前奏的交響樂,常見的狂風乍起,加上畫面的程式化表演,讓人感到皮膚的寒冷。
聽覺轉化為視覺的情況比多,較典型的是音樂形象鮮明、反復多的作品。比如《彼得與狼》里的形象與不同的樂器和旋律對應,聽賞時很容易轉換為視覺形象。另外,在一些影視劇的音樂中,也賦予了音樂視覺形象的功能。比如電視劇《渴望》中多次出現《梁祝》的片段,每次都與是王亞茹與羅剛的情感糾葛有關。《梁祝》響起,勾起觀眾對二人戀愛形象的回憶。轉換在視聽藝術中結合直觀的畫面,更為顯著,比如:《舌尖上的中國》,隔著熒屏,音樂與美食、故事同時出現,勾起觀眾甜、酸、香、辣等味覺體驗的聯想。
(三)替代
替代有兩個層面:一是指以音聲替代語言的表達;二是以音聲替代情感。生活中,除了音樂,語言也是豐富、有序的聲音。作為符號的語言有兩種功能:一種是表義性,主要傳遞語言信息,另一種是表現性,用來造型,傳遞感性的信息。表義性的語言特點是概念、邏輯、規范,能夠精準表達信息、思想。表現性的語言指文學藝術(小說、詩歌等)。文學藝術的符號雖然也是文字,但其更追求表達情感和思想內涵,是感性信息。音樂與文學性(有聲)語言的區別在于,在音域、音階、節奏等方面音樂突破了語言的界限,在更為廣闊音響領域表現情感。換言之,音樂表達情感較之語言更為細膩、更為豐富。語言概括表達了生活的現象、情感,音樂替代語言可以更為深刻的表達情感,即語言的盡頭,就是音樂的開始。
替代在歌曲中,常常表現在拖腔,“啊”“呀”“啦”“哎”等虛詞,沒有實在的意思但往往是歌曲的高潮,可以表達豐富細膩的情感。比如歌曲《我愛你中國》在結束句“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獻給你,我的母親,我的祖國”前,是兩個氣息悠長的樂句,歌詞是嘆詞“啊”。這里,通過前面的鋪墊,音樂推向高潮,用“啊”句替代表達最真摯深厚的感情,內涵深刻豐富,與實詞部分虛實相生,相得益彰。
音樂是表情的藝術,以音聲替代情感是音樂的表達和音樂的審美共同遵循的原則。“音樂藝術是一種替代:有關對象的極其細微的意象的替代,亦即,有關對象的在場在目睹者心靈中激發的情感替代。”[10]
(四)夸張
夸張是藝術的法則,比如詩歌里的“白發三千丈”,影視劇里的特技,寫意的雕塑,等等,通過夸張令人思想、視覺受到沖擊,獲得豐富的聯想和美的享受。夸張也是音樂進行抒情的重要手段。音樂的夸張在音色、力度、旋律、表演等多方面表現。比如戲曲里的哭腔,民族器樂中的大滑音,嗩吶曲《百鳥朝鳳》里各種鳥類鳴叫聲,是夸張的模仿生活中的音調,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形成民族音樂的一些特色。交響樂《野蜂飛舞》中用半音和快速進行的樂句模仿成群的蜜蜂飛舞,形象很生動,但這些音響也并非自然界音響的復制,而是通過了藝術化的處理,突出某些音樂特性,進一步夸張處理。歌曲里的夸張常常表現在襯詞襯腔處。比如山東民歌《包楞調》,一長串的“包楞楞楞楞”,歡快的旋律,夸張的樂句長度和速度,雖沒有具體的概念和敘述,但歡樂爽快的情感淋漓盡致表現出來。
(五)簡化
簡化就是將無關緊要的細節轉變成有意味的形式,簡化即高層次的概括。音樂是最為凝練和簡潔的藝術形式,通過簡化,更為集中地表達感情、表現思想,更具審美價值。比如中國的琵琶名曲《十面埋伏》,只是一部十分鐘左右的器樂曲,而它展現的卻是歷史上著名的楚漢之戰,如果不是高度的簡化,一只小小的琵琶怎么能形象地表現出千軍萬馬的征戰呢?無獨有偶,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是一首單樂章交響曲,音樂形象呈現了1812年俄國的庫圖佐夫帶領俄國人民擊退拿破侖大軍的入侵,贏得了俄法戰爭的勝利后的凱旋。音樂作品不能夠準確表達敵軍多少人,將領身高幾許,指揮時怎么想的,怎么說的,用了哪些武器,各用了多少等,這些是音樂所不擅長的。作品巧妙地用音樂呈現了戰爭的幾個重要階段,概括而濃重塑造了俄軍的矯健和戰爭激烈以及勝利后的歡慶的音樂形象。對于欣賞者而言,能夠直接感受到的是戰爭激烈的氣氛、歡慶的情緒和作曲家對于俄軍勝利的由衷褒揚。《梁祝》中,封建家長勢力的形象表現是用較低的音域、下行的進行、銅管樂器組的合奏,較強的音量等技術手段,高度概括了封建家長強勢、腐朽的藝術形象。
四、音樂的黏合性來自音樂的時空性
眾所周知,音樂是時間的藝術,音樂作品是在時間中按順序依次出現,每個音出現之后就消失了,欣賞只能按順序傾聽;在有電場域之前,音樂不能完全重復或逆向傾聽。音樂也是空間的藝術嗎?答案是明確的:是。音樂的空間有兩層內涵: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
(一)音樂的物理空間
音樂的物理空間包含兩個層面:一是音樂音響的空間,由直接傳到耳朵的聲音和通過墻體等物體反射到耳朵的聲音產生的立體空間感;二是音樂表演的場所和傳播的路程,即傳播空間,音樂聲波在空間或電介質傳播,其空間存在但不容易界定,具有不確定的。傳播空間最常見的規律即音樂在不同的空間傳送會產生不同的聲音色彩,而歷史上不同的空間格局又孕育出不同的音樂風格。古羅馬圓形劇場的橢圓形空間,歌手和樂隊都不借助任何擴音設備,卻能將聲音傳送到每一個角落,聲音非常好聽。離開這一劇場,這種聲音效果完全不會有。再如室內樂特指規模不大的聲器樂合唱(合奏),最早起源于歐洲上流社會的家庭音樂會。因此,在藝術品格上,室內樂追求抒情、高雅、不溫不火,這與歌劇院上演的歌劇和音樂廳表演的協奏曲有很大的區別,形成了獨有的曲目、技術和格調。音樂的時間空間性使音樂具有了時空轉換的功能。影視劇和電視欄目中,音樂一方面渲染了氣氛,塑造了藝術形象,烘托了情節;一方面也能夠起到切割畫面,分割板塊的作用。
(二)音樂的心理空間
音樂的心理空間指音樂的表演和音樂的審美時,音樂引發的超越曲譜符號的想象、聯想的空間,這是一個沒有疆界的空間。對于音樂表演者,音樂的想象能夠幫助表演者完成音樂技巧,又不受到技巧的束縛,按照個人對音樂的解讀塑造音樂形象,對于音樂審美者,心理空間是指音樂給受眾制造了一個聽覺的空間,受眾有更多的自由,憑借思緒和經驗,自由想象、聯想、理解。當然,聯想和想象是以音樂的音響和個人經驗為基礎和中介的,因此因人而異。
結 語
音樂的黏合性來自它的有聲性、不確定性、抒情性、時空性。音樂的實踐滿足了欣賞者審美與實用的需要,音樂的黏性使得音樂成為活躍的要素,與眾多藝術門類走向融合和創新。甚至,音樂能夠滲透藝術以外的領域,為生活添精彩。可以預見,由于音樂藝術的黏合性,在日新月異的新媒體時代,音樂的可開發、可利用、可創新的領域還有很多。新的科學技術與古老而又年輕的音樂藝術的結合是音樂藝術發展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