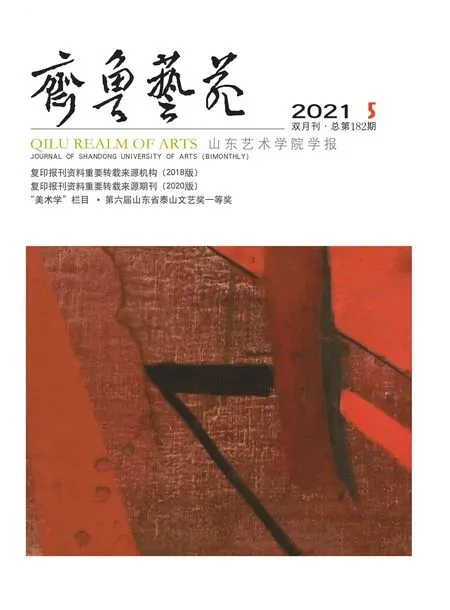生命共同體理念下的生態(tài)話語呈現(xiàn)與城市意象建構
——以紀錄片《我們的動物鄰居》為例
劉夢迪,牛光夏
(山東藝術學院傳媒學院,山東 濟南 250330)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這一論斷,并進一步強調(diào)“我們要建設的現(xiàn)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1]。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共同體理念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內(nèi)涵一脈相承,它“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尋求永續(xù)發(fā)展之路”[2],同時又批判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統(tǒng)一的價值理念。“突破了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tài)中心主義兩種傳統(tǒng)生態(tài)價值觀的根本對立,實現(xiàn)了與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有機統(tǒng)一”[3](P103-110)。生命共同體理念體現(xiàn)了生態(tài)思想的整體觀。“在頂層設計的介入下,中國生態(tài)文明建設力度空前,生態(tài)文明話語的建構與傳播成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話語體系的重要內(nèi)涵之一”[4](P81-85)。紀實影像作為最有效力的傳播媒介,成為生態(tài)理念抵達現(xiàn)實的重要載體。紀錄片《我們的動物鄰居》(2019)是由北京五星傳奇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央視紀錄頻道播出的4集自然紀錄片,影片以“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為核心敘事話語,聚焦于北京這一都市空間中的動物,通過生態(tài)理念與生態(tài)反思的雙重呈現(xiàn),傳達一種人與動物、與大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理念,激發(fā)民眾的生態(tài)環(huán)保意識與生態(tài)實踐者的身份認同。也通過一個個“人與動物”共生共存的故事與細節(jié),建構了“生態(tài)北京”“文明北京”的城市意象,是宣揚生態(tài)理念的影視作品中獨具特色的一部。
一、生命共同體理念的紀實影像傳播
紀錄片《我們的動物鄰居》集“生命共同體”理念、北京城市文化于一體,拋棄片面強調(diào)人與自然對立的人類中心主義視角,以獨特的敘事主體和敘事空間,展開個性化的“命運共同體”故事講述。
(一)從動物出發(fā)的人文情懷表達
在中國紀錄片發(fā)展曲線蜿蜒的時空流轉中,人作為主體呈現(xiàn),是一個逐漸被重視、人文化色彩漸次豐盈的過程——從最初“人文化”時期,依托于宏大民族精神而被忽視的個人意識;到“平民化”時期,個人生存狀態(tài)成為主題表征;再到“社會化”紀錄片時期,“轉向把人置于事件當中、把背景因素放大的新的敘述結構”[5](P151)。這種個人主體意識的凸顯,也影響了自然類紀錄片的命題顯影,沿著更為注重從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路不斷探索,傳達切實的人文關懷與生態(tài)理念。從最初人類全知視角的主觀闡釋,到人對環(huán)境影響的哲思,再到命運共同體的故事講述,“這種變化既是‘人類中心主義’不斷消散的過程,也是人類對‘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不斷加深理解的過程”[6](P95-102)。20世紀80年代,《話說長江》(1983)、《話說運河》(1986)、《黃河》(1987)等自然類紀錄片,所承載的更多是科普與教化功能,以黃河、長江等自然母體為對象彰顯民族精神,從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來審視自然。“社會化”紀錄片時期的《英與白》(1999)、《野馬之死》(2000)等許多關注人與動物關系的紀錄片,開始體現(xiàn)人與自然關系的哲思。2007年《森林之歌》的出現(xiàn),開啟了中國自然類紀錄片創(chuàng)作的新時期,片中對于森林與人類和諧共生的展現(xiàn),具有濃厚的生態(tài)主義色彩。此后中國自然紀錄片開始呈現(xiàn)出多元化發(fā)展趨勢。圍繞生態(tài)文明建設之國策,中國自然類紀錄片創(chuàng)作,重在展現(xiàn)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tài)主題,通過微觀個體的故事,傳遞人文關懷與生態(tài)環(huán)保意識,涌現(xiàn)了《我們誕生在中國》(2016)、《重返森林》(2017)等一批優(yōu)秀紀錄片。《我們的動物鄰居》對人與動物關系的探索、生態(tài)文明話語的建構,更是抵達了新的高度。
紀錄片《我們的動物鄰居》是首部以北京市為背景的動物自然類紀錄片,同時,這也是一部以北京市的野生動物為主角的紀錄片——這次擔當主角的動物大約有50種。北京,這座容納了上千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同時也是眾多野生動物的家園。影片以北京這座城市中的野生動物為觀照對象,改變了以往“人類中心主義”的自然類紀錄片敘事母題,也非片面強調(diào)自然至上的“自然中心主義”呈現(xiàn),而是從整體生態(tài)觀出發(fā),通過人格化的動物,來表現(xiàn)具有獨特氣質(zhì)的“自然北京”,傳達北京這座城市特殊的生態(tài)理念與人文價值觀念。并且注重人類與動物在同一城市空間下是如何發(fā)生關聯(lián),互相介入,互相影響的。人與動物都不再是獨立存在的個體,人與動物的“命運共同體”,成為了新的價值建構。片中講述了北京市民曲喜圣建造野鴨群島及西單胡同的居民幫助家燕搬家的故事,揭示了雨燕與古建筑之間的現(xiàn)實矛盾。影片在人與動物“命運共同體”的話語講述中,展現(xiàn)了二者休戚與共的依存關系,傳達出人文與生態(tài)并重的價值觀念,對于當代城市建設目標與方向的確立,具有重要的指導與引領意義。
(二)非奇觀化的共情敘事
“奇觀是非同一般的具有強烈視覺吸引力的影像和畫面,或是高科技電影手段創(chuàng)造出來的奇幻影像和畫面及其所產(chǎn)生的獨特視覺相關。”[7](P256)紀錄電影自誕生之初便與“奇觀”建立了聯(lián)系,弗拉哈迪《北方的納努克》(1922)中,獵捕海象的鏡頭留下了紀錄電影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契合于湯姆·甘寧對于“吸引力電影”本質(zhì)的論述,“吸引力直接訴諸觀眾的注意力,激起視覺上的好奇心,通過令人興奮的奇觀提供快感”[8](P17-22)。奇觀影像的展現(xiàn),也在自然類紀錄片中,得到了延續(xù)與發(fā)展。中國自然類紀錄片對奇觀的呈現(xiàn),起始于《再次攀登上珠穆朗瑪峰》(1975),此后其發(fā)展便一直延續(xù)著類似的模式。自然類紀錄片的奇觀,來源于對人類“未至之境”的影像呈現(xiàn),同時著重關注瀕危野生動植物的真實記錄。《森林之歌》開啟了中國的商業(yè)化自然類紀錄片之路,“借助擬人化的手法建立起動物奇觀與人類社會的鏡像聯(lián)系”[9](P95-102),成為此后該類作品的重要創(chuàng)作方法。《美麗中國》(2008),涉足沙漠戈壁、積雪高原;《秘境中國——天坑》(2013),探秘“天坑”地質(zhì)奇觀;《航拍中國》(2017)系列紀錄片,以獨特的空中視角拍攝中國,展示美麗神州、生態(tài)華夏。《蔚藍之境》(2020),則將空間延伸,全面、系統(tǒng)地拍攝海洋故事。《第三極》(2015),將人們的視線,引向青藏高原,展現(xiàn)這片神奇的沃土,看對于人類而言極度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如何經(jīng)由信仰,達到某種哲學意義上的生態(tài)平衡與和諧共生。此類紀錄片充分利用奇觀化的陌生空間,來傳達自然生態(tài)理念。
紀錄片《我們的動物鄰居》,規(guī)避了以往自然類紀錄片陌生空間奇觀化敘事手法,將鏡頭聚焦到北京這座現(xiàn)代化、人文性極強的都市之上,極具空間接近性與熟悉感,再現(xiàn)“頭腦里的盲點”,呈現(xiàn)熟悉的陌生化。它選取了鬧市、園林、古城、郊野四個空間,從北京的商務中心區(qū)CBD到城外郊野,作品為我們呈現(xiàn)了城市中不為人知的動物世界。摩肩接踵的鬧市,人造景觀極多,同時也是刺猬和紅隼的居住地;擁有百年植被的天壇,是許多鳥類的家園;長城腳下的荒野——康西草原,是貓頭鷹的聚居地。頤和園、西單胡同、法源寺、十渡景區(qū)、南海子園林等地,無論是人們熟悉的空間,還是容易被忽視的角落,都存在著動物的身影。城市中的動物族群與人類有著相似的生命歷程,像許多在北京為生活而打拼的“北漂一族”一般,片中談到的鳥類——紅隼,也需要為生存而奮斗,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倔強,才能在北京謀得一席之地。鳳頭鷉的幼鳥出生一周后,便要脫離父母的懷抱。在北京,居鬧市不易,對動物與人類來說都是如此。在如此這般的共情敘事中,動物被賦予與人相類似的命運,彼此重合的生命軌跡,交織在北京這座城市中。從動物的視角切入北京,以非奇觀化的共情敘事,完成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敘說的話語建構。
二、生態(tài)城市的意象建構
紀錄片《我們的動物鄰居》,從動物視角展現(xiàn)了北京的城市風貌,也通過人與動物的共同體故事講述,構建了“生態(tài)北京”“文明北京”的城市意象。影片從“環(huán)境意象”與“人文意象”角度,對北京“城市意象”進行了闡釋,展現(xiàn)了北京居民與野生動物和諧共處的環(huán)境風貌,傳達了全民生態(tài)理念提升的人文價值觀念,從而展示出首都業(yè)已形成的獨具特色的生態(tài)文明發(fā)展體系,以及能夠滿足市民生態(tài)愿景的自然環(huán)境,由此建構了北京的生態(tài)城市意象。
(一)城市意象與生態(tài)城市意象
美國城市研究學者凱文·林奇在其《城市意象》一書中,從城市設計學角度對“城市意象”的相關概念做了闡釋分析。“似乎任何一個城市,都存在一個由許多人的意象復合而成的公眾意象”。[10](P35)城市意象是多個公眾意象的復合體,是人們認識城市、解讀城市的結果。在談到城市意象的構成時,凱文·林奇從物質(zhì)結構角度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城市意象由道路、邊界、區(qū)域、節(jié)點、標志物五個要素構成。城市內(nèi)部的人文內(nèi)涵與文化底蘊,則內(nèi)化為一種抽象的符號存在。結合凱文·林奇對“城市意象”相關概念的闡釋,我們可以進行再定義,即是在一定文化背景與價值體系下的發(fā)展規(guī)劃,能夠滿足人們生理、心理需求的物質(zhì)環(huán)境,以及從中所體現(xiàn)出的城市內(nèi)涵與文化意蘊。
城市意象的形成與傳播,受多種因素影響,除了作為公眾個體的內(nèi)部因素之外,外部因素也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紀實影像作為一種直接來自于現(xiàn)實世界的媒介形態(tài),對城市意象的生產(chǎn)與傳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影像中的城市,不僅僅包含自然風光、環(huán)境空間等外在物質(zhì)形態(tài),它更多承載的是城市的社會形態(tài)與文化內(nèi)涵,可以記錄下過去和現(xiàn)在人們對其生存的城市空間的認識,可以見證這座城市的發(fā)展過程。北京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都城,同時也是面向世界的國家形象中心,《北京的星期天》(1956)、《流浪北京》(1990)、《北京記憶》(2011)、《五百元的幸福》(2019)等關于北京的紀實影像,就從不同層面,塑造和建構了不同時期北京的城市意象。
在生態(tài)文明建設這一宏觀背景下,生態(tài)城市建設也應運而生。生態(tài)城市意象,即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價值體系的一系列城市發(fā)展規(guī)劃,能夠滿足人們生態(tài)城市愿景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環(huán)境,以及從中所體現(xiàn)出的城市內(nèi)在的生態(tài)文化意蘊。生態(tài)城市意象是以生態(tài)意識與生態(tài)理念來觀照城市、感知城市、解讀城市的結果,也是生態(tài)文明觀加持下,媒介對城市形象的生動反映。
(二)《我們的動物鄰居》中城市意象的表達
紀錄片《我們的動物鄰居》,從“環(huán)境意象”和“人文意象”兩個層面,建構了北京當下獨特的生態(tài)城市意象,用真實的視聽影像、故事化的敘事方式,記錄了北京以“天藍、水清、森林環(huán)繞”,建城市森林,創(chuàng)森林城市為目標的生態(tài)城市建設歷程,而其在當下大力推進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背景下,已初見成效。
從城市意象的構成因素來說,“環(huán)境意象”即城市意象中最直接可觀的部分,包括城市的自然風貌、建筑構造等物質(zhì)環(huán)境部分,它們共同構成了整個城市的空間環(huán)境。紀錄片《我們的動物鄰居》,從空間環(huán)境、標志性景觀、自然風貌等多個方面,對北京的環(huán)境意象做了最為直觀的呈現(xiàn)。作品選取了北京的鬧市、古城以及郊野等幾個具有代表性的環(huán)境空間。從極具工業(yè)性的中心CBD,到充盈自然性的城外郊野,空間轉換之間,北京的環(huán)境意象,也自然呈現(xiàn)出來。鬧市,是城市中最具工業(yè)性和城市感的環(huán)境意象。鼓樓、故宮、角樓,都是極具“京城”特色的古建筑,“景觀也充當著一種社會角色,充當著一個巨大的記憶系統(tǒng)”[11](P95)。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古建筑,承載著古老而又極具魅力的老北京記憶,它們是北京乃至中華文明的見證,構建出北京歷史悠久的環(huán)境意象。郊野,位于城市的邊緣,是彰顯自然之感的環(huán)境意象。位于市郊的十渡鎮(zhèn),有著北方罕見的喀斯特地貌,是珍稀動物黑鸛的居住地。野鴨湖自然保護區(qū)是北京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濕地,在此居住著兩百多種鳥類,呈現(xiàn)出渾然天成的環(huán)境意象。《我們的動物鄰居》,通過影像呈現(xiàn)了北京這座城市的環(huán)境意象,鬧市、古城、郊野,人類與動物生存在同一空間。高樓林立的都市意象與獨具魅力的古城意象相互碰撞,野性的自然融入城市的縫隙,現(xiàn)代的北京、歷史的北京、野性的北京,共同構成了獨具特色的北京城市意象。
“人文意象”即城市意象內(nèi)部抽象的存在,人文意象的呈現(xiàn),能夠使人們感受到城市的地域風格、人文風情與文化底蘊,能夠在人們心中,構建起獨特的城市人文意象。紀錄片《我們的動物鄰居》,通過對北京民眾日常生活的描述,展現(xiàn)了“生命共同體”背景下,北京對生態(tài)城市建設的探索與實踐,構造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人文意象。紀錄片《我們的動物鄰居》中,對城市人文意象的呈現(xiàn),大致可以分為“公眾組織”與“居民個體”兩部分,二者共同參與人與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促進了生態(tài)道德倫理的建構傳播,以鮮活影像實現(xiàn)了生態(tài)責任的具象外化。公眾組織作為城市公眾形象的代表,體現(xiàn)了地方政府對于共同體理念構建的身體力行。該片記錄了北京多個動物保護組織的行動,例如正陽門管理部門致力于對雨燕的觀測記錄工作,試圖找尋一條古建筑維護與動物保護雙贏的道路。片中還記錄了位于北京市的全國唯一一家猛禽醫(yī)院,如何通過切實的運作,給予城市中野生動物更多生存機會的細節(jié)。野生動物保護組織是動物在城市中的避風港,同時也是共同體理念下的人類生態(tài)意識的實踐載體。民眾是城市生活的主體,紀錄片《我們的動物鄰居》,用平民化視角來拍攝普通民眾的生態(tài)實踐行動。大學退休教師高武和趙欣如,多年來一直堅持對頤和園廓如亭雨燕的環(huán)志工作;青少年科技館的自然教師岳穎,帶領孩子們認識學習長耳鸮;中學生李耳自制樹洞巢穴,保護野生鴛鴦等等。通過這一個個人與動物“命運交織”的有趣故事,《我們的動物鄰居》呈現(xiàn)了北京市民對于“人與動物是生命共同體”理念的切實踐行,構建了全民生態(tài)理念提升的城市人文意象。
三、生態(tài)城市意象的建構價值與紀實影像的傳播效應
生態(tài)城市意象的建構,通過生態(tài)理念的傳達及生態(tài)理想的呈現(xiàn),重塑觀者的文化觀念,促進生態(tài)實踐者的身份認同,最終達到二者對于生態(tài)主義的價值認可。生態(tài)紀實影像在建構生態(tài)城市意象的同時,通過社會生態(tài)問題的呈現(xiàn),引發(fā)觀者的生態(tài)反思,激起人們的生態(tài)責任意識。
(一)生態(tài)理念重塑文化認同
情景國際主義創(chuàng)始人居伊·德波在《景觀社會》一書中曾經(jīng)指出,“在現(xiàn)代生產(chǎn)條件占統(tǒng)治地位的各個社會中,整個社會生活表現(xiàn)為一種巨大的景觀的積聚。直接經(jīng)歷過的一切都已經(jīng)離我們而去,成為一種表現(xiàn)”[12](P3)。居伊·德波的論述,揭示了現(xiàn)代社會象征符號消費的實質(zhì):“消費社會本質(zhì)上是一個景象社會,商品即景象(Spectacle,形象、影像、奇觀)”[13](P120),在這樣的文化中,人們趨向于從景觀的外在符號價值中,尋找身份認同與欲望滿足。影像的視覺特性,使其成為消費社會的代表性景觀符號,“消費社會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視覺消費的社會,是符號的視覺化和視覺意義交換的復雜語境。”[14](P110)生態(tài)城市意象的建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對于消費社會的反叛與對抗,具有重塑社會主流話語的巨大價值,“促使生態(tài)環(huán)保理念和意識成為當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15](P57-60),并且促成觀者對生態(tài)理念的認可,建立生態(tài)實踐者的身份認同。紀錄片《我們的動物鄰居》通過頤和園、鼓樓、南海子、天壇等多處頗具代表性的環(huán)境意象,為觀者呈現(xiàn)了自然與歷史建筑等文化符號相融的生態(tài)理想與城市文化意蘊。自然野性的北京與歷史人文的北京,彌合于意蘊之中,南海子麋鹿、故宮角樓雨燕、法源寺家貓、頤和園松鼠、天壇長耳鸮,這些承載著北京歷史文化的景觀意象的生成,從未遠離自然的力量。歷史與自然的碰撞與交融,也由此豐富了北京文化的內(nèi)涵,呈現(xiàn)了自然與歷史交匯的生態(tài)理想,加強觀者的文化認同。其次,《我們的動物鄰居》通過人文意象的建構,傳達出北京居民熱愛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tài)文化理念,展示了他們更為直接的公眾生態(tài)實踐行動。“鄰居”一詞,在這部紀錄片中,已經(jīng)超越了人類文化在傳統(tǒng)意義上所具有的自身局限性,紅隼、家燕、烏鴉、刺猬、蜜蜂等等都是人類的鄰居,它們與人類是相互獨立而又平等互助的存在。紅隼筑巢于人類的屋檐之下,綠頭鴨因為人類的幫助而留在了什剎海,拒馬河的黑鸛也因人類的投喂度過了寒冬。作為同一城市的鄰居朋友,人類也接受著動物們的饋贈,養(yǎng)蜂人把蜜蜂帶到果園代替人工授粉,甘甜的瓜果數(shù)月后便會豐富人們的餐桌。人類從未遠離自然,只是未曾發(fā)現(xiàn);自然也未曾“拋下”人類,一直虛左以待。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tài)文化理念,豐富了北京的城市文化內(nèi)涵。生態(tài)城市意象的建構,體現(xiàn)著北京這座城市繼承傳統(tǒng)、與時俱新的文化發(fā)展追求,傳遞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tài)理念,展示了城市個體的生態(tài)實踐,成為中國現(xiàn)代化都市向生態(tài)文明城市轉型和發(fā)展的文化典范,能夠有力促進公眾對生態(tài)理念的認可與生態(tài)實踐者的身份認同。
(二)生態(tài)反思喚醒責任意識
美國紀錄片研究學者尼科爾斯認為,“紀錄電影不僅激活我們的審美意識,而且也激活我們的社會意識”[16](P104)。紀錄片《我們的動物鄰居》,在對北京這座城市的環(huán)境、人文意象進行呈現(xiàn)的同時,也揭示了許多現(xiàn)實中存在的生態(tài)問題。由于“媒介的放大效應和議程設置功能能夠促使生態(tài)環(huán)境得到更多關注”[17](P57-60),從而引起觀者反思,可以喚醒公眾的生態(tài)道德感與責任感。人類對于自然過多地干預,破壞了生態(tài)平衡,過度地開發(fā)利用,導致生物資源短缺,城市的發(fā)展改造,導致動物棲息地喪失,而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狀況惡化,又直接影響著人類的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我們的動物鄰居》對此類生態(tài)問題進行了具象化呈現(xiàn),如北京法源寺的流浪貓,雖受僧人善待,卻也逃脫不了疾病的傷害,人類的拋棄,導致流浪貓數(shù)量增多,流浪貓捕食鳥類,導致鳥類數(shù)量減少,人類的不當行為,影響到了整個生態(tài)環(huán)境,或許減少拋棄,領養(yǎng)代替買賣,才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人們的過度捕撈,導致北京房山區(qū)拒馬河的魚類大量減少,黑鸛因此失去食物來源,只能靠人類的補給度過寒冬。螳螂因為人類的行為,被迫從鄉(xiāng)村來到城市,投身于這個不適宜自身居住的復雜環(huán)境。作品所呈現(xiàn)的生態(tài)問題,揭示了人類的行為在無形之中,對自然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以此警醒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只有尊重客觀規(guī)律,自然才會善待我們。探索實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價值,是紀錄作品所傳遞的現(xiàn)實意義。習近平生態(tài)文明思想,將“人民性”確立為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的價值取向,生態(tài)城市意象的建構,恰是對這種觀念的順應與踐行。“滿足人民群眾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需要、保障人民群眾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權利、發(fā)動人民群眾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行動、保障人民群眾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共享,是人民性價值取向的要求和體現(xiàn)”[18](P68-75,196)。生態(tài)城市意象,即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價值體系的城市發(fā)展規(guī)劃的產(chǎn)物,觀者能夠從中一窺滿足人們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生態(tài)城市愿景,以及城市空間獨有的生態(tài)文化意蘊。作品中所呈現(xiàn)的生態(tài)城市意象,亦是社會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的實踐成果。
結語
紀錄片《我們的動物鄰居》,以“生命共同體”理念為核心,展開“命運共同體”故事的講述,雖只聚焦于北京這座城市,卻以小見大地展開對人與自然如何和諧相處的更大社會議題的探索。而北京作為一座凝聚千百年時光之韻的歷史名城,在文化生產(chǎn)與價值傳播層面,本就具有鮮明的特色和引領性,該片將人與動物這一關系納入敘事,更加有利于“生態(tài)北京”“文明北京”這一城市意象的建構,突顯了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以及北京作為首善之區(qū)所應有的社會責任與人文素養(yǎng)。[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