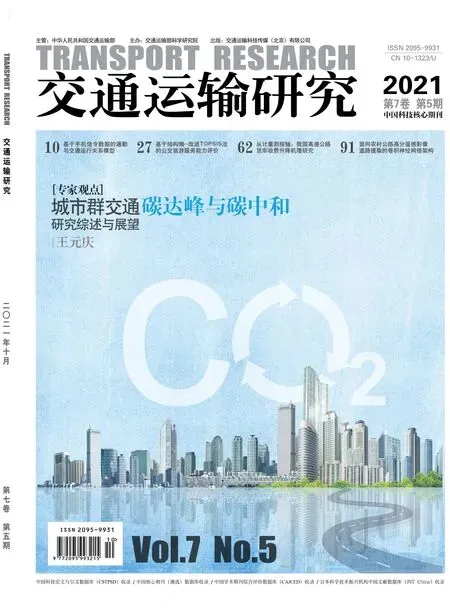交通可達性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度分析
——以四川省為例
吳宜耽,孫 宏,張培文
(1.中國民用航空飛行學院機場工程與運輸管理學院,四川 廣漢 618307;2.中國民用航空飛行學院飛行技術與飛行安全科研基地,四川 廣漢 618307)
0 引言
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兩個系統,良好的交通運輸系統能提升運輸效率并降低運輸成本,隨之產生的聚集效應和擴散效應會促進區域內產業發展,提升區域整體經濟水平,區域經濟水平的提高又會反作用于交通系統,推動其建設發展[1]。研究地區交通與區域經濟的作用關系,有助于改善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滿足新時代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需要。
部分學者利用交通可達性指標討論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之間的關系[2-5]。交通可達性是指經過一定的交通系統從一個節點到達另一個節點的空間位移能力,是各區域進行經濟交流的基礎和保障[6]。國內學者通常采用兩種方法建立可達性模型,一種基于空間阻隔模型、空間相互作用模型計算可達性,部分學者用最短旅行時間矩陣建立城市的可達性模型[2-5]。姚一民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改進,以目標城市的經濟規模為權重,建立加權平均旅行時間模型[7]。另一種通過對交通基礎設施水平量化或賦值評分建立可達性模型[8-9],但綜合考慮兩種模型的研究較少,單一模型不足以全面反映地區交通可達性。國外學者通常基于旅行費用和引力模型建立可達性模型[10-11],在此基礎上,Benenson[12]、Caschili[13]等人進一步考慮了城市間的高鐵班次,在傳統引力模型的基礎上加入了高鐵班次吸引力系數。研究視角方面,國內外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公路可達性和鐵路可達性,忽略了航空運輸對于地區可達性的影響。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大多數研究只分析了公路可達性或鐵路可達性,而交通系統是一個整體,應綜合考慮地區的所有主要交通方式;第二,現有研究較少綜合考慮空間阻隔模型與交通基礎設施水平;第三,關于實證分析的研究少有提出具體的解決措施和規劃建議。
鑒于此,本文以四川省18個地級市為研究對象,綜合考慮公路、鐵路、航空運輸方式,結合最短旅行時間矩陣與交通基礎設施水平構建可達性模型,以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產業增加值構建經濟規模指數模型,將交通可達性與經濟發展水平進行量化測算。在此基礎上,利用耦合協調模型對四川省18個地級市的交通可達性和經濟規模指數進行耦合協調度分析,并根據分析結果提出對四川省未來交通與經濟發展的規劃建議。
1 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域概況
四川省地處中國西部,地域遼闊,人口數量龐大且資源豐富,獨特的省情使其地區資源要素分布存在很大差異。經濟建設方面,多年以來四川省一直面臨著成都市“一市獨大”的局面,2019 年成都市GDP 為17 012.65 億元,占四川省18 個地級市總和的38.5%[14]。交通建設方面,四川省仍存在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大多數城市的交通潛力沒有得到充分開發。四川省是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四川省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關系,能為改善四川省交通與經濟發展不平衡現狀提供理論支撐,同時也能為西部地區其他城市提供發展經驗。
1.2 數據來源及處理
四川省地級市的經濟數據來源于《四川統計年鑒2019》[14]及四川省統計局;火車站及機場等級分布來源于《四川交通年鑒2019》[15]及四川省交通運輸廳相關統計資料;公路旅行距離來源于《西南地區公路里程地圖冊:四川省、重慶市》[16]、《四川省交通地圖冊》[17]及“國家1∶100 萬基礎地理信息數據庫”;城市之間的鐵路旅行時間來源于“中國鐵路客戶服務中心”網站(www.12306.com);航空旅行時間來源于“攜程旅行”網站(www.ctrip.com);公路旅行時間數值為兩城市中心點之間的公路旅行距離除以規定平均車速;原始經濟數據通過SPSS 軟件進行Z-Score 標準化處理和主因子分析,得到元件評分系數矩陣,再經過正值化調整和均值標準化得到社會經濟規模指數值。
2 模型建立
2.1 經濟規模指數模型
多數學者采用城市GDP、人口等指標計算城市的經濟規模指數[7,18],考慮到單項指標過于片面,選擇三項較有代表性的經濟指標: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產業增加值作為經濟規模指數Mi的測度指標,如式(1)所示:

式(1)中:Gi為城市i的GDP(億元);Ii為城市i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元);Zi為城市i的第三產業增加值(億元);n為所研究城市個數(個);λ1,λ2,λ3分別為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產業增加值在經濟規模指數中的權重,由主成分分析法確定其具體值。
2.2 交通可達性模型
各地級市之間的對內連通程度影響物流的集疏便捷性,對外可達性影響城市對外貿易及交流的便捷性,因此影響各地級市交通可達性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為對內可達性與對外可達性[19]。
2.2.1 對內可達性模型
四川省各地級市之間的交流聯系可通過公路運輸、鐵路運輸和航空運輸實現,故以三種運輸方式中的最短旅行時間建立對內可達性模型。為消除城市地理位置對可達性的影響,強化城市經濟發展與交通可達性的聯系,將目的地城市j的社會經濟規模指數Mj作為城市之間最短旅行時間的權重,建立加權旅行時間模型,如式(2)所示:

式(2)中:Ai為城市i的最短加權旅行時間;分別為城市i通過公路運輸、鐵路運輸和航空運輸到城市j的旅行時間(h);Tij為從城市i到城市j的最短旅行時間(h),取Tij=。
設Di(in)為對內可達性,其計算模型如式(3)所示:

2.2.2 對外可達性模型
遠距離交通運輸方式主要有公路運輸、鐵路運輸、航空運輸和水路運輸。四川省水路運輸占比較小,故基于公路運輸。鐵路運輸和航空運輸分析四川省各地級市的對外可達性。城市的公路里程數可以反映公路運輸效率,利用城市的公路總里程和高速公路總里程計算公路相對評分值。交通基礎設施等級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的交通可達性,參考已有研究[8-9]并結合四川省實際情況,對機場、火車站等級進行賦值,計算航空和鐵路相對評分值,見表1。據此計算城市的航空、鐵路、公路相對評分值模型,如式(4)所示。

表1 交通設施等級劃分及賦值

對外可達性模型如式(5)所示:

式(5)中:β1,β2,β3分別為火車站、機場、公路相對評分值在對外可達性中的占比,可由專家咨詢法確定,在此取等權賦值,β1=β2=β3=0.333。
2.2.3 綜合交通可達性模型
綜合交通可達性結合了對內可達性和對外可達性,能反映城市的整體交通水平,其計算模型如式(6)所示:

式(6)中:Di為城市i的綜合可達性,其數值越大表明整體交通水平越高;θ0,θ1分別為對內可達性和對外可達性在綜合可達性中的占比,由專家咨詢法確定,在此認為對內可達性與對外可達性同樣重要,取θ0=θ1=0.5。
2.3 耦合模型
耦合指兩個及以上的系統或運動形式經過一定的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現象,可描述系統或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程度。參照相關研究并考慮本研究實際[6,21-22],利用耦合度分析城市交通可達性與經濟規模指數的交互作用,構建耦合度模型如下:

式(7)中:Ci為城市i的交通可達性與經濟規模指數的耦合度,Ci越大則Mi和Di耦合程度越高,即兩者的聯系越緊密。
由于耦合度模型只反映兩者的作用程度大小,無法反映作用水平的高低,進一步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作為耦合度模型的補充:

式(8)中:Ti為城市i的交通可達性與經濟規模指數的絕對量評價指數;ω1和ω2分別為經濟規模指數和交通可達性的重要程度,鑒于交通運輸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重要程度相當,取ω1=ω2=0.5;Oi為城市i的交通可達性與經濟規模指數的耦合協調指數,Oi值越大,則交通運輸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相互作用能力越好。
3 結果分析
3.1 四川省地級市經濟規模指數
將四川省2010—2018年的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產業增加值進行Z-Score 標準化,再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出3 個指標的元件評分系數矩陣如表2所示。

表2 元件評分系數矩陣表
將以上3個指標的評分系數值代入式(1)進行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四川省部分地級市經濟規模指數
由表3 可知,成都平原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落差較大,成都、綿陽、德陽、樂山排名前六,且成都的經濟規模指數遠高于其他地級市;眉山、遂寧、資陽排名較靠后,雅安排名僅高于巴中,經濟發展落后。川東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兩極分化嚴重,南充和達州分別排在第五和第七,經濟發展水平較好;廣元、廣安和巴中均排在后六名中。川南地區經濟發展較平均,宜賓排第四,瀘州、自貢、內江排在第八、第九、第十一,屬正常發展水平。攀西地區的攀枝花排第十,經濟發展仍有提升空間。
3.2 交通可達性
四川省18 個地級市的對內可達性Di(in)、對外可達性Di(out)、綜合可達性Di計算結果如表4 所示。分析表4 可知,可達性良好的城市經濟規模指數也較高,整體上兩者具有同步趨升一致性。但也存在個別錯位現象,如經濟規模排名第十的攀枝花可達性為18個地級市排名中倒數第二,交通建設阻礙了經濟發展,可達性排名第十的廣元經濟規模僅排名十六,經濟發展滯后于交通建設。此外,各地級市的交通可達性水平落差較大,按數值將18個地級市劃分為樞紐型城市、副樞紐型城市、交通便捷型城市、交通發展型城市、交通落后型城市、交通閉塞型城市(見表5)。

表4 四川省部分地級市交通可達性計算結果

表5 四川省部分地級市交通可達性等級劃分結果
由表5 可知,四川省18 個地級市的可達性水平參差不齊。川東北地區交通發展落差最大,有屬于副樞紐型城市的南充,也有屬于交通閉塞型城市的巴中。成都平原地區的交通發展水平落差也較大,成都屬于四川的樞紐型城市,對內可達性和對外可達性都排在第一,且數值遠高于其他城市;綿陽和德陽分別屬于副樞紐型城市和交通便捷型城市,但遂寧、眉山、資陽、雅安均屬于交通落后型城市。川南地區交通發展水平趨于平均,瀘州市和宜賓市屬于交通便捷型城市,可達性較好;內江和自貢屬于交通發展型城市,地區整體可達性水平相差不大。攀西地區的攀枝花市屬于交通閉塞型城市,可達性水平僅優于巴中,交通水平亟待改善。
3.3 耦合協調度
四川省18個地級市交通可達性與經濟規模指數的耦合度Ci、絕對量評價指數Ti和耦合協調度Oi計算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四川省部分地級市交通可達性與經濟規模指數耦合協調度計算結果
由表6 可知,四川省18 個地級市的交通可達性與經濟規模指數的耦合度都較高,即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水平有極密切的關聯性,但可達性與經濟規模指數的耦合協調度落差較大。參考已有研究[6,20-21]并根據數據特點,將耦合協調度發展階段劃分為高水平耦合協調、較高水平耦合協調、磨合階段、拮抗階段、低水平耦合協調7個階段,如表7所示。

表7 四川省部分地級市耦合協調度劃分結果
3.4 發展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對四川省各地區交通和經濟發展規劃提出如下建議。
(1)成都平原地區
成都是四川省的交通樞紐中心和經濟中心,虹吸作用顯著,但溢出效應不明顯,未來建議實施必要的功能疏解和資源外移,促使成都產生溢出效應,輻射帶動中小城市發展。綿陽的交通可達性和經濟規模僅次于成都,未來可將綿陽作為成都平原地區的副中心發展,分擔成都的城市負擔。德陽是我國重大技術裝備制造基地,未來應在保持原有優勢的基礎上繼續提升現有交通運輸業水平,滿足制造業的發展需求。對處于磨合階段的樂山,應引導交通基礎設施適應區域經濟發展,幫助其順利度過磨合期。對處于拮抗階段的遂寧、資陽、眉山,未來應加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并以政策促進其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增長。應將唯一處于低水平耦合協調階段的雅安作為重點扶持對象,完善其交通基礎建設,促使交通與經濟盡快進入良性互動。
(2)川東北地區
目前川東北地區交通可達性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度落差較大,巴中仍處于低水平耦合協調階段,應首先注重其發展需要。巴中屬于交通閉塞型城市,可達性在地級市中最差,應從改善公共交通建設水平開始,促進巴中的交通與扶貧、旅游、鄉村振興融合,推動交通建設與經濟共同發展。
(3)川南地區
對處于較高水平耦合協調階段的宜賓,應在現有基礎上穩步發展。對處于磨合階段的內江、自貢、瀘州,應加以政策引導,促使它們盡快進入較高水平耦合階段。
(4)攀西地區
攀枝花國有經濟發達,由于地形限制仍屬于交通閉塞型城市,交通嚴重阻礙了經濟發展和未來規劃進程,故未來應盡量克服地形條件限制,解決交通問題,釋放被抑制的經濟潛力。
4 結論
本文綜合考慮公路、鐵路、航空運輸方式,結合最短旅行時間矩陣與交通基礎設施水平構建可達性模型,研究了四川省18個地級市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和交通可達性及其耦合作用水平,得出以下結論:
(1)四川省地級市經濟發展水平與交通可達性分布不均衡,地區差異明顯。川東北地區與成都平原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交通建設水平兩極分化較嚴重,川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交通建設水平分布較均衡,攀西地區的攀枝花經濟處于平均水平,但交通較閉塞。
(2)四川省地級市交通可達性與經濟發展水平具有同步趨升一致性,但也存在個別錯位現象,表現為城市交通建設滯后于經濟發展或經濟發展滯后于交通建設。
(3)四川省地級市交通可達性與經濟規模的耦合協調度落差較大,地區差異顯著。成都平原地區和川東北地區耦合協調度兩極分化嚴重。川南地區整體水平較好且趨于平均,攀西地區的攀枝花市處于低水平耦合階段。
(4)解決四川省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可從交通可達性與經濟規模處于低水平耦合階段和拮抗階段的城市入手,對處于磨合階段的城市的交通與經濟發展進行適當引導。
本文以四川省18個地級市為研究對象,綜合考慮公路、鐵路、航空運輸方式,結合最短旅行時間矩陣與交通基礎設施水平構建可達性模型,彌補了現有可達性模型的不足。在此基礎上,利用耦合協調模型對四川省18個地級市的交通可達性和經濟規模指數進行耦合協調度分析,并根據分析結果提出對四川省未來交通與經濟發展的規劃建議,以期為改善四川省交通與經濟發展不平衡現狀提供理論支撐,同時也能為西部地區其他城市提供發展經驗。但本文僅研究了四川省18個地級市的交通可達性和經濟發展水平在固定時間節點上的作用水平,未考慮其時間演化關系,進一步研究中可結合多年的面板數據考慮其演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