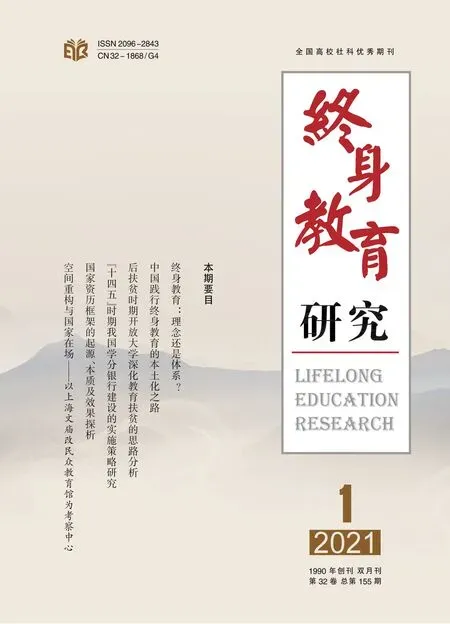空間重構與國家在場
——以上海文廟改民眾教育館為考察中心
□ 周慧梅,湯浩澤
民眾教育館作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社會教育的綜合機關,在政府行政力的強力鋪設下,數量、規模不斷擴增,文廟、貢院、關帝廟、鐘鼓樓舊址等地方公產成為其空間布局的主要憑借物。對于公共空間在民族與國家建構中的作用,學界已有廣泛認同①,對于民眾教育館借助傳統公共祠廟產生的社會功能,筆者亦進行了些許嘗試②,從社會文化史角度揭示傳統公共空間現代轉型中的教育意蘊、社會秩序與政府職責之間的博弈,探索集體儀式與國家認同的互動。張國鵬以上海文廟為中心考察了政權與信仰變革下的民國文廟的空間演變③。從學界成果看,甚少涉及文廟舊有管理者以及社會各界與政府、政府不同機構之間的博弈。有鑒于此,筆者以上海文廟改設民眾教育館為考察中心,梳理政府對文廟空間重構與意識形態的滲透輸送、民眾對傳統空間新象征意義的接受和認同的過程,分析上海市教育局與工務局如何聯手通過一整套符號與集體儀式的空間重組及儀式操演,使得傳統公共空間得以“舊貌換新顏”,分析文廟改建過程中各方權勢博弈以及空間布局的價值取向,通過文廟這一公共祠廟的現代賦形看空間重構與國家在場之間的互動。
一、社會輿論與傳統空間轉向
上海文廟始建于元代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明清兩代屢有增建修,幾經遷移,清咸豐五年(1855年)重建于海防道署遺址,建成后占地28畝,作為“廟學合一”場所,上海文廟承擔了官方祭典和府學教化的雙重功能,春丁祭孔典儀式最為社會矚目,官府要員及佾舞諸生“莫不整肅衣冠,恪恭將事。于五鼓時恭詣西門外大成殿,隨班行禮,次及兩廡先賢前,陳太牢之供,舉釋采之典。時則鼎彝悉備,管合龠具陳。舞則按部就班,樂則和聲依詠。(旁觀者甚形擁擠)莫不嘆為觀止”。[1]除去隆重莊嚴的春秋丁祭,還有新進生員“入泮”,地方長官、學憲的文廟拈香和先哲入祀等系列儀式,彰顯文廟在地方社會中的作用。民國肇基,隨著社會輿論變化,文廟作為儒學象征的傳統空間開始轉向。
1912年7月,上海文廟成為國民公會上海部的辦公地點,定期舉行講演會,向民眾宣傳共和理念,灑掃局董陸蔚臣還提出孔子誕辰日允許普通民眾進入文廟觀禮的建議[2],以便文廟適應共和政體的新政治語境,表明文廟管理者開始思考文廟在新政體的空間轉向。次年9月孔子誕辰日“在滬各團體暨各學校教習及男女學生”三千余人的規模集聚文廟,[3]禮節亦新舊雜陳。1914年丁祭日“由觀察使楊君主祭,洪知事張汪兩廳長暨崔朱賈三君為陪祭,均行三鞠躬禮,孔教會會員仍行三跪九叩禮,各學堂及紳商等次第行三鞠躬禮”[4]。民主共和理念被嵌入“以正人心,以立民極”的儒家道德教化傳統中。
1915年8月26日,江蘇省教育行政第二次會議開幕,江蘇巡按使提出各縣文廟內附設通俗教育館提案,內文稱在其內陳列普通書籍、圖報、理科衛生之模型以及圣賢遺跡、遺像等,并附設通俗講演會,“裨眾展覽,而堅信仰”,職員則由縣教育行政人員兼任,該提案獲得一致通過。[5]次年1月,江蘇巡按使公署與滬海道尹公署聯衙飭令屬地知事,對在文廟內設立通俗教育館做進一步的闡明,“竊維崇圣德而風后世,文廟之設,由來尚已。晚近以還,弦歌不作,遺澤浸衰。入夫子之門,舉凡文物章服禮器之屬,蕩然無存,即當年禮樂之堂、宮墻之地,非傾圯亦荒蕪矣”,提議按大總統頒布教育綱要中社會教育專條規定, “修而葺之,量地為用,凡所陳列之品物圖書等,悉以供公共閱覽為目的,啟智慧于群黎,即所以垂德化于無窮”[6],將文廟辟為社會教育場所,面對普通民眾開放。次日,上海縣知事將附設辦法登載于《申報》,聲稱將在該館附設通俗講演會。[7]惜經費無著,直至省署所定籌備期限屆滿無果而疾[8],但文廟改建、面向公眾開放的社會輿論已悄然埋下。
1924年5月,上海市文廟灑掃局董事王慕結提議將文廟改建成公園,對公眾開放,使儒家文化傳諸民間。此提議得到多名局董贊同,列名發起將文廟改建為“上海文廟園”議案,并移交縣議會辦理。[9]其時上海輿論正處于租界公園“華人與狗不能入內”的漩渦之中,此議一經公布,贏得眾多響應,“上海的租界亦有數處公園,但是他們的門首往往懸著‘華人與狗不能入內’的示牌,咳,這不是最恥辱的事,嗚然,而亦是華人‘自取其咎’,一則中國人沒有道德心,二則自己沒有公園,供人們的游息,所以西人才有這種的舉動”,而“文廟是尊孔子而設的,每年除了祭祀的日子,一年兩度的開放,就終年封閉,非但失了尊孔的真諦,反而作了鳥巢獸窟,很大的房屋,就此頹敝不堪”,認為改建成公園后,“大可供人瞻仰,引起他崇拜孔子的思想”。[10]該年12月,《申報》上登載《文廟宜開放》,簡便經濟被作為宣傳要點,“孔子固圣之時者,也當亦顧而樂之,許為移風易俗之良法矣。各地之辦理教育經管公產者,曷起圖之?慎勿以文廟為神圣之地而任令其頹廢至失觀瞻也”。[11]當然,輿論提倡與實際運行是兩碼事,文廟灑掃局局董們改建公園的議案石沉大海,縣議會卻先后通過改建四祠、規復文廟舊制的決議,1925、1926年的上海文廟在孔子誕辰日舉行祀禮,增加鄉賢入祀忠義孝悌祠、節孝祠,以示褒揚孝悌節烈。可見,文廟的傳統空間價值仍備受重視,傳統士紳仍把持著文廟改制的話語權。隨著新政權確立,文廟改建才得以落到實處。
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攻克上海,6月4日,江蘇省政府飭令各縣撤銷文廟奉祀官[12],文廟灑掃局隨即改做上海市教育協會會址,7月13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第四團團長俞濟時將新兵招募處遷至文廟辦公。1928年2月21日,大學院訓令廢止春秋祀孔大典,從制度上規定政府不得再參與孔子祭祀。2月29日時值孔子春丁祭日,上海紳學兩界同人公推社會活動家姚文楠為主祭,自發前往文廟舉行祀禮,因大學院訓令限制,舍棄牛羊三牲,無學舞鼓樂,僅供設魚肉籩豆菜酒等物,春丁祭場面凄清。[13]4月20日,江蘇大學區縣教育局聯合會上,興化縣教育局呈請江蘇大學區通令各縣文廟一律改設通俗教育機關,以免任其荒廢,會議以決議形式通過。[14]上海市教育局摩拳擦掌,為將文廟改設通俗教育館而積極運作。
9月18日,以改良風俗、開展社會教育為己任的上海少年宣講團發起人汪龍超致函市長張定璠,以推動社會教育發展為由,提議將孔廟改建為公園,并附設通俗教育館,“竊念公園為社教之一種設施,查滬南人口稠密,市肆繁盛,獨公園之設尚無”,“應就原有公共建筑而改造之,事半功倍,易于功成。查文廟地處滬南中部,占地廣闊,建筑堅固,有泮水之池,魁星之閣,明倫堂可作公共講演之用,改廢物為利用,又可表孔子之圣賢。群眾得以游覽,不若只閉之無益。并得加以建設,如通俗講演所、通俗教育館、閱覽書報所、改良茶館等”。21日,上海特別市政府將呈文下發至新成立的工務局,令其“核議具覆”。接到市政府飭令后,該局局長、留德工程學博士沈怡親赴文廟實地勘察,23日回復張市長,認為文廟的位置、交通和內部布置都適合改建公園④,支持汪龍超的改建提議。
為了擴大輿論,汪龍超將其提議刊登于《民國日報》,社會人士紛紛響應。市民尹勇等11人具名呈文市政府,表明他們贊同將文廟改建為公園,“滬南文廟,地處中心,建筑堅固,內有魁星閣、泮水池、明倫堂,可作講演之所,藉此宣傳三民主義,既可將黨義灌輸民眾,又可表示尊孔,供人游覽,即社會教育亦可發展,將此廢物,化為有用”,“且滬南民眾,渴望有年,因前軍閥鐵蹄所壓,雖提議者不乏其人,而未得效果,今既處于為民眾謀幸福之青天白日旗下,可解決一切,故有公園之建議于前,同人等響應于后,用特具呈請求鈞府鑒核,賜予允準,則社會幸甚,黨國幸甚”。尹勇等人直接以宣傳三民主義、黨義灌輸等政治目標,并借民眾對新政府期望心情,給市長巧妙施壓。[15]文廟向普通民眾開放,已與將尊孔“傳諸民間”無關,而是國民政府權力下潛的政治需求。
在多方合力下,市長張定璠很快做出決定,10月2日,訓令工務局會同教育局核復尹勇等人呈請,擬定文廟改建公園的計劃。工務局第二科科長許貫三負責草擬計劃,提出大成殿“為全廟大小各殿堂內神像收容所”,作為尊孔之遺跡,崇圣祠則改作圖書館,大成殿旁的“走廊廂房暫改作國貨售賣所、標本陳列所、國貨陳列所或民眾茶點室”,而舊有的長約七十丈的高圍墻“均應拆去”。⑤
這個計劃遭到上海市教育局的反對。教育局遵從內政部給蘇省政府飭令[16],10月15日,上海市教育局接管文廟[17],積極籌劃將文廟改建為民眾教育館。教育局之所以公開與工務局抗衡,從《申報》披露的信息看,皆因在接收前已與市政府就文廟改建達成共識:“上海特別市教育局,前以設施民眾教育館及圖書館,無適當地點,而事實上又極為需要,勢難再緩,后以文廟地方寬泛,足供設施,曾奉到市政府訓令接收在案,茲悉教育局方面,已與縣政府接洽就緒,定于下周一前往接收,想將來本市社會教育方面定有一番新設施矣。”[18]教育局接收后,馬上籌備民眾教育館,并計劃在其中附設兒童樂園、博物館、公共講演廳、簡易體育場等。[19]很有意思的是,同日《申報》第25版刊登市政府給予工務局的飭令,稱“現文廟業已收歸市有,已著工務局計劃一切,對于園內各項布置以及花草樹木,將參照各大都市公園情形,并根據科學原理,以期盡美盡善云。又本市以市政進行,貴有開明之市民,否則市政進行,定有阻礙,是以開辦民眾學校及采取種種宣傳方法,闡揚市政真諦外,并亟謀圖書館之設立,以增進市民之智識,現以南北兩市之公園地址既經覓定,擬即在該兩園內附設圖書館各一所,并責成教育局籌備一切”。[20]顯而易見,上海市政府將文廟的改造,實際上交由工務局、教育局共同負責。
教育局接收文廟后,局長韋愨(留美博士、大學院院長蔡元培親薦)深諳中央政府社教政策,11月14日,在未與工務局溝通前提下,呈文市政府,“上海縣之文廟,自經本市教育局接收后,即擬利用其地設立民眾教育館一所,該局以此為推廣民眾教育之第一步,亦即民眾教育中之重要工作,經積極計劃,務使之成為事實,昨該局將該館計劃及概算書呈請張市長審查”,提出將文廟全部改建為民眾教育館的訴求。[21]面對教育局單獨行動,工務局局長沈怡致函張定璠市長,重申文廟改建公園計劃及市政府批文,請市長裁奪。2月4日,張定璠訓令維持前次批文,否決教育局擅自將文廟改設民眾教育館的提議,飭令教育局重新遞交計劃及預算書。⑥教育局采取“遲遲不遞交計劃及預算書”等消極應對策略,加上經費難以落實,⑦這份市長訓令成為一紙具文。5月初,韋愨調任中央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宣傳部部長陳德征接任教育局局長。工務局利用新舊局長交接之際,于5月15日致函教育局,要求其按照前議盡快制定民眾教育館的詳細計劃;同日在國民黨上海執委會常會上以一區黨部名義,呈請咨詢市府文廟改建公園議案;與此同時,工務局再次呈文市政府申明文廟改公園的必要性,請求市政府盡快飭令財政局撥還墊款,飭令教育局從速擬定民眾教育館計劃。⑧一個月后,教育局遞交了如工務局所愿的詳細計劃。
工務局通過各種努力得到了如愿結果,卻因市長更迭化為泡影。張群作為政學界的核心人物,于4月1日接替張定藩出任上海市市長。他就任后,面對工務局與教育局之間改建文廟的糾紛,根據教育部、內政部、財政部會銜公布孔廟保管辦法⑨,決定將文廟全部改為民眾教育館:“本府一百二十七次市政府會議決議,將孔廟改設民眾教育館,其中古跡名勝務加保留,并使之公園化。”⑩市政府的決議,使得前任教育局局長韋愨的主張“原地復活”,同時兼顧了工務局改建文廟為公園的計劃,傳統空間的現代賦形正式拉開帷幕。
二、傳統空間重構與布局變化
根據市政府決議,教育局與工務局聯手推動文廟空間改造。兩局首先統一文廟修葺方案:分步改建文廟。11月20日,工務局局長沈怡會同教育局局長徐佩璜(1930年接任陳德征)同至文廟詳為勘察,就文廟修葺達成共識。12月13日,工務局、教育局聯銜會呈市政府,以“保存原有古跡名勝暨發展民眾教育為原則,并于設備上務使之公園化”為整體思路,“凡古跡名勝,俱照舊保存,并利用余地,增建屋舍為辦理民眾教育之用。廟內原有建筑物,如門首、牌坊、橋拱、大成門、大成殿、崇圣祠、明倫堂、魁星閣,或以先圣關系,或以古建筑之美麗,悉家保存,并重行修葺。惟舊有大成二門及東西兩廡房屋,因無修理價值,俱擬拆除,使各部分聯成一貫,形勢上也可頓見宏偉,并改筑沿文廟路之墻垣,以壯觀瞻。復于廟內依照公園布置方法,加駐步行路線,栽植花草樹木,并將魁星閣前之池水設法澄清,俾市民于瞻仰廟貌、閱覽書報之余,并獲身心游息之所”,并于四周空地上建筑圖書館、音樂廳、博物館、動物園等,建筑形制力求與廟內原有建筑物收相得益彰之美。這份呈文,強調保存文廟原有建筑,以便文廟空間象征成為社會教育發展助力,究其原因,既與外界批評輿論有關,更與國民政府的“致敬傳統”的社會教育發展路徑有內在聯系。1931年1月16日,張(群)市長批準此項計劃,市政府指撥改造經費。[22]
經費到位后,兩局分二期工程,將文廟改建落到實處。一期工程主要是整理文廟景觀,文廟南面圍墻完全拆除,用磚墩、冬青樹來做裝飾,每墩相間五六尺距離,中植冬青樹,路人得見園內景色;文廟中的兩座牌坊因年久風蝕全部卸下,將石柱拋潔后重新砌造;文廟內四座石橋一律拆除重建。第二期主要修理建筑,如大成殿、崇圣祠、明倫堂等,修補竹籬、浚池疊石、種植花草樹木,大成殿“加大髹漆,金碧輝煌,至為壯觀”,10月初全部竣工。從空間布局上看,保留了文廟的大部分建筑及景觀。10月12日,上海市民眾教育籌備處遷入文廟崇圣祠辦公。教育局職員李大超兼任館長,負責民眾教育館的籌辦工作。1932年4月1日,專任館長楊佩文到任,鑒于“本市人口稠密,適合高尚娛樂之場所,公園惟租界有之;南市一帶,近年來人口激增,地無閑隙,民眾業余,無可游覽,佩文接任以后,第一步即著手規劃園景”[23], 6月1日,民眾教育館允許民眾入內參觀; 10月10日全館全面開放。
教育局主導下的文廟空間塑造發生了大的變革。大成門被改造成民眾教育館的時事展覽室、兒童閱覽室及娛樂室,崇圣祠為該館的“一·二八”戰績展覽室、生計展覽室,明倫堂為演講廳、民眾學校及閱報處,藏經閣成為市立圖書館所在地,魁星閣被改造為民眾教育館的會客室,儒學署成為公民教育展覽室、東北戰跡展覽室、健康教育展覽室;而政府令保留的大成殿,變成了“祀孔彝器陳列所”。從這種空間塑造看,培養時代公民、激發民族精神、倡導科學健康等西方理念是民眾教育館的主體活動,文廟固有的儒家文化象征僅保留了一個“祀孔彝器陳列所”,文廟建筑作為歷史陳跡被展覽。很有意思的是,上海市民眾教育館將景觀與展覽的開放時間做了分別規定,可窺教育局對文廟原有空間舊有文化象征及固有功能并未沿襲之意,僅僅是借助建筑空間,“舊瓶裝新酒”,這種態度在1934年后祀孔儀式中得到更淋漓盡致的體現。[1]
工務局對民眾教育館的如此空間布局,實際上并不十分認同,背后是文廟改造利用理念不同的現實投射。教育局在于尋求最大限度推行社會教育的場所,如正式開館月余,民眾教育館因館舍不敷使用,專門呈文教育局,稱“查該館館舍狹窄,確感不敷應用,經派員實地查勘,認為大成門兩旁空屋,稍加修改,尚能切合使用,并與中央規定利用文廟辦理社會教育之旨亦相符合,且大成門之名稱照院令規定,應在廢除之列,修葺利用,更無妨礙之處”。教育局轉請工務局施工改造,擬將大成門南向木柵及中間橫壁拆除,并于兩壁隊旗墻壁、裝置門墻改建為房屋,以便辟為民眾問字處、民眾代筆處、民眾診療室及時事展覽室之用。此改造動議,遭到工務局強烈反對而擱淺, “工務局力持保存原有之大成門樣式之主張,不允改造,是以所謂大成門者,仍只有屋頂而無墻壁門窗之過路門埭耳,本館為舉辦事業計,自未便因噎廢食,所有時事展覽,遂不得不因陋就簡,布置在不蔽風雨之大成門內,致使展覽品難于管理,誠莫大之憾事也”。[23]事隔半年,民眾教育館館長楊佩文提及此事,依然意難平。
民眾教育館的空間塑造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通過實現所設定的目標來表達舉辦宗旨,辦理者(館長、館員)通過空間布置、事業開展對宗旨進行生動展示。從該館概況記述可知,該館主要活動可分為塑造國家與革命精神,實施普遍社會教育如健康展覽、巡回文庫、改良說書等。就展覽室效果記錄看,民眾教育館幾乎均統計了展覽開放以來的參觀人數,如“一·二八”戰跡展覽室半年參觀人數為635 342人,健康教育展覽室、公民教育展覽室開放3個月參觀人數分別為388 439、286 249人,而大成殿設的孔廟祭祀禮服陳列所,僅有“開放后,參觀者紛至沓來,均欲一睹為快,幸大成殿地位寬大,未見擁軋”的籠統說法,并無詳細統計數據。[23]結合民眾教育館對文廟舊有建筑的布局安排,可見其空間塑造 “以教育改造達社會改造”的社會教育功能,以期形成一個共同而明確的精神氣質,“大成殿仍是大成殿,魁星閣仍是魁星閣,池沼依舊,樹木無恙,而風景卻大不相同”。[24]文廟的舊有建筑經此塑造有了“學者”氣質:“在文廟公園,不僅使你感到空氣的新鮮,他還會告訴你,這是什么花或什么樹,屬于那一類那一科的,并且,在一·二八紀念室里,你可以見到六百磅的重量炸彈,你可以見到忠勇健兒用鐵血換來的種種戰利品,你可以見到那些畏死的獸類的護身符,在這里,你會聽到衛國健兒悲壯底呼號,在你耳畔重復的喊叫。其他,他會告訴你祀禮的用具和一些普通的衛生常識。”[25]開放的、免費的“文廟公園”變成了上海市民眾教育館的代名詞。
三、儀式操演與國家在場
國民黨政府建立后,面臨著嚴重的道德重建任務,遂采用“固有的民族道德”來挽救這種“隱世厭世、浪漫頹廢”[26],祭祀孔子成為以傳統儒家道德來建立新的道德規范、恢復民族自信心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儀式。
1934年開始,國民政府重新開始舉行孔子誕辰紀念,設在文廟舊址的民眾教育館責無旁貸,自然承擔了這個儀式操演,孫中山遺像、黨國旗等國民黨政黨符號,與原本孔廟的儒家傳統無縫對接起來,傳統空間的現代賦形得到進一步加強,體現出強烈的國家在場。
1934年8月27日,上海市黨政機關在民眾教育館大成殿舉行孔子誕辰紀念大會,舉行前《申報》曾進行連篇累牘的報道,比如市府將在民教館舉行孔子誕辰紀念、用什么音樂等[27],紀念大會當天更是隆重,“紀念大會會場,設在市立民教館內大成殿,頭門上交懸黨旗國旗,上有白布橫匾,上書‘本市各界舉行先師孔子誕辰紀念大會’字樣,殿之正中神龕上,懸掛總理遺像及黨國旗,市府特繪之孔子遺像,則供于前面桌上,兩旁分列鐘鼓琴瑟廟堂之樂,四周壁柱上,滿貼標語,殿外搭有臨時涼棚,為各界代表席,布置頗為莊嚴肅穆,原有祀孔彝器,已遷至該館講演廳陳列,任人參觀,以資觀摩”。紀念會議程如下:(1)全體肅立;(2)大同樂會奏中和韶樂;(3)唱黨歌;(4)向黨國旗、總理遺像及孔子遺像行三鞠躬禮;(5)主席恭讀總理遺囑;(6)主席吳鐵城報告紀念孔子意義;(7)童行白、潘公展演說;(8)公安局奏樂;(9)禮成。[28]本次紀念大會計到各界代表1 000余人,市黨部童行白、市長吳鐵城為會議主席,全市各機關團體、學校及工廠各休假一天。
無論市長吳鐵城、市黨部代表童行白,還是市教育局局長潘公展,他們在孔子誕辰紀念大會上的發言基調均著力闡述三民主義與孔子道義的內在切合性。吳鐵城認為,“國民黨奉行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總理革命思想的結晶,總理的革命思想,固然很多激發于現代的科學,然蘊育于中國固有文化者也很多……我們可以說孔子是集古代的大成,而總理是集古今中外的大成,因此我們要完成中國國民革命,我們必須實行三民主義,而要實行三民主義,必要發揚中國固有的文化,要發揚中國固有的文化,必要尊崇孔子。今日之尊崇孔子,并非復古,也不是崇拜偶像,今日之尊孔,乃是謀民族之復興”,宣傳孔子學說的時代精神。潘公展將孔子的民族精神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對接,“紀念孔子誕辰,必須要紀念孔子那種民族的精神……孔子的精神,是‘攘夷狄’,攘夷狄就是孔子學說的結晶,也就是總理的民族主義,攘夷狄又可做復仇的解釋,顧今日紀念孔子,應有復仇的精神”。[28]以孔子學說來攀附復仇,激發民眾應對強敵的信心和勇氣。在儀式中,突出世俗黨國的價值取向,文廟“圣域”傳統被刻意消解。
借助紀念孔子誕辰的儀式,新生活運動亦攀附進來而被大力宣傳。“蔣委員長提倡新生活運動,亦是根據舊禮教,出發點是禮義廉恥,現在國家的毛病很多,就是大家思想沒有標準,沒有重心,沒有中心信仰。孔子可以說是表率人物,要按他的言行去做,拿他的言行統一意志,形成全國的思想中心。”[29]很明顯,紀念活動中,孫中山被作為當時中國政治文化的符號象征,彰顯國民政府的統治合法性,借紀念孔子來宣傳國民黨的政治主張,宣傳新生活運動,集體儀式背后隱含著國民黨政治權力的滲透與運作,體現的是意識形態如何被創造、被傳播,在宏大的集體儀式中,不僅完成了“對歷史文化的認同”,還達到了“政治上的認同”。延亙千年的孔子誕辰祭祀,悄然換上了國民政府倡導的新道德的“芯”。
文廟作為上海市標識性很強的建筑,市黨政機關充分利用了大成殿的獨特空間,頭門上交懸黨旗國旗,神龕上懸掛總理遺像、黨國旗等空間符號,與神桌上放置的孔子遺像一起,一段隱喻之旅引導著孔子誕辰集體儀式的整個過程。其中政府明確將黨國意志、革命話語附加在文廟場域,從紀念對象上看,由原來孔子及先賢先儒變成了黨旗國旗、總理遺像和孔子遺像,作為紀念主角的孔子被排在了第三位;而整個典禮議程完全套用“現代禮儀”:用唱黨歌、向黨國旗總理遺像及孔子遺像行三鞠躬禮、恭讀總理遺囑和主席報告、演講等現代集會的程序,代替了“迎神、初獻、亞獻、終獻、撤饌、送神”等傳統祭孔儀式,大力宣揚孫中山符號,孫中山已超越孔子而居于祭孔儀式空間的中心位置。從典禮到儀式、內容都被納入國民黨黨化的軌道,孫中山作為政黨符號和三民主義的政黨意識,貫穿在整個孔子誕辰活動中,祭祀先師孔子的文廟儀典的回歸不過是“舊瓶裝新酒”,并非儒家信仰在社會層面的復活與地方傳統士紳的話語權回歸,文廟曾有的相對獨立的“道統”更多演變成了象征意義。國家權力利用儀式呈現和發揚“固有之道德”的社會政治形象,充滿韻律和生動象征的黨歌替代了一詠三嘆的孔子贊歌,有效地營造了一個富含時代感、滿含民族自豪感的國家團結情感和氛圍。
政府通過恢復孔子誕辰紀念來重新詮釋儒家文化,并將之鑲嵌到民族國家、三民主義、新生活運動等時髦話語中。對于文廟空間秩序的部分回歸,在贏得遺老遺少情感的同時,也引起社會人士的擔憂:“該館并為推廣民眾的見識將原來珍藏在灑掃局的祀孔器服在孔子廟開放‘祀孔彝器陳列所’,現在,這些祭器、祭服、樂器、舞器,不再僅僅乎展覽,而要真的用得著了。那民眾教育館,也許就在不久將來仍舊變回神圣的文廟吧。”[30]各式精英之所以支持民眾教育館的象征性重建,為民眾呈現一個祭祀先師孔子誕辰的盛大場面,是出于回應儒學衰微、國內各界對移植來的“新式教育”指責增多以及為國民政府提供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形象的需要。換言之,他們理解并深深相信紀念孔子誕辰集體儀式的力量,它有助于為國民政府的社會結構提供情感支持,既安撫了那些對儒學留戀的“遺老遺少”,同時,通過把這些儀式和想象中的儒家文化主導、曾經強盛的中華帝國歷史聯系在一起,試圖喚起了民眾的國家認同。
福柯認為“空間是權力運作的基礎”[31],空間布局作為政治權力付諸實踐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空間如何定位,相應會氤氳不同的政治氛圍。文廟作為一種有廣泛民間基礎的固態文化存在,作為一種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威權空間,國民政府非常重視,假址于此的民眾教育館更是通過用黨國旗、總理遺像等進行內部布局以及相應的集體儀式操演等來實現其空間的現代重構。
上海市教育局之所以能在新任市長張群支持下取得壓倒性勝利,在于國民政府將文廟園林化以便民眾娛樂的同時,更期望將之塑造成社會教育的平臺,成為“喚起民眾”“改造社會”的憑借,將文廟全面改建為民眾教育館便是最佳方案。
任何一個空間的命名都是一種觀念、意識對空間進行控制的體現,孔廟、貢院、關帝廟、鐘鼓樓等具有政治和文化象征含義的建筑群被改設為民眾教育館,其本身就是對原有空間意義的重構,反映出政府對空間新生意義的強調。在文盲率高達80%的民國時期,普通民眾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了解孫中山,理解國民政府政策規定,很大程度上與設在傳統或新式的公共空間的民眾教育館有很大關系,民眾在潛移默化的狀態下形成關于孫中山、三民主義及國民黨的集體記憶。民眾教育館作為社會教育的綜合機關,作為黨治主義象征、話語宣傳與實踐的空間展示場域,改變了原有的物理性空間狀態,成為承載意識霸權的異質空間,在塑造現代新型國民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國民政府利用這些傳統公共空間改設社會教育機關,不僅是一種經濟選擇,更是政府意志在空間重構中的體現。國民黨通過傳統公共空間更名和改建,將黨旗國旗、總理遺像等政黨符碼鑲嵌其中,增添各種時髦游藝項目,設立各式展覽室,通過開展種類多樣的活動,將社會教育機關打造成一個大眾化、免費的公共空間,實現國家權力滲透方式的轉變。
當然,在文廟公園、民眾教育館等社會教育機關的定位上,精英與民眾之間一直存在著明顯差異,政府和知識精英期望這些由傳統空間重組的社會教育機關成為教化民眾、塑造國民的場所,寓教育于娛樂,而實際上民眾對此并不能完全認同。一方面,他們會受到黨旗國旗、總理遺像所營造的政黨符號的意識形態的影響,認為這個免費的“文廟公園”有“學者”氣息;但另一方面又不會全然接受,他們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在民眾教育館、公園活動。鑒于政府對文廟建筑的保護和傳統士紳的堅持,由文廟改設的民眾教育館內部空間與布置發生變化,但依然廟宇高聳,大成殿里依然陳列了雕刻精美的孔子像及其從祀弟子、歷代先賢,欞星門、魁星閣等依然巍峨,“我們一行六個人,先瞻仰孔圣暨諸賢神座,無不肅然起敬意”。[32]特別是1934年國民政府恢復祭祀先師孔子誕辰后,在一般民眾心目中,文廟儼然再次恢復到原來儒學圣殿地位,“進門先見魁星閣,大門口三架石牌坊。小假山,小池塘,小涼亭,小橋梁,小小景致小地方,鐘鼓高架多威顯,大成殿閣居中央。先師神位高高供,名賢排列在兩旁”。[33]只不過由原來的“閑人免進”變成了免費游覽、“白衣人也可游泮水”的”“公園文廟”而已。無論社會教育機關如何努力對傳統空間來進行空間重構,但在普通民眾觀念中,傳統空間的象征意義仍沒有多少改變,欞星門、魁星閣、大成殿等傳統建筑依然是昔日祭祀先師孔子的符號,對假址于此的民眾教育館舉行的教育活動沒有多少情感認同。政府的制度設計與民眾情感接受之間存在著縫隙和張力。這一方面的問題,在傳統空間改組的社會教育機關中普遍存在,值得進一步關注。
注 釋:
① 法國記憶社會學家Pierro Nora(皮埃爾·諾拉)、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南京大學教授陳蘊茜等研究成果尤具代表性。諾拉對法國“記憶的場所”進行了大量研究,特別探討了紀念性空間具有回溯性、前瞻性雙重功能,前者主要是喚起民眾對該類教育空間的固有記憶,后者則通過紀念空間的布置營造,將民眾舊有的記憶與未來設想相互勾連,從而讓民眾通過參觀、參與紀念空間而獲得理解認同,從而適應未來的發展趨勢,特別強調公共性紀念場所作為“記憶的界質”對社會記憶的影響;安德森認為,近代國家之所以能形成“想象的共同體”,就是因為人們擁有共同的記憶,而提供這些記憶資源的載體之一就是紀念空間,這些紀念空間以不同的形式講述或呈現相同的故事逐漸演變成民眾的集體記憶,為民族和國家提供認同的資源;陳蘊茜教授考察了中山公園、中山陵等空間建構,揭示了總理遺像等作為國民黨政府符號的廣泛應用。具體詳見:Hue-Tam Ho Tai,Pierre Nora and France National Mem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6.No.3.Jun.2001,pp.906-92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睿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頁;陳蘊茜:《空間重組與孫中山崇拜——以民國時期中山公園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1期;《國家權力與近代中國城市空間重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3期。
② 詳見周慧梅:《民眾教育館館舍的教育意蘊》,《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9年第2期;《社會秩序與政府職責:以北平市第二民眾教育館附設影院風波為中心》,《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6年第6期;《集體儀式與國家認同:以山西省立民眾教育館為考察中心》,《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③ 張國鵬:《政權與信仰變革下的民國文廟——以上海文廟為考察中心》(1911—1934),南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中國近現代史方向,2016;張國鵬:《民國時期的上海文廟改制》,《中國文化研究》,2020年夏之卷。
④ 詳見:《上海市工務局關于文廟整理文書》,Q215-1-8090,藏于上海市檔案館。
⑤ 詳見:《呈為響應滬南公園建議將文廟開辟公園請求核準事》,《上海市工務局關于文廟整理文書》,Q215-1-8090,藏于上海市檔案館。
⑥ 詳見:《文廟改建公園抑改為民眾教育館清核示呈悉仰查照原案辦理由》,《上海市工務局有關民眾教育館文書》,Q215-1-8251,藏于上海市檔案館。
⑦ 詳見:《為陳明文廟公園經費業已制定的款擬仍照原案辦理由》,《上海市工務局關于文廟整理文書》,Q215-1-8090,藏于上海市檔案館。
⑧ 詳見:《為函請迅將擬建文廟公園內民眾教育館設備計劃擬送過局俾便進行由》,《上海市工務局有關民眾教育館文書》,Q215-1-8251,藏于上海市檔案館;《為陳明文廟公園經費業已制定的款擬仍照原案辦理由》,《上海市工務局關于文廟整理文書》,Q215-1-8090,藏于上海市檔案館。
⑨ 鑒于各地孔廟財產處理頗多爭執,三部會銜發布孔廟保管辦法,其中第二條提到“孔廟財產,均應撥充各地方辦理教育文化事業之經費,不得移作他用”;第四條規定“孔廟房屋,應有各該保管孔廟之教育行政機關及時修繕,其原有之大成殿,仍應供奉孔子遺像,于孔子誕辰開會紀念”;第五條“孔廟地址應充分利用,以辦理學校,或圖書館民眾學校等”。這一政策出臺,為教育局利用文廟辦理社會教育提供了政策依據。詳見:《教財內三部公布孔廟保管法》,《申報》,1929-03-07,第10版。
⑩ 詳見:《上海特別市市政府訓令第1310號》,《上海工務局有關民眾教育館文書》,Q215-1-8251,藏于上海市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