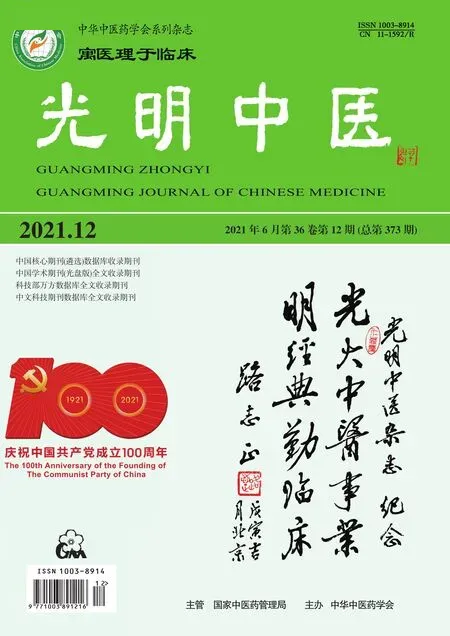中醫治療痛風臨床進展淺談
陳 川
1 概述
痛風是長期嘌呤代謝紊亂引起的疾病。發病前多數患者存在高尿酸血癥,發作時以反復出現小關節炎為特點,后期常累及大關節,形成痛風石導致關節畸形,其癥狀為多為關節的紅、腫、熱、痛,病情反復,遷延難愈,其本質為持續的高尿酸血癥引發尿酸鹽沉積導致關節畸形。
中醫對于痛風的描述,最早見于《華佗神醫秘傳》,該病最接近于“腳氣病”范疇,書中記錄:“人病腳氣與氣腳有異者,即邪毒從內而注入腳者,名曰腳氣”。《中藏經》也提出了氣腳與腳氣病名,并區別為:“夫喜怒憂思、寒熱邪毒之氣,流于肢節,或注于腳膝,其狀類諸風、歷節、偏枯、癰腫之證,但入于腳膝,則謂之氣腳也。若從外而入于足,從足而入臟者,乃謂之腳氣也”[1]。后孫思邈、李東垣等醫家對“腳氣病”的描述多予以贊同。直到元代,朱丹溪才正式明確提出“痛風”之名,他在《格致余論》描述,“彼痛風者,大率因血受熱已自沸騰。其后或涉冷水,或立濕地,或扇取涼,或臥當風,寒涼外摶,熱血得寒,污濁凝澀,所以作痛;夜則痛甚,行于陰也”。又在《丹溪心法·痛風》記載:“痛風者,四肢百節走痛,方書謂之白虎歷節風證是也”。 同時期名醫龔廷賢在《萬病回春》也說:“痛風者,遍身骨節走注疼痛也,謂之白虎歷節風”。明代王肯堂在《證治準繩·痛痹即痛風》中記載:“痛痹即痛風,留著之邪,與流行榮衛真氣相擊搏,則作痛痹”[2]。張景岳在《景岳全書·雜證謨風痹》中將痛風謂之“風痹”。 李梴撰《醫學入門·痛風》曰:“……以其循歷遍身,曰歷節風;甚如虎咬,曰白虎風”[3]。后世醫家對痛風多有描述,但未統一病名,清代張璐總結:“按痛風一癥,《靈樞》謂之賊風,《素問》謂之痹,《金匱要略》名曰歷節,后世更名曰白虎歷節,多由風寒濕氣乘虛襲入經絡,氣血凝滯所致”。綜合歷代醫家所言,中醫之痛風較西醫痛風的范圍更廣。針對現代醫學“痛風”而言,朱良春[4]認為: “濕濁瘀滯內阻才是其主因”,故將痛風稱之為“濁瘀痹”。路志正[5]認為,現代痛風范圍小于中醫學之“痛風”,故將其命名為“痛風痹”,以區別于中醫學中痛風的概念。
2 病因病機
因痛風的主要表現為關節紅、腫、熱、痛及痛風石的形成,且病情反復難愈。近現代醫家多從“痹病”論治,結合當代醫學認為高尿酸血癥才是導致痛風的主要原因,因此痛風的病因病機區別于普通的“痹病”,也非單純的寒、濕、瘀等邪氣閉阻經絡導致。
痛風的病因病機多因先天腎氣不足,后天脾胃運化失調,水濕內蘊,繼發痰濕、瘀血、濕熱、濕毒等。脾為中州之土,主運化水濕,腎主開合,司水液氣化。脾腎功能失職,則易導致水濕代謝紊亂,水濕停留體內,聚而生痰,阻礙氣血運行,導致瘀血停留,痹阻關節,蘊發濕熱、濕毒。痰瘀之邪閉阻日久則易化火,加之不通則痛,故患處容易出現紅腫熱痛的臨床表現。正如《素問·評熱病論》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外臺秘要》提出“大多是風寒暑濕之毒,因虛所致,將攝失理……晝靜而夜發,發時徹骨絞痛”[6],即身體虧虛,感受風寒暑濕之毒誘發痛風。《素問·痹論》中記載: “骨痹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腎; 筋痹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肝。所謂痹者,各以其時重感于風寒濕之氣也”,也提出了該病的病因病機為本虛標實之證。《景岳全書》也指出“歷節風痛是氣血本虛……致三氣之邪遍歷關節”,其發生在于氣血生化乏源,外邪趁虛侵入所致。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提出痹本“血虛有熱”之說: 他認為,痹證患者素體陰血不足,日久生熱,在此基礎上感受外邪所致。《類證治裁·痹證論治》云:“久痹不愈必有濕痰敗血瘀滯經絡”[7]。綜上,歷代醫家對痛風病因病機的描述雖然不盡相同,但對于“素體虧虛,感受外邪”的基本觀點是大致統一的。
后世醫家在上述基礎上進行了更加詳細的闡述,楊潤蘭[8]認為,痛風急性期以濕熱瘀滯經絡為主。張荒生認為瘀血阻絡貫穿痛風始終[9]。劉孟淵[10]認為,痛風病機為氣血虧損,濕痰陰火流滯經絡而發生。任延明等[11]認為,中老年人腎中精氣漸衰,氣血虧虛,陰陽失衡,肝腎虧虛,外邪乘虛而入,引發痛風。畢翊鵬等[12]從中醫氣血津液辨證理論出發,認為痛風與“血”有著密切的關系,血虛證、血瘀證、血熱證均可導致痛風。隨著對痛風病因病機描述的深入,不難看出,臨床更應圍繞發作期和緩解期展開治療。
3 辨證論治
3.1 發作期發作期一般有受累關節的紅、腫、熱、痛,活動受限,甚至關節變形,兼有發熱煩躁、大便干燥等,舌紅,苔黃膩,脈弦滑數等,治療一般以化濕祛痰,清熱逐瘀為主。魏合偉等[13]入選32例痛風患者,以清熱祛濕、涼血止痛為治則,自擬清熱涼血方,1周后,效果明顯,總有效率達96.9%。傅南琳[14]認為,急性期以祛風清熱,利濕泄濁,活血止痛為治則。常用藥物有:萆薢、土茯苓、澤瀉、海金沙、金錢草、薏苡仁、丹參、澤蘭等。認為土茯苓性涼,清熱解毒,通利關節;萆薢祛風,利濕,治風濕頑痹,腰膝疼痛;金錢草清利濕熱、通淋消腫;澤瀉利水,滲濕,泄熱。王守富[15]認為痰濕郁熱為痛風性關節炎的主要病機,治以化痰祛濕、平肝清熱為主,自擬夏麻除濕湯加減(丹參15 g,赤芍15 g,法半夏10 g,澤瀉15 g,茯苓15 g,白術15 g,天麻10 g,陳皮15 g,鉤藤30 g,川芎15 g,荷葉10 g,土茯苓30 g),經臨床實踐,效果顯著。李高興[16]在治療痛風急性期以驅邪為主,兼以通絡活血止痛為治則,多取桂枝芍藥知母湯、麻杏苡甘湯、烏頭湯加減,常用經驗藥:祛風散寒類:麻黃6~9 g,桂枝9~12 g,防風12 g,羌活15 g;祛濕類:白術12~15 g,炮附片9~15 g,薏苡仁30 g,土茯苓30~60 g,萆薢15 g;清熱類:秦艽30 g,地龍12 g,生地黃15~30 g,知母12 g;活血通絡止痛類:紅花15 g,丹參30 g,威靈仙30 g,田七5~9 g。朱良春[17]提出“泄化濁瘀”的治療大法。他認為: “恪守泄化濁瘀大法,貫穿于本病始終”,并結合多年臨床經驗,創立了泄化濁瘀代表方劑——痛風方。該方中含有土茯苓、萆薢、威靈仙、澤蘭、澤瀉、車前子、薏苡仁、桃仁、紅花、土鱉蟲、地龍等藥物。他認為: “痛風日久,絕非一般祛風除濕,散寒通絡等草木之品所能奏效,必須借助血肉有情之蟲類藥,取其搜剔鉆透,通閉解結之力”。因此常在方中配用土鱉蟲、地龍等蟲類藥,經實踐,該方對痛風發作期效果較好。
3.2 緩解期緩解期是發作之后的緩解階段,或2次發作的中間階段,患者臨床癥狀減輕或緩解,結合病因病機,治療應以“緩則治其本”為大法,臨床應注重補益肝腎,化濕醒脾,益氣養血為主。蔣小敏[18]認為緩解期的治療應以扶正祛邪為原則,以補腎健脾、調和氣血為主,臨床善用金匱腎氣丸或知柏地黃丸加減。王東等[19]在緩解期采用化痰行瘀,蠲痹通絡,兼調補脾腎為治則,擬方薏苡仁湯加減(薏苡仁30 g,蒼術10 g,當歸15 g,僵蠶15 g,全蝎3 g,秦皮10 g,川芎10 g,防風15 g,獨活15 g,桃仁15 g,紅花10 g,雞血藤25 g,地龍10 g,蜈蚣2條等)施治,全方既可清泄濁毒,又可燥濕健脾,起到祛邪扶正的作用。經臨床實踐,該方療效顯著,方中秦皮清熱燥濕,現代藥理研究顯示秦皮苷有促進尿酸排泄等作用。張磊[20]認為痛風緩解期因久病損傷臟腑氣血,脾腎虧虛,兼之前急性期水濕代謝紊亂,痰濕痹阻,治療更應緩和。治則為健脾化濕,活血養血。方選二陳湯、四妙散合千金葦莖湯配健脾溫腎泄濁活血中藥,方藥:茯苓、半夏、陳皮、炒蒼術、黃柏、生薏苡仁、冬瓜仁、桃仁、澤瀉、土茯苓、山慈菇、丹參、當歸等。經過 1 個月的治療,關節疼痛、局部皮膚暗紅、高尿酸、高血糖、高血脂也能同時得到改善。趙振發在痛風緩解期以化濕醒脾,溫陽補虛為治則,代表藥物有黃芪、白術、何首烏、山藥、杜仲、牛膝、肉蓯蓉、厚樸、附片、蒼術、補骨脂等。
3.3 個體化治療現代醫家通過臨床實踐,在中藥方向繼續探索的同時,也在結合針灸、刺絡拔罐等,使治療痛風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孫濤[21]不拘泥于辨證分期,自擬痛風湯(基礎組方為:黃柏10 g,蒼術15 g,生薏苡仁30 g,川牛膝30 g,澤瀉10 g,海風藤15 g,青風藤15 g,車前子20 g,滑石20 g,秦艽15 g,威靈仙15 g,桂枝5 g)為基礎方辨證加減,治療痛風患者30例,經20余天治療后,對比臨床癥狀及血尿酸水平,總有效率為93.3%。結論:自擬痛風湯治療痛風療效顯著。鄧云明[22]提出補氣健脾、 清熱利濕、通絡止痛的治療法則,自擬痛風清消湯(白術15 g,蒼術15 g,薏苡仁15 g,黃柏10 g,牛膝 10 g,白豆蔻15 g, 金錢草15 g,車前草15 g,徐長卿15 g,土茯苓30 g,重樓15 g,萆薢15 g,蒲公英15 g)加減辨證,該方標本兼治,既可用于發作期,又可用于緩解期,臨床效果較好。曹文萍等[23]予 42 例患者秋水仙堿片口服,另予44 例針刺足三里、太白、行間、血海、陰陵泉、三陰交、曲池、阿是穴并配合軍虎止痛散(生大黃200 g,虎杖200 g,生川烏200 g,生草烏200 g,水蛭150 g,山慈菇200 g,乳香200 g,沒藥200 g,生南星200 g)外敷患部,經對比,后者總有效率明顯高于前者。謝麗琴等[24]將毫針于酒精燈上燒至紅白后快速、準確地刺入阿是穴、足三里、大椎、三陰交等穴,刺入完成后使用跌打萬花油外敷針孔。7 d后與口服西藥組比較,雖在改善關節癥狀上效果相當,但其鎮痛效應優于西藥。
4 總結
多年來,對痛風的研究趨于完善,由淺至深,觀點眾多,但基本明確了先天腎氣不足,后天脾胃運化失調,水濕內蘊,繼發痰濕、瘀血、濕熱、濕毒的病因病機。作為醫務工作者,臨床中應恪守辨證論治,治療以“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為基本原則,發作期以“清熱利濕,活血止痛”為治則,緩解期以“化濕醒脾,溫陽補虛”為治則,充分發揮中藥、針灸、拔罐、刺絡等臨床手段,做到多學科、全方位診療。同時,我們還應認識到本病的發病率逐年升高,這與當今人們不合理飲食、作息等因素密切相關,作為醫者,我們在遣方用藥的同時,還應告知患者保持合理飲食,適當活動,按時作息對本病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