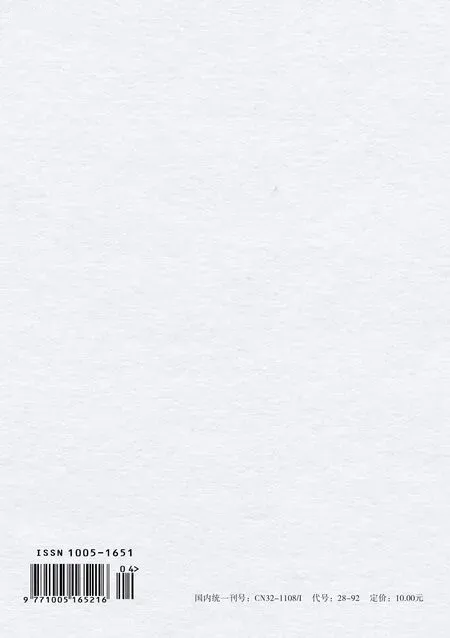徐柯和張天植的房產糾紛
方慧勤
徐柯是明代遺民,張天植曾是清朝侍郎。兩人在蘇州有過一樁房產糾紛,故事的始末,被徐柯洋洋灑灑寫成《上張侍郎書》,收錄在《一老庵文鈔》。冤有頭,債有主,這個張侍郎名天植,字次仙,號蘧林,嘉興人。
徐柯信中所說的房產在何處呢?其實正是位于吳趨坊周五郎巷的二株園,他父親徐汧遺留的老宅。
明朝覆亡后,徐汧投虎丘新塘橋下殉節,徐枋在父親歿后隱居天平山上沙村,賣畫營生。徐枋和徐柯雖為兄弟,但性情迥異,據尤侗回憶:“昭法(徐枋)天資木強,硁硁古道人也。貫時(徐柯)則風流佻達,有翩翩之概。”故而徐柯并未和兄長一樣退隱山林,而是隨俗浮沉,繼續居住在二株園中。
晚明之時,徐柯“豐姿姣好,宛若璧人,坐則琴樽,出則裘馬”,他沉酣于清嘉水木,跌宕于酒旗歌扇,曾招攜賓客繪制《二株園春玩圖》,將園中姬侍、音樂、狗馬、禽魚、花木、亭榭、水石一一勾勒,其豪侈可見一斑。隨著明清易代,徐柯無經濟來源,他父親的門生孫廷銓、高爾儼多次勸他為官,他都笑而不應,仍然固守園中,只與楊炤、丁觀旂等二三人交游,其余人都閉戶不見。順治十六年(1659),徐柯在二株園里作《白眼居士傳》。這篇自傳色彩濃厚的傳記即是徐柯清高孤傲的自畫像:
白眼居士者,不詳其姓字,眼多白,故以自號焉。慕謝康樂之為人,又自號曰江海人,或曰澹蕩人。家吳郡之西偏,有園亭,水木甚美,凡詩酒琴棋搏簺之事,好之而多不精。筑精廬,讀書其中,題其楹曰“蘊真”以見意。性峭直軒豁,絕去雕飾,意所否者,即公卿貴人、當世高名之士,蔑如也。
徐柯自號東海一老,二株園的位置又和“吳郡之西偏”相吻合,這篇傳記的落款,也正是識于二株園的蘊真館,和白眼居士讀書處一致,說明徐柯即白眼居士。他在傳記中說:“阮嗣宗比當世于裈襠之群虱,而劉伯倫亦視二豪如螟蛉。吾亦飲吾酒,讀吾書,白吾眼,而何惜彼營營。”阮籍對熱衷名利者白眼以待,對志趣相投者青眼相加,而劉伶則縱酒避世,蔑視權貴,只與阮籍、嵇康相交甚篤,這兩人可謂徐柯的異代知己。白眼居士的形象也不難讓人想到和徐柯同時代的遺民畫家八大山人,他筆下的鳥獸魚都是白眼向人,呈現出一種蔑視的神態,流露出和徐柯相同的孤傲情緒。
尤侗曾評價徐柯僻居二株園:“雖避世墻東,而胸中塊壘,少可多怪。”這與遺民張岱較為相似。明亡后,張岱賃居快園,試圖重塑明亡前的美好世界,抑或是一種精神世界。他的祖父曾以“瑯嬛福地”形容自己造的快園,而瑯嬛福地與桃花源相似,都隔絕了兵燹和易代之滄桑。張岱曾在快園和三五好友談天說地,依然如昔,這里是他心靈的寄隱。徐柯既是遺民,和二三友人在二株園狂歌醉舞,也未嘗不可看作遺民心緒的體現,畢竟在封閉的園中,可以盡訴前塵往事,假裝繁華未央。然而,隨著年歲漸久,徐柯又不善持家,遭遇了姬侍竊金等變故,日子困窘,不得不售出二株園來維持生計。
再說張天植,他是順治六年(1649)進士,順治九年(1652)任兵部右侍郎,順治十五年(1658)年,北闈科場案案發,其他人都招供被斬刑,張天植堅決為自己辯護,又因受皇帝器重,改流徙尚陽堡,經年赦歸,來到蘇州。
就在這一年春天,張天植物色新居,看中了徐柯的二株園。初見面,徐柯對張天植還是比較敬仰,云其“淵岳渟峙,鸞鵠羽儀”,表示自己“傾風慕儀,積有歲年”,并感嘆:“生平未嘗見大人,若閣下者,其殆是乎?”當然,徐柯曾自述生平有三罪:生無媚骨,性復好辯,離眾特立。因此,對張大人的夸贊只是客套話,畢竟接下來此人與徐柯要展開一場搏斗,細嚼這稱呼,讓人反而感到一股嘲諷之氣。
二株園定價為“六百之銀”,張大人覺得不錯,要“以廿金立數百金契”。用二十兩來立六百兩的契約,說給周圍人聽,都覺得不大對勁。徐柯認為,那可是大人,磊磊落落,有什么好懷疑的!話雖這么說,他心里還是有點沒底,當時張天植沒有貿貿然收契約,徐柯也沒有貿貿然收那二十兩。兩人找了一位中間人——申菽老(姓名不詳),將二十兩存放在了申菽老處。徐柯心想,張天植未執契,我也沒收定金,我們依據的,就是當日各自拿著的議單了。議單上寫明:“過五月張處不交房價,聽從徐處解議”。這意味著五月張天植如不交付二株園的全款六百兩銀子,協議自動解除,二株園聽從房主徐柯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徐柯提及交易初期兩人所執憑證用的是“議單”一詞,議單相當于正式交易的前奏,處在協商階段,在議單上會議定正契交易的房屋、時間、金額等事項,并不是正式合同文件。而張天植一開始就是要求“以廿金立數百金契”。契,即大契或正契,是正式的契約了。兩人各執憑據上的“五月”,其實應該是正契交易時間,那徐柯自然將憑據定義為議單而非正契。
從徐柯敘述的內容看,兩人簽訂的也確實是議單而非正契。更何況,張天植只付了二十兩,理所當然只能看作議單商定的定金。徐柯認為,“四月之約,閣下自爽之,五月之期,閣下自逾之,六百之銀,未見分文也”,那么這張議單實際上已經作廢了。但是賣者無意,買者有心,到了五月,徐柯沒有等來張天植的全額付款,卻等來了申菽老的口信:
“徐柯欺誑,必罰契面加一方已。”
既云“契面”,可見申菽老和張天植都視當日所立議單為正契,反咬徐柯一口。既云“欺誑”,就意味著是徐柯沒有信守承諾,違背了契約精神,需將二株園房產賠付給張大人。徐柯怎么沒有信守承諾?“產非爭執,交無重疊,價未入手,所欺何事?所誑何物?”徐柯一聲哀嘆。這“欺誑”,莫非表現在都五月了徐柯還沒有搬離此屋,把約好賣掉的二株園拱手讓人?估計徐柯半天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好一個空手套白狼!將議單當作正契,總價二十兩騙走了我的百年老宅!
徐柯心中納悶,但轉念一想,為張大人的致富奇路拍案叫絕:
“吳中故家棄產者眾矣,閣下盡將一二十金誘之立契,或千金,或數千金,而閣下飄然遠行,許以過期解議而盡罰之。閣下此役,可以致富矣!”
清初因易代、戰亂,許多望族破產,家業蕭條,失去收入來源。那么多人靠變賣祖業維持生計,您張大人每次以十兩、二十兩誘騙別人立契,然后出去逍遙到所議期限之后回來,再以“必罰契面加一方已”來找人賠付房子,豈不是能發家致富,成為房產大亨?
徐柯還在想著的時候,申菽老傳話了:“你到底搬不搬?你再不搬,張大人要出動撫憲、道憲趕你了啊!”申菽老不是開玩笑的,話音剛落,官府的朱票已經塞到了徐柯手中。朱票剛到手,押逐的朱簽也飄然而至。朱簽、朱票相當于法院傳票,說明張天植未和徐柯商量,已經告官并獲批,是真正的有恃無恐,好一場精心策劃的攘奪房產陰謀!
握著朱票、朱簽,徐柯徹底清醒了,清朝新貴一到,自己的百年祖業必須騰籠換鳥,官府對徐柯一家下了驅逐令,徐柯賭氣表示“愿身率妻子,露處道周”。
他必須空出大宅子恭候張大人大駕光臨,并倔強地說:“即有價銀,有死不敢領矣。”您張大人就算給我六百兩銀子,我徐柯也萬萬不敢要。話雖如此,徐柯還是耐著性子給張大人說了個蘇軾買房的故事:蘇軾在陽羨五百兩買了座宅子。有一天月下散步,聽到有人慟哭。過去一問,老人哭哭啼啼說:“我家祖傳的老宅,被我兒子賣了,轉徙來此,悲從中來呵!”蘇軾打聽下來,這老宅竟然是被自己買了,立刻回家取券當著老人面燒了,又讓老人兒子扶著她回家了。也許是想要喚回張大人的良知,說罷這個故事,徐柯恭敬地稱張大人“今日之蘇文忠”,好意勸張大人去申菽老處領回二十兩,議單作廢,這事就此了之。如若不然,徐柯聲稱自己“室真懸磬,命等鴻毛”,實在不行,“干冒威嚴,得死為幸!”然而,“今日之蘇文忠”不比真正的蘇文忠,徐柯的故事應該不會奏效。
這場因二株園而起的房產糾紛是否平息了呢?徐柯沒有再提及,根據尤侗《東海一老傳》和徐柯《田孺人小傳》記載,他離開二株園之后,去了湖州,后來潦倒落魄,又回到蘇州,輾轉流落于紫瑯、采蓮涇、陰陽里,又僑于雙井里,最后寓居臨頓里女兒家。康熙二十九年(1690),徐柯作《同潛夫、蕙農仲元宅看牡丹,酒間次潛夫韻》,小序中對二株園仍念念不忘:“余有牡丹癖,二株園數本,亂后重植,自甲午、乙未至乙卯、丙辰,花時賓客,升沈存歿,星離雨散。今又十四年,親朋喪亡略盡,而聞園花尚無恙。”此時的徐柯已六十五歲,二株園早已落入他人之手,昔日眼前的數本花中之王牡丹,如今雖然無恙,卻已經不能看,只能聽聞了。
九年后的中秋,尤侗在虎丘船上偶遇徐柯,這一次相遇,令尤侗感慨萬分,徐柯幅巾布袍,手扶藜杖,雞皮鶴發,皤然已成老翁,再無初識時的翩翩之概,兩人追話疇昔,慷慨傷懷。此次見面竟成訣別,次年二月初七,遺民徐柯在齊門的某一處寂寂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