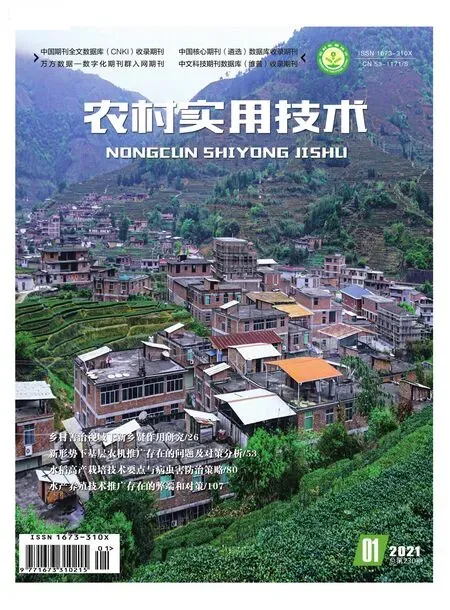鄉村善治視域下新鄉賢作用研究
宋雨
(山西師范大學,山西 臨汾 041000)
俞可平將“善治”歸納成十個基本因素,即合法性、法治性、透明性、責任性、回應性、有效性、公民參與、穩定、廉潔和公正。他認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治理過程”,從某種程度上說,實現善治的過程就是國家權力不斷下放的過程,是在處理社會事務中公民群體更發揮更大的作用。基于本文的研究對象——鄉村社會,因此“鄉村善治”可以被界定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農村基層治理過程。而實現鄉村善治的一個重要參與者便是脫胎于傳統社會中的新時代鄉賢(也被稱為新鄉賢)。新鄉賢有知識,有能力,最重要的是有鄉情,他們成長在鄉村,深深嵌入到鄉土社會的關系網絡之中,是鄉村共同體不可分割的一員。而鄉賢文化源遠流長,具有深厚底蘊,在傳統社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新時代鄉村振興的背景下,鄉村治理面臨著嚴峻挑戰,這是構建鄉村善治的時代要求,也是重塑新鄉賢文化的實踐所向。
1 新鄉賢是鄉村自治的重要參與者
鄉村自治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重要途徑,自治能夠有效調動村民的積極性,發展鄉村基層民主,維護村民合法權益,推動鄉村社會和諧有序的發展。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在三十多年的實踐過程中,農村基層自治所面臨的現實困境。
一是村民的參政意識淡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受教育水平程度所限,大多數農民對自身權利與義務認識不夠明確,同時缺乏法律意識,難以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傳統的“官本位”思想依舊在農村大行其道。在很多農村,村干部、村民對農村基層自治制度以及權責的權責認識不清,村干部覺得自己就是村里最大的“官”,擁有絕對的權力,村里一切事物都由自己做主。村民覺得村干部就是領導,是管理自己的人,不敢對他們提要求,更別說進行民主監督。錯誤的角色定位,某種程度上造成了村民與村委會的對立,公共權力的異化使得本該服務村民的村委會,變成了村干部以權謀私的工具,村干部把村委會當成了自己斂財的工具,民主監督、民主管理形同虛設。這種行為不僅影響了村委會的正常運行,更加嚴重阻礙農村基層治理的現代化發展。
二是村民自治的內驅驅動力不足。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鄉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追求更好的生活,大批青壯年勞動力紛紛外出求學、打工,農村剩余人口大多為婦女、老人、兒童,社會空心化現象嚴重。另一方面,中國傳統鄉土社會中的村規民約正在逐漸弱化。數千年來,鄉約在教化民風、實現鄉村有序管理上發揮重要的作用,某種意義上鄉約成為村民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村民自治的現實基礎。而現在農村精英的流失和村規民約的弱化導致了村民自治的內驅動力嚴重不足,缺乏凝聚力,自治效果自然并不理想。
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成為鄉村自治環節的協作者和參與者,將極大改善當前自治局面。在“皇權不下縣”的傳統社會中,鄉村社會的穩定正是依靠著鄉賢主導,鄉約保障。鄉賢作為鄉土社會最有權威的一個群體,對于當地的社會建設、風俗教育發揮了主導力量,是我們去研究鄉村自治發展的重要歷史依據。新時代鄉賢群體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傳統社會的架構沒有完全坍塌,鄉村社會中錯綜的人際交往方式,以血緣維系的家族和鄰里關系依然廣泛存在于鄉村之中”,新鄉賢再一次成為了村民自治的重要參與者,成為鄉村多元協同治理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在參與農村基層自治過程中,新鄉賢擁有親緣、人緣、地緣的天然優勢,可以及時掌握村民所想所需以及實際情況,在處理人際矛盾,維護社會良俗、引領鄉風文明建設方面,做到有的放矢,充分發揮多元協同治理的作用,致力于農村社會和諧有序發展。2011年云安縣成立了該縣第一個橫洞村鄉賢理事會。成員主要由企業家、學者、離休干部以及外來代表所組成,旨在與促進村民自治,提升公共服務,堅持“民事民辦、民事民治”原則,對村莊的重大問題進行民主決策,公開透明,便于監督:“一事一議”,“三議三公開”。理事會動員全體村民以及“不在場”鄉賢籌措資金,進行村莊改造,完成了垃圾分類、人畜分離、污水分流等環境綜合治理工程,同時修建了閱覽室、廣場、議事廳等休閑娛樂場所,集合村民力量推動鄉村公益事業的發展。在鄉賢參事議事會的協助配合下,不僅可以有效化解鄉村治理危機,而且能夠推動鄉村公共服務事業的發展,推動基層治理能力現代化。“村兩委+新鄉賢”有利于彌合村兩委與村民之間存在的疏離感,解決村民自治能力確實的問題,適應農村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生巨大變化后對“鄉土社會”的治理結構進行調整的要求。
2 新鄉賢是鄉村法治的踐行者
“法者,治之端也”,法律是實現國家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全面依法治國深入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全面建設法治國家不僅在于國家層面、社會層面,更關鍵的是基層法治,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在基層,工作重點在基層”,“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勢在必行。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提出“積極發揮新鄉賢作用”,要“建設法治鄉村”。
經過四十多年的民主法治建設,我國鄉村法治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期間國家頒布了20多項農業法律 ,制訂了60多項惠農行政法規、加上460多部部門規章、大批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的實行,鄉村法治體系基本完成。但是與城市法治建設相比較,鄉村法治建設總體較為薄弱。輕法治重人治的現象仍然十分普遍,多數村民法律意識淡薄,打架斗毆、越級上訪時有發生。不僅僅是村民如此,村干部中有些人同樣缺乏法治觀念,不懂法更不會用法,工作中依法辦事能力十分有限。導致村民與村兩委產生隔閡,難以有效推進農村法治工作有序進行,更影響了農村基層治理現代化。而新鄉賢由于知識文化水平高,相較于普通村民法制意識也更有優勢,因此發揮鄉賢參與鄉村法治建設,對破解現實困境具有積極的意義。
新鄉賢群體大都是專家、學者、退休干部或是企業家,他們接觸法律的機會相對較多,不僅法律知識豐富,也更加了解法律程序,明白法治的意義。憑借天然的優勢,新鄉賢有能力更有條件憑借自己的法治素養去幫助村民提高法律素養,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帶頭人,協同推進鄉村法制建設。首先,新鄉賢能夠帶動村干部、村民提高法治意識、增強守法觀念。新鄉賢大都是專家、學者、離退休干部和企業家,這些人相較于普通村民擁有更高的法治素養,不僅懂法、守法,更會用法。在開展普法教育宣傳,提供法律援助活動的時候可以憑借親緣、地緣優勢,針對村民實際情況進行,令村民從具體實踐中學習法律,從而理解法治,接受法治,潛移默化中培養法治精神,增強法治素養。另一方面,新鄉賢群體在當地都擁有一定的影響力,不僅是“法律明白人”,更是法律的踐行帶頭人。他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依法辦事,嚴于律己為廣大村干部做出表率,促使村干部以更加規范的標準要求自身,提升學法、守法、用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為農村基層治理能力現代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其次,新鄉賢可以有有效監督基層政府的執法行政行為,引導村民用法律解決問題、化解矛盾沖突。新鄉賢具有較強的權利意識、責任意識,因此他們在參與鄉村治理的過程中,可以憑自身知識儲備和影響力對公職人員開展有效監督,推動基層政府實現依法行政,監督基層政府在處理救災扶貧、土地拆遷和集體財產處置等工作時,做到公平、公正、公開。實踐證明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新鄉賢的功能得到進一步優化,新鄉賢的示范引領作用也大大降低了基層政府的行政成本,使得村民在“潤物細無聲”中受到法律的熏陶。
近年來黎川縣成立了15個“鄉賢說事堂”,60多名新鄉賢參與化解林權、家庭和鄰里等矛盾糾紛300多起,將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本著“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的原則,能夠解決的問題村兩委和新鄉賢馬上組織人員進行調解處理,對處理不了的及時報告。與此同時,縣里廣泛開展“法律顧問+明白人”工程,進行普法教育,讓村民知法、用法、守法、敬法、護法,創設辦事依法、遇事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環境。培養村民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維與習慣,打通法律服務最后一公里。
3 新鄉賢是鄉村德治的推動者
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提升鄉村德治水平,深入挖掘鄉村熟人社會蘊含的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進行創新,強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導農民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重義守信、勤儉持家。鄉村治理體系中,德治起著重要的引領作用,是提升鄉村社會治理能力水平、實現鄉村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德治不同于法治,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規章制度。德治是一種柔性約束,是從內在約束人們的一言一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的擴張,鄉土社會原子化,“熟人社會”逐步瓦解,傳統的價值觀念受到猛烈沖擊。與此同時,多元化的思維觀念,互聯網的發展也讓村民的道德規范向碎片化、邊緣化發展,給鄉村德治建設帶來極大地考驗。
一是傳統鄉村中倫理道德解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加深了村民自我意識的覺醒,與此相對他們的集體觀念和公共意識一定程度上也被削弱。個人意識在市場經濟的催生下不斷放大,村干部以權謀私,失職瀆職現象時有發生;村民為追求個人利益,常因宅基地,補貼等問題與鄰里產生糾葛。金錢主義大行其道,尊老愛幼等傳統美德被人遺忘,出現了大批空巢老人、留守兒童,老無所依,幼無所養。此外,鄉村環境也急速惡化,傳統中的鳥語花香,裊裊炊煙已經被各種垃圾,殘垣斷壁所替代,公共衛生環境十分惡劣。二是鄉村德治主體缺失。為了更好的發展,大批村民選擇背井離鄉,進城務工、求學。主要原因是城市的擴張不斷壓縮鄉村的發展,鄉村社會無法滿足村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年輕一輩渴望更高質量的生活環境,不再接受傳統的鄉村生活方式。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鄉村社會空心化愈演愈烈。三是鄉約衰微,約束力減弱。相較于法治的強約束力——讓村民不敢為,德治更像是軟治理——讓村民不想為,自發地遵守鄉土社會的行為規范。傳統社會中德治外化于鄉約,涉及到鄉村的方方面面,事無巨細,引導村民更好的生活。而城市化的沖擊,鄉土社會的萎縮,鄉約的權威衰退,人們對于傳統的規范不在無條件遵守,鄉約作用的發揮受到了極大地限制。考慮到這三個方面,新鄉賢參與補充鄉村德治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新鄉賢本身具有較高的思想道德素質,是鄉風文明和良好家風的示范者和引領人。 以新鄉賢為主的社會力量參與鄉村德治不僅有助于完善目前鄉村德治體系,而且能夠改變當今鄉村德治徒有其表的狀態,有助于鄉村德治建設從口號宣傳到實踐落實,使鄰里糾紛從事后控制轉變為事前調解。廣東省云浮市新興縣采用了“村兩委+新鄉賢”模式,新鄉賢充分發揮道德示范作用,積極協助村兩委工作,幫助解決鄰里之間的矛盾,建設和諧友善的美麗鄉村;同時,他們還成立了助力鄉村發展的智囊團,樹立榜樣、身先垂范,動員村民齊心協力一起建設家園;積極引導村民向上向善,促進家庭和睦,營造尊老愛幼的良好氛圍。
2011年,澤羅坊成立了鄉賢理事會,在村兩委的支持和鄉賢理事會的推動下,澤羅坊建立了鄉風文明長效機制,建立星級文明戶評比制度、黨員責任區、清潔衛生評比等一系列制度,穩固治理成果的同時促使工作逐步完善開展。每個季度,鄉賢理事會都會協助村兩委,和村民代表一一打分。評選內容主要有“愛黨愛國”、“院有凈香”、“家有書香”“創業有成”和“家庭和睦”5個部分,各部分依次打分,按照總分評定星級。分數高的家庭,鄉賢理事會發放各種獎品作為獎勵。新鄉賢所帶來鄉村德治水平的提高,在稔村鎮壩塘村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2009年壩塘村成立了鄉賢理事會,新鄉賢在村兩委的大力支持下積極改造鄉村,在大家的努力下街道干凈了,村容整潔了,大家休閑娛樂也有了去處,廣場舞、舞龍舞獅代替了賭博、麻將,傳統的文化煥發了新的生機。
新鄉賢是村民和村兩委之間的粘合劑,也是破除陋習樹立新風的榜樣力量。在實現鄉村善治的過程中要積極融合運用多元治理資源,以黨建為引領,以人民為中心,以自治為基礎,以法治為保障,以德治為支撐,使民意、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同時,為解決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過程中的困境,一方面要建構法治框架,給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提供合法平臺,保障自身權益;另一方面要從思想上進行引領,調動地方政府和村兩委對于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引導和扶持,從根本上激發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協助黨和政府最終實現鄉村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