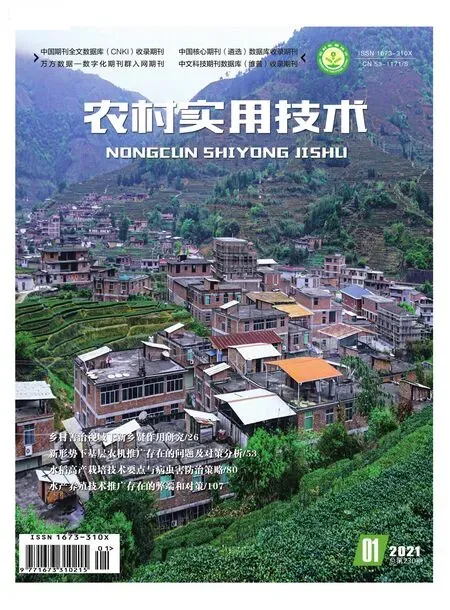中國特色生態扶貧理論在青海的實踐
賈東燕
(青海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青海 西寧 810008)
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扶貧理論
關于生態扶貧的相關論述:“生態扶貧指從改變貧困地區的生態環境著手,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從而改變貧困地區的生產生活環境,使貧困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新的扶貧方式”[1]。從一定意義上說,一個地方的貧窮是由于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系失敗導致的,貧窮使得人們無法可持續的利用自然資源,對生態系統也造成了極大壓力。我國還是一個正在發展的國家,國土廣袤,地形地貌千差百態。東部地區毗鄰海洋,降水豐富,可利用的資源較為豐富。西部地區海拔較高,氣候干燥,以高山高原為主,海拔較高,氣候相對來說比較寒冷,生態環境也很脆弱。導致我國扶貧開發工作與生態建設工作在區域與目標上都存在著高度的重疊[2],決定了我國的扶貧工作必須要兼顧二者,難度也大大增加。基于這樣的現實條件也形成了我國獨特的生態扶貧理論。
2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理論在青海的實踐
坐落在青藏高原東北部的青海省,擁有超過3000多米的海拔,是典型的的高原山地省,山地的面積超過了全省總面積的一半,可以說是生態環境非常脆弱的地方。在國家劃分14個特困區中,青海省就占了兩個,除此之外,全省的40多個縣級單位被劃入。在2012年,三江源區和環青海湖地區仍然有432個貧困村不通電,167個村子不通公路,貧困人口有84.6萬,400多萬頭牲畜飲水困難[3]。青海省為保護生態環境采取了很多措施:
2.1 通過資源的定向供給,實現了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2019年,青海省頒布了一系列政策,實施了打好藍天、水源保衛戰等相關措施。退耕還林和森林保護等生態工程開展的如火如荼,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綜合治理了山、水、林、田、湖泊。
2.2 依托原有的生態資源開展扶貧產業,實現經濟的包容性增長
習總書記講過“生態就是資源、生態就是生產力”。應習總書記的號召,青海在原有的生態資源的基礎上,發展了牦牛、藏羊為主的養殖業以及黑枸杞、蔬菜為主的種植業。當地的文化產業、民族手工業和鄉村旅游業等作為扶貧產業,通過賦予產業生態新的實踐,形成了一條生態鏈和產業鏈互相融為一體的“生態+”特色產業扶貧路徑,村民的收入也得到了極大地提高。
2.2.1 發展生態系統循環的經濟產業,推行種養立體循環發展管理模式
青海省少數民族眾多,就拿哈勒景蒙古族鄉來說,全鄉的發展思路是“保生態、調結構、提質量、穩增長”,在這個思路的影響下形成了“一個村子打造一個品牌、主業和副業全面發展,全鄉安排的很整齊”的發展格局,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當地的經濟向著良好的方向發展,農業和牧業巧妙的融合發展。農牧民的收入提高,日子也過得越來越好。除此之外,哈雷景鄉的循壞可利用的養殖模式,使得土地的肥沃力得到改善,飼草產業得到了良好的發展。畜牧業由原來傳統的分散養殖向規模化養殖的方向發展,由單一的飼養向標準化經營的方向發展。
2.2.2 利用特色生態產業,實施差異化“生態+”產業
青海省實施生態帶動扶貧戰略。青海強調生態與產業一體化,并在此基礎上,利用生態多樣性復雜的優勢,根據資源、產業和市場需求的不同,全省采取了“區域地帶”的發展格局,堅持依據人口分配土地,依據文化農牧業等先天資源對產業進行分類,使得當地人依托天然的優勢有效的利用資源脫貧致富,如青海省東部地區由于緊緊圍繞著湟水、黃河,種植了樹莓、核桃以及蔬菜為主的特色果蔬產品;環湖周邊地區水源充足,枸杞、蔬果、草料和珍貴藥材為主的種植業、藏系綿羊、牦牛繁殖術為主的生態農業畜牧業在這塊地方得以發展。除此之外,借助自然地理條件,打造精品旅游景點發展旅游業。青南地區建設試驗區,即關于生態畜牧業里的有機畜牧業的發展,由于青南地區自然條件相對而言較為優越,物流業得以發展,因此現代化的商貿市場得以產生。隨著三江源國家公園的成立,旅游資源得以充分發掘。例如:曲麻萊,被稱為“江河源頭第一縣”擁有高質量的空氣,沒有經過污染的土地和達標的水源,具有種植半野生中草藥的天然優勢。將這些中草藥打造成品牌,通過網絡傳播,取得更好的生態效益。
2.2.3 生態旅游產業
青海省民族眾多,每個民族都由各自的文化,自然資源條件獨特,屬于高原高寒區,藏傳佛教文化甚是有名,擁有獨特的旅游資源,形成了三大旅游區:塔爾寺在內的東部旅游區、青海湖和鳥島奇觀在內的青海湖區、昆侖山和黃河谷地大峽谷的西部旅游區。依托獨特的文化生態資源,省內存在著眾多的名勝古跡和藏族、回族、土族和撒拉族等少數民族保留的豐富且獨特的民族風情和習俗。青海省現有世界級旅游景點、國家級旅游和省級旅游景點數量眾多。除此之外,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小汽車迅速普及,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傳統的旅游模式得到了更新。舊模式團隊旅游由于存在著人身自由受到束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同游不方便等問題,自駕游有效的規避了這些問題,得到了蓬勃發展,因此青海湖騎行、自駕游、茶卡鹽湖旅拍成為了最受年輕人喜愛的旅游方式。總而言之,青海省將各具特色的民族風情、民族民間文化融入旅游,帶動扶貧,例如,格爾木依賴于昆侖山脈豐富的文化遺產和柴達木盆地資源,依靠旅游帶動了周邊的餐飲、文化、藝術和手工藝的發展,不僅激發了農村經濟的活力,而且使少數民族文化得以保留。
2.3 扶貧生態移民,生態扶貧的逆向開發與環境移民的逆向創新
以上所列的生態扶貧路徑,都是建立在原有生態環境的基礎之上的,將生態資源的優勢得以轉化,轉化為“生態+”的扶貧開發模式。但是在青海省有些生態極其脆弱的區域內,自然條件限制無法修路,解決這些地區百姓的生活問題,是一個難題。對于這些無法在生態方面實施加法的自然環境條件極其惡劣的地區,無論采取什么措施幫扶措施都是“當地資源養不起當地人”,從而造就了一批最貧窮的人;還有一些是生態環境非常脆弱但承載著及其重要的生態功能的地區。在這些地區,企業無法通過實施上述產業扶貧方式來解決當地的貧困問題。因此,青海省創新扶貧思路,通過加法的逆向即減法,進行生態旅游扶貧的反向開發。
3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理論對青海省的啟示
青海省的生態扶貧模式,為其他省份地區的生態扶貧工作提供了可以借鑒的成功經驗,但是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1)生態扶貧不僅要保護自然生態環境,也要重視社會治理和增權制度的完善。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緊迫,在扶貧的過程中對于生態環境的保護開發有所側重,但是對社會生態性治理的側重點有所偏弱。最近幾年,扶貧資金的不翼而飛、空頭項目、重復申報等事件屢見不鮮,地方政府對于現代化治理能力的培訓缺乏,在產業扶貧當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更嚴重。“扶植大戶”模式,儼然成為象征著國家產業扶貧的代表,“大戶”成為了國家產業扶貧的主體,而那些貧困小農戶發展個體經濟,得不到國家政策的支持,在逆境中艱難成長。貧困農戶幾乎沒有被分配到任何的資源和權力,成為了社會治理利益的受損者。基于這樣的事實,社會生態的有效管理在扶貧的過程中應當加大,扶貧資源應該公平分配,確保人人享有,不能讓貧困農戶脫離,扶貧機制就能得到更進一步的完善。貧困群體能夠參與其中,讓他們不會覺得自己跟社會精英的差距越拉越大。增強了社區合理分配利益機制的能力,擴大了在社區的管理和發展中的影響力。習總書記強調“增強人民群眾特別是貧困群眾的‘獲得感’的要求”。青海省的生態扶貧,筆者將其歸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扶貧理論下的扶貧模式,就是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涵,既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義市場放任模式,又不同于傳統的過度依賴指令性計劃和高度行政化的救助式扶貧,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基礎上的實踐和創新。
(2)進一步完善生態扶貧策略,并將其納入到國家常態化發展戰略之中。生態扶貧選擇的策略是“因地制宜”,即“適合種植農作物就種植農作物、適合經商的就來經商、適合發展工業的就開設工廠、適合旅游的就開辟旅游勝地”。短期效益明顯,在較短的時間內就能取得經濟效益,將扶貧安排至“規模化、一體化”。在實際扶貧工作的實踐中,將重點放在初具經濟效益的農戶。根據當前扶貧減貧的成果來看,生態農業經濟的規模化、產業化使得農民的就業途徑有效拓寬,收入得到極大的增加。但是由于農業經濟的自身組織結構和農業生產方式存在很大的問題,更為豐富而廣大的農村經濟活力并沒有釋放出來。
在扶貧過程中存在的生態移民工程,雖然貧困戶在城鎮中得到了集中的安置,農村貧困戶享受到了城市的資源,在城鎮化工業化的進程中,貧困農戶歸根到底是在土地中解放出來的,在城市中生活困難。所以,生態扶貧的區域性和短期性政策實施,從長遠來看可能脫貧 未必致富,也未必如政府所預期的那樣“帶動貧困農戶發展”,相反卻可能同時出現“勞動不充分”和“勞動力不足”的矛盾現象,進一步強化資本對貧困人口的支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