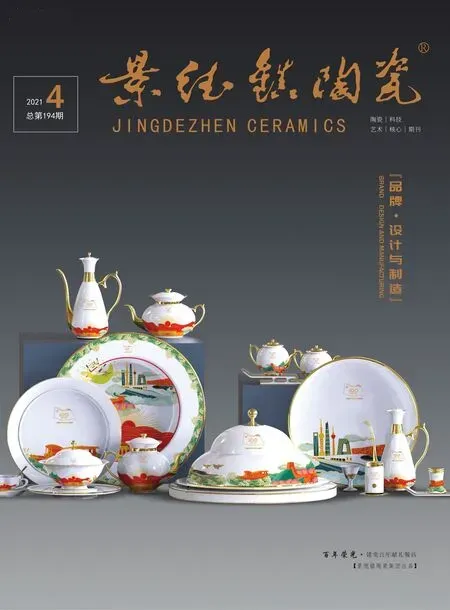“景德鎮學”應當成為國際顯學
鄭云云 李燕芬
一、“景德鎮學”的構建背景和現狀
景德鎮享有“世界瓷都”的榮譽。這座被兩千年瓷魂窯火養育的古城,曾將中華民族的偉大發明——瓷器推向極致,對世界文化和人類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
然而,自古以來,創造了燦爛的景德鎮陶瓷文化的大量陶瓷匠師,受到文化的制約,無法著書立說。而由于中國儒家“重道輕器”的傳統,文人普遍將陶瓷藝術視為“君子不器”的工匠之作,很少將其提升到文化層面來審視。雖然古代已有南宋蔣祈《陶記》、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陶埏》、清代唐英《陶冶圖說》、藍浦《景德鎮陶錄》等有識之士研究景德鎮陶瓷文化的珍貴文獻,但數量之少,與景德鎮在歷史上、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與影響并不相稱。
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對于景德鎮陶瓷文化的研究,伴隨著中國陶瓷藝術的復興,開始活躍起來,出現了一批陶瓷考古與鑒定、陶瓷歷史與理論、陶瓷工藝與材料、陶瓷裝飾技法與藝術、陶瓷交流與傳播、陶瓷文獻校注與研究、陶瓷鑒賞與審美等相關的著作。如耿寶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鑒定》、劉新園先生的《瓷藝與畫藝》、楊永善、秦錫麟主編的《中國現代美術全集》之《陶瓷卷》、秦錫麟先生主編的《珠山八友》、傅振倫先生的《陶說校注》、熊寥先生的《陶瓷美學與中國民族的審美特征》《中國陶瓷與中國文化》與方李莉女士的《景德鎮民窯》《中國陶瓷史》等等。不少學者對景德鎮陶瓷文化進行了考察與研究,但此前景德鎮陶瓷文化并沒有作為一門獨立性學科進入學術界,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景德鎮陶瓷文化研究的深入與推進,也制約了當代景德鎮陶瓷文化的創新和傳播。
2004年10月,國家“十五”規劃重點圖書《中國景德鎮陶瓷文化研究叢書》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該叢書共計六本,首次對景德鎮陶瓷傳統工藝、陶瓷習俗、陶瓷文化進行了詳盡系統的介紹,作者寫作認真嚴謹,均為對陶瓷工藝有深厚了解和實踐經驗的專家。該套叢書的價值在學術界受到公認,在社會上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叢書主編、景德鎮陶瓷文化研究專家陳雨前博士首先在書中提出構建“景德鎮學”的觀點,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反響,并得到景德鎮陶瓷學院領導層的支持。陳雨前認為,江西應集中力量在陶瓷文化、陶瓷美學、陶瓷工藝、陶瓷技術史、經濟史、傳播史、陶瓷考古與鑒定、民俗學等方面,對景德鎮陶瓷文化進行全方位研究,建設一個完整的“景德鎮學”學科體系和價值體系,重現并傳承、弘揚并重塑優秀的景德鎮陶瓷文化。他認為憑借景德鎮獨一無二的陶瓷文化遺產,“景德鎮學”有望成為國際顯學。
2006年9月上旬,江西省社科院完成了對“景德鎮學”研究課題的論證報告;9月16日,景德鎮陶瓷研究文化所暨“景德鎮學”研究中心在江西省社科院掛牌成立,并舉辦了第一次“景德鎮學”的學術報告會,自此,“景德鎮學”作為一門具有江西地方特色和中國文化特色的獨立學科由江西省社科院正式推出。
“景德鎮學”一經提出,便受到社會和學術界的重視,江西日報刊發專版文章《“景德鎮學”能否進入國際視野》,呼吁贛人應合力打造中國最大的文化品牌,借助景德鎮得天獨厚的歷史優勢,聚合人才資源,使景德鎮陶瓷文化研究經歷跨越性的發展。景德鎮陶瓷學院為此開設了全院性的“景德鎮學”選修課,又在“陶瓷美學”的碩士方向上,開設了“景德鎮學”課程。十余年來,“景德鎮學”已經在探索的基礎上,向系統性、學科性方向發展,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例如以原文影印的方式出版的《中國古代陶瓷文獻影印輯刊》(30冊),該輯刊為中國有史以來對古陶瓷文獻(清末以前)的一次大整理大匯集,這對于傳承和弘揚中國陶瓷文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彌補了中國古陶瓷文獻研究的空白,對于此前國內外學術界對于中國古代陶瓷文獻的研究和利用,有著正本清源的作用,輯刊所收集、輯錄和存留下來的大批古代陶瓷文獻第一手資料,是“景德鎮學”的最寶貴的研究資源,它的出版本身,也是“景德鎮學”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此外,經過編撰者10年的努力,《中華大典·藝術典·陶瓷藝術分典》于2015年5月正式出版,中國——瓷之母國,終于有了自己的陶瓷大典!《中華大典·藝術典·陶瓷藝術分典》從文獻角度見證了中國古代陶瓷發展的脈絡和中國古代各時期陶瓷生產的狀況,還原陶瓷在中國各民族各階層上至帝王貴族,下至平民百姓的精神生活與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狀況及作用,呈現中國陶瓷在國內外流通、影響與“陶瓷之路”的盛況,以翔實的無可爭辯的原始文獻,雄辯地證明“中華向號瓷之國”的歷史榮光,有利于提升我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這套叢書的出版,是景德鎮得名千年之后,第一次以學術形態,以系統完整的學術構架和文化視野來研究景德鎮陶瓷文化。
二、構建“景德鎮學”文化大格局的必要性
景德鎮是中國最早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的城市。
景德鎮的制瓷歷史綿長。由唐入宋,是中國古典文明達到極致的時代,也是景德鎮陶瓷開始走向高峰的時代。當時,中國的瓷窯遍布大江南北,并通過絲綢之路、海上陶瓷之路遠銷海外。景德鎮陶瓷在不斷發展工藝的同時,也在吸納異域文化而不斷演化,并極大地豐富了陶瓷的美學品位,從技術和藝術方面開始在國內獨領風騷。
至元明清,景德鎮儼然成為世界瓷都,它的產品輻射全球市場。同一時期外銷瓷興旺的窯口,還有德化窯、宜興窯、石灣窯、潮州窯、泉州窯等等,但景德鎮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城市。而此時,也正是歐洲文藝復興方興未艾之時。歐洲人通過瓷器的輸入開始認知中國。與歐洲中世紀貴族世襲的制度相比,中國特殊的文化傳統,政教分離卻又相互影響的體制,龐大多元的思想體系及其對異域文化的吸收而非照搬和排斥,讓平民可以通過考試進入國家管理階層的科舉制度,無疑屬于當時先進文化之列。而對待宗教的平和與寬容空間,儒、釋、道三教中所蘊含的哲學智慧,也是中世紀歐洲的宗教制裁所不能相提并論的。美麗的青花瓷背后的那個富庶神秘的禮儀之邦,讓剛剛走出中世紀黑暗的歐洲人無比神往,并繼而形成了長達兩個多世紀,前所未有的“中國熱”。無論是從歷史資料,還是文學藝術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由中國瓷器引發的這種影響:從貴族到平民,從皇族到學者,都對中國文化極為推崇。雖然興奮點不一樣,但對中國文明的濃厚興趣卻是一樣的。這一時期,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規模接觸和交流。雖然這種交流和碰撞是互動的,但如果說東方的審美觀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歐洲和世界,并不夸張。
宋元時期,我國古代經濟中心已完成南移,改變了漢唐以來經濟一直以黃河流域為重心的經濟格局。尤其是重心向東南方向移動,越來越靠近擁有優良海港的沿海地區。廣州、明州(今寧波)、杭州、泉州等大型港口城市相繼興起,表現出向海洋發展的強烈傾向,為中國由封閉性的自然經濟向開放性的商品經濟過渡提供了歷史機遇。
元代時,景德鎮工匠和中國商人有意識地主動進行國內外的市場開拓。在針對中東、西亞地區生產的景德鎮外銷瓷中,出現了伊斯蘭藝術風格的裝飾圖案瓷器。伊斯蘭藝術具有強烈的民族特色,崇尚青、白二色,這恰恰與青花瓷的藍白色調的特點所契合,而景德鎮此時燒制成熟的青白瓷和樞府卵白釉瓷,為青花瓷的脫穎而出創造了最優良的條件。元青花采用景德鎮優質白瓷土為胎,用進口的鈷料蘇麻尼青彩繪,紋樣繁麗豐滿,形成前所未有的藝術風格。景德鎮瓷器一反宋代追求的端莊嚴整、秀麗簡潔的外表形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碗、大盤、大罐、大瓶等青花大器。這是一次重要的文化嫁接,嫁接的前提一方面是工藝的進步,如高嶺土的二元配方使瓷胎有了做大的可能,另一方面,受東西方文化交流影響,除各種工藝創新外,元代景德鎮瓷器無論從造型還是裝飾風格上,都有了突破原有傳統的嶄新變化。
元代有一位中國歷史上最出色的民間航海家汪大淵,他在至順元年(1330年)開始從泉州兩次乘船出海,考察世界,并為后世留下珍貴的《島夷志略》。《島夷志略》中,汪大淵十分詳盡地記錄了元朝中國陶瓷外銷的國家和地區,以及陶瓷器的外銷品種。一項項具體的記錄中,在傳統的青瓷、青白瓷器之外,出現了“青白花碗”“青白花器”等不同以往的品種。從前人們以為是景德鎮青白瓷的異稱,自上世紀元青花傳世之作漸漸浮出歷史水面后,專家們認定汪大淵書中的青白花瓷器指的便是指元朝中期以后,對外貿易中最獨具特色的新瓷種:青花瓷器。據書中所載,他乘坐的商船以青花瓷器進行貿易的地區和國家有十多處,包括伊朗和北非。也就是說,元朝中后期,景德鎮青花瓷已作為外銷瓷品種遠銷到海外各國。事實上,除了《島夷志略》中所指的那些國家和地區,在東非沿岸的一些國家古遺址中,都曾發現了元青花瓷器或殘片。如在埃及,出土過龍紋玉壺春瓶、云龍蓮瓣紋瓶和蓮池鴛鴦紋碗等的殘片;在東非伊斯蘭地區,景德鎮的青花瓷,除作為日常的生活用品外,還被鑲嵌在宮殿、寺廟的墻壁、天花板上,視同鑲嵌珠玉寶石。
據筆者了解,近年考古發掘中發現景德鎮在元代有3處生產青花瓷的窯址——湖田窯址、落馬橋窯址和珠山遺址。湖田南岸的遺物大而厚重,紋飾繁縟華麗,與伊朗、土耳其的傳世品一致,而北岸的小瓶、小罐、小杯與菲律賓一帶的出土物完全相同。落馬橋至正地層出土的青花則主要是為了滿足國內各地區各階層及東南亞一帶的普遍需求而制作的商品瓷;而珠山遺址則完全是為元代皇帝燒造的宮廷用瓷。
世界上收藏元青花瓷器最著名的地方,是伊朗阿迪拜爾神廟以及土耳其伊期坦布爾的托普卡帕宮。托普卡帕宮收藏著來自中國的玉器、青銅器和上萬件瓷器,所藏40多件元青花瓷器都屬至正型精品,瓷器上以伊斯蘭多層裝飾帶風格,繪著牡丹、菊花、松、竹、芭蕉、瓜果、池塘游魚、山水以及中國傳統的麒麟、鳳凰、龍等紋樣。伊朗阿迪拜爾神廟則是收藏中國瓷器最為著名的收藏館之一。關于神廟所藏的中國瓷器,美國華盛頓菲莉亞美術館波普先生在1956年曾出版過《阿迪比爾寺中的中國瓷器》一書,介紹了代表性器物。其中元青花32件,藍釉瓷1件,還有幾件青瓷。元青花之中,有19件盤,2件大缽,5件梅瓶,3件廣口罐,1件葫蘆瓶,2件扁壺。在德黑蘭考古博物館里也陳列著37件元青花大型器,同伊斯坦布爾托卡普帕宮博物館性質相似,器型有梅瓶、缽、大盤等等。
里奇的這段話提醒我們,照片的標題和文字說明對攝影的社會性使用可能是好事,但它也將照片限定在單一的狀態里,無法開啟多元的意義,自然也就會阻礙攝影的多元拓展。然而,“多元性”“態迭加”是量子—數碼攝影時代攝影的最重要特征。筆者簡單提取這段話的關鍵詞就可以引出里奇對數碼攝影的定義:“引發能量共享狀態”“承認空間—時間的可塑性”“更多延展”“非線性的”“多層次的復雜存在”,這就是數碼攝影,這些也成為其區別于傳統攝影的關鍵。因此,我們可以用牛頓力學—傳統攝影和量子力學—數碼攝影來理解傳統攝影到數碼攝影的發展轉向以及它們之間的差異。正如里奇置評說:
中國元青花的數量極少,以至上世紀初人們還都認為元朝無青花。為什么這兩地會保存有這么多的中國元青花瓷?為什么元代景德鎮青花瓷采用的鈷料被人們稱為“蘇麻尼青”?在梳理這些問題時,筆者深感歷史與文化的交織是多么的奇特,它永遠不會讓一件事物孤立存在,就像春天花開,秋天落葉,總有它的緣由。就像一棵大樹,下面盤根錯節的樹根遠比上面的枝葉更為龐大復雜。
且讓我們回顧一下中古的歷史。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原名君士坦丁堡)是一座海港城市,曾經是古代陸上絲綢之路通向歐州的唯一通道。唐代中期以后,當陸上絲綢之路因戰爭時阻時斷后,它又成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點。在這里集中發現中國古代最大宗貨物之一的瓷器,是一點不奇怪的。在托普卡帕宮收藏的40多件元青花中,有碗、盤、梅瓶等不同器皿,圖案以花卉、龍紋、鳳紋為主,沒有人物圖案,這也與伊斯蘭教有關,因為自古以來,伊斯蘭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這些器皿的青花發色濃艷,紋飾繁密,具有濃郁的伊斯蘭裝飾風格,可以看出在當時就是面向伊斯蘭地區生產的瓷器。上世紀初,中國的一個專家代表團經土耳其總理的批準,進入該宮考察元青花,并親自上手考察了幾十件館藏作品,這是參觀者從沒有過的待遇,見證了土耳其人民對源遠流長的中土兩國文化交流之感恩。因為上手考察是所有研究古物的專家最渴望的一種方式,但也是所有博物館最忌諱的方式。
2007年,一批中國元青花研究學者應邀來到伊朗國家博物館,進行元青花的考察。這是雙方第一次合作。而此前,伊朗方面已將館藏的28件元青花的所有正面、底面、細部圖片給了中國客人。中國專家們兩次進入庫房,總共工作了八個小時,拍攝了200多幅寶貴的青花釉面微觀圖,成為國內研究元青花的重要資料。
此行中,伊朗國家博物館的專家告訴中國客人,波斯古籍中有過記載,元朝時,波斯工匠曾被派到中國去學習制瓷。元朝時期,伊朗與中國都是蒙古人統治,1260年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率兵占據波斯并建立以波斯為中心的伊利汗國。此后,蒙古人逐漸接受了伊斯蘭教,并任用波斯人為行政官吏。當時的伊朗地區是阿拉伯——波斯文化的中心,元代時兩地交往之頻繁密集超過任何一個時代,波斯工匠到中國來學習制瓷也完全有可能,元朝時中國瓷器裝飾風格和造型都深受阿拉伯和波斯文化影響,元青花的脫穎而出,正是這種東西文化大回旋的璀燦結晶。
就在伊朗首都德黑蘭南部大約400公里的地方,有一個叫“Ghamsar”的村莊,屬于卡尚市。這個小村莊的人在古代就發現了閃著銀色光芒的石頭,當地人叫“穆罕默德藍”,即現在學名叫“鈷”的礦物,石頭經粉碎提煉后為黑色,但一經火焙燒便發出藍艷之色,波斯人用以裝飾清真寺。因為石頭的神奇,當地人用伊斯蘭圣人的名字“Soleimani”(蘇來麻尼)稱呼它。這種礦物,經研磨后即中國人所謂的“蘇麻尼青”。
西亞早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500年就已使用含砷鈷料制造藍色玻璃釉,西亞一帶先后發掘出許多帶有鈷藍釉裝飾的文物。此外,西亞伊斯蘭世界9至10世紀就已接受中國長沙窯彩繪瓷的影響,出現白釉藍彩陶器,色調類似青花。英國學者哈里·加納在他的《東方的青花瓷器》一書中提到“首先使用氧化鈷為著色劑進行彩繪裝飾,使畫面呈現美觀藍色的方法的地方是在近東(西亞)。九世紀時,米索不達米亞生產了一種軟陶,在其深顏色的胎骨上罩上一層含有氧化錫而不透明的白釉石,在釉面上用氧化鈷做彩料繪上簡單的圖案,然后入窯焙燒而成”,“用藍彩裝飾直接應用在胎體上再罩以透明釉的技法,首先于13世紀在卡尚被波斯陶工所使用”。
“蘇來麻尼”與“蘇麻尼”,只省略了一個音而已,古波斯的詞尾很多是“-ni”,中國典籍常譯為“尼”或“泥”,而青字,很可能是中國工匠根據鈷料的特色加上去的后綴。由此看來,中國專家們爭論不休的蘇麻尼青產地,最大可能是在伊朗。“蘇麻尼青”一詞最早出現于明朝中后期的私家著述,如成書于萬歷17年(1589年)王世懋的《窺天外乘》中云“永樂、宣德間,……以蘇麻離青為飾”。成書于萬歷19年(1591年)的《遵生八箋》有“宣窯之青,乃蘇勃泥青”。《長物志》著錄有宣德“蘇麻尼青盤”。它們發音近似,應該是同一名詞的異音。
在一些元青花瓷上,人們還發現過波斯文字,經伊朗專家分析,可能是工匠的簽名。伊朗工匠有對自己作品留名的習慣。如果真是伊朗工匠的簽名,就是說元朝時景德鎮曾有伊朗工匠生活在那里,并根據西亞人的審美要求在景德鎮瓷坯上,繪制具有典型波斯風格的青花瓷,運往西亞。而景德鎮當地的工匠也從伊朗工匠那里學習了這種構圖,并在隨后的生產中加以中國化的改進,從而出現了一種嶄新風格的裝飾,為明清青花瓷的崛起作了最扎實的鋪墊。
元青花所用鈷料來自波斯地區,已有許多事實依據,并被絕大多數學者認可。青花瓷作為一種影響深遠的裝飾形式,主要是在中國發展起來的。或者說青花瓷最初在中國出現,是為出口伊斯蘭世界而生產,但在具有吸納異域文化博大胸懷的中國工匠手中,它們完成了與固有的民族文化相結合,在元代工匠們集體創造性改造下,最終形成了新的民族藝術形式。
明清時代,瓷器成為西方人眼中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的載體。永樂大帝修建的南京瓷塔,作為中國標志物,在歐洲廣為人知;鄭和下西洋的文化壯舉,不僅確立了明初永樂朝世界強國的地位,也將中國文化傳播四方;明朝中期,中國商品經濟已開始處處顯示出它的活力;市民階層正在成為活躍的社會力量。最先感受到時代氣息的知識分子,推動了明代在思想和文學藝術各個領域出現的變革和繁榮。在西方文化和市民文化影響下,景德鎮瓷器開始展示出一種闊大的世俗美,因此有了吳昊十九這樣的制瓷名家和他的卵幕杯,有了宋應星和他的《天工開物》,有了偶然出現在明朝馮夢龍小說中,而在景德鎮處處可見的“紅店”現象。風靡西方的中國青花瓷和五彩瓷,正是大量出自這些從事彩繪業的民間“紅店”。
在此一歷史階段,在西方人心目中,中國是世界文明的巔峰,是一個奇妙的完美國度。當時歐洲各國的君主紛紛聘請藝術家們仿制中國瓷器、餐具,建造中國風格的亭臺樓閣。而明清開始,中國青花瓷作為“國瓷”,在世界的流布之廣,則是因為它以唯美的方式,凝聚了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結晶。在逐步同化了元代伊斯蘭風格的影響后,從儒、釋、道哲學和中國傳統美學中產生的青花紋飾,將大自然與萬物之靈相融一體,古老的中國哲學所崇尚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形象地展現在青花瓷的動植物圖案、山水、人物和花鳥的紋飾上。任何自然形態的物象,一旦進入藝術領域,必定是人工與自然的高度和諧,青花就是從這個前提下進入人文世界的,并在創燒以后的幾百年間始終成為中國外銷瓷器的主流。明清時代景德鎮并無近海港運輸之便利的條件,當時能在外銷瓷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除了瓷器的不斷創新精美無雙,與它創造和擁有了當時最先進合理的物流業也是分不開的。當時景德鎮成為中國瓷器產銷中心,除了國內市場擴大,海外貿易更是“器行九域”。其他名窯在景德鎮窯所產精美豐富的品種沖擊下,漸趨沒落之勢,從而使景德鎮瓷器最終占領了全國市場,也成為外銷瓷中最受歡迎的品種。各地商賈聚集景德鎮,更使景德鎮日益走向繁榮。“工匠來八方,器成天下走”,成為明清景德鎮制瓷業興盛景象的真實寫照。
這么龐大的銷售網絡,而瓷器又不是棉麻絲帛,運輸起來必須得十分小心,以免破損。當時是怎么做到的呢?
可以說,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奇跡,因為從明代開始,景德鎮就有了今天所說的現代意義上的物流業,而且與現代物流業的功能不相上下,甚至更加細心和完備,因為瓷行的出現,不僅為客商包攬運輸,還能為客商提供采買和住宿的一條龍服務。也許因為瓷器是一種特殊商品,也許是因為自古以來商人的地位在景德鎮就受到重視,明清時景德鎮為長途販賣瓷器的商賈服務確實周全到位,并以誠信為第一,瓷器在運輸過程中,甚至無須貨主押運,均能如數到達。這是當時其他手工業發達城市所無法相比的。
十六世紀國際貿易民間文化交流新航線的開拓,引發了新一輪的規模空前的東西方經濟文化互動。16至18世紀,是中國外銷瓷生產與貿易的黃金時代,歐洲市場對中國瓷器的巨大需求,國內民間海外貿易的高度活躍,共同促進了長達兩個世紀以來中國外銷瓷龐大的對歐輸出量。明初,景德鎮民窯開始為國內和國外市場大量生產日用青花器皿。明中期以后中國社會的結構改變,商品經濟的活躍已開始逐步削弱皇權的影響,晚明時期中國社會的思想極其活躍,資本主義的萌芽已開始生長并壯大,這一切都刺激了景德鎮瓷器由藝術特性向商品特性的轉換,并迎來了一個完全嶄新的發展期。此時的景德鎮民窯青花瓷繪畫吸收了宮庭院體畫、文人畫,明代小說插圖版畫等藝術給養,同時納入了民間繪畫自由瀟灑開放的格局和性情,百花齊放,異彩紛呈,加上各地國產青花料的成功開采,從而開創了明代民窯制瓷業發展最為輝煌的時代,為清康熙時期青花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