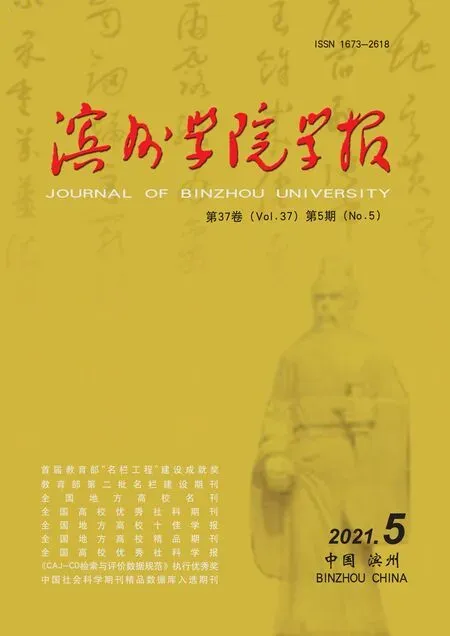嵌入與發展:社會工作介入社區治理的現實邏輯與推進策略
劉艷艷
(濱州學院 乘務學院,山東 濱州 256603)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中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在全新的社區治理格局中,專業社會工作介入社區治理成為社區建設實踐發展中的普遍模式。專業社會工作參與社區治理主要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實現,社會工作如何有效嵌入基層社區治理,進而實現嵌入式發展,成為當前亟須回應但尚未解決的核心議題。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體制及社區、社會工作者、社會組織協同合作的“三社聯動”體制的逐漸成熟,專業社會工作獲得了嵌入基層社區治理的結構性框架。社會工作以其獨特、專業的方法參與到社區治理之中,小至一對一的居民服務,大到推動居民參與和社區自治,運用個案、小組、社區組織、政策倡導等多種專業方法,面向社區居民尤其是貧困者、老年人、兒童、青少年、婦女、下崗失業人員、殘疾人、流動人口等社區弱勢群體開展柔性化、專業化服務,形成了與傳統社區治理迥然不同的工作手法及工作內容,為社區治理內容的優化與革新做出了突出貢獻。
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包括購買社會工作崗位與購買社會工作項目兩種形式。
購買工作崗位的操作模式為由政府提供資金為企事業機構、社區等進行社會工作崗位的購買,通過社會工作機構來對社會工作崗位進行競標,這些機構在中標之后派遣社會工作者入駐服務機構來提供服務。如杭州、青島等城市曾采用購買社工崗位的形式向社區派駐社工,協助開展養老服務。[1]崗位購買最大的優勢在于確保了服務的長期性和穩定性,其最大的弊端在于由于社會工作主體性弱而易被派駐單位的行政力量同化。購買社工服務項目的形式源于廣州,后來在全國范圍推開,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招投標流程。廣州市政府購買社工項目的具體做法是,街道建立居家養老服務中心,民政部門向社工機構招標,競賣家庭綜合服務,中標機構簽訂合同,提供服務。項目購買的優勢在于:一是項目服務具有綜合性,能夠滿足社區居民多層次的服務需求。二是實現了社區資源的整合利用。社會工作者可以充分動員社區內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為居民提供多種形式上門服務。三是促進了社區融合及社區關懷。其局限性在于項目的時限性難以保證服務的穩定性。服務項目的時限一般為1~3年,項目結束通過評估之后項目工作組通常會撤離社區,不再為該社區提供服務,若沒有新的服務項目進駐,會導致社區服務供給的中斷。鑒于“崗位購買”破冰難、融入難、易被行政化的弊端,“項目購買”成為當前被政府、學界較為認可的購買服務方式。
為探討專業社會工作嵌入基層社區治理何以成為可能這一核心議題,筆者對某市多家社會工作機構、社區服務中心進行了實地研究,采用參與式觀察、半結構化訪談等方式收集資料,通過實地研究發現,在復雜的街居權力網絡之內,社會工作“貌似參與”了基層社區治理,卻面臨著“難進入、難融入、難扎根、難合作”等難題[2],社會工作懸置于基層社區治理網絡不能有效建立自己的專業地位,未能實現“有效嵌入”,“嵌入而不能發展”[3]。上述情形的存在,只能說是社會工作參與社區治理的嵌入失敗。基于此,本文探討的核心問題在于,導致社會工作未能有效嵌入基層社區治理的核心障礙是什么?如何重塑基層社區治理脈絡及社區工作與街居權力關系?社會工作如何有效嵌入基層治理實踐?
二、表層嵌入與反向嵌入:社會工作參與社區治理的現實邏輯
王思斌教授提出了社會工作應當“嵌入性”發展的觀點,并認為,從政府主導下專業弱自主性嵌入到政府—專業合作性深度嵌入的跨越,是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現實路徑。[4]專業社會工作作為舶來品,其進入中國社區治理體系之初,中國基層就已經存在著邏輯嚴密的行政化治理體系,即以街居為核心的權力框架。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時,政府作為唯一的治理主體,掌握著幾乎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資源。改革開放之后實行了市場經濟體制,在經濟領域由市場參與資源配置,但在社會領域,社會力量仍然薄弱,行政全能主義雖然有所弱化,政府仍是權力、資源的中心。在社區維度上,行政全能主義管理機制的具體表現為:“政府并未和社會形成清晰的分工,基本上是政府負責對社區治理和建設的所有工作進行大包大攬,這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社區群眾、社會組織積極自覺介入社區管理與建設的體制構建。”[5]一方面,社區治理開展過分依賴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動,社區組織發育不完善,社區居民參與不足,尚未真正形成多元參與的社區治理格局;另一方面,由于社會工作機構獨立性差,過度依賴政府提供的各種資源,制約了其參與社區治理的廣度和深度。在行政全能主義的制度背景和街居為核心的權力框架之下,社會工作要獲得生存和發展,只能“嵌入”到當前成熟的基層治理體制之內主動適應,形成了社會工作弱自主性——街居強權力的現實格局。恰恰是這一現實格局,限制了社會工作的深度嵌入,使其懸浮于社區治理核心議題之外,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更遑論深度發展。筆者對某市多個社區內社會工作機構的實地研究證實了這一現實困境。以最早通過政府購買項目服務進入某市D社區的Z機構為例進行分析。
(一)案例簡介
D社區位于華東地區某市西部,成立于1990年,當時該社區內有多個破產企業,社區總人口約12 000人,其中下崗職工2600人,占總人口的22%;貧困戶1532人,占總人口12.8%。下崗職工、貧困人口數量在該市各個社區中是最多的。另外,由于該社區集中了較多的老舊小區,老年人口比例大,老齡化嚴重。鑒于社區居民對社區服務的迫切需要,2012年通過政府購買服務,Z機構中標獲得該社區服務項目運營,正式進入D社區。Z機構是該市第一家社會工作機構,成立于2011年,入駐D社區時有專職社工4人,其中持證中級社工師1人,其余皆為畢業兩年以內的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
Z機構進入社區后,在社區服務、社區治理中逐漸出現一些矛盾問題,如專業能力未能有效展現、服務成效不明顯、高度依附于原有社區治理主體、組織及資源動員能力微弱、服務項目推進處處受限與主體性薄弱逐漸被行政化、邊緣化等。Z機構在D社區的實踐表明,專業社會工作未能有效嵌入原有的社區治理體制之中,更無法進入社區治理權力格局的核心,而是浮于表面,淪為擺設。
(二)表層嵌入:Z社會工作機構的依附式發展
入駐D社區之時,Z社會工作機構努力試圖嵌入原有的基層社區治理框架,然而困難重重。傳統行政全能主義的社區治理體制,難以真正接納作為“新事物”的社會工作,對社會工作機構存在隱形排斥,社會工作機構與街居組織看似是平等的合作關系,實則被排斥于基層社區治理核心之外。
社會工作機構人員流動性強、實踐能力不足是當前困擾全國社會工作發展的普遍問題,作為三線不發達內陸城市的第一家社工機構,Z機構的這一問題更加突出。三年政府購買服務合同期內,由于人員頻繁流動,Z機構項目負責人換了3次,為彌補人手不足,新畢業的社會工作畢業生一入職就被派駐到核心崗位,新人實務經驗不足而又沒有資深督導進行專業指導,工作中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上述種種讓居于社區治理核心的街居組織形成了社會工作專業度不高的印象,也使社會工作未能在社區服務、社區治理中有效發揮作用,逐漸淪為社區治理體系中可有可無的存在。Z機構不能有效嵌入社區治理的根源在于,社會工作機構與傳統街居治理主體關系極其不對等,社會工作機構在社區治理中缺乏自主性、獨立性、話語權。
1.工作上缺乏自主性社會工作機構與傳統街居主體在關系上是不平等的,傳統治理主體居于權力中心地位,社會工作機構處于傳統治理主體的變相管轄之下。Z機構開展活動需要向社區居委會申請,有關活動場地、資金等方面的問題,需要社區書記同意才能使用,社會工作機構完全依附于傳統治理主體,為了生存下去,只能遵循街居主體的意志行動。
2.資源調動上缺乏獨立性社會工作開展服務時最重要的能力是資源調動、整合、鏈接能力。社會工作應把社區內的人才、物力、財力、文化、組織等諸多資源,以社區為平臺整合起來,同時也將社區居民、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等多方主體整合到社區一體化平臺之中。資源調動、整合能力關系到社工機構社區服務活動能否順利推進,決定著社工機構有效嵌入社區治理的成敗,反映社會工作是否真正“扎根”社區。然而,Z機構社工團隊想要調動社區內的組織、財力、物力等資源,都要聽從社區居委會的安排。社工需要取得社區書記的支持和同意,才能順利調動諸如老年人協會、婦女或殘疾人組織等社區自組織,服務的開展極大依附于社區居委會,Z機構社工團隊獨立開展社區服務的能力非常單薄,如果缺乏居委會的場地支持、沒有(被允許)的社區自組織的配合和居民參與,社工團隊在基層社區寸步難行。
3.社區治理決策層面缺乏話語權表面來看,社會工作機構與社區居委會關系上是平行的,地位上是對等的,社會工作機構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接受政府委托而進駐社區的獨立的第三方社會組織。事實上,街居治理主體處于社區治理框架的權力核心,掌握著最多的資源并擁有社區事務的決策權。社會工作機構“寄人籬下”的現實處境,使其難以站在平等地位上與街居組織進行對話、博弈、合作。社區居委會對駐區社工的管理權限延伸到社區服務的方方面面,D社區會干涉Z機構社工的具體服務,如規定社工的服務內容、服務范圍、服務指標、外出工作的時間安排,甚至隨意向社工指派超出服務范圍的行政性任務,導致社工團隊在社區內極為被動。
(三)反向嵌入:Z社會工作機構的邊緣化
在Z社工機構入駐D社區開展服務期間,街居等傳統治理主體并非被動接受或執行上級指令,而是“主動出擊”、順勢而為,工具性地與社會工作開展合作,目的是利用社工團隊為其完成一些工作任務。例如社區居委會有時會將基層政府委派的項目、活動交托給Z機構社工團隊去做,以借助社工機構來完成社區居委會不想做或難以完成的任務。可見,D社區傳統治理主體為完成社區治理目標對Z社工機構進行了“反向嵌入”[2]。街居等傳統治理主體通過其居于權力、資源中心的治理主導地位,將部分規則、資源等要素嵌入到社會工作機構,使其更好地“為我所用”。
1.難以落地的“外來者”專業社工始終難以打破“外來者”身份,未能實現扎根于社區。一方面,Z機構社工團隊在D社區沒有群眾基礎,不能與社區居民建立良好的關系,無法有效融入社區,而Z機構社工團隊頻繁的人員流動加劇了這一困境。另一方面,社會工作雖然具有專業的價值理念和科學的實務方法,但Z機構社工團隊多數為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實務工作經驗和社會經驗雙重缺乏,相比D社區資深的工作人員,開展社區工作并無優勢,反而D社區資深的工作人員與社區居民之間相互配合度、信任度更高,開展工作更順暢,工作手法更嫻熟。Z機構工作團隊對于居民、社區工作者而言始終是“外來者”,社會工作懸浮于社區,難以深度嵌入本土社區治理網絡之中。
2.為我所用的“外來者”Z社工團隊入駐D社區后,往往被認為D社區的工作人員或社區居委會的下屬,共同為社區居民服務且服從于社區居委會的安排與指揮。D社區需要完成上級委派的工作任務,但囿于人手不足或習慣于選擇性應付[6],Z機構社工團隊的入駐,為社區增加了“人手”,D社區可以把難以完成或不愿意做的工作交給社工團隊,而社工團隊由于在資源、權力方面高度依附于社區居委會,對于居委會交辦的工作常常無力拒絕。Z機構社工團隊一邊被作為“外來者”排斥于社區核心治理網絡之外,一邊作為可以被街居治理主體指揮調動的人力資源,基本沒有與街居治理主體平等對話、平等合作的可能。
綜上,社會工作難以有效嵌入社區治理有兩個原因:一是街居等傳統社區治理主體未能真正“接納”社會工作,在資源、權力等方面有形無形對社會工作的排斥、疏離使社會工作難以有效進入社區治理網絡;二是社工機構先天能力不足,不能發揮專業優勢,有效開展社區服務。雙重困境使社工機構、傳統社區治理主體之間處于不平等的權力狀態,此種治理格局社工機構難以獲得有效發展的空間。
三、有效嵌入:社會工作介入社區治理的推進策略
要破解社會工作有效嵌入的難題,需要解決上述社會工作嵌入社區治理的雙重困境,對外重塑社工機構與傳統街居治理主體的權力格局,重建平等關系;對內重塑社會工作機構專業優勢,提高自主性。
(一)身份合法性:重塑社區治理格局
作為社區“外來者”,專業社會工作需要合法的身份和地位參與到社區治理當中。只有賦予社會工作“身份合法性”,才能打破傳統街居主體在治理結構中的壟斷地位,重塑治理格局,重建平等關系。徐選國等對深圳市M社區的實地研究發現,通過黨建核心引領,“將社工項目團隊與社區工作站、社區居委會等共同納入社區黨群服務中心的架構當中,由社區綜合黨委書記進行統一整合與管理”[2],這種調整解決了社工機構的“身份合法性”問題,社工機構項目團隊與社區居委會一起,被納入社區綜合黨委書記的核心領導之下,某種程度上獲得“準體制”身份,這種“準體制”身份使社會工作機構獲得了政治合法性,有利于社會工作機構在社區內獲得社區居民、服務對象、社區工作者等的信任、支持,也重塑了社會工作機構與社區居委會等傳統治理主體的關系,將之置于黨委書記領導的平等地位之中。黨建核心引領一定意義上重塑了社區治理格局,使社會工作機構與傳統街居治理主體的平等合作成為可能。社區居委會、社區社會組織、社工項目團隊能在“黨委領導”之下相互協作,共同推動社區發展。黨建引領下重塑社區治理格局,實質上是黨組織打破原先治理主體之間的隔閡,基于社區治理、社區發展、社區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等共同目標,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多主體社會治理格局。[2]
(二)社會合法性:重塑社會工作機構專業優勢
社區治理格局的重塑賦予了社會工作機構身份合法性,而社會工作機構通過專業服務獲得社會認同,有效參與社區治理,關系到社會工作機構“社會合法性”的建立。社會工作機構應深入社區開展廣泛調研,以社區需求為導向,確定專業服務的內容和重點,并注重與社區綜合黨委、社區居委會、社區居民建立良好關系,在治理體系中有效發揮作用。積極發揮專業優勢,是社會工作得以有效嵌入社區的基礎。社會工作專業團隊應努力提升自身的資源整合能力、服務提供能力,使自身自主性不斷發展,服務持續深化,進而在社區內獲得更廣泛的認可和支持。由此可在社區治理格局內實現良性循環,社會工作機構提供的專業化服務既契合了社區居民的實際需要,又深度契合了社區黨委領導的“民生關切”,雙重契合反過來又提高了社會工作機構參與社區治理的底氣、資本和能力,極大拓寬了其在社區中的生存發展空間。
四、結語
在社區治理新格局中,社會工作既作為參與主體發展著其治理作用,又作為多主體之間的連接紐帶或“橋梁”,扮演著溝通協調的中介人角色,發揮著信息溝通、關系協調、資源鏈接等多種作用。社會工作的工作手法專業而綜合,既有微觀層面的個案服務,又有宏觀層面的社區組織、政策倡導等,是社區工作領域的“多面手”,在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鏈接社會資源、發動社會參與等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從長遠來看,如若能夠有效破除社會工作介入社區治理的現實困境,其必將成為社區治理的“有力幫手”。打破傳統社區治理網絡,塑造社會工作機構、街居治理主體平等協作的新型格局,必須對外重塑社會工作“身份合法性”,對內重塑社會工作“社會合法性”,才能真正破解“嵌入而不能發展”的現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