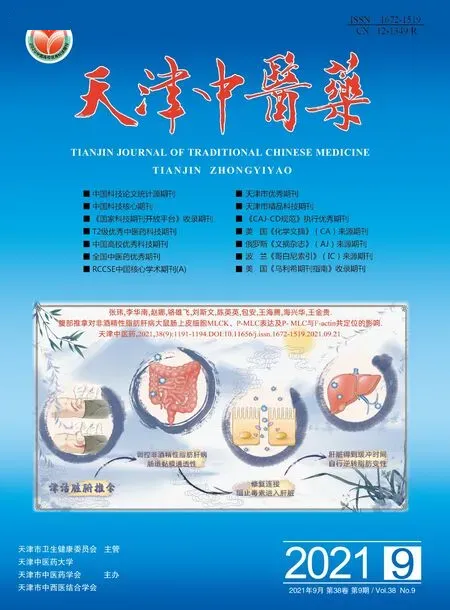基于“脾為吞”理論探討橋本甲狀腺炎的病機和治療*
吳袁元,尹昀東,趙進東,方朝暉
(1.寧國市中醫院,寧國 242300;2.安徽中醫藥大學,合肥 230031;3.安徽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合肥 230031)
目前隨著自然、社會環境的改變,橋本甲狀腺炎(HT)已然成為發病率增長最為迅速的慢性甲狀腺疾病。系統評價結果顯示近年來HT的比例已占到總體甲狀腺疾病的25%左右,其中以30~50歲中青年女性發病率較高[1],約為男性的8~10倍。西醫認為HT主要的病理因素和慢性T淋巴細胞免疫反應有關,標志檢驗結果為高滴度的甲狀腺球蛋白抗體(TG-Ab)和甲狀腺過氧化物酶抗體(TPO-Ab),相應癥狀體征有頸前阻塞感或疼痛,伴有吞咽不適以及甲狀腺結節[2]。HT發病早期可見甲狀腺功能亢進,但隨著疾病的發展,大多演變為甲狀腺功能減退,出現倦怠乏力、畏寒怕冷、月經推遲等癥狀[3],甚者而后可轉變為甲狀腺癌。目前西醫對于HT的針對性治療方案通常以調節甲狀腺激素的分泌功能為主,如左甲狀腺素鈉替代治療,必要時可采取糖皮質激素以及生物制劑如白介素(IL)-10和干擾素(IFN)等,目的在于使一些T細胞輔助因子滅活,從而阻止自身抗體形成,抑制遲發型變態反應的發生發展進程[4]。
《素問·宣明五氣篇》云:“五氣所病,心為噫,肺為咳,肝為語,脾為吞,腎為欠為嚏。”結合足太陰脾經“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的特點,歷代醫家對于“脾為吞”有不同的注釋,總體上可概括為3種含義[5]:一是吞涎,如清代張志聰認為“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脾氣病而不能灌溉于四臟,則津液反溢于脾竅之口,故為吞咽之證”,意為脾氣運化失職,津液不布,上行于口但不溢于口外,導致涎液過多,出現異常的吞咽癥狀。二是吞引,多見于痰氣互結,咽中如有物阻,津液失于敷布,常伴口咽干澀,頻頻吞引,可疏導氣機以暫緩不適。三是吞酸,如《內經今釋》:“吞,即吞酸。”脾虛濕盛,郁久化熱,患者自覺有酸水從胃中上泛,導致吞咽不止。“脾為吞”也可以理解為以吞咽不適為典型癥狀的疾病大多與脾有關,而HT常表現為不同程度的頸前阻塞感或吞咽不適等癥狀,正是屬于此類疾病[6],因此筆者基于“脾為吞”理論,從“吞引”層次加以揆度,以期從脾之陰陽平衡及“脾主運化”的角度探討HT的病因病機和治療方法。
1 從脾論HT的病因病機
HT通常歸為中醫“癭病”“虛勞”“郁證”等范疇,病機總屬本虛標實,虛實夾雜,本虛有心、肝、脾、腎之虧虛,標實有氣滯、痰凝、血瘀、熱毒等,其虛實之偏重與疾病的發展密切相關[7]。筆者認為,“脾為病”是HT發病的主要原因,脾之陰陽失衡,運化不利是各種復雜病機的共同之處,貫穿整個HT的病程。
1.1 HT的病因
1.1.1 情志失調,影響脾運 《諸病源候論·癭候》[8]云:“癭者,由憂恚氣結所生。”《三因極一病證方論·癭瘤證治》云:“此(癭瘤)乃因喜怒憂思有所郁而成也。”均提示精神抑郁,憂思日久導致癭病。雖早期HT可有甲狀腺功能亢進狀態[9],多表現為煩躁易怒,失眠多夢等肝郁化火、肝陽上亢的證候,而據“五行乘侮”規律,見肝之病,知肝傳脾,肝失疏泄,肝氣犯脾,繼而脾虛,又脾因肝郁而失于健運,納谷不馨,雖納而精微不化,水液聚集成痰。此外,肝失條達之性,氣機郁結周身,氣不布津,易于呆凝,痰氣抱結,聚于頸前導致吞咽不利,并形成早期甲狀腺結節。另一方面,脾在志為思,久思則氣結,《圣濟總錄》中首次提出:“婦人多有之(癭瘤),緣憂恚有甚于男子也。”《醫學入門·癭病篇》載:“癭氣,今之所謂癭囊者是也,由憂恚所生。”可見,憂思是構成HT發生發展的重要情志因素。若長期憂思則傷心脾,導致心失推動,脾失健運,日久氣血失運,造成水液輸布不利,痰濕聚于頸前化為結節。據臨床觀察來看[10],HT患者大多在發病之前經歷過一段較長時間的情緒低落期,表現為思慮過度,郁郁不歡,伴有口淡乏味,甚者納差少食,乏力倦怠,臨證中可通過疏肝理氣、消郁散結的方法,在肝郁氣滯改善、情緒穩定的同時,緩解HT的進程。
1.1.2 后天失養,先天有匱 《醫宗金鑒》曰:“脾主肌肉,郁結傷脾,肌肉淺薄,土氣不行,逆于肉里,致生肉癭。”脾乃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飲食不節,調護失宜導致脾胃運化功能失調,水谷精微不化,濕聚痰凝發為癭病。一方面,脾的健運失職可造成水液輸布不利,痰濕膠著于頸前,脾絡不通化為結節;另一方面,氣血不榮,則枯以榮經,經脈失養而致頸前阻塞而拘急不舒。此外,脾胃虛弱,后天失養,勞損體虛,體質衰減也會導致HT的發病。西醫認為,生活中由飲食不當引起的亞健康狀態會導致機體免疫力下降,是HT一個重要發病原因,亦有不少醫家以顧護脾胃,以養后天貫穿于治療始終[11]。后天匱乏,不能養先天,則會波及腎中精微物質,出現元陰、元陽失衡,表現為腰膝酸軟、怕冷畏寒、小便頻數、肢體浮腫等癥狀。同時,若本身腎精不充,則稟賦失衡,易而受外來因素影響產生HT。
綜上所述,結合“脾為吞”理論和足太陰脾經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的特征,可見HT的早期癥狀如頸前不適、吞咽不利與脾為病有著密切的聯系。情志不遂和先后天失養雖為發病的重要誘導因素,但是脾失健運、脾絡不通才是引起相關病理改變的主要原因。
1.2 從脾論HT的病機 中醫界通常將HT的病程分為早中晚3期[12],前中期具有“癭病”和“虛勞”的特征;后期則頸部腫塊和吞咽不適減輕,主要表現為“虛勞”。《外科正宗》曰:“夫人生癭瘤之癥,非陰陽正氣結腫,乃五臟瘀血、濁氣、痰滯而成。”在情志失調、先后天失養的病因基礎上,脾失健運,土壅木郁,久郁成熱,灼津生痰,心失所養,血脈不利,氣滯、痰凝、血瘀互相搏結,是本病的主要病機。其中脾失運化,陰陽失衡,生化乏源,無力輸布精微是加重邪實與正虛的主要原因。
1.2.1 脾陰虧虛,陰陽失衡 脾陰虧虛是指脾陰不足,失其濡養所表現的證候,常伴有陰不能制陽,虛熱內生的表現。繆希壅在《神農本草經疏》[13]中言:“胃主納,脾主消,脾陰虧則不能消……”之后又在《先醒齋醫學廣筆記》以“脾陰不足之候”首次提出脾陰虛證候。與臨床多論的胃陰虛不同,脾陰虛多見于內傷雜病者,一般病程較長,而胃陰虛多見于外感熱病或嘔吐傷津者[14]。因脾陰和脾陽互相制約,維持平衡,才能完成脾主運化,主肌肉,升清,統攝血液的功能。HT患者在疾病的前中期常有煩熱、失眠、舌紅少津等癥狀,西醫稱之為HT甲狀腺功能亢進期,為自身免疫性炎癥反應導致甲狀腺濾泡破裂損傷,其內部存儲的甲狀腺激素分泌至外周血液所致。從中醫學角度分析此階段實為情志失調,后天失養,日久耗傷脾陰。《素問·生氣通天論》有“臟真濡于脾”的記載,五臟氣陰不足,脾陰亦有虧耗。如肝郁日久,氣郁化火;心失所養,虛火上炎;憂思過度、勞思傷脾等均可暗耗脾陰。脾陰為后天水谷精微所化生,長期飲食不節,陰精化生無源,也可導致脾陰不足。脾陰虛而生火疢,《醫貫》有言:“滯則病,息則死。”脾陰不足,運化失職,故見食少,腹脹,或大便秘結;脾陰虛致脾經失于濡養,故頸前不適;“脾之液為涎”,脾陰匱乏,涎液減少,故口干舌燥,舌紅少津;手足為脾之外候,掌心屬陰,脾陰不足,虛火內擾,故見手足心熱,舌苔少或無苔,脈細無力。以上均為脾陰不足,陰虛火旺之候[15],也是HT甲狀腺功能亢進的表現。中焦陰虛火旺,以傷有形之氣血津液,外加肝氣郁結,脈絡不利,日久氣滯、痰阻和血瘀相互搏結更甚,頸部腫塊加重。脾陰虧虛,營血不能輸布而濡養全身,故倦怠乏力,形體消瘦,面色無華;脾陰與脾陽相互依存,脾陰虧虛損及脾陽,終致陰陽兩虛。臨床上按照“益其不足,損其有余”理論,以甘淡之味實脾滋脾,滋陰益氣[16]。安徽省中醫藥領軍人才,首屆安徽省名中醫及首屆安徽省江淮名醫方朝暉教授認為脾為陰土,是三陰之長[17],HT脾陰虛階段需以滋養為主,臨證擇太子參、山藥、蓮子、扁豆、石斛、茯苓、谷麥芽、白術、甘草等味健脾益氣,尤以大劑量山藥為佳,可遵張仲景《虛勞風氣百疾·薯蕷丸》之法;另可入味酸性寒之白芍,斂津液而護營血,收陽氣而瀉邪熱,以補脾陰而獲效。
1.2.2 陰損及陽,脾腎陽虛 脾主運化,為后天之本,腎藏精,為先天之本,兩者相互資助。脾病日久,運化失職,陰損及陽,機體失于溫煦,痰濁血瘀壅阻更甚,此為HT后期主要病機,西醫稱之為HT伴甲狀腺功能減退期。隨著疾病的發展,前期諸如肝郁氣滯等癥狀逐漸消失,而脾腎陽虛則成為主要證候。脾陰陽失衡日久,后天精微生化乏源,先天失于充養,而脾陽又依賴腎陽溫煦,日久反復可致脾腎陽虛,表現為面色蒼白,畏寒肢冷,神疲乏力,苔白膩,脈沉遲。機體陽氣衰弱,化氣行水乏力,脈道失養,血運不利,痰濁與瘀血化生,久病入絡。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痰》曰:“有腎虛水泛為痰者,此亦由土衰不能制水。”通常HT患者在多方面治療后,頸前腫塊或有減輕,但脾病及腎仍是該階段的主要表現,也是后期HT多屬于“虛勞”范疇的原因之一。
2 從脾論HT的治療
2.1 未病先防,見吞調脾 未病先防是中醫“治未病”思想的體現,因此在早期發現頸部吞咽不適時就應及時注意疾病發展成HT的可能。“脾為吞”之意亦可解讀為癥狀體現為吞咽不適的疾病,需要注意調理脾胃,“脾胃內傷,百病由生”,在早期HT預防和治療的過程中,應注重“助脾土,通脾絡”。對于日常生活中多有郁怒情緒的患者,需疏肝解郁,健脾散結,在HT早期可用逍遙散加減,藥用甘草、當歸、茯苓、白芍、白術、柴胡、生姜等,肝郁嚴重者可聯用柴胡疏肝散、丹梔逍遙散或四海舒郁丸。臨床研究表明逍遙丸具有良好的抗抑郁和抗焦慮作用[18],可顯著降低早期HT患者血清抗甲狀腺過氧化物酶抗體(TPO-Ab)和甲狀腺球蛋白抗體(TG-Ab)水平,有效延緩甲狀腺濾泡細胞的損害進程,保護甲狀腺功能[19]。若患者憂思日久,心脾兩虛,以面色蒼白,心悸失眠,納差,脈細弱為主要表現,可治以健脾益氣,養心安神,方用歸脾湯加減,方中以黃芪、黨參、白術健脾益氣,使水谷精微生化有源;當歸、茯神、酸棗仁、龍眼肉、遠志滋養陰血,寧心安神。心火亢盛,煩躁失眠者,可加用麥冬、百合、夜交藤等清熱安神之品。西醫研究發現歸脾湯對于下丘腦-垂體-甲狀腺軸的功能紊亂具有顯著的改善效果,尤其對于HT患者的血清三碘甲狀腺原氨酸(T3)、四碘甲狀腺原氨酸(T4)、促甲狀腺激素(TSH)及促甲狀腺激素釋放激素(TRH)異常有明顯的改善作用[20]。對于平日體質較差,癥狀不明顯的患者,臨床可佐以黃芪、黨參、白術、山藥等健脾益氣,定要注重納化相得,可加用麥芽、神曲、薏苡仁等消食和胃以健脾;對于咽部吞咽不適較重的患者,則可加用射干、夏枯草、山慈菇、桔梗、甘草等清咽之品[21]。補益后天脾胃之虛亦有助于固護正氣,一方面調理脾胃有助于延緩情志和飲食等因素誘發HT;另一方面,早期發現頸部吞咽不適的癥狀,從脾治療,具有未病先防的作用。
2.2 健脾散結,平衡脾之陰陽 由于HT虛實夾雜的證候特征,因此在發病階段多采用扶正祛邪雙重治法,其邪實多屬經絡阻滯,痰瘀互結,治以行氣化痰、活血化瘀。對于此類患者,諸多醫家采取不同的方藥加減進行治療,如張金梅等[22]將本病歸納為實證與虛證,對于實證如肝郁氣滯、肝郁化火,痰郁化火分別采用四海疏郁丸、龍膽瀉肝湯和消癭丸治療。唐漢鈞等[23]指出本病病機為正虛邪戀,治則為扶正消癭,方中常用黃芪、黨參、白術、黃精、山茱萸、白芍、茯苓、柴胡、郁金、香附、浙貝母、夏枯草等藥。然而,HT的脾陰虧虛證候通常較少被提及,相應的陰虛癥狀常被認為是肝腎陰虛所致,繆希壅有云:“胃氣弱則不能納,脾陰虧則不能消,世人徒知香燥溫補為治脾虛之法,而不知甘寒滋潤益陰之法有益于脾也。”由于癭病本身病機復雜,故滋養脾陰不能拘泥于滋陰之法,需辨證分析。體虛日久,心脾兩虛者,需甘淡養陰,甘能滋陰補益,淡能化濕利水,兩者結合,滋養脾陰而不礙脾運。方用繆希壅的資生丸或喻昌輝的益脾湯加減,藥用白術、茯苓、人參、橘紅、神曲、澤瀉、白扁豆、薏苡仁、山藥、麥芽、芡實、炙甘草等。對于肝郁日久,化火傷陰者,需酸甘化陰,肝在味為酸,酸能增液生津,柔肝緩急,與甘藥合用,有助于柔肝養肝,疏肝健脾,方用參苓白術散配合味酸、甘的中藥加減,藥用白術、茯苓、山藥、烏梅、五味子、白芍、防風、石榴皮等[24]。此外,雖然脾陰虛是一種獨立于脾氣虛的證型,在滋養脾陰的同時,需注意脾氣運化功能的失調,HT甲亢期患者常自訴偶有神疲乏力,少氣懶言,舌淡苔白,脈細澀的癥狀和舌脈,可用四君子湯或補中益氣湯加減,常用藥物如黃芪、黨參、山藥、白術、柴胡、升麻、白芍等。總體而言,不論是健脾益氣還是滋養脾陰,都需要注意藥性甘平,養陰而不滋膩,補氣而不化燥。
2.3 脾腎同治,益火補土 HT后期通常表現為脾腎兩虛,即機體的代謝功能減低,癥見渾身乏力,四肢寒冷,厭食,精神不暢,表情淡漠,面色、瞼結膜蒼白,行動遲緩[25]。但在部分患者有可能無明顯癥狀,需要根據各項檢查指標,如甲狀腺功能、超聲檢查等判斷患者疾病進展情況[26]。無明顯癥狀的患者多因邪氣驅散,正氣未虛,但治療仍需扶助正氣,以防復發。而對于脾腎陽虛的患者,多采用“益火補土”法,即以溫養先天命門之火,改善脾腎陽虛[27]。HT后期雖然邪實已袪大半,頸部吞咽不適癥狀減輕,但久病耗傷正氣,仍需補益脾腎,養中氣以固護正氣,祛除余邪,以防久病入絡,正虛邪戀,遷延不愈。張介賓言“以形治形”,當助以甘溫,方可用腎氣丸或建中湯加減,藥用肉蓯蓉、山茱萸、菟絲子、黨參、干姜、白術、甘草等。腎陽得充、脾陽得健,三焦水道通調、周身血脈流暢,水濕、痰瘀等余邪方可得陽化解。
3 典型病案
患者女性,44歲。2019年8月6日初診。以乏力、畏寒、面色少華伴頸部不適1年余,加重1月為主訴。患者1年前無明顯誘因下自覺全身倦怠乏力,畏寒,不喜涼食,少汗,伴頸部腫脹不適感,至當地社區醫院診斷為甲狀腺功能減退癥,予左甲狀腺素鈉每次50 μg,每日1次口服治療。患者服用1周后自覺癥狀緩解后自行停藥。后癥狀反復,自行間斷服用上述藥物。1個月前患者上述癥狀加重明顯,時值長夏不吹風扇不覺煩熱。刻下癥:乏力、畏寒怕冷、頭暈、腰膝酸軟、夜尿頻數、夜寐差,納食尚可,大便尚調。末次月經(LMP):2019年7月20日,月經周期延遲,量少,色淡,無血塊,痛經(-)。查體:雙側甲狀腺Ⅰ°腫大,質軟,觸痛(-),皮色正常;心肺(-),肝脾不大,雙眼瞼輕度水腫,舌質淡白,舌體胖大,邊有齒痕,舌苔薄,脈沉細。甲狀腺功能檢查提示:游離三碘甲狀腺原氨酸(FT3)0.18 pmol/L、游離四碘甲狀腺原氨酸(FT4)5.73 pmol/L、TSH 35.48 μU/L、TG-Ab>1 000 U/mL,TPO-Ab>1 000 U/mL。甲狀腺彩超提示:甲狀腺彌漫性病變。心電圖示:竇性心律。西醫診斷:甲狀腺功能減退癥合并HT。治療上給予左甲狀腺素鈉50 μg,每日1次。中醫診斷:癭瘤(脾腎陽虛,氣結痰凝),治以溫脾益腎,行氣散結。處方如下:茯苓 15 g,山藥 20 g,炒白術 10 g,百合 12 g,當歸 10 g,炙黃芪 30 g,山慈菇 12 g,夏枯草 8 g,桂枝 8 g,干姜 9 g,陳皮 8 g,合歡花 12 g,女貞子 12 g,墨旱蓮15 g,杜仲15 g,山茱萸10 g,炙甘草8 g。水煎服,14劑,每日1劑,水煎早晚分服。
2診:患者2019年8月20日前來就診患者上述方藥服用2周后,乏力癥狀明顯減輕,眼瞼浮腫好轉,仍有畏寒怕冷,夜寐因小便頻數欠佳,仍有頸前部腫脹感。LMP:2019年8月18日,正值經期,腰酸明顯,量少,色淡,無血塊,痛經(-)。納可,未訴腹脹不適,大便尚調,舌淡苔薄白,脈沉細。方藥:上方去干姜、山慈菇,加山豆根6 g,金櫻子10 g。14劑,每日1劑,水煎早晚分服。
3診:患者2019年9月4日前來就診,乏力、畏寒等癥狀基本緩解,偶有頭暈,自覺頸部較前舒緩明顯,無明顯腰酸,夜尿頻數癥狀改善,小便每晚2~3次。納寐尚可,大便尚調。舌質淡紅,苔薄,脈沉細。甲狀腺功能檢查提示:FT33.88 pmol/L、FT410.53 pmol/L、TSH 4.45 μU/L、TG-Ab 921.8U/mL、TPO-Ab 910.1 U/mL。方藥:上方去山藥,加延胡索12 g,葛根10 g。14劑,每日1劑,水煎早晚分服。囑左甲狀腺素鈉片維持12.5 μg,每日1次,定期復查甲狀腺功能。
4診:患者2019年9月24日前來就診,頸部無明顯不適,無乏力、畏寒癥狀,未訴頭暈,月經按時來潮,守方微調,3個月后臨床初愈。囑左甲狀腺素鈉片維持12.5 μg,每日1次,每月復查甲狀腺功能。
按語:該患者為HT中后期,伴有甲狀腺功能減退且病程日久,陽氣不振,失于運化,痰氣郁結頸前,發為癭腫。《黃帝內經》有言“精氣奪則虛”,機體氣、血、津液等生成障礙,不能濡養機體組織器官,即導致臟腑損傷。該患者雖脾虛癥狀非十分明顯,然先后天之本皆無力振奮,血運無力。筆者基于“脾為吞”理論,先“見吞調脾”,當補益中土為先,擇茯苓、淮山藥、炒白術補脾養脾;《藥性歌訣》云:“黃耆入藥,為強壯劑,具有益正氣,壯脾胃……”大劑量黃芪除補氣外,亦乃健中州之要義,配合干姜溫中散寒,上幾味使氣血生化得其源,加以補腎溫陽,滋養肝腎,以復“虛之精氣”;益氣行氣活血藥物配合桂枝溫陽通脈,如春水潺潺共掣形寒錮冷;百合、合歡養心安神,又可疏肝清心,配以山慈菇、夏枯草散結消腫。同時,針對兼證化裁,先后天精氣俱復,月經尚可復調。然HT標實日久,行氣、消瘀、散結不可貪功,需徐徐圖之,于復脾腎之陽后加重祛痰利咽,消癭散結之法。
4 小結
目前對HT尚無明確統一的中醫辨證和治療方案,各位中醫學家對于該病不同證型的辨治結果有著不同的看法。筆者基于“脾為吞”理論對該病進行分析后,認為脾為病貫穿了該病的前后病程,是各階段病機的核心。在辨證論治的過程中,需要注意未病先防,平衡脾之陰陽,并結合行氣解郁,化痰消瘀,補脾益腎之法進行治療。在中醫整體觀念的指導下,同時兼顧其他臟腑在HT發病及治療中的作用,方可取得更好的治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