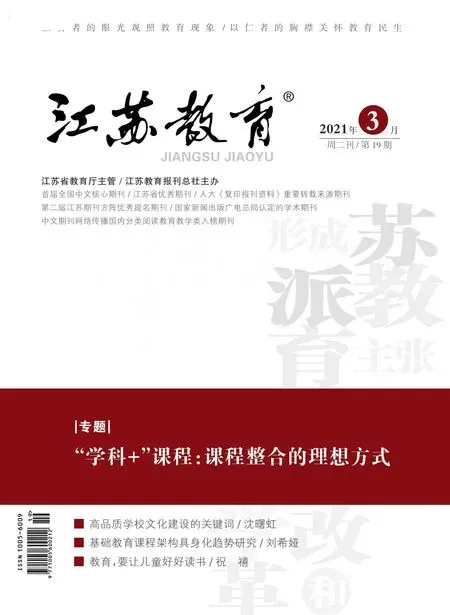教育驅(qū)動城市文化精神建構(gòu)*
——以江蘇省南通市為例
劉 鋒
對一個(gè)城市而言,雖然支撐外在形態(tài)的是其物質(zhì)發(fā)展,但豐富內(nèi)在形象的是城市文化精神。我們認(rèn)為,城市文化精神的豐富,必定依賴其教育。否則,縱然歷史文化遺產(chǎn)豐富,其城市文化精神依然會沒有健康靈魂。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播,更是文化的傳承與創(chuàng)造。重視城市教育品格的塑造,是城市文化精神建構(gòu)的基石。
被譽(yù)為“中國近代第一城”的江蘇南通,20世紀(jì)初即享有“模范縣”“模范城市”的稱謂。對彼時(shí)的中國城市來說,是何等難得的光環(huán)。英國人E. G. Lowder 在《海關(guān)十年報(bào)告》中指出南通是“一個(gè)不靠外國人幫助,全靠中國人自力建設(shè)”[1]的模范城市。是什么成就了南通“模范”概念的形成?梁啟超先生在1922 年到南通時(shí)說“南通是我們?nèi)珖J(rèn)第一個(gè)先進(jìn)的城市,南通教育會和各團(tuán)體是我國教育界中的先進(jìn)者。他們價(jià)值之高,影響之大,國人共知”[2],突出了南通教育。英文報(bào)紙《密勒氏評論報(bào)》主編J. B. 鮑威爾羅列的“促成南通形成模范城市”的十二個(gè)元素中有三個(gè)是教育元素。他還著重介紹南通的教育狀況:在這一地區(qū)大約有334所各類學(xué)校,逾2 萬名常規(guī)學(xué)生。可以說,這是一個(gè)所有孩子都有機(jī)會獲得教育的地區(qū),擁有醫(yī)學(xué)學(xué)校、師范學(xué)校、農(nóng)業(yè)學(xué)校、商業(yè)學(xué)校以及眾多的基礎(chǔ)與中等教育機(jī)構(gòu)。[3]查爾斯. T. 保羅在美國出版的《中國的召喚》(1919 年)中介紹南通現(xiàn)代化改革的十個(gè)標(biāo)志性成就中就有六個(gè)是與教育相關(guān)。[4]由此可見,南通現(xiàn)代城市建設(shè)及城市精神的建構(gòu)中教育及教育建設(shè)成果都發(fā)揮了關(guān)鍵性作用。考查、梳理教育建設(shè)對南通現(xiàn)代城市文化精神塑造的作用,可以啟發(fā)當(dāng)代中國城市文化發(fā)展、城市發(fā)展的價(jià)值取向與基本策略。
一、南通傳統(tǒng)教育文化的“破”
文化發(fā)展過程中,破舊立新是常態(tài),因?yàn)闀r(shí)代的變化需要文化的革新與之呼應(yīng)。所以,既有文化中與時(shí)代的需要格格不入的舊文化元素就需要破除。2002 年,吳良鏞教授從中國近代城市發(fā)展的角度提出:“張謇先生經(jīng)營的南通堪稱中國近代第一城!”20 世紀(jì)初,以張謇為代表的南通地方先賢,以民族振興的歷史定位、世界性的眼光、現(xiàn)代建設(shè)的標(biāo)準(zhǔn),對江海之濱的小城南通進(jìn)行本質(zhì)化、現(xiàn)代化的重構(gòu)。張謇等先賢所重構(gòu)的不只是地方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社會治理,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教育文化的重構(gòu)。雖然“南通自古重教”,孕育了“崇文、厚德”精神,雖然“古代南通,官設(shè)州學(xué),此外還有書院、小學(xué)、社學(xué)、私塾,教育體系比較完備,培養(yǎng)出許多德才兼?zhèn)涞娜瞬拧保?]。但是,這樣的教育文化傳統(tǒng)是舊中國“科舉”制度引導(dǎo)下各地普遍踐行的共性教育文化常態(tài)。張謇等先賢在20 世紀(jì)初對教育文化的重構(gòu),完全顛覆了這一傳統(tǒng),讓南通教育從面對精英的傳統(tǒng)教育走向了面對大眾的現(xiàn)代教育。
1.轉(zhuǎn)變教育目的。
在“科舉”引導(dǎo)下的中國傳統(tǒng)教育也被稱為“舉業(yè)”,是中國社會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人才產(chǎn)生的唯一路徑。路徑的單一性決定了全社會必然形成讀書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功名的傳統(tǒng)認(rèn)知。1400年的“科舉”制度在選拔人才、促進(jìn)社會階層流動的同時(shí),也培養(yǎng)了不少讀書人,如“孔乙己”式的迂腐、“蒲松齡”式的屢試不第、“范進(jìn)”式的中后癲狂。“讀書”與“功名”構(gòu)成以“科舉”為中介的共名關(guān)系,可以說是歷千年而不破。1902年,張謇、沙元炳等南通先賢著眼于現(xiàn)代教育,在南通、如皋兩地開辦師范。雖然在兩三年后擁有1000多年歷史的科舉被廢除,但彼時(shí)科舉在讀書人心里的影響尚未松動,入師范轉(zhuǎn)而赴科考者都有人在。學(xué)校用禁止、開除等手段表明態(tài)度——師范、科舉是兩條路,斷“讀書”與“功名”的聯(lián)系,促進(jìn)教育向現(xiàn)代發(fā)展。
2.擴(kuò)大教育對象。
受制于“科舉”制度,中國社會在20 世紀(jì)之前的教育是被壟斷的精英教育,受教育者都是以“科舉”為目標(biāo)的“舉子”。教育對象的局限性決定了當(dāng)時(shí)中國社會整體文化水平的落后。張謇在“上學(xué)部請?jiān)O(shè)博覽館議”開篇便論:“竊維東西各邦,其開化后于我國,而近今以來,政舉事理,且骎骎為文明之先導(dǎo)矣。撢考其故,實(shí)本教育之普及,學(xué)校之勃興”[6]。在這樣的認(rèn)識基礎(chǔ)上,張謇等人在南通等地興辦師范。張謇在“師范學(xué)校開校演說”中指出創(chuàng)辦師范學(xué)校的目的在于“與諸君協(xié)興普及國民教育”。而后他又辦小學(xué)、中學(xué)及大學(xué)等,他明確不同層次類型學(xué)校的功能:“師范啟其塞,小學(xué)導(dǎo)其源,中學(xué)正其流,專門別其派,大學(xué)會其歸。”在這樣的重構(gòu)中,教育的受益者從有限的應(yīng)考“舉子”擴(kuò)大為一般“國民”。在此影響下,南通各地學(xué)校興起,獲得“模范縣”之譽(yù),逐漸建立與健全現(xiàn)代教育體系。
3.注重師資培養(yǎng)。
傳統(tǒng)中國社會少有書院,多為私塾。書院偶有大儒講學(xué),而私塾教師多為落第舉子或“前程絕望”“邊教邊考”舉子的謀生之舉。教師本質(zhì)上是“技藝”嫻熟的代名詞,與韓愈所謂“授之書而習(xí)其句讀者”相當(dāng),但在這里,教師卻變成了讀書人的附帶之業(yè)。張謇無論是在他的《變法平議》中,還是在他后來興辦教育的實(shí)踐中,都主張“首重師范”。他倡導(dǎo)以專門培養(yǎng)現(xiàn)代師資的方式為教育的普及提供現(xiàn)代化的師資基礎(chǔ)。在張謇的改革下,教師逐漸成為有門坎、有要求、有專長的特殊人才,不再是什么人讀過幾年書便可以從事的行業(yè)。
二、南通現(xiàn)代教育文化的“立”
中國城市是在20世紀(jì)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后快速發(fā)展起來的。這段時(shí)期內(nèi),城市規(guī)模不斷擴(kuò)大,城市形態(tài)日新月異,但城市文化相對匱乏。大部分城市更多地承繼著傳統(tǒng)地域文化特質(zhì),并沒有進(jìn)行真正與城市化進(jìn)程相匹配的文化建設(shè)。所以,對絕大多數(shù)中國城市來說,城市文化要做的是“立”大于“破”。南通先賢打破舊的教育傳統(tǒng)時(shí),正是新的教育生態(tài)發(fā)軔生長之際。無論是教育體系還是教育文化都獲得了新的面貌。
1.建立現(xiàn)代教育體系。
“近代第一城”南通在城市發(fā)展中堅(jiān)持張謇所秉持的“父教育、母實(shí)業(yè)”的基本思路,在破除舊的教育傳統(tǒng)中重建了城市新的教育體系,1902 年從創(chuàng)辦師范入手,同時(shí)創(chuàng)辦初等小學(xué),3年后建成高等小學(xué)、女子師范。而后,小學(xué)(僅當(dāng)時(shí)通州)的數(shù)量平均每年遞增10 所,1910 年已達(dá)87所。到1920年,南通初高等小學(xué)數(shù)量達(dá)到334所,教育普及率達(dá)到21.99%,領(lǐng)先全國十年。在小學(xué)設(shè)立的同時(shí)還興辦公立中學(xué),更在師范附設(shè)測繪、土木、農(nóng)、桑等科,繼而開辦銀行、商、醫(yī)、紡織等專門學(xué)校,1920 年農(nóng)、醫(yī)、紡、商各校籌設(shè)南通大學(xué),此外還應(yīng)地方建設(shè)需要先后開辦了法政、國文、巡警等各類職業(yè)訓(xùn)練、培訓(xùn)機(jī)構(gòu)。由此,一個(gè)比較完整的現(xiàn)代教育體系在南通率先建立,南通的教育普及有了堅(jiān)實(shí)的保障。而這得益于先賢們現(xiàn)代教育建設(shè)的“立之有本”“行之有方”“次第有序”[7]。
2.生成城市教育文化。
在教育格局的巨變中,南通教育的精神也有了新的內(nèi)涵。從城市的教育文化角度,筆者認(rèn)為南通具備以下主要教育文化特性:首先,南通的教育文化有胸懷天下的氣度。南通的教育文化兼顧面向現(xiàn)代和繼承傳統(tǒng)。張謇等先賢在布局南通的教育,舉辦南通的師范培養(yǎng)師資時(shí)就希望學(xué)生能“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既是傳統(tǒng)士大夫“家、國、天下”的繼承,也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面對時(shí)代的精神與擔(dān)當(dāng)。南通雖然地處江海平原,但近百年來南通人能吃苦、肯擔(dān)當(dāng)?shù)木癯闪缩r明的城市氣質(zhì)。其次,南通的教育文化重視“做人”教育。強(qiáng)調(diào)“做人”是南通教育文化中繼承傳統(tǒng)的又一重要特征。儒家文化強(qiáng)調(diào)并深化“做人”的教育立場,張謇在南通師范開學(xué)典禮的演說中滿懷深情地對學(xué)生提出“開拓胸襟,立定志愿……不妄自菲薄,自然不妄自尊大,忠實(shí)不欺,艱苦自立”等期望。他認(rèn)為教育的目的,在學(xué)會“做人”的道理。再次,南通的教育文化強(qiáng)調(diào)面對現(xiàn)實(shí)。張謇先生認(rèn)為“欲雪其恥,而不講學(xué)問則無資,欲求學(xué)問,而不普及國民教育則無與,教育欲普及國民而不求師則無導(dǎo)”,其邏輯起點(diǎn)就是現(xiàn)實(shí)。他主張學(xué)生要“艱苦自立”,也是當(dāng)時(shí)的南通、當(dāng)時(shí)中國不可回避又不得不面對的實(shí)際。最后,南通的教育文化有鮮明的“學(xué)而為用”意識。張謇認(rèn)為:“自其成童至于弱冠必責(zé)以盡讀全經(jīng),而經(jīng)乃徒供弋取科舉之資,全無當(dāng)于生人用。”他主張“求應(yīng)用學(xué),復(fù)本體明”“求人之長,成己之用”。對張謇等先賢而言,國力衰弱、危機(jī)四伏的中國不可閑而論道,要以“致用”為目標(biāo)而學(xué)。
進(jìn)入21 世紀(jì),南通提煉出“包容匯通,敢為人先”的城市精神,繼承了100 年前南通先賢敢為天下之先的勇氣精神,也展示了南通開闊包容的胸襟,彰顯出“中國近代第一城”的格局與氣度。當(dāng)下南通的發(fā)展是在中國現(xiàn)代城市格局大變的背景下進(jìn)行的,雖然南通一度發(fā)展的速度落后于明星城市,但南通人對教育的重視依然如故。近20 年南通經(jīng)濟(jì)、社會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與其提出的城市精神相契合,而其背后,是南通堅(jiān)持“崇文重教”“百年大計(jì),教育為本”的教育執(zhí)著。
三、教育滋養(yǎng)城市文化精神
雖然馬克思證明“物質(zhì)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雖然城市如南通,其先賢實(shí)際上也是通過發(fā)展工業(yè)為基礎(chǔ),而后逐步提升南通城市的文化教育,但人類文化發(fā)展史也清楚地表明,文化的發(fā)展并不是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的附屬物,它并不是全然地跟從物質(zhì)基礎(chǔ)的步伐,有時(shí)會先于社會經(jīng)濟(jì)先行繁榮。城市的文化不但要繼承和積淀,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斷滋養(yǎng)與豐富。我們認(rèn)為,對既有文化要素在繼承的同時(shí)注入時(shí)代雨露,使其以更燦爛的面貌呈現(xiàn)于世人的面前,并影響人們的文化認(rèn)同,這就是“滋”。對新生的文化形態(tài)、文化精神,以積極開放的心態(tài)為其提供發(fā)展的空間,為其更接近于城市文化精神,更契合人們?nèi)粘N幕枰峁┍憷蛑Γ@就是城市文化的“養(yǎng)”。無論“滋”或“養(yǎng)”,教育都是最關(guān)鍵的手段和內(nèi)容。從教育入手主動營造、創(chuàng)造文化的氛圍,是城市文化精神塑造的內(nèi)在發(fā)展動力。
1.教育促進(jìn)城市文化扎根。
變化是事物的常態(tài),發(fā)展是城市的追求。借助現(xiàn)代科技的物質(zhì)發(fā)展突飛猛進(jìn),但文化的發(fā)展并不可能如物質(zhì)建設(shè)那樣日新月異。雖然流行文化、大眾文化的發(fā)展也是此起彼伏,但其本質(zhì)大體上是穩(wěn)定的。這就說明,社會文化一方面會伴隨社會其他要素的發(fā)展變化而變化;另一方面,社會文化中一些與區(qū)域、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的內(nèi)在質(zhì)地相統(tǒng)一的文化要素會在表面的變化中呈現(xiàn)相對的穩(wěn)定。因此,城市文化中變化的部分受其他社會要素的影響,而穩(wěn)定不變的部分需要我們梳理與重視。南通城市文化中穩(wěn)定不變的部分就是南通學(xué)子“艱苦自立”的精神。南通學(xué)生呈現(xiàn)給世人的印象是——“學(xué)霸”,這不僅是因?yàn)槟贤ǜ呖嫉募芽儯菍δ贤▽W(xué)子拼搏精神的認(rèn)可。當(dāng)代城市過度強(qiáng)調(diào)其變化與發(fā)展,而忽略城市相對穩(wěn)定的精神氣質(zhì),各城市走出的學(xué)生大多沒有地方文化的底色。因此,結(jié)合地方文化特色,在小學(xué)或初中階段開設(shè)介紹本地文土歷史的“市本”文化課程作為中國文化課程的必要補(bǔ)充是當(dāng)前各城市必須實(shí)施的工作,是促進(jìn)城市文化扎根的重要舉措。
2.教育揭示城市文化價(jià)值。
文化總給人以抽象的感覺,而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則清楚,文化既有其精神性的抽象部分,也有實(shí)實(shí)在在的載體與形態(tài)的具象部分。如果說抽象的部分需要更長時(shí)間的積淀與篩選,那么具象的文化項(xiàng)目、文化工程就是政府、文化工作者可以著力關(guān)注的部分。比如,城市中具有文化代表性的建筑、風(fēng)物的保護(hù),城市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與傳承等。只有通過教育,人們才可能從紛紛擾擾的物質(zhì)世界中抽身出來,逐漸重視自己身邊文化載體的精神價(jià)值;只有在教育的不斷深入中,人們才能在質(zhì)態(tài)的世界里尋找到自己精神寄寓之處。南通建立了師范教育博物館、紅色師范紀(jì)念館等優(yōu)秀的教育文化載體,編修了南通地方的教育文化史,借助教育相關(guān)的途徑讓南通的城市文化有了切實(shí)的載體和育人的價(jià)值。
人是文化生成、傳播、積淀的根基,脫離了人的文化是沒有生命力的。南通先賢對南通教育變革的根本,是讓教育走進(jìn)大眾的生活。這從根本上讓南通獲得了別樣的城市文化精神面貌,也從中獲得了發(fā)展的生機(jī)。當(dāng)代南通承繼教育文化傳統(tǒng),胸懷天下重做人,面對現(xiàn)實(shí)重實(shí)用,形成了“中國教育看江蘇,江蘇教育看南通”的教育口碑。在新的發(fā)展契機(jī)面前,南通建立“導(dǎo)師團(tuán)”,以培養(yǎng)李吉林式“兒童教育家”提升教育質(zhì)量;通過集團(tuán)化、師資流動形成良性的教育生態(tài),提升教育內(nèi)涵,為南通基礎(chǔ)教育的高層次均衡發(fā)展提供動力,滋養(yǎng)新時(shí)代南通的城市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