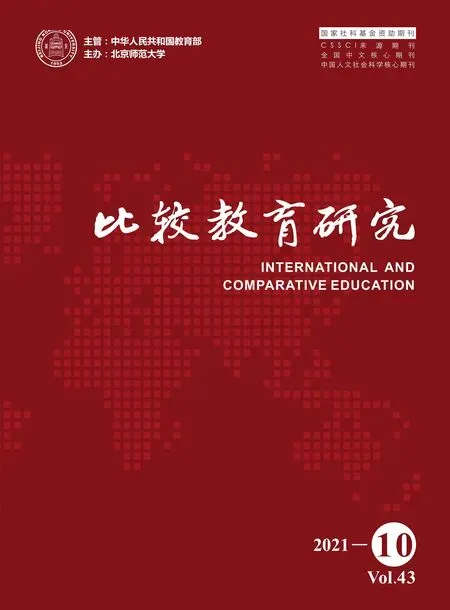德國社團主義傳統及其對職業教育立法影響
榮艷紅,傅修遠
(1.河北大學教育學院,河北保定 071002;2.南京工程學院工業中心,江蘇南京 211167)
社團主義是一種介于多元主義和國家主義之間的中間形式。對于社團主義概念的理解,有學者從體系特征的角度認為社團主義是一套具有獨特內在結構的不同利益團體代表系統;[1]有學者從公共政策形成角度認為社團主義是制度化的政策形成機制;[2]有學者簡單認為社團主義是一種強有力的促進團體之間矛盾解決的協調機制;[3]還有學者指出社團主義政治無涉,它是持有不同政治主張的政府實施管理的手段……[4]不論從哪個角度理解社團主義,主張共同體由不同利益團體構成,與共同體利益相關的重大問題都應依靠團體之間的談判或協商方式來解決,是不同派別學者公認的社團主義概念核心的特征。德國具有濃厚的社團主義傳統,社團主義在德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包括在職業教育立法領域均有著鮮明的體現。
一、德國社團主義的傳統
德國社團主義的傳統源自中世紀其內部各邦國、城市以及行會之間彼此相處的方式。由于中世紀德意志皇帝抱有建立真正的全球帝國的夢想,為了獲得屬地領主們更多的幫助以達成對羅馬教廷的征服,德意志皇帝經常與追求獨立的領主們商議并結成聯盟。至14世紀中葉,在德意志統一的外表下出現了一大批獨立的邦國和邦君,除七大選帝侯外,還有10多個大諸侯,200多個小諸侯,1000多個帝國騎士。他們的領地就是大大小小的邦國。[5]由于邦國數量較多且力量相對均衡,在重大的沖突過后,談判協商是解決問題的普遍做法。1648年《威斯特法利亞合約》的簽訂就是這一做法的典型代表。除了以上具有德國特色的政教管理方式,中世紀歐洲城市經濟恢復之后,包括德意志在內的歐洲國家再次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手工藝行會。作為一種自治機構,行會內部的事務依據共同制定的行規來管理,而行會之間的事務依靠彼此的協商來解決;[6]自治城市是與行會一同出現的中世紀政治、經濟管理的新單元(在歐洲某些地方,行會和自治城市就是同一組織),這些具有自治功能的城市擁有獨立的行政機構。[7]為了促進城市之間人員流動和貿易開展,城市之間還締結了同盟,較為有名的萊茵同盟、士瓦本同盟、漢薩同盟等就具有明顯的社團主義特征。
近代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促進了與德國毗鄰的英、法等國自由經濟的發展,也為這些國家新興資產階級的出現以及其國內政治、經濟等的巨大變遷奠定了時代的基礎。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其革命主張幾乎令所有歐洲貴族及宗教特權者不寒而栗,之后法、英等國先后推出了自由貿易法案,傳統的行會制度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箱……面對鄰國的巨大變化,依舊是封建農業國家的德意志該何去何從?此時期,無論是參與德意志浪漫主義運動的思想家還是持保守主義、民族主義思想的上層人物都對鄰國的變化充滿警惕,他們大多主張反其道而行之。比如,一些思想家竭力為傳統國家管理模式辯護,他們明確提出權利和義務不是源自民眾的意愿、自然法或者叫作憲法的那一張紙,而是來自古老的、源遠流長的習俗和傳統;[8]一些思想家反對經濟領域的個人主義、貿易自由,他們甚至倡議創建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借助國家壟斷來實施對外貿易……[9]當然,更多的思想家反對君主專制統治,他們理想中的國家是以中世紀的城市或行會為模板的,即這樣的國家既不會壓制個人自由,又對君主專制有所限制。黑格爾(Georg Friedrich Hegel)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認為國家并不是一種外在于個人且把自己強加于個人之上的異己的權威,相反,國家就是個人本身,個人只有在國家中個性才能得到真正地實現。[10]基于國家普遍的最終目的和個人特殊利益的統一性,他提出國家要承認市民社會不同構成單元的地位、合法權益并給予其特定的保護。黑格爾將其所認為的市民社會的不同構成單元稱為“等級”,而這樣的“等級”主要包括:由貴族莊園主所構成的實體性等級、行政官吏所組成的普遍等級、工商業代表所形成的私人等級以及同業公會等行業組織。黑格爾認為以上“等級”是個人參與公共事務最好的中介,“國家通過它們進入人民的主觀意識,而人民也就開始參與國事”[11],當人們在實現個人目的的同時也為他人服務,他們將更具公共精神,而更為廣闊和普遍的社會目的就更容易達成。[12]黑格爾的以上看法為社團主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進行了完美的闡釋。
1848年之后,德國國家社會主義者卡爾·馬里奧·溫克爾布萊奇(Karl Mario Winkelblech)等人進一步推動了社團主義理論的發展。溫克爾布萊奇提出理想的社會應該通過創建全面的行業協會章程,以確保在絕對不需要考慮其特權的基礎上,每個社會成員都能獲得與其工作能力相當的謀生手段。此外,他還建議各行業按照有產者、無產者和其他類型的職業活動者一定的數量比例關系組成“社會議會”(social parliament),所有代表均可以在議會中就與其自身利益相關的事情進行充分協商,同時,該議會還可以向傳統的政治議會(political parliament)遞交決議。在他所設想的這一和諧的社會秩序中,行會式的業主協會在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工業自治”將取代官僚集權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而國家的作用僅限于確定總體經濟政策、管理不多的公共行業和改進社會立法。[13]
德國保守主義運動吸納了溫克爾布萊奇等人的主張,遂在此后的社會管理中加以運用。比如俾斯麥(Otto Von Bismark)所希望創建的強大的君主政體就是受到不同團體限制的一種聯合政體,[14]魏瑪共和國臨時由工業、勞工、消費者和自由職業者以及專家組成的經濟委員會也是溫克爾布萊奇思想的體現。1920年,魏瑪政府頒布的《工作委員會法》更是將這一思想拓展到了整個經濟領域。該法授權在各企業工會之外創建由雇員組成的工作委員會,以最終促成勞資雙方就企業內部所有重大事務相互協商、共同決策模式的出現……[15]盡管納粹統治期間該制度遭到破壞,但是在德國工會的努力下,1946年,工作委員會的部分功能得以恢復;1947年德國煤、鋼產業率先建立了由工人和雇主一起決策的機制;1952年德國《工作章程法案》再次將雇員參與企業決策變成了國家意志。196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主政后,由于該黨明確主張所有政策都應該建立在雇主協會、工會和國家機構協商一致的基礎上,因此,社團主義更是逐步滲透進了德國公共生活的各個領域。[16]如,德國聯邦就業辦公室業務活動的正常開展仰賴于雇主和雇員之間的合作,作為利益相關者,聯邦層面的雇主和工會代表與聯邦政府機構代表共同構成了該辦公室管理、決策部門的主體;德國郵政和電信管理局同樣擁有一個由工會、雇主協會代表以及金融和電信領域專家所構成的管理機構……社團主義除了體現在聯邦層面的管理和決策過程中,在區域或部門層面以及在個體企業層面的各項管理和決策中,也都有明顯的表現。
二、德國職業教育立法籌備、倡議和創制活動中的社團主義
職業教育法律法規是一個國家法律法規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德國的職業教育法律法規是由聯邦和各州職業教育法律法規體系構成的。在聯邦層面,1953年頒布的《手工業法典》和1969年頒布的《職業培訓法案》是兩部最為重要的法律,《職業培訓法案》更是奠定了德國獨具特色的雙元職業教育制度的基礎。與以上法律相配合,德國聯邦還擁有一批相關的、輔助性的職業教育立法。從各州的角度來看,在各州常設教育和文化事務部長會議所確立的基本原則和框架指引下,各州獨立制定本州的職業教育法律法規。整體來看,無論是德國聯邦還是各州的職業教育法律法規,在立法籌備、倡議以及創制的過程中,社團主義均有著明顯的表現。
(一)立法籌備、倡議活動中的社團主義
如果將國會正式開始對某一立法提案審議之前的與該立法主題相關的所有討論和協商都算作立法籌備或倡議活動的話,那么,該階段任務的艱巨性、復雜性以及時間跨度都將遠遠超過國會立法創制過程。整體來看,這一階段的社團主義主要有兩種表現方式。
第一種是社會范圍內的討論和協商。自近代德國政府肯定了行會(后為商會)對于職業培訓的直接管理權之后,工會方就強調學徒培訓的公共屬性,質疑將大量的年輕人置于私人企業手中的合理性,批判學徒培訓過于依賴經濟而非教育邏輯,認為將企業作為主要培訓基地不合時宜。而雇主方則堅持企業承擔培訓成本、負責學徒培訓無可厚非,且行業自主管理有助于避免國家集權,增加企業應對市場或技術變遷的靈活性。此外,關于學徒培訓是教育關系還是工作關系的爭論也很多,工會方面認為培訓合同是一種工作協議,而雇主方由于擔心培訓津貼被視為工資而陷入工資糾紛更愿意其為教育關系……諸多關于職業教育本質、其該如何發展的爭論不僅見諸各類媒體,而且在不同層面的專業會議上也有所體現。[17]偶爾出現在司法領域的一些訴訟也會進一步加劇此類紛爭的激烈程度。
第二種是立法提案起草過程中的討論和協商。由于除了政府、政黨、議會黨團或議員個人之外,德國公民個體、公民小組、工會、經濟協會、教科文衛各種聯合會等均有權對各自領域的重大事宜提出立法或修法要求,并同時起草參考法案,參考法案經一定審批程序后可以轉變為正式遞交國會的議案。[18]加之德國《工作委員會法》《工作章程法案》以及之后的《共同決策法案》很早就構建了不同利益團體在機構內部就重要事務協商的機制,因此,與美國等國家在立法倡議或辯論環節臨時組建大型游說集團或者依靠個人活動來強化影響不同,[19]各類團體參與機構內部共同決策早已經成為正式制度滲透進了德國社會的機體中,特別是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民主進程的加快,這種現象更為明顯。[20]
從職業教育立法提案起草的角度來看,自1919年德國工會向國會遞交職業教育立法提案后的半個世紀時間內,先后有多個職業教育立法提案被遞交到國會,它們絕大多數是經過內部多種不同利益團體協商之后的結果。比如1969年3月由聯邦議院職業培訓法小組委員會遞交的提案就歷經了13次的內部會議協商。[21]
(二)國會立法創制活動中的社團主義
國會是社團主義表現得最為集中的地方。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德國國會的機構設置方式為不同利益團體參與討論與協商奠定了組織的基礎。德國國會由聯邦議院和聯邦參議院組成,其中參議院由各州代表組成,其主要代表各州人民參與聯邦立法過程。聯邦議院代表來自公民直選,德國選民在大選中可以投兩張票,其中的一票投給自己認可的候選人,另一票投給自己認可的某一政黨。因此,聯邦議院中就擁有兩種利益代表,他們對議院組織機構創建、議事規程制定、大會發言及其時間分配、表決安排等,甚至對聯邦政府的組成,政府政策或法案能否在議院順利通過等均有著重要的影響,而其建立影響的方式就是不斷地協商、討論與投票。其次是德國國會的立法程序確保了不同政黨和利益集團對于重要事務的全程參與。德國基本法規定無論哪一種渠道的立法提案,其一般都要經過前置和三讀程序,而在每一道關口,傾聽不同機構或利益群體的意見并做出積極回應是其順利進入下一步的前提。比如在前置程序,來自聯邦政府的立法提案一般要先經過參議院的審讀,參議院的立法提案也會先經聯邦政府的審讀后,才會遞交議院議長。而聯邦議院本身的法律提案,也必須首先在議會黨團內部取得一致意見,由議會黨團提出,或由5%的議員聯合提出后才能直接交給議長。此外,在議院的正式審議程序,除了聯邦議員、參議員、聯邦各部委代表會全程參與討論協商外,借助媒體,公眾也會對正在進行的立法過程有所了解并開展討論,而有關方面正好借此機會向議員、政黨和政府開展院外活動,以期法案能順利通過。[22]
以上特征在1969年《職業培訓法案》的國會創制過程中就可見一斑。此期間,各相關利益團體就職業培訓是否具有公共屬性、企業培訓與學校職業教育的關系如何協調,聯邦和州政府應該如何劃分職業教育與培訓的責任以及即將制定的法律究竟應該規范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哪些領域等一系列問題展開了充分的討論。期間,德國社民黨著重強調職業培訓的公共屬性,德國教育委員會則提醒人們不要忽略企業培訓也是一種“教育”,議會勞工事務委員會則提出公司和校內職業培訓必須盡可能相互協調,議會職業培訓法小組委員會主張新創制的法案應該冠以“職業教育和培訓法”而非單純的“職業培訓法”……可以這樣認為,幾乎所有的德國聯邦或州職業教育立法的議會創制過程都有社團主義的重要影響。
三、社團主義對德國職業教育立法全面深刻的影響
(一)社團主義決定了德國職業教育立法出臺的可能性
由于社團主義最為本質的特征就是沒有哪個部門擁有絕對的權力,重大事務的處理結果往往是多個利益集團協商討論、博弈之后的均衡解,這就導致德國包括職業教育法在內的幾乎所有法案的出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受社團主義的影響,在條件適當的情況下,原本已經擱置的議題也可能由于一些利益集團的支持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因此,社團主義既是大多數法案經歷漫長的立法準備的原因,也是一些法案最后得以頒布的最重要決定因素,這一點鮮明地體現在《職業培訓法案》的出臺過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工會希望創建由國家牽頭的、獨立于手工業和工業部門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23]但是由于工會的提案直接動搖了原有學徒制的基礎,遂遭到了工業和手工行業代表的強烈反對,加之其他立法條件并不具備,該提案遂被擱置。之后,盡管社民黨利用聯邦議院的平臺,在1962年4月曾呼吁聯邦政府向國會遞交職業培訓立法提案,社民黨希望該提案能夠將職業培訓領域的多個條款捆綁在一起,同時新提案能夠調控青年人就業領域的所有培訓關系和雇傭關系,[24]但是聯邦政府以此領域許多問題懸而未決為理由拒絕了此要求。1966年,在看到社民黨代表和議院的其他5位成員聯合向國會遞交了關于勞動力市場調整的相關提案,借此良機,多黨聯合政府隨即在兩個月后遞交了職業培訓提案,盡管該提案很快進入了一讀程序,但是由于多種原因也不了了之。1968年10月至次年3月,聯邦議院職業培訓法案小組委員會在社民黨主席哈里·利爾(Harry Liehr)的領導下,重新起草了一個職業培訓提案,從那時起,討論協商了40余年的職業教育立法事宜才邁入了實質性的立法階段并很快成為法案。
(二)社團主義決定了德國職業教育立法的最終形式
一般來說,在社團主義影響較大的國家,提交國會的立法提案與國會最終通過的法案之間會有著巨大的差異,其原因就在于任何通過的法案都是在多方面吸取各團體意見后集思廣益的產物。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立法中“雙元”“行業自治”等典型特征的形成就是社團主義的產物。
德國教育委員會早在1964年就已經提出了“雙元”概念,但是由于德國基本法對于聯邦教育權力的限制,1966年由多黨聯合政府遞交的提案僅僅提及了工業部門的職業培訓,1969年由社民黨牽頭遞交的提案,僅僅關注手工業和工業部門的培訓,傳統由各州負責的職業學校的教育并沒有涵蓋在立法提案之內。為此,學校方面提出了強烈的抗議,他們堅決要求國會采取措施確保職業學校成為工業和手工業部門培訓重要的合作者。由于1969年法律對于聯邦政府在教育資助、管理方面的限制已經解除,黨派格局也朝向有利于職業培訓法案出臺的方向發展,因此,在社民黨最終遞交的提案即將被國會通過之前,學校方的意見終被采納,雙元職業教育制度遂正式形成。
當然,除了“雙元”這一特征之外,德國工會1959年提案提出的希望創建由國家管理的、具有現代意義的、完整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的建議之所以不可能通過,也是社團主義影響的結果。一方面由于德國商會的力量非常強大,且1953年頒布的《手工業法典》已經對行業自治做出了必要的規定;另一方面,國內主要政黨也對國家過多干預教育持反對的態度。因此,多方博弈和協商的結果就是行業自治得以保留。
(三)社團主義決定了德國職業教育立法實施的方式
德國職業教育立法在實施過程中也會受到社團主義的影響,主要依靠各類理事會或委員會來實現該影響。如,聯邦職業教育培訓部是《職業培訓法案》規定的聯邦層面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宏觀管理機構,其內部的主要決策機構是理事會,理事會8名成員中來自雇主、雇員和州的代表各1名,其余的5名來自聯邦政府,教育培訓部所有重大決策均出自理事會各派代表的共同協商。商會是直接規約企業培訓活動的主要領導機構,《職業培訓法案》要求每一種類型的商會均要建立自己的職業培訓委員會,凡與職業訓練有關的重要事項,均應通知該委員會并向其提出咨詢要求。法案要求各商會職業培訓委員會由6名雇主代表、6名雇員代表和6名職業學校教師代表組成,職業學校教師有發言權但是沒有投票權。只有擁有投票權的半數以上成員到場才符合法定的人數,所有的決定都必須獲得委員會多數贊成票后才能產生。[25]法案要求聯邦各州也要建立職業培訓委員會,盡管各州職業培訓委員會接受的是州政府的管理,但是各州委員會也同樣是由同等數量的雇主、雇員、州最高當局代表組成……[26]重要事務由不同利益群體共同參與、共同協商,是德國職業教育立法實施的重要特征。
(四)社團主義決定了德國職業教育立法的監督方式
社團主義決定了德國職業教育立法的監督絕不可能來自單一部門。首先不應該忽略上文提到的各類理事會、委員會,它們同時具備監督的功能。因為不同來源的代表在各類理事會、委員會共同決策時,他們之間的相互協商、爭論,對于確保法律運行在正確的軌道有著重要的作用。除了發生在理事會或委員會中的相互監督,德國職業教育立法的設計方式,也確保了各層面的重要事務隨時能夠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比如,企業參與學徒培訓是雙元職業教育立法的基點,為了使單個企業的培訓滿足國家經濟發展的要求,《職業培訓法案》第4條明確要求企業必須在國家認可的培訓行業名單內進行培訓。而法案同時規定:聯邦經濟技術部和其他主管部門應與聯邦教育研究部在達成一致意見后(可無須經聯邦議院批準)正式發布這一名單……如果培訓名單或其他事情發生變化,主管部門應及時通知州政府相關部門,并讓他們參與協商。[27]此外,對于培訓企業自身的資質問題,法案也要求多個管理部門協商后首先要達成一致意見,然后向聯邦職業教育培訓部征詢意見之后再行發布。由于企業與學徒之間簽訂的合同是確保初始培訓(Initial training)沿著預定軌道進行的重要保障,因此,簽訂好的合同不僅需要在各類商會注冊登記,且商會還會雇傭專門的培訓指導員對所轄企業的培訓活動和學徒考試質量實施全程的監管。當然,除商會監管之外,工會、雇主協會也會對公司的培訓過程及培訓質量實施多次的檢查。除了以上來自企業外部的監督力量,所有的學徒都持有培訓日志本,該日志詳細記錄了學徒如何向企業方進行咨詢、學徒的日常行為、學徒與同事的關系等內容,負責任的企業培訓人員會定期檢查該記錄并簽字,各商會考試局也非常看重這一記錄。[28]
(五)社團主義對德國職業教育立法實施效果有著重要的影響
社團主義也影響著德國職業教育立法的實施效果。由于立法確保了企業培訓領域的幾乎所有重要事情都是由政府、商會、工會等多部門集體協商、一致同意后決定的,這一機制不僅是培訓企業高度認可培訓活動的前提條件,同時也為各相關利益團體積極參與與培訓相關的各類活動奠定了良好的輿論和心理基礎。因此,與英、美等國企業更為經常地從市場直接招募合格勞動力的做法相比,德國企業更愿意參加雙元制培訓。據統計,2015年,德國有占總量近20%的企業提供了各種類型的學徒培訓,其中,超過81%的大型企業參與了各種類型的培訓。[29]這些企業不僅是培訓場所、培訓活動、培訓費用、學徒津貼的提供者,而且培訓結束后,培訓企業還將為至少60%的學徒提供在本企業任職的機會。
德國企業的以上做法不僅強化了員工對于企業的忠誠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該國青年的失業率。2018年3月,德國15~24歲青年失業率為4.8%,為歐盟最低,而歐盟所有成員國青年的平均失業率為15.9%。[30]此外,由于相對較高質量的雙元制培訓,德國企業還收獲了源源不斷高水平的員工,從而使德國產品的質量得到了較好保障。當然,由于社團主義是一種將不同利益團體捆綁進職業培訓命運共同體的一種方式,在經濟發展良好、變化相對緩慢的時代,社團主義可能對職業教育立法實施效果帶來更多正面的影響。但是,在技術更新速度加快、競爭更加激烈的環境中,由于各個團體的利益都要平衡,社團主義不僅可能降低企業決策的速度,還可能降低企業參與培訓的意愿,進而對立法實施的效果帶來負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