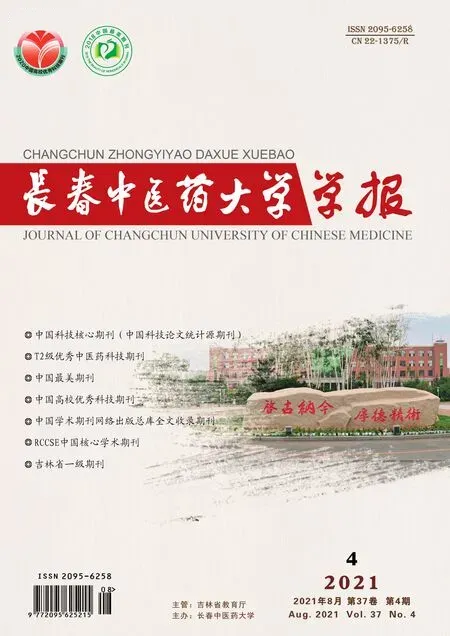吳有性《溫疫論》之“證、法、方”淺析
馬金玲,于 海,魏 巖,張文風
(長春中醫藥大學,長春 130117)
吳有性,字又可,“溫疫學派”創始人,約生活于公元1582~1652年,是明末清初著名醫學家。據史料記載,崇禎辛巳年,南北直隸、山東、浙江等地爆發了大規模瘟疫,在運用治療傷寒的方法無效的情況下,吳有性推究病源,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總結臨床經驗,寫下了《溫疫論》這一著作。《溫疫論》分上、下兩卷,系統論述了疫病病因、病邪傳變、治則治法,用藥宜忌、預后調攝等,體現了吳有性學術思想的精髓。在治法上,重視驅邪兼顧扶正,具體治法強調疏利與分消;借鑒前人對外感病的治法及處方,并融匯自身感悟,自擬達原飲、三消飲等名方,開創治疫新思路,相關理論與臨床經驗對于疫病防治具有重要價值。秉承中醫“隨證立法、依法處方”的原則,本文試從辨證、治法、處方三方面進行總結,意將“證、法、方”相聯系,從整體上剖析吳有性學術思想。
1 辨析病證,注重病因病性病位
吳有性在《溫疫論》中提出了異氣致病學說,奠定了溫病學的理論體系。在辨證中注重病因、病性、病位的辨析,從多方面剖析病證,化繁為簡,為“隨證立法”提供依據。
1.1 病因
《溫疫論》開篇即言:“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1]。“異氣”又被稱為“疫毒”“戾氣”“疫氣”“癘氣”等。吳有性認為,瘟疫是由“異氣”所引起,其雖為外感,但有別于六淫,吳有性創立的異氣學說,彌補了外感六淫為致病病因的傳統觀念,揭示了異氣發病的諸多規律。預測到了致病“微生物”的客觀存在,指明了異氣的物質性,對傳染病的病因研究提供新思路,與現代微生物學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2]。吳有性認為,異氣不僅是外感病致病因素,也是諸多內科疾病的致病因素[3]。因此,在治法及選藥組方上《溫疫論》更注重表里兼顧而非單純解表。
1.2 病性
吳有性在病性的辨別上強調了特異性、指明了傳染性、突出了物質性,他認為溫病、熱病、溫疫都屬于“溫熱病”的范疇,均為“陽邪”,它們的主要區別在于邪熱的程度不同和是否有傳染性[4]。熱輕者為溫,重者為熱;溫病、熱病均不傳染;能引起傳染的則稱為溫疫[5]。吳有性還區分了一般傳染與烈性傳染的不同,他認為傳染病由雜氣而引發,雜氣之中危害大的傳染性更強的為戾氣[6]。正如《諸病源候論·疫癘病候》所載:“其病與時氣、溫、熱等病相類……病無長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厲之氣,故云疫癘病”[7]。吳有性又指出,疫病具有特異性,即某些異氣只傳染人,不一定傳染動物;某些異氣只傳染動物,不傳染人。
1.3 病位
以醫圣張仲景為代表的多數醫家都認為,外感病證均是邪犯肌表,病位在表,吳有性創造性的提出,邪從口鼻而入,首創“邪伏膜原”之說,《溫疫論》云:“邪自口鼻而入,則其所客,內不在臟腑,外不在經絡,舍于夾脊之內”[1]。吳有性首次將膜原定位在“半表半里”,并明確指出,膜原為表里之分界[8]。對于邪伏膜原的感邪途徑,吳有性指出,邪可自口鼻直接傳到“膜原”,溫疫邪氣從口鼻進入人體后,先伏于膜原,之后再產生傳變。吳氏觀察到疫邪侵襲人體后,在不同人體內傳變方向不同,故將其概括為“九傳”。
2 酌定治法,攻邪為主兼顧扶正
《溫疫論》對病因的認識為疫戾之邪外感,因此,《溫疫論》中的治法都是圍繞“驅邪外出”而展開,逐邪為《溫疫論》治法的核心內容。邪氣經由肌表及口鼻而入,根據前文對病因、病位的介紹,驅邪以汗、吐、下為主,而在三法之中,吳氏偏愛汗、下二法,如《溫疫論》強調“疫邪表里分傳,里氣壅閉,非汗下不可。汗下之未盡,日后復熱,當復下復汗”[1]。疫戾之邪侵襲,必傷正氣,邪氣性質不同,故引發不同病證,需依據邪氣的致病性予以治療,治療之法為攻邪兼顧扶正。攻邪秉承“給邪氣以出路”的原則,因勢利導。扶正重在養陰,繼承了《黃帝內經》“實其陰以補其不足”的思想。
2.1 汗法
汗法是使外感之邪潰出膜原,由表而出的治療方法。吳有性在《溫疫論》中多次以汗作為診斷及治療依據,涉及到戰汗、盜汗、狂汗、自汗等。簡言之:戰汗,邪留氣分解以戰汗,使精氣輸泄,可以頓解;盜汗,此盜汗與陰虛盜汗不同,外感盜汗邪在經,以清透為治療之法;自汗,此自汗與表虛自汗不同,此自汗應以清、下為法;狂汗,汗解熱瀉而狂止。因寒、溫之性不同,各有其特異的致病性,故吳有性所稱汗解,并非專用麻黃、桂枝等辛溫發汗之品,這一點與傷寒汗法有所不同。吳有性掌握了汗法的真諦,即汗法不以發汗為最終目的,汗只是用于驅邪的手段及途徑,汗法的最終目的是驅邪外出,故其注重疏通氣道,為邪從外解創造有利條件[9],這一思想為后世“治上焦如羽”“透熱轉氣”法的創立奠定了基礎。
2.2 下法
吳有性對于下法的運用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其中以“溫病下不厭早”之說對后世溫病治療的影響較為深遠。針對張仲景的“傷寒下不厭遲”理論,吳有性提出“溫病下不厭早”,其明確指出:溫疫中的下法亦是以“逐邪”為目的的,與“汗法”相似,“瀉下”也只是祛邪的一種手段[10]。吳有性在《溫疫論》中論述了“下不厭早”的原因,即:客邪貴乎早治,因機體正氣未衰,方能與邪氣相爭,邪去則正自安。依法統方,故有“溫疫邪毒傳于胃,用達原飲加大黃下之”;又如“溫疫邪毒最重,復瘀到胃時急投大承氣湯”[1]。吳氏根據自己立法依據,歸納了三承氣湯的適應證,即:熱邪傳里,僅出現上焦痞滿,用小承氣湯;中有堅結者,可加芒硝,軟堅而潤燥,助大黃有滌蕩積滯;若無痞滿,惟有宿結瘀熱者,用調胃承氣湯。吳有性攻下之中不乏謹慎辨證,善用下法而不妄用,繼承中更不乏創新,對后世下法的運用提供了新思路。
2.3 養陰
從《溫疫論》的論述中可知,吳有性認為,疫病為熱性病,邪氣內盛,陽氣內郁,積而化火,“陽勝則陰病”,煎熬陰血,故扶正應以養陰為主。扶正的前提是邪氣已除,邪去則正氣得通;若邪未去而妄用補法,補益藥過于滋膩會使余邪留伏,日后必生變證。吳氏創諸養榮湯以驅邪護陰,強調藥后調護,若調理之劑,投之不當,不如靜養節飲食[9]。
3 選藥組方,表里上下進退有度
從辨證及治法的確立上,不難看出吳有性在疫病的診療上從整體著眼,以疏利透達為主要治法,講求實效、快速,可謂匠心獨具。因此,在方劑的藥物選擇及配伍上力求兼顧表里上下,代表方劑如達原飲、三消飲。吳有性還提出了“一病一藥”治療疫病的大膽設想,即每一種疫病都會有與之相應的藥物可以治療[4]。
3.1 達原飲
達原飲為《溫疫論》治疫第一方,吳有性創造性的提出“邪伏膜原”,用此方開達膜原,辟穢化濁。原方組成為:檳榔二錢,厚樸一錢,草果五分,知母一錢,芍藥一錢,黃芩一錢,甘草五分[1]。從藥物功效分析,此方本身并無“汗”“下”之功,但溫病初期使用,亦可收到出汗、下瀉之效。方中君藥檳榔破氣消痰,除伏邪,疏利氣機;厚樸理氣化濁除濕;草果芳香辟穢,化濁止嘔,與厚樸共為臣藥,君臣相伍,藥力或向外或向下,使邪氣分散潰敗,速離膜原。佐以黃芩清熱燥濕;驅邪兼顧扶正,熱傷營陰,加知母、白芍以養陰和營,甘草護胃安中、調和諸藥。全方合用,內外兼顧,透達膜原而不傷陰。
3.2 三消飲
因膜原位于“半表半里”“邪伏膜原”若不能及時驅邪,后續傳變既可見外犯三陽而出現表證,又可逐漸化熱入里而出現里證。表里分傳,治以表里分消,吳有性創三消飲,此方所治之證為邪伏膜原的后續發展,故方由達原飲加大黃、柴胡、羌活、葛根、生姜、大棗而成。達原飲堅守膜原,羌活治太陽之證,葛根治陽明之證,柴胡治少陽證,大黃通便瀉下,生姜、大棗補脾和胃。命名為“三消”,即消外、消內、消不外不內,即能疏解膜原之伏邪,在外可消除浮越在三陽經之表證,在內可清除入胃之邪熱,特別是對邪毒表里分傳[11],治以內外兼顧、補瀉兼施,體現了吳氏辨證立法的獨到見解。
綜上所述,《溫疫論》作為第一部治療疫病專論,以吳有性自述的形式全面論述了疫病的發生發展、傳變轉歸、治法處方思路及典型醫案。雖然全書僅有上下兩卷,字數不多,但所載內容均源于吳有性臨床實踐中的診治經驗和心得體會,有重要的臨床及研究價值。筆者在學習本書過程中,整理了吳氏對疫病病證診療的見解,發現吳有性在辨證上,突出邪氣的外感性、特異性、物質性、傳染性,重視病位及傳變途經,以膜原為主要病位,為治法的確立提供依據;立法以驅邪為要,重視“因勢利導”,輔以養陰及調攝;根據治法選藥組方,達到驅邪為主兼顧扶正的立方思想,創達原飲、三消飲等名方。《溫疫論》為溫病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寶貴的思路,為后世醫家所遵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