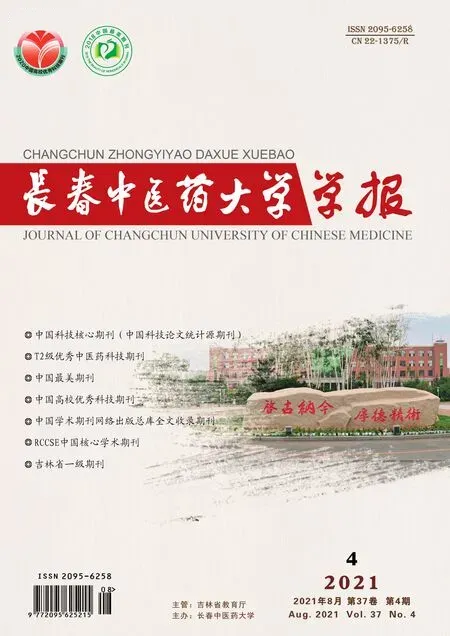基于詮釋學視野的《溫疫論》學術思想研究
閆敏敏,黃作陣,楊必安,姚 鑫,朱 志
(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北京 100029)
己亥冬末至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肆虐全球,中華舉全國之力抗擊疫情,終贏得初步勝利。回顧整個抗疫階段,中醫藥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這與千百年來中國人民在與疫病斗爭過程中所積累的實踐經驗及相應的醫學理論有分不開的關系。中醫學對疫病的認識早從先秦時期就開始了,經過歷代醫者在結合自身實踐下的不斷詮釋,至明末清初,江蘇醫家吳有性創造性地提出,瘟疫病因“異氣說”,且在瘟疫傳播方式、致病路徑及治療方法上皆有開創性的見解,其所撰《溫疫論》亦成為我國首部瘟疫學專著,在中醫疫病學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而從詮釋學的視角來看,《溫疫論》所體現的學術思想實為特定時代下、醫者在結合自身醫療實踐及學術背景基礎上進行的一次經典理論的重新理解和解釋,中醫經典文本在形成后,其自身對讀者的開放性亦為確立其經典地位及歷久彌新的生命力提供了必要條件,本文試在詮釋學視野下對《溫疫論》學術思想的形成作一分析,以期為當前時代下中醫經典研究和理論創新路徑提供參考思路。
1 詮釋學概念內涵
詮釋學(hermeneutics)興起于近代西方,是一門有關對文本的理解、解釋和應用的新興學科,其最鮮明的特征是強調理解與解釋,是與時俱進的,讀者的歷史性對文本意義具有決定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是伽達默爾,伽達默爾主張理解不是一種對于某個被給定對象的主觀行為,而是屬于效果歷史,即理解是屬于被理解東西的存在,讀者對文本意義具有決定性作用[1]。任何傳承物在每一個新的時代都面臨新的問題和具有新的意義,因此,我們必須重新理解,重新加以解釋。傳承物始終是通過不斷更新的意義表現自己,這種意義就是對新問題的新回答,而新問題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在歷史的過程中新的視域融合形成,而我們的解釋從屬于這一視域融合。所謂視域融合,即每個人都有從先見而來的理解視野,在理解前已具有自歷史而來的觀念、假設、前提等,而歷史典籍、歷史事件等也都帶有由其特定的歷史文化所賦予的視野,這就出現了兩個視野,解釋者的視野和被解釋者的視野,理解的過程即是兩個視野在更高層次上的融合,在這種融合下產生的理解是一種效果歷史[2],即理解者(讀者)對文本或歷史事件的解釋實際上是一種融合了自身背景的重構,文本本義和作者本義實際上不可達到,理解和解釋的過程以讀者所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這一過程也往往是實現學術理論、文化或實踐創新的關鍵。
2 詮釋學在中醫學中的應用
上世紀90年代楊學鵬先生發表“開辟中醫學第二戰場——中醫詮釋的研究”一文,文章首先提出了“中醫詮釋”的概念,但該篇文章所闡釋的并非西方詮釋學的相關概念及理論,而是強調梳理原義,用現代語言對中醫理論進行詮釋和“破譯”。較早將詮釋學理論引入中醫研究當中來的當為陜西中醫藥大學邢玉瑞先生,其指出詮釋學在《內經》學術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義[3]。近年來,王永炎院士團隊在詮釋學與中醫學方面做了較多相關研究,王永炎先生認為,詮釋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如施萊爾馬赫的重構學說、伽達默爾的效果歷史意識等對實現當代中醫理論的創新具有重要指導意義[4-5],并據此提出了構建中醫詮釋學的想法,指出歷代以來注釋中醫經典的傳統中與詮釋學在實踐要素上具有一定的契合度,這為詮釋學理論在中醫學繼承和創新過程中發揮作用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在研究后世醫家對經典醫籍進行解讀時是否采用了 “文本中心論”“作者中心論”及“讀者中心論”的問題上有重要指導意義。此外,趙京生等學者皆從不同角度發表了詮釋學視野下研究中醫學術的相關論文,包括中醫經典的詮釋學研究、中醫理論的詮釋學研究、中醫詮釋學方法探討、創建中醫詮釋學的探索及詮釋學在中醫其他領域的應用等五個方面,并有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韓彥華[6]與北京中醫藥大學張濤[7]在博士論文中運用詮釋學的理論及方法對中醫相關學說和思想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表明詮釋學對當下中醫學術的研究確有指導價值,不失為探究中醫理論創新路徑的一個新方向,筆者不揣淺薄,通過對吳有性《溫疫論》學術思想的溯源,試以當代哲學詮釋學最具代表性理論即伽達默爾的視域融合理論分析其形成過程,從中可管窺古人在經典詮釋與理論創新之間的通道。
3 《溫疫論》學術思想溯源
《溫疫論》一書共兩卷,上卷載文51篇,闡發瘟疫病因病機、證候、治療,并從不同角度論述了瘟疫和傷寒之間的區別;下卷載文36篇,敘述瘟疫各兼夾癥的臨床表現及其病因病機與治法等。總結而言,全書圍繞瘟疫所體現的學術思想主要有四:一是病因方面提出“異氣說”,即“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突破了前人所認為的“四時不正之氣”的觀點,且認為致病因素除風、寒、暑、濕、燥、火六氣之外,尚有“雜氣”“是氣也,其來無時,其著無方,眾人有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為諸病焉”,而不同的“雜氣”可引起不同類型的瘟疫癥狀;二是在瘟疫傳播途徑上認識到致病邪氣“從口鼻而入”(空氣傳播),亦可謂超越前人之見;三是病位和傳變上指出疫病之邪處于半表半里之間(膜原),臨近于胃,有九種傳變方式;四是治療方法上創制達原飲并強調使用下法。然結合中醫瘟疫學術發展史來看,這四方面實際上有源可尋,乃是吳有性在自身學術背景(醫學和理學)及實踐基礎上,對經典文本和前人論述在繼承基礎上的突破性解釋,且在不自覺間運用了正確的敘述方法,進而實現了理論上的創新,反過來又對臨床實踐產生了較大的指導性價值。從下文對其各學術思想的溯源中可明顯發現這一路徑。
3.1 病因異氣說
吳有性在《溫疫論》上卷“原病”中即開宗明義地指出:“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之癘氣,在歲有多寡,在方隅有濃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8]。首先否定了前人“非其時而有其氣”的瘟疫致病說,提出瘟疫乃“天地之癘氣”所引發的觀點。從中醫瘟疫發展史來看,自王叔和(約公元201~280年)在《傷寒例》中提出“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的說法之后[9],后世各家如龐安時、郭雍、朱丹溪等在對瘟疫病因的認識上多遵此說;然“天地之癘氣”的概念并非吳氏首先發明,早在東晉時期,葛洪《肘后備急方》中即有“其年歲中有厲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之說[10],其后巢元方(公元605~616年)在《諸病源候論》又有“若因歲時不和,溫涼失節,人感乖戾之氣而發病者,此則多相染易”的記載,提出“乖戾之氣”的概念[11],明初王安道(公元1332~1383年)《醫經溯洄集》中亦有:“彼時行不正之氣所作,及重感異氣而變者,則又當觀其何時何氣,參酌傷寒溫熱病之法,損益而治之,尤不可例以仲景即病傷寒藥通治也”,已有“異氣”之說[12]。此外,明·王綸“天地之病氣”的見解及《素問·刺法論》所論述的內容皆為吳又可創立異氣病因學說起到了比較直接的啟示作用。從對瘟疫病因認識的發展來看,早期帶有巫術色彩和迷信模糊印象漸漸呈現出與自然氣候等客觀因素相關的清晰認知,無疑是很大的進步,吳有性整合了前人之論并結合自身所處之時代背景及其臨床實踐經歷,以正確的敘述方式加以抽象闡發,方實現了理論創新。
3.2 邪自口鼻入
長期以來,諸醫家對瘟疫的討論多集中在病因方面,如從病因上分析傷寒、寒毒、時行、瘟疫之間的區別等,北宋·龐安時(約1042~1099年)在《傷寒總病論》卷五有“天行溫病論”一節曰:“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者,皆由冬時觸冒寒毒所致,自春及夏至前為溫病者,《素問》仲景所謂傷寒也。有冬時傷非節之暖,名曰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即時發病溫者,乃天行之病耳”[13],認為冬天感受寒邪,不即時發病,至春天及夏至前發為溫熱性質疾病的為《素問》和仲景所說的傷寒;而冬天應寒反暖,人感非時之氣所發病者,則為天行瘟疫。郭雍(公元1106~1187年)《傷寒補亡論》“傷寒瘟疫論”一條中指出:“若夫一鄉一邦一家皆同患者,是則溫之為疫者然也,非冬傷于寒自感自致之病也,蓋以春時應暖而反寒,夏熱反涼,秋涼反熱,冬寒反暖,氣候不正,盛強者感之必輕,衰弱者得之必重,故明溫疫,亦曰天行時行也。設在冬寒之日,而一方一鄉一家皆同此者,亦時行之寒疫也”[14],認為傳染性是瘟疫區別于傷寒的主要特征、而氣候反常、四時不正之氣是引起瘟疫流行的主要原因。而有關瘟疫之邪侵入人體的途徑在諸醫家闡述中鮮有提及,但并非完全沒有,《靈樞·口問篇》即有:“口鼻者,氣之門戶也”[15]的認識,元·王好古《此事難知·辨陰陽二證》[16]就已指出,寒邪屬無形之氣,可從口鼻進入人體,為吳氏“邪從口鼻而入”的提出提供了先行之資。
3.3 病位內伏膜原
吳又可認為,瘟疫之邪從口鼻侵入人體后,病位“內不在臟腑,外不在經絡,舍于伏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為半表半里,即《針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此處“膜原”說則是對《內經》論述的直接引用和發揮,《素問·瘧論》載:“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于五臟,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素問·舉痛論》曰:“寒氣客于腸胃之間,膜原之下……”[17],吳又可所論疫病初起,伏于膜原,不得不說其理論基礎是直接來源于《內經》之論,又結合自身臨證觀察及實踐經驗所做出的理論重構。
3.4 創制達原飲,強調通下法
在對瘟疫的治療上,吳又可根據臨床實踐創制了治疫名方達原飲,提出“溫疫初起,先憎寒而后發熱,日后但熱而無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脈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其時邪在伏脊之前,腸胃之后……宜達原飲”,治法上擅用大黃,強調下法,雖立九種傳變方式,但在辨證上依然運用仲景三陰三陽辨證法,并未脫離《傷寒論》,是對仲景治法及金元四大家等前人理論在實踐基礎上的進一步詮釋運用。
4 詮釋學視野下的《溫疫論》學術思想形成分析
總結上文,細究有性之論,實非完全原創,乃是在我國古人對瘟疫已有認識的基礎上結合自身實踐經歷和學術背景對原有理論的重新整合和建構。《溫疫論》中雖體現出吳氏有創立不同于傷寒思想之意圖,但在辨證、治療等方面仍在不自覺間有所運用,且《內經》及金元四大家等前人之論亦為其新理論的構建有重要影響,但這種影響是如何實現的,同樣的時代條件下,吳有性是如何從眾醫家中脫穎而出,成為豎起新標桿的那個人呢?
4.1 生活時代瘟疫頻發
據《明史》記載,從永樂六年(公元1408年)至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中國發生瘟疫流行達19次之多,其間以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即《溫疫論》成書前一年)流行程度尤為嚴重,疫情遍及山東、河北、江蘇、浙江等省[18]。吳有性在《溫疫論》自序中即記載道:“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崇禎辛巳即公元1641年,時明王朝已至暮年,風雨飄搖,社會動蕩,受常年戰亂、人口集中及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全國各地疫病流行,波及范圍廣、程度深、歷時長,給人民生命安全造成了極大損失。張志斌先生《中國古代疫情流行年表》中羅列了現存一些古籍中對當時疫情的記載,大多數雖字詞寥寥,仍可看出疫情的嚴重程度:張廷玉等《明史》卷28《五行志》第4“永樂六年正月,江西建昌、撫州,福建建寧、邵武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萬八千四百余人”,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崇禎十三四年(1640~1641),大疫”“(崇禎十四年)山寇披猖,官兵駐巢,多嬰癘疫”,周揚俊《溫熱暑疫全書》卷4“崇禎壬午、癸未(1642~1643),時疫盛行,道殣相藉”[19]。吳有性所生活的吳縣當時疫情流行亦頗為嚴重,《吳縣志》載道:“一巷百余家,無一家幸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僅存者”。吳有性身為醫者,目睹疫病慘狀,又痛心于當時大多醫師不明瘟疫病機而“誤以傷寒法治之”,以致延誤病情,“病者日近危篤,病愈急,投藥愈亂,不死于病,乃死于醫”,于是深入疫區,“靜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其傳變之體”,將自己的實踐經驗總結而成《溫疫論》。
4.2 學有所承思維獨特
廖育群先生指出,吳有性具有極強的思辨性頭腦,他之所以能夠看出疫病與一般外感傷寒的不同,正確地解釋了傳染病的病因、傳播方式,正是受惠于這種思辨過程,而這種理性思維,與宋明理學格物、窮理的思想有直接的關系,但從他的學術思想來看,則可以發現他的思維方式更接近于近代西方科學[20],可知學術背景和思維方式(即前見)是影響理論創新的主要因素之一,但與此同時,歷史事件和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在當下又該如何保持呈現出來?伽達默爾說:“每一時代都必須按照它自己的方式來理解歷史傳承下來的文本,因為這文本屬于整個傳統的一部分,而每一時代則對這整個傳統有一種事實意義上的興趣,并試圖在這傳統中理解自身”[1]5。吳又可《溫疫論》的問世顯然遵循這一理論,吳又可首先接受了來自理學及醫學經典和前輩的學術視野,之后在對多次瘟疫的實際考察和研究中,產生了新的經驗和新的感覺認識,在這個過程中實際上實現了來自自身前見和實踐兩方面的視域融合,經過歷史效果下的理解和解釋,并運用正確的敘述方法,從而實現了一次中醫學上的理論創新。
漢末三國與明末清代是中國古代疫病流行的兩個高發時期,而回顧中國醫學史的發展歷程,兩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瘟疫創新亦產生發展于這兩個時期[14]。由此可見,在時代背景下去傳承、理解和解釋傳統文本,善用其中的理論解答當下的新問題,是經典文本保持源源不斷的活力并產生新意義之根本,而文本、作者和讀者在這一過程中分別側重的占比是需要進一步思考和研究的問題。中醫學依靠文本和師傳解釋,逐漸形成了“以文本為中心”的醫學,實踐經驗是其最為突出的特點,對中醫文本的解釋不同于其他學科最大的一點即在于從醫者自身的醫療實踐,實踐所帶來的“前見”使醫者在理解和解釋前人之作時不會拘泥于文本本身,而是在不自覺間的一種再創造活動,吳有性正是在此基礎上所實現的理論創新,為溫病學的獨立成派做出了很大貢獻。
5 結語
黃龍祥先生研究認為,理論創新的完整過程分為兩條道路:第一條為研究階段“從具體上升到抽象”,即從感性具體到抽象規定;第二條道路為敘述階段“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即從抽象規定到思維具體。而理論體系的創新必須通過第二條才能最終完成。中國古人思維在第一條道路上優勢明顯,有包括演繹法在內的整套方法,甚至其相比于西方方法表現出更高的有效性,但中國古人忽略的是對第二條道路敘述方法的積極探索和自覺應用。而這則可以解釋,中國古代有許多偉大的發明創造,有極為豐富的經驗積累、規律發現,也不乏對經驗規律的理論假說,但由于缺少正確敘述方法支撐而極少成功構建出嚴謹統一的理論體系。從中醫學方面來講,歷史上那些橫空出世的中醫理論系統化經典之作如《黃帝內經》《針灸甲乙經》《脈經》《諸病源候論》《溫疫論》等多是醫家對理論體系構建正確方法的天才把握和不自覺應用,這種不自覺使得中國古代醫家應用公理化方法構建的理論,雖然也有邏輯起點以及串連理論推導的邏輯鏈,但這條“鏈”多半隱而不見,鏈上所系的命題也常常沒有按邏輯序列嚴格“對號入座”[21]。
黃龍祥先生通過多年探索,前瞻性地指出了中醫學理論創新的規律,可以發現這種規律恰與伽達默爾所主張的歷史效果事件一致,即后世醫者在理解和解釋中醫經典及前人論述時,是根據自己的當前語境和現實問題對傳統文本的把握,理解是陌生性與熟悉性、過去與現在、他者與自我的綜合,但敘述方法的缺如和對構建理論體系的不自覺又限制了中醫乃至中國文化中邏輯性和公理化理論體系的形成。這啟示我們,在對當前的中國傳統醫籍進行研究時,對作者、文本及讀者之間關系的側重性當有不同于以往的眼光,對傳統醫籍文本的詮釋只有跟隨時代背景,實現與當下的視域融合,并以正確的敘述方法進行闡釋,才可穿越時空,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得中醫古籍在當前時代煥發新的活力,為維護人類健康做出更為深刻而廣泛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