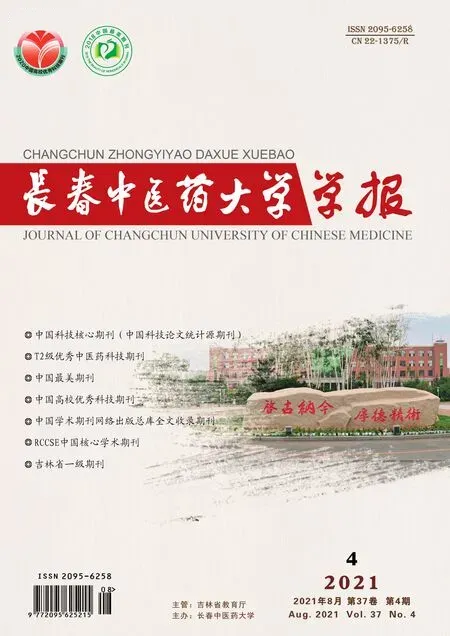吳深濤自擬潤魄湯治療糖尿病便秘
管媛媛,張春陽,吳深濤*
(1.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國家中醫針灸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天津 300381;2.北京中醫醫院平谷醫院,北京 101200)
糖尿病便秘是糖尿病患者常見的胃腸道神經病變之一,約25%的糖尿病患者可出現便秘[1]。該病以排便周期延長,或周期不延長而排便困難、糞質干結為主要臨床表現。便秘輕癥患者可出現腹痛、腹脹等,反復發作者可誘發肛裂、痔瘡等;嚴重便秘者可誘發或加重心腦血管疾病。除此之外,長期便秘患者常出現焦慮、煩躁等不良情緒,導致胰高血糖素、腎上腺素等激素水平升高,引起血糖波動[2]。總之,對患者的生活質量與心理造成持續性影響。目前對其發病機制尚不十分清楚,主要與患者長期服用降糖藥物破壞腸道內菌群結構等原因相關[3]。西醫治療在調控血糖的基礎上,以對癥治療為主,如:口服瀉藥、外用納肛藥物等。長期服用各種刺激性瀉劑,易出現瀉劑依賴性結腸、電解質紊亂等不良反應,并可引起結腸黑變病,增加導致大腸癌的危險性[4]。中醫療法如中藥穴位貼敷、穴位按摩、敷臍加灸療、電針等非藥物療法獲得較好效果[5-8]。
吳深濤教授,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第六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天津市名中醫,入選首批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全國優秀中醫臨床人才”。吳深濤教授從事中西醫結合治療內分泌代謝疾病、腎臟疾病的臨床及科研工作近40年,通過大量臨床病例觀察總結,發現便秘進展往往滯后于“三消”病程特點,遂將糖尿病便秘分為前、后兩期,前期病輕易治,后期病機復雜。依據糖尿病患者年齡分布特點及便秘進展特點,證屬精血虧虛者具有廣泛性,自擬潤魄湯治療屢獲良效(藥物組成:當歸30 g,炒萊菔子30 g,郁李仁30 g,火麻仁20 g,熟大黃10 g,生白術45 g,炒桃仁20 g,升麻10 g,太子參30 g,蜜紫菀30 g,鎖陽20 g,蓯蓉20 g)。筆者有幸師從吳深濤教授,現將本病病因病機、組方思路介紹如下,旨在為臨床實踐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1 病因病機
1.1 便秘之病因病機
對便秘的認識早在《黃帝內經》中就有記載,根據臨床表現可歸于“秘結”“大便難”等范疇,并認為二便與腎密切相關,如《素問·金匱真言論》曰:“北方色黑,入通于腎,開竅于二陰。”東漢張仲景《傷寒雜病論》提出以麻子仁丸治療“脾約”;明代張景岳《景岳全書》以理陰煎合參附、大承氣湯合芒硝、豬牙皂分別治療 “陰結”與“陽結”,效如桴鼓;清代沈金鏊《雜病源流犀燭》首提“便秘”之名,并沿用至今。歷代醫家大多數認為便秘之病,病位在大腸,基本病機為大腸通降不利、傳導失司。病因主要有飲食不節、情志失調、久坐少動、勞倦過度、年老體虛、病后產后、藥物所致等,部分患者與先天稟賦不足有關[9]。
1.2 糖尿病便秘之病因病機
祖國傳統醫學中并無糖尿病便秘病名,多依據其臨床表現歸屬為“消渴”“便秘”范疇。糖尿病病機為陰虛為本,燥熱為標。中焦為氣機升降之樞,脾主升清,胃主降濁,又脾主運化,則水谷及其糟粕得以下行。清代陳士鐸之《辨證錄·大便閉結門》云:“肺能生水,肺與大腸有表里之關切,豈無津液之降,以救大腸之枯竭……以大雨淋之,則汗魃之氣頓除,而河渠盡通矣。”便秘前期主要以津液不足為特征,病位在肺與脾胃,表現為大便干結難出,虛坐努責,肛門撕裂痛,常伴有口渴、多飲、多尿等津液耗傷之表現,治當滋陰補液,以增液湯為代表方。津液不足,糟粕留滯,損傷腸絡,久之損傷陽氣與精血,腎主開合,司二便,病位主要在腎。臨床表現為腸道失潤、大腸蠕動緩慢。其中仍有津液不足的表現,但此時以精血和陽氣虛弱為主。若仍以初期津液不足治之,則鞭長莫及。此階段常兼有神疲畏寒、氣短乏力、懶言喜臥、小便清長、腹滿無便意等。陽氣虛則腸道蠕動之動力不足,精血虛則蠕動之精華物質不足。正如《醫宗必讀·大便不通》所言:“更有老年津液干枯,婦人產后亡血……病后血氣未復,皆能秘結。”故臨床中老年人、久病體虛、久臥、婦人產后等患者常見精血虧虛型便秘。綜上,糖尿病便秘具有從津液不足到精血虧虛演變的病機特點,病位在肺、脾胃、腎。吳深濤據其病機特點,總結出“溫、潤、升、降”4字心法,并在此法的指導下,自擬潤魄湯廣泛應用于臨床,療效頗佳。
2 潤魄湯之組方思路
《難經·四十四難》:“唇為飛門……下極為魄門,故曰七沖門也。”名曰潤魄湯。本方具有“溫、潤、升、降”的組方特點,潤魄湯適用于精血虧虛便秘者,治以益精養血、潤腸通滯之法
2.1 溫而不燥
《景岳全書·秘結》篇云:“凡下焦陽虛,則陽氣不行,陽氣不行則不能傳送而陰凝于下,此陽虛陰結也。”方中當歸、鎖陽、肉蓯蓉為君,當歸養血和血,辛潤通便;肉蓯蓉、鎖陽溫腎益精、潤腸通便。朱丹溪之《本草衍義補遺》中記載:“鎖陽無毒,大補陰氣,益精血,利大便。虛人大便燥結者,啖之可代蓯蓉,煮粥彌佳。”又《得配本草》謂:“益精興陽,潤腸壯筋。”可見鎖陽質潤性溫,常同肉蓯蓉作為對藥使用。現代研究表明,總寡糖是肉蓯蓉有效作用部位,具有良好的潤腸通便作用[10]。現代毒理學研究表明,肉蓯蓉及其提取物對人體安全無毒性[11-12]。
2.2 潤而不膩
《素問·靈蘭秘典論》:“大腸者,傳導之官,變化出焉”。大腸主通降,有節律地將糟粕向下傳導及“變化”,以免艱澀之難。萊菔子、郁李仁、火麻仁、桃仁等籽類藥為臣,其富含油脂而質潤,具有潤腸之共性。萊菔子善于破氣消積,以除便秘之氣滯。同時,消渴病因“數食甘美而多肥”而發,萊菔子具有消食除脹之功效。桃仁炒制后用,取其潤腸之用。諸籽合用,具有潤腸、下氣之協同作用。《藥品化義》:“紫菀……因其體潤,善能滋腎,蓋腎主二便,以此潤大便燥結,利小便短赤,開發陰陽,宣通壅滯,大有神功。”又《本草正義》:“紫菀,柔潤有余,雖曰苦辛而溫,非爆烈可比,專能開泄肺郁……且柔潤之質,必不偏熱,較之二冬、二母,名為滋陰,而群陰膩滯,阻塞隧道者,相去猶遠。”生白術甘而柔潤,質多脂液。《本草經讀》云:“以其豐于脂膏,故宜于煎劑。”《本草崇原》云:“白術作煎餌,則燥而能潤,溫而能和。”白術水煎服,更有利于其脂液的溶解,有效成分的流出,發揮柔潤通便之效[13]。多項臨床研究表明,重用生白術(30~50 g)療效確切,安全性尚可,且對于長期使用果導片、開塞露、番瀉葉等瀉藥無效或停藥復秘者,白術亦有肯定療效,治療中及治療后尚未見腹痛、腹瀉及其他明顯副作用與不良反應[14-16]。
2.3 升降相因
方中生白術、太子參、紫菀為臣藥。為護其正氣擇之甘潤之太子參,其味甘、微苦,性平。其職有二:一是同白術補益肺脾,補氣生津,祛邪而不傷正;二是同升麻升已而降,群策群力。《醫經精義》云:“大腸之所以能傳導,以其為肺之腑。肺氣下達,故能導”。肺與大腸相表里,大腸承接下降之肺氣,以司通降之能。紫菀為善補肺氣以開郁,則通降有源,且性涼柔潤,以免徒增壅遏之虞。其中升麻之用藥思想取之濟川煎。先升后降,升已而降,升清降濁。此方中熟大黃為使藥,保留其寒涼之性,以司清熱通腹之能,且防溫熱藥傷津之弊,起輔助作用。其性已不似承氣湯類中峻猛,且用量亦有所考慮。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蒽醌苷類為大黃瀉下作用的主要有效成分,鞣質類為澀腸的主要有效成分。生大黃經炮制成熟大黃后,蒽醌苷類和縮合鞣質類成分含量明顯降低,游離蒽醌和單體鞣質的含量明顯增加,熟大黃在蒽醌苷及單體鞣質的瀉下和澀腸雙向作用調節下表現出穩定的弱瀉下作用[17-18]。
2.4 隨癥加減
吳深濤以潤魄湯為基礎底方,臨證圓通,常取古方之代表二三味藥配入方中,療效尤佳。兼口干、口渴、舌苔干者,加沙參、玉竹,取沙參麥冬湯之意;情態憂郁者,加合歡花、柴胡,取逍遙散之意;兼便血者,加地榆、槐花,取槐花散之意;下陷脫肛者,加柴胡取升陷湯之意;面白眩暈者,加白芍,取四物湯之意。
3 病案舉例
排便艱澀案 閻某,女,41歲,2019年7月15日初診。主訴:排便艱澀不暢10年余,加重伴胸悶太息2周。既往2型糖尿病病史12年,現血糖控制尚可。頸動脈硬化,斑塊形成,高脂血癥。心電圖提示:心肌缺血。刻診:便干,努責難出,2日一行,需服藥助便。平素精神不振,耳鳴似蟬,舌淡苔白,脈沉細弦。西醫診斷:糖尿病便秘。中醫診斷:便秘(證屬精血虧虛證)。治以益精養血,潤腸通便。處以潤魄湯加減:當歸30 g,炒萊菔子30 g,郁李仁30 g,火麻仁20 g,熟大黃7 g,生白術45 g,桃仁20 g,升麻10 g,太子參20 g,蜜紫菀30 g,鎖陽20 g,酒蓯蓉20 g,丹參25 g。7劑,水煎溫服,每日1劑。2019年7月22日2診,大便2日一行,較前容易排出,但有大便不暢感,腸鳴及矢氣增多,偶有腹脹。現已經停服西藥瀉藥,胸悶較前明顯減輕,精神狀態亦轉佳。舌淡苔白,脈沉。上方加制首烏20 g。14劑,服法同前。原方化裁共進35劑,諸癥消失,排便順暢,精神狀態好轉,心情愉悅。隨訪6個月,未再復發。
按語:該患者排便艱澀10年有余,病程長,兼癥紛雜。下焦不通則上焦壅滯,在上焦表現為耳鳴、時胸悶太息;在下焦表現為大便艱澀不暢。腎藏精,充于腦,腎之精血不足發為耳鳴。精神不振,舌淡苔白,脈沉弦則陽氣不振,脈道不充。辨為精血虧虛證。同時兼有胸悶、心肌缺血之表現,予丹參以活血祛瘀,養心通絡。二診時,腸鳴、矢氣增多,排便較前容易,仍有大便不暢感,此為氣機通暢,糟粕下行之征,當乘勝追擊,予制何首烏增強養血滋陰、潤腸通便之功。在祛邪的同時予以扶正,且緩下有度,逐漸恢復腸道功能。
排便周期延長案 王某,女,61歲。2018年12月20日初診。主訴:排便周期延長3年余,加重伴腹脹10天。既往2型糖尿病病史8年余,現血糖控制尚可。刻診:大便7~8天一行,平素無便意,大便干硬,呈羊屎狀,氣短懶言,納差,腹脹,畏寒。舌淡略紫,苔白干,脈沉細。西醫診斷:糖尿病便秘。中醫診斷:便秘(證屬精血虧虛證)。治以益精養血,潤腸通便。處以潤魄湯加減:當歸30 g,炒萊菔子30 g,郁李仁30 g,火麻仁20 g,熟大黃7 g,生白術45 g,炒桃仁20 g,升麻10 g,太子參20 g,蜜紫菀30 g,鎖陽20 g,炒決明子15 g。14劑,水煎溫服,每日1劑。2019年1月3日2診,藥后5天始,便意明顯,大便2日一行,轉暢,且便時無腹瀉、腹痛表現。余癥均明顯緩解。唯今晨起身時眩暈,自覺胃中反酸,舌紅苔薄黃,脈弦滑。中醫診斷:眩暈(痰熱擾神證);治以清熱化痰,清利頭目。處以溫膽湯以收全功。2019年12月陪同家人來診,訴停藥至今大便通暢,1~2日一行,秘結未發。
按語:排便周期延長,腑氣不通,阻礙人體氣機升降,清氣不升則氣短懶言,濁氣不降則腹脹、納差。綜合“畏寒”及舌脈則兼有陽虛瘀結之象,治以溫潤通便,暢達氣機。二診時,便意明顯,大便轉暢,且排便周期縮短,氣短明顯緩解。糖尿病以陰虛燥熱為病機基礎,熱象漸起,轉而清熱化痰以收全功。排便周期延長,在于胃腸蠕動功能不足。若一味選用行氣、破氣之品,病情僅有一時好轉,非長久之計,且易出現腹痛、下腹墜脹等不適癥狀。治療時要注重“調氣機”與“益精血”同施,以患者能夠自覺有便意,便前無腹痛,便時無下墜感為最佳。
4 結語
潤魄湯以溫潤為先,暢達氣機,寓通于補,標本同治,既益精養血以治其本,又潤腸通便以治其標,具有溫而不燥、潤而不膩、升降有序、祛邪不傷正的特點。潤魄湯適用于便秘之精血虧虛證,主癥表現為:大便秘結、腹脹無便意、形寒肢冷;兼癥表現為頭暈耳鳴、氣短、健忘、腰膝酸軟、小便清長等,多見于糖尿病久病患者,另外,老年人、久病體虛、偏癱久臥、婦人產后等精血虧虛、陽氣不足者亦可化裁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