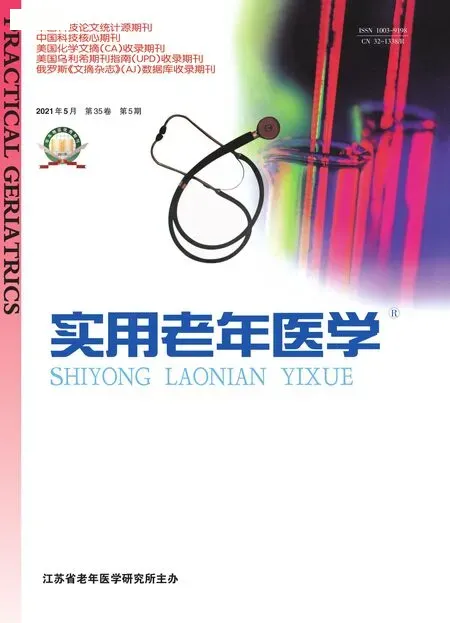基因型引導的抗血小板治療在冠心病病人中應用的研究進展
錢雯雯 韓志君 楊承健
CHD在全球死亡原因中占第一位,且近十幾年來,CHD的發病率及死亡率在我國也有明顯升高的趨勢。雙抗血小板治療(DAPT)由阿司匹林和P2Y12抑制劑組成,是CHD二級預防的基石[1]。氯吡格雷是一種二磷酸腺苷受體拮抗劑,是迄今為止世界范圍內應用時間最長、范圍最廣和研究證據最多的P2Y12抑制劑,具有抑制血小板活化與聚集的作用。但氯吡格雷的反應存在顯著的個體差異,約1/3的病人即使應用標準劑量的氯吡格雷,仍易發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包括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和支架血栓[2],即存在氯吡格雷抵抗。氯吡格雷抵抗主要受基因多態性、病人臨床特征、血小板生物學特性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有研究指出,CYP2C19基因多態性是氯吡格雷抵抗的獨立預測因素[3]。2010年3月, FDA宣布氯吡格雷抵抗的“黑框警告”,提醒應用氯吡格雷后出現心血管不良事件與攜帶CYP2C19功能缺失的等位基因有關[4]。但目前的臨床實踐指南均不常規建議進行CYP2C19基因型檢測和血小板功能檢測,這是因為盡管在幾個觀察性研究及小型的隨機研究中相繼提示了對CHD病人進行基因檢測以指導個體化抗血小板治療的可行性[5],但比較基因分型來指導DAPT的大型隨機試驗尚未完成,且老年病人具有基礎疾病多、合并癥發生率高、用藥種類多、代謝功能減退等特點。因此,對病人尤其是老年病人采取基因型引導抗血小板治療的臨床收益仍存在爭議。
1 CYP2C19基因多態性
氯吡格雷是一種無活性的前體藥物,約15%的氯吡格雷在肝臟經細胞色素P450酶代謝為活性產物。整個過程需要兩步生物轉化,第一步為經CYP2C19、CYP1A2和CYP2B6催化代謝為2-氧-氯吡格雷,第二步為經CYP2C19、CYP1A2、CYP2B6、CYP2C9、CYP3A4和CYP3A5等催化生成活性硫醇代謝物[6],其中CYP2C19是氯吡格雷活化的關鍵酶。CYP2C19基因具有高度多態性,有2000多個遺傳變異,其中大部分為內含子變異,少數為編碼區變異。目前已知的CYP2C19等位基因有34個,野生型CYP2C19*1是CYP2C19介導代謝的功能等位基因。很多研究已經證實,與不攜帶CYP2C19功能缺失(LOF)等位基因的病人相比,攜帶LOF等位基因的病人氯吡格雷生物激活能力降低,血小板抑制作用受損,發生MACE的風險更高[7]。最常見的LOF等位基因是CYP2C19*2和*3等位基因,他們常導致蛋白降解或生成非功能蛋白。單倍型CYP2C19*2含有一個變異(c.681G>A),該變異會導致提前出現終止密碼子而產生非功能性的截斷蛋白[8]。這種單核苷酸的等位基因變異頻率因種族而異,在南亞(32.5%)和東亞(31%)最普遍,其次是非洲(18%)、非芬蘭歐洲(15%)和拉丁美洲(10%)。其次是單倍型CYP2C19*3(c.636G>A),他也含有一個因過早出現終止密碼子而生成非功能性蛋白的變異。這種單倍型在歐洲和非洲人中很少見(分別為0.025%和0.037%),在南亞不常見(0.4%),但在東亞比較常見(6.3%)[9]。研究顯示,雖然還有其他CYP2C19等位基因的報道,但是在多民族人群中,CYP2C19*2和*3占比≥99%,且是亞洲人群中2個主要有意義的基因突變,其突變率遠高于白種人群,與心血管疾病風險的增加有較強的相關性。
2 CYP2C19功能缺失等位基因與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效應的關系
已有多項研究描述了氯吡格雷治療的CHD病人中攜帶CYP2C19 LOF等位基因與臨床結果之間的關系[10]。有2項薈萃分析總結了大部分研究結果,但得出了不同結論。其中一項薈萃分析研究對象主要是接受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CI)的病人(占比91%),其中9685例參與者[急性冠脈綜合征(ACS)病人占55%]服用氯吡格雷,分析顯示,攜帶1個LOF等位基因(HR=1.55,95%CI:1.11~2.17)或攜帶2個LOF等位基因(HR=1.76,95%CI:1.24~2.50;P=0.002)的病人,發生MACE的風險顯著增加。此外,攜帶1個LOF等位基因(HR=2.67,95%CI:1.69~4.22;P<0.0001)或攜帶2個LOF等位基因(HR=3.97,95%CI:1.75~9.02;P=0.001)的病人,發生支架血栓的風險顯著增加[11]。這項薈萃分析表明,CYP2C19基因分型提示大約30%的人群在接受PCI治療后,采用標準劑量的氯吡格雷預防復發性缺血性事件未得到理想的效果,考慮到氯吡格雷被廣泛用于治療心血管疾病病人,臨床需要確定針對個別病人的最佳抗血小板治療劑量或方案。另一項薈萃分析表明,當Meta分析局限在事件≥200的研究或進行效應修飾研究時,CYP2C19基因型與氯吡格雷治療及心血管事件的發生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性[12],這與藥物遺傳學研究的設計與分析相關。以上這些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盡管研究顯示對于接受氯吡格雷治療的病人,攜帶CYP2C19 LOF等位基因時發生MACE的風險增加,但研究中并沒有前瞻性地對病人進行基因分型,并根據基因分型結果改良治療方案,這將導致研究結論的偏差。此外,這些研究只對收集了基因資料的病人進行藥物遺傳學分析,并沒有對整個研究隊列進行藥物遺傳學分析。因此,目前仍缺乏前瞻性的臨床數據證明基于CYP2C19基因型改良抗血小板治療的臨床收益。
3 基因型引導的抗血小板治療的前瞻性研究
截至目前,大型隨機對照試驗還不能有力地證明使用基因型引導的抗血小板治療的臨床益處。Cavallari等[13]對1815例穩定型CHD及PCI后的ACS病人進行基因分型,并由臨床醫生決定是否采取替代治療(普拉格雷或替格瑞洛或更高劑量的氯吡格雷),結果顯示, PCI術后對CYP2C19 LOF等位基因的病人選擇個體化抗血小板治療可以降低MACE的風險。但由于研究中缺乏隨機分組,氯吡格雷治療組相比替代治療組,其合并糖尿病、卒中及周圍血管疾病的病人比例更高,年齡更大,這可能導致結果出現偏倚。PHARMCLO試驗將因ACS住院的病人隨機分為標準護理組和藥物基因組(包括ABCB1、CYP2C19*2和CYP2C19*17),隨訪(12±1)個月,觀察的主要復合終點為心血管死亡以及首次發生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卒中和大出血。標準護理組的114例病人(25.9%)和藥物基因組的71例病人(15.9%)發生MACE(HR=0.58,95%CI:0.43~0.78;P<0.001)[14]。此項研究提示,未來的藥物遺傳學試驗應著重關注缺血性并發癥風險最高的病人,如ACS病人和(或)正在接受復雜支架植入手術的病人,以及出血風險高的病人,如老年病人、有出血病史病人等,這些類型的病人最有可能從基因型引導的抗血小板療法中獲益。但本項研究的局限性在于,除了CYP2C19*2 LOF等位基因外,研究中還含有CYP2C19*17等位基因(增強代謝型)和ABC1變異等,這些遺傳變異對降低氯吡格雷藥物反應的影響尚不清楚。此外,研究在納入888例(25%)病人后,因基因分型平臺缺乏認證而提前停止。因此雖然研究提示相比常規標準治療,根據ACS病人臨床特征和氯吡格雷代謝相關基因分型結果進行個體化抗血小板治療,可能會顯著減少ACS病人的缺血和出血事件,但研究的可靠性仍需探討。ANTARCTIC試驗是一項對老年ACS病人進行血小板功能監測與治療調整的隨機試驗,該試驗納入了75周歲以上的老年ACS病人,并按1∶1隨機分配到常規組(每日口服普拉格雷不足5 mg)與監測組(每日口服普拉格雷5 mg),隨訪12個月后,2組在主要終點事件發生率(HR=1.003,95%CI:0.78~1.29;P=0.98)及出血事件發生率中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15]。這項研究提示我們,對于老年ACS病人來說,與標準的氯吡格雷治療方案相比,更為有效的P2Y12抑制策略并沒有明顯改善老年病人的臨床缺血結果,且老年病人更容易受到抗血栓藥物的不利影響,故對這一人群基因引導型抗血小板治療的風險-利益評估是很困難的。基于基因分型的個體化抗血小板治療能降低發病率及死亡率的觀點仍未得到證實,需要更多大型、多中心、前瞻性的臨床隨機試驗來驗證。目前,有2項大型隨機試驗正在進行,分別為流行遺傳學(http://www.clinicaltrials.gov)和TAILOR-PCI(http://www.clinicaltrials.gov)。
4 氯吡格雷抵抗病人的替代治療
4.1 換用其他抗血小板藥物 大量研究表明,普拉格雷和替格瑞洛與氯吡格雷相比,表現出更迅速、更有效和更穩定的血小板抑制作用[16]。TRITON-TIMI 38隨機試驗納入了13 608例經PCI治療的ACS病人,并將病人隨機分為氯吡格雷組和普拉格雷組,其中氯吡格雷組給予300 mg負荷劑量及75 mg維持劑量,普拉格雷組給予60 mg負荷劑量及10 mg維持劑量。治療6~15個月后,作者觀察到12.1%服用氯吡格雷的病人及9.9%接受普拉格雷治療的病人出現主要療效終點(HR=0.81,95%CI:0.73~0.90;P<0.001),且普拉格雷組發生心肌梗死、進行緊急靶血管重建術、出現支架內血栓的風險較氯吡格雷組顯著降低[17]。在JUMBO-TIMI 26、PRINCIPLE-TIMI 44等試驗中也觀察到了同樣的結果[18]。然而,普拉格雷被證實與較高的大出血風險有關。在PCI前后,使用普拉格雷抑制血小板聚集會更頻繁地出現出血事件,尤其是危及生命的致死性出血。研究中還提到,對于年齡≥75周歲的老年病人,缺血事件的減少往往伴隨著更高的出血風險。因此,對于這一部分病人的抗血小板治療方案,要更為謹慎的選擇。此外,很多試驗證實替格瑞洛在降低ACS病人MACE風險方面優于氯吡格雷。PLATO試驗是一項多中心、隨機、雙盲試驗,試驗比較了接受替格瑞洛治療(180 mg負荷量及1日2次90 mg維持量)及接受氯吡格雷治療(300~600 mg負荷量及75 mg維持量)的ACS病人之間的主要終點事件發生率,結果接受替格瑞洛治療病人的發生率為9.8%,而接受氯吡格雷治療病人的發生率為11.7%(HR=0.84,95%CI:0.77~0.92;P<0.001);在次要終點上,與普拉格雷相同的是,替格瑞洛組較氯吡格雷組發生心肌梗死及心血管死亡的風險顯著降低,但與普拉格雷不同的是,替格瑞洛組在降低卒中風險上的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值得一提的是,替格瑞洛組并沒有增加ACS病人的總體主要出血風險(11.6%比11.2%,P=0.43),而是與較高的非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相關出血率有關[19]。因此,雖然普拉格雷和替格瑞洛比氯吡格雷在降低MACE方面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但兩者可能引起更高的出血風險,且兩者都比氯吡格雷昂貴,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普拉格雷及替格瑞洛有著更高的停藥率[20]。且對于老年病人,使用普拉格雷或者替格瑞洛加強抗血小板治療的臨床收益并不明顯,故氯吡格雷仍然是臨床最為常用的P2Y12抑制劑。
4.2 氯吡格雷劑量遞增方案 CUHRENT-OASIS 7研究提示,病人接受雙倍劑量(第1天600 mg,第2~7天150 mg,之后75 mg/d)的氯吡格雷較接受標準劑量的氯吡格雷(第1天300 mg,之后75 mg/d)治療,可顯著減少MACE發生率,同時顯著減少支架內血栓的形成。然而也有一些研究顯示增加氯吡格雷劑量獲益并不明顯。GRAVITAS試驗招收了2214例采用PCI治療后接受DAPT治療但仍表現出高血小板反應性(HPR)的病人,并將他們隨機分到高劑量氯吡格雷組(150 mg/d)或標準劑量氯吡格雷組(75 mg/d),結果顯示2組之間MACE的發生率差異并沒有統計學意義(HR=1.01,95%CI:0.58~1.76;P=0.97)[21]。雖然這些使用基因型引導氯吡格雷劑量遞增的研究結果令人失望,但由于研究限定HPR病人每天使用150 mg氯吡格雷,而不是225 mg或者更多,因此不能完全證明氯吡格雷遞增方案無效。在ELEVATE-TIMI 56試驗中,攜帶一個CYP2C19 LOF等位基因的病人每日服用225 mg的氯吡格雷與沒有攜帶LOF等位基因的病人每日服用75 mg氯吡格雷是等效的。而攜帶2個LOF等位基因的病人,即使服用氯吡格雷的每日劑量高達300 mg也不能產生等效的血小板抑制作用[22]。綜上,通過增加氯吡格雷劑量以強化傳統DAPT來影響臨床結果的有效性仍存在爭議。
綜上所述,現有的證據不足以充分證實常規基因檢測指導抗血小板治療的臨床收益。如何根據基因型選擇抗血小板方案也缺乏充足的臨床證據,對于出血風險較高的病人,如老年病人以及有卒中史、出血史、血小板功能降低的病人等,如何評估風險及收益仍顯艱難。此外,目前大部分試驗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ACS病人(尤其是接受PCI治療)這個群體,對于隱匿型CHD、穩定型心絞痛及缺血性心肌病、兒童、孕婦等的氯吡格雷用藥指導還有待大規模的臨床試驗加以研究。基于上述原因,臨床仍需更多的大型隨機對照試驗來解決這一問題,最終幫助指導醫師個體化選擇抗血小板治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