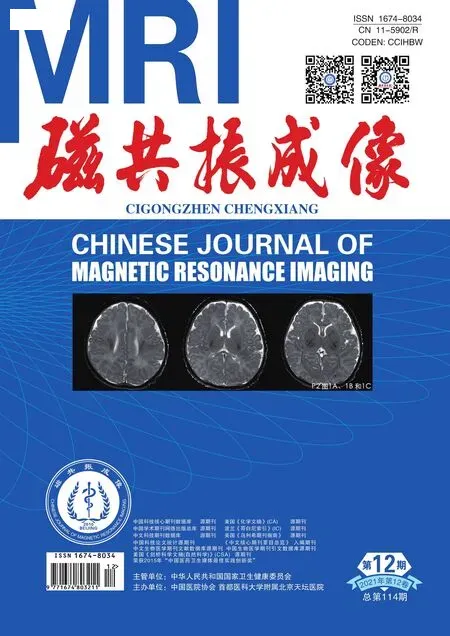磁共振彈性成像在肝纖維化定量診斷與分期中的研究進展
趙俊蘋,李紅,劉昊沅,李娜,馬會浩
作者單位:三峽大學附屬仁和醫院放射科,宜昌443000
肝纖維化(liver fibrosis,LF)是指肝臟細胞外基質尤其是膠原纖維的異常積累,LF 不加干預可發展為肝硬化甚至肝癌。早期LF是可逆的,專家共識[1]認為Sun等[2]提出P-I-R分類可用于評估LF動態變化,在組織學上進一步明確了LF逆轉的定義。磁共振彈性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elastography,MRE)可無創評估組織機械特性,對早期LF做出有效診斷[3-4],為臨床盡早采取干預措施提供依據,減少肝硬化及肝癌的發生。現已有多個研究表明其診斷效能高于超聲、CT、擴散加權成像及血清學等臨床評分系統[5-11]。
1 MRE在評價肝纖維化嚴重程度及其分期中的應用
1.1 LF分期
肝臟損傷常以纖維化的程度和肝硬化的形成來分期,用于評估疾病進展情況,影響治療及預后。現國內外對LF 進行分期的標準有很多,較常用的是Scheuer 法即根據穿刺活檢后的結果分為F0 期(無纖維化)、F1 期(匯管區擴大)、F2 期(纖維間隔形成)、F3 期(纖維間隔伴小葉)、F4 期(可能或肯定肝硬化)。Scheuer法雖然認識到炎癥對肝纖維化的嚴重性,但對分期的定義尚不明確。而Sun等[2]根據纖維間隔的所占比例不同,將LF分為進展型(progressive,P)、逆轉型(regressive,R)和不確定型(indeterminate,I)三類,即P-I-R分類,此分類不僅在病理學上明確了LF分期,且指出了LF逆轉的定義。
1.2 MRE彈性值與LF相關性的研究
LF所致的組織機械特性(應變、剛度和粘彈性等)改變可通過測量彈性圖的肝臟硬度值(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LSM)來顯示人體組織硬度的差異,從而作為診斷LF 程度的依據[12,13]。
袁鴻鵬[14]、Jayakumar等[15]分別通過自己的研究表明MRE的肝臟硬化與纖維化顯著相關。Ajmera[16]團隊的一項前瞻性隊列研究對102 例經活檢證實的肝硬化患者先后進行MRE 和肝活檢,然后重復配對肝活檢和MRE 評估。結果顯示在未經調整的分析中,MRE肝硬度增加15%與組織學纖維化進展的概率增加呈正相關(OR 3.56;95%CI:1.17~10.76;P=0.0248)。即使在對年齡,性別和身體質量指數進行多變量調整后,這些發現仍具有臨床和統計學意義(校正后OR 3.36;95%CI:1.10~10.31;P=0.0339)。此研究表明MRE 肝硬度增加15%可反映肝纖維化組織學進程,且MRE肝硬度增加15%是進展為晚期纖維化的最強預測因子(OR 4.90;95%CI:1.35~17.84;P=0.0159)。然而,此研究雖然對肝組織學的縱向變化與MRE 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嚴格的評估,但通過對快速進展期的患者進行長期隨訪顯示,其中60%可能被肝活檢錯誤分類,導致不能反映真正的組織學進展。另一方面,由于進展超過一個纖維化階段的患者數量有限,使得“劑量反應”不能得到充分說明。因此,更多跨纖維化分期的進展性病例研究是值得期待的。
1.3 MRE在LF分期中的應用
張顯怡等[4]通過MRE 對20 名健康志愿者及57 例肝活檢證實為LF 患者的肝臟彈性值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MRE 對早期LF 具有較高的診斷效能,其診斷LF F1~F4 期的ROC 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別為0.92、0.94、0.95、0.99。Xiao等[17]的一項薈萃分析表明MRE和實時剪切波彈性成像對LF 分期的診斷準確率最高,一項對100 多名患者進行的前瞻性橫斷面研究[18]也顯示MRE在識別LF (第1期或更多期)方面比瞬時彈性成像更準確。與Lefebvre 等[19]的研究結果一致。
張凱等[20]選取40例LF病例,先行MRE檢查,后經肝臟穿刺病理活檢確診。其中MRE 漏診2 例,2 例均經活檢證實為F1期,誤診1例F2期為F1期,漏診率5.00%、誤診率2.50%,F3、F4 期檢查結果與活檢結果一致。在Loomba 等[21]的研究中也有12 名患者被錯誤分類,其中9 名活檢顯示為F0~F2 期纖維化的患者被歸類為晚期纖維化,3 名F3~F4 期纖維化的患者被歸類為F0~F2 期纖維化,MRE 將晚期纖維化與F0~F2 期纖維化區分開來的AUC 為0.924 (P<0.0001)。雖然張凱等[20]與Loomba 等[21]的研究均表明MRE 對晚期纖維化的預測更加準確,但其二者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出了MRE 對早期LF 良好的診斷效能。人體組織彈性模量在部分區域內可能存在重復情況,當正常組織和病理組織重復時會影響MRE 的診斷,這也造成了張凱等[20]研究中的兩例漏診。但是總的來說,MRE對各期LF 的檢出都是有效的,指導臨床早期干預,逆轉早期LF,防止晚期LF 進一步發展,這對降低肝硬化乃至肝癌的發生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
2 MRE技術進展
2.1 設備
在目前的肝臟MRE 掃描中應用較多的是剛性塑料驅動器,這給患者的檢查過程帶來了不適,丁麗等[22]開發的一種柔性氣動驅動器,極大地改善了患者的體驗感,相比于剛性驅動器,柔性驅動器更加貼合胸壁,能夠使得波的傳播更加均勻,且二者獲得的肝臟硬度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3]。
2.2 序列
目前常見的MRE 序列是梯度回波序列(gradient echo,GRE)、自旋回波序列(spin echo,SE)、自旋回波-平面回波序列(spin echo-echo planar imaging,SE-EPI)及平衡穩態自由進動序列。其中GRE-MRE序列是最常用的序列[24],但其容易受肝臟鐵質沉積的影響[25-27],導致肝臟硬度的測量不穩定。而鐵超載在慢性肝病患者中并不少見,對此,SE-EPI序列成為了更佳的選擇。已有研究表明,SE-EPI 對磁場的均勻性不太敏感[28,29],且該序列基于視圖共享的重建策略可以避免呼吸運動偽影,這使得其在鐵超載、屏氣困難的患者中仍然能夠準確地進行圖像采集[30]。
2.3 后處理技術
目前常用的后處理方式分為二維(2D)和三維(3D),2D即選擇肝臟最大層面處掃描4 層圖像并從兩個方向上的波傳播數據進行分析,此種后處理方式可能由于波的傳播不完整導致肝臟硬度的測量誤差[31]。而3D后處理方式可以對全肝進行掃描,實現對波的傳播數據進行全面分析,并且能夠消除產生干擾的縱向傳播波,使得到的肝臟硬度值更加穩定、準確[32]。Loomba[30]的一項前瞻性研究也表明3D-MRE 的成像模式較2D-MRE 更為準確。此外,更有研究表明,將3D 后處理技術與SE-EPI序列結合,不僅能增加掃描范圍、提高圖像信噪比及準確率,還能在肝纖維化分期診斷中顯現出良好性能[32-34]。但是由于3D-MRE 掃描時間長,技術要求更高,故普及率不高,但其應用前景是值得期待的[35]。
2.4 ROI的勾畫
常規ROI 的勾畫往往是手動的,避開肝臟邊緣、膽管及大血管等,取平均值作為肝臟硬度值,或者直接選取肝臟最大截面的平均值。此種手動勾畫方法易受勾畫者的主觀影響,且對于不均勻性肝纖維化患者、LF 進程不一致者等不能準確評估其纖維化分期[36]。而Rezvani[37]等提出的一種基于全肝容積的容積分割測量法可以通過分析軟件對肝臟進行分段,進而提供LF 硬度值的分布情況,使得LF 評估更加準確、具體。此外,還有學者提出自動肝彈性計算[38,39]算法來通過自動在圖像中定位肝臟,檢測肝臟邊緣、繪制ROI。
3 展望
現已有多個研究表明MRE對早期LF的診斷及評估具有顯著優勢,這將有利于臨床早期干預,降低肝硬化及肝癌的發生率。同時,MRE還可檢出由肝臟病變引起的尚未見臨床癥狀的食管靜脈曲張[40,41]和門脈高壓癥[42]。當聯合脾臟硬度一起測量的時候,肝臟硬度值似乎更加準確、穩定[43]。
此外,MRE 還可用于肝臟腫瘤、炎癥的特征描述。Thompson等[44]的一項初步研究顯示原發性肝癌的組織病理學分級和腫瘤硬度之間可能存在關系,低分化肝細胞癌往往比高分化和中等分化肝細胞癌具有更高的硬度,且原發性肝癌早期就已有外周硬度的升高,這可能有助于早期原發性肝癌的檢出。急性炎癥可由于炎癥細胞的募集以及炎癥造成的肝臟水腫和充血導致肝包膜的實質擴張和拉伸,從而使得肝臟硬度普遍增加,而慢性炎癥或亞急性炎癥僅導致肝臟硬度的輕度增加(低于3 kPa)[45]。雖然目前的MRE技術很難對肝臟硬度進行量化和與纖維化分開,但這一目標有望隨著MRE 技術的進展在未來實現。
總之,肝臟MRE 是一個很有前景的研究領域,其技術的發展更是進一步提高了肝臟疾病診斷的準確性及特異性。
作者利益沖突聲明:全體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