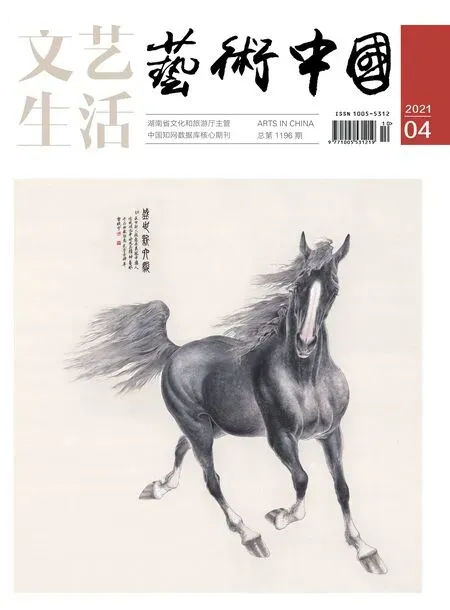讀書于我及其他
——寫在常德石門逸邇閣書院民間讀書界高端論壇
◆周實(長沙)
讀書于我
那天,我與一個朋友通話,問他正在做什么。他說在看書。我說,呵,你在讀書。他說不,他在看書。他說你才是在讀書。我問為什么。他說他翻書是因為無聊,而我若是翻開書那就是在做事了。所以,他翻書只是在看書,而我翻書是讀書。
我無語。我承認,他說出了我們之間翻書時的某些差別。年輕時,當編輯,一干就是幾十年,很多時候翻開書,確實就是為了做事。不過,我在很多時候,或者大部分的時候,翻書也是在看書的。為了做事而翻書多少都有點乏味。
我是喜歡看書的,喜歡看小說,不是讀小說,只有評論家才會讀小說,因為他要寫評論,當然就要仔細讀,而且認真地分析,然后扼要地歸納,然后說出一二三四,讓作家都感到驚訝,看到自己的白日夢,原來是這樣!
小說是作家的白日夢,很多人這樣說。那么,我們看小說就是進入白日夢了。問題是,看完后,你從夢里醒來了,會發生些什么呢?有時候,也許會。有時候,一絲半點都不會,就像沒有讀過一樣,就像我們自己的夢。很多早上,我們醒來,夢就煙消云散了,似乎根本沒做過。
好的小說能讓你脫離當下所處的世界進入另外一個世界。你在那個世界里,能夠看到許許多多你在平時所忽略的或者意識不到的東西。你在那個世界里,走過來又走過去,你會認識一些生人,也會碰到一些熟人,你會面對一些眼睛,那些眼睛所閃爍的是些完全不同的眼光,透過那些不同的眼光,你會看見不同的心。
好的小說是開放的,沒有封閉的結尾,你讀完后還能回來,回到你的當下的世界。
好的小說能夠讓你增加那么一段記憶。那些記憶是存在的,也是子虛烏有的。
無論什么樣的小說,只要是好的,都會是這樣,都會是一種存在的記憶,無論它是多么朦朧,或者,甚至虛無飄渺。
相對于中國小說來,我更喜歡外國小說。為什么?很簡單,他們寫得更自在。托爾斯泰的感人至深、福樓拜的細微精準、卡夫卡的K、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愛倫·坡的皮姆、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梅爾維爾的巴托比、果戈理的柯瓦廖夫、海明威的男子漢咆哮以及沉默寡言的隱忍,即便顯得有些可笑,但你亦會覺得可愛。還有巴別爾和他的騎兵軍、梭羅的瓦爾登湖,他所寫下的每個段落都可以擴展為一部作品,他使自己的整個人生都保持了精神的青春。
當然,除了看小說外,我還會看別的書。這些書也像好的小說,能夠徹底地顛覆你,完全地改變你,摧毀你對這個世界所懷有的種種假設,把你猛地那么一下拋到一個新的地方。在那里,人、事、物,突然間就不一樣了,而且以后依然會不一樣地繼續下去,只要你還繼續活在你自己的時間里,并在這個世界上擁有你的自己的空間。這樣的書是什么書呢?大都是關于靈魂的。它們就像一股勁風,從你腦海呼呼吹過,吹跑了那些堆積在腦溝里的陳腐垃圾。這樣的書所提出的都是一些基本的問題。這樣的書告訴你,不要害怕從頭開始,要走前人未走的路。這樣的書,放下之后,你還會被所讀過的點燃,升騰,激動不已,并在日后的很多夜晚,無論醒來,還是睡去,你都會在心里覺得:世界生機無限,一切皆有可能。
總之吧,一句話,讀完一本好書之后,你會感到你的生活多了一種別樣的色彩,你會覺得空氣之中彌漫某些格外的清新,哪怕就是積毀銷骨,也會感到一陣快慰。
我的書房
關于書房,我一直都是這樣認識的:我的書房對我來說就是我的大腦。
我的大腦以我的所喜歡的方式方法分布在我書房的各個不同角落里,你若進入我的書房就進入了我的大腦。
我的書房里,當然,很多書,整整一面墻,拐過兩個角,我就坐在一個角里,面向一個角,背對一個角。
有的書,我讀過,有的,我還沒有讀。
讀書也要有緣分的,就像一個人結識另一人,五百年修得同船渡,書與人的緣分也是。
所有的書對我來說都是非常寶貴的,不僅僅是書的本身——書的封面、書的背脊、書的內芯——書的寶貴還在于它所喚回的已逝時光和它產生的那個年代。
一般來說,我不歡迎別人進入我的書房,就是家人,也不例外。
誰也別碰我的書(不管什么書),誰也別碰我的紙(即使就是一片紙屑),誰也別碰我的電腦以及鼠標和鍵盤。
我的書房的那扇窗子裝配的是雙層玻璃,無論多么嘈雜的聲音,哪怕就是呼嘯的警笛(警車、救護車、消防車所拉響的那種鳴笛)也都被我擋在窗外。這樣,我的這間書房也就自成一個世界,成了我的世外桃源。
我就是這樣喜歡一個人呆在我的書房里。
一個人,在書房,就像一個人在這世界上,你想要怎樣你就能怎樣。
可惜,這也是個夢想,要實現還真不容易。
時不時的總有人走進我的書房里,不是現實中的人,就是幻覺中的人。
每當這時候,我的心與思,就會被打亂,就像一個玻璃杯,稍一不小心,掉到了地上,砰的一聲響,支離破碎了。
隨著這破碎,我的靈與魂,也會飄出來,像一個醉鬼,左右地晃蕩。
這個時候,我想讀,也沒辦法再集中已經零亂的精神了。
這個時候,我想寫,那動筆的結果也是一個字都寫不出來。
這時的我,自然煩躁,只能對著自己苦笑,只好走到書柜之前,抽出一本看一看,再抽一本看一看。然后,我的心里會想:為何那些美好的氣質在我自己或朋友的身上壓根看不到呢?
書對我來說,真的就是人。
作為一個人,一個讀書人、一個做書人,你在做好人還是做壞人?
每天,我都這樣自問,這么樣的捫心自問。
書也有其命運的。書的命運和人一樣,有的窮,有的富,有的待遇高,有的待遇低,有的只是徒有其名,有的確實名副其實,有的可以升入天堂,有的卻要打入地獄。
你要做個什么人呢?或者做本什么書?
何謂書房?在我看來,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一個私人藏書的地方,一個使我能夠安心看書或者寫作的地方,一個使我這個人獲得心靈渴求的地方,它是物質的,但在我心里,它更加是非物質的。
我的筆名
一般來說,所謂筆名是作家們用的了。而我卻是一個編輯。我之所以有過筆名,恰恰因為我是編輯。那是上個世紀的事了。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辦報有了一些變化。我所在的《湖南日報》一下辦了兩個子報。一張是《文萃》,一張是《文化生活報》。這張《文化生活報》放在我所在的部辦。我所在的部就是文化生活部。
《文化生活報》,聽起來好聽,辦起來卻不太好辦。那時的生活雖有變化,但若要說文化生活,到底又有多少文化?
這就要看編輯了。看你有多大的發掘工夫,看你有多強的原創能力。有時,稿子實在不夠,只好自己動手寫了。
自己寫,沒問題,要署名就有問題了。自己寫,自己編,每期都發自己的稿子,感覺不太好,影響也不佳。
于是,只好起筆名。不知起了多少筆名,不知用了多少筆名。相對用得比較多的,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洲石,一個是羅雀。洲石很明顯,一是與我的本名諧音,二是表示自己渺小,只是那條湘江河中橘子洲上的一塊石頭。羅雀呢,也清楚,從“門可羅雀”剪切而來,表示自己是無名之輩,門前自然可羅雀了(好多年之后,在編《書屋》時,寫那開篇的“書屋絮語”,也曾用過這個筆名)。那時,還用這個筆名,在一些報刊發表作品,如《人民文學》《文匯月刊》《長江文藝》《鴨綠江》等。作品雖然發表了,影響卻是近于無,真的就如筆名所示,真的就是門可羅雀。門可羅雀就羅雀吧,我對自己這樣說,這不正是你自己所做出的選擇嗎?
現在的時代又不同了,現在是網絡時代了。
現在的人,網上寫作,很多都有自己的網名(ID?綽號?或者也可叫做筆名)這些網名較之先前作家們所用的筆名,真的是要瀟灑得多,也要豐富有趣得多。這也多多少少表明時代確實是不同了。
我當然也上網的。不過,我用的是真名。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現在的我,喜歡這樣。這是我今天的選擇。
我的閑章
若說閑章,有兩枚,一枚“小石頭”,一枚“無有齋”。是否算得閑章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它們在我眼里,好像就是兩枚閑章。
“小石頭”是吉霞刻的,吉霞是我的好朋友。在刻“小石頭”之前,她從未刻過什么印章。那天,她突然來了興趣,說:我想我也能刻章子!我說那就幫我刻吧。她問:刻個什么呢?我說是啊刻個什么。她說:就刻“小石頭”吧。我說好。“小石頭”是我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寫的一首修路長詩,發表在1981年的《江南》文學叢刊上。我很喜歡這首長詩,恕我在此朗誦一段:“詩句跌落在人的心中/像露珠降落在青青的草叢/這首詩從哪里寫起好呢/愿開頭像風吹樹葉般輕松/風吹樹葉聲多么美妙/美妙得就像上下班哨音//上班哨音環繞山巒/東方飄出一縷霞云/鋼釬、鎬頭、風鉆、斧子/叮玲哐啷,哐啷叮玲/叮玲哐啷在干什么/挑順手的工具呀,我的老兄//下班哨音回蕩幽谷/西山落下幾只雄鷹/披兩肩硝煙,抖一身塵土/隊伍爬坡走向工棚/走向工棚去干什么/松一松筋骨呀,我的親人//當然,沒有這一切并不要緊/但沒有小石頭可不行/小石頭——我的主人公呵/簡直是個歡樂的化身/他喜歡發點機智的議論/就像孩子喜歡吃冰/這些議論實在逗人/就像美酒使人精神//這就是我要認真寫的/一篇修路人的詩文/詩里沒有神奇的幻夢/也不在辭令上跳舞抒情/我只想用純樸的語言/觸動那些淳樸的心……”今天讀來,這詩寫得確確實實有點直白,但情感是真摯的,這點應該沒有異議。吉霞的章子也是一樣,雖然顯得笨拙稚嫩,但每一刀都很用心,讓我看到她的本真。
“無有齋”是弘征刻的。弘征先生精于刻印,大陸、臺灣、香港三地都曾出過他的印譜。“無有”二字,意思明顯,想來無須多說的,想說也無多的可說:無中生有,無即是有,有也是無,有無相間,有無相生,就看你是如何看了。人不相同,看法不同,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這枚章子,到我手后,就在那里一直閑著,等于就是一塊石頭,一塊刻了字的石頭。沒有刻字,它是石頭,刻了字就成了一方印了,成了一方藝術的印,成了一塊可看的石頭。于是,想起《石頭記》,想起那塊冥頑的奇石,想起書中那一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白茫茫大地真干凈嗎?是啊,看上去是很干凈。
我讀的第一本字書
我記得我讀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時候,家里面,除了一些小人書,大人所看的書里面,只有這樣一本小說。那時,我是多大呢?應是九歲多,大概是小學四年級。
讀的時候糊里糊涂。喜歡看保爾如何打架,喜歡他和冬妮亞那段美好純真的戀情。一個野小子、一個大小姐,相愛了,多么好!我盼他們愛下去,能結婚,能生子,能夠和和睦睦地快快樂樂過一生。可是,后來,當我看到他倆相遇鐵路工地,保爾拿著一把鏟子,對著冬妮亞這樣說,他首先是屬于黨然后才能屬于她時,我就更加糊涂了。我不明白為什么保爾非要這么說不可。難道他一定要如此才能把握冬妮亞對他所懷的情與愛?后來,我,長大了,雖然知道相對時代,愛情總是那么脆弱,卻又總是覺得保爾心里還有一些別的東西在起作用。一些什么東西呢?一種莫名其妙的自卑?一種不可言說的自尊?一種他那樣的男人面對某類女性時所特有的爭執本能?我能感到這種本能,想要說又很難說清。如今,過去這么久了,半個多世紀都過去了,還是無法把它說清。
后來,我又看了《茶花女》,看了《紅樓夢》,讀了普希金,還有萊蒙托夫的詩。萊蒙托夫有兩首詩給我的印象特別深。一首是《短歌》,一首是《乞丐》。《短歌》說的是一個青年為了證明他的愛情,跳入波濤洶涌的大海為他的情人打撈項鏈。他將項鏈撈上來后,女郎又要他再次下海為她采取海底珊瑚,結果他沒再浮上來,他被大海吞沒了。《乞丐》寫的是一個青年總是含著辛酸的眼淚向他的情人乞討愛情,可是他的美好的感情卻又總是被那情人隨意地玩弄和欺騙。這兩首詩使我看到愛情冷漠殘酷的一面。我不明白詩中的女郎為何要如此證實愛情。難道她也非要如此才能把握他的愛情不可?愛是奉獻,當然不錯,但如果是如此奉獻,就是可悲可憐的吧。愛情對于男女來說,真像有人說的那樣只是一場決斗嗎?只是一場男人女人曠日持久的戰爭?
想到決斗,想到戰爭,我又想起那位佛陀與其門徒安那達的那段令人莫名的對話:
“應當怎樣對待女人?”
“應當避免她的凝視,安那達!”
“不過,如果看見了她,我的主,我們應當做些什么?”
“別同她講話,安那達!”
“可是,如果同她講了,我的主,怎么辦?”
“那對她就要戒備,安那達!”
男人對女人要戒備,是怕女人是禍水。反之,女人也一樣,也怕男人是禍根。事情為何會這樣?我想說也難說清。很多事情開始之時給人的感覺總是朦朧,但這并非就意味著以后你會變得清晰。此一時,彼一時,凡事總是因時而異,凡事總是因人而異,因你說話的對象而異。哲人尼采論及男女在他所寫的兩本書里就是如此絕然不同。一是“當你走向女人時,不要忘記帶鞭子!”(《扎拉圖士拉如是說》)一是“人們在同意結婚時應當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你相信你同這位妻子直到老年能夠很好交談嗎?婚姻中一切其他事情都是時過境遷的。但是交往的大部分時間是屬于談話。”(《人性,最人性的》)由此,我又想到保爾,想到他和冬妮亞,慶幸他倆沒有結婚。我想他倆若是結婚,他倆那些婚后的日子又能說些什么呢?還是說他先屬于黨然后才能屬于她?他為何就沒想想,一個人活在這個世上,首先是屬于自己的。一個人只有做好了自己,才有可能有益于他人,同時有益于時代和社會。
我出的第一本書
有人問我:你出的第一本書是哪一本?我說,這個問題對于我還真的是一個問題。他問為什么。我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曾與人合作寫過《劉伯溫》三部曲、《李白》三部曲,還化名為書商寫過愛情小說武俠小說等,但我以自己的本名一個人出版的第一本書應該還是詩集《剪影》。這本書是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出版的時間是2000年。“湖南文藝”之所以愿意出是因為社里當時有個決定:凡是在“湖南文藝”工作過十年的編輯可以給個書號出本書。而那時,我雖然離開文藝社,調到出版局創辦《書屋》已經五年了,但我確實曾在“湖南文藝”工作過十年,從1985年到1995年,并曾經在社里擔任過《芙蓉》編輯部副主任、文化藝術室主任、小說室主任、副社長等職。因此,社里礙于面子,還是給了我一個書號。書號有了,出什么呢?當時手里沒有什么,只有一些平時記在本子上的分行句子,我把它們叫作詩,又不敢把它們叫作詩,但又只能把它們叫作詩。其中,有的摘出來發表過,大部分都未發表。于是就想,就出它吧,出了也算沒白寫吧。于是,就把同一類的也就是內容相近的編進同一個章節里,取上“關于詩”“雨”“夜”“我”“你”“他”等題目,然后再在章節下面標出一、二、三、四、五……那是一些什么詩呢?請看我的“關于詩”吧:
一,隨著幾縷香煙的飄起/煩躁的靈魂安靜下來//多少話兒憋在心里/能說也很難說出口來//就像麻繩在頸上絞著/就像開水在灶上燒著/就像深潭在山里睡著/潭里的魚兒卻莫名的驚慌//這時,真是需要香煙/需要它溫柔無聲的勸慰。
二,常常,有很多話/想說,又無處說/久了,也就無話可說//常常,有很多事/想做,又無法做/久了,也就無事可做//常常,抱有一種希望/久了,一切皆成幻像。
三,不知有多少辭匯/在心窩里丟失了/就像江水/在眼前流過//不知有多少心情/在時空中消逝了/就像浮云/在頭上飄過//留下的/惟有這副軀殼/臨風獨立/日曬雨淋。
四,述說人生的故事/不知有幾多幾多/就像一個漩渦/套著另一個漩渦//故事隨波而去/沉入深深的河底/就像一顆卵石/挨著另一顆卵石//卵石挨著卵石/鋪成寬寬的河床/人生這條大河/流向無言的遠方。
五,總是只有這么幾句/很難湊成一首詩/總是沒有一塊時間/托著下巴想想詩//這么幾句能算詩嗎/不算又有什么關系/天上的星星零零散散/誰會說它毫不稀奇。
這就是我對詩的感受,我就是基于這樣的感受來寫我的所謂詩。
比如“雨”:你看過雨中的飛鳥嗎/從東至西,一閃而過/就像一粒漆黑的石子/從孩子手中頑皮地彈出//就像一顆白晝的流星//就像流星是那夜空/被突然射殺的一只鳥。
比如“夜”:闃寂無聲/真可怕/陷入一條漆黑的巷道//向前,空氣凝滯了/往后,風也正僵化//放開嗓門喊一聲/話在心頭被消掉//寂寥,寂寥,寂寥//不敢想一聲鳥叫//哪怕有張小門/吱呀一聲也好。
比如“樹”:不知是互相喜歡/還是互相折磨/這土地,這樹/生存在一起//一個那么瘦/一個那么弱//瘦弱的土地瘦弱的樹/為什么偏偏在一起呢//為什么偏偏沒有例外。
比如“我”:在這靈氣飛揚的世界/我只是一塊普通的頑石/既不能讓人摸起來舒服/又沒有絲毫觀賞價值//我只能歪在大路邊上/踩我的腳有千只萬只/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我倒一點也不在意//有時,我也曾這么想/我可能進那精品屋嗎/如果這世上有一個人/能把我掂在手上試試。
比如“你”:孤獨的時候/你端起酒杯/你說——/酒能使孤獨發出聲音//有聲的孤獨/比無聲的孤獨/總要好那么一點點//一點點/是“——咕——嚕——”/是酒滑過喉結的響聲。
比如“他”:他要向上爬了/卻沒有落腳的地方/茫然四下環顧/只有朋友的肩膀//(敵人的肩膀踩得著嗎/敵人的肩膀會讓他踩)/能踩的只有朋友的肩膀/朋友的肩膀多好踩呀//他使勁踩著朋友的肩膀/一點一點向上爬了/向上一點,蹬掉一個/蹬掉一個,向上一點//隨著最后一位朋友/最后一聲凄厲的慘叫/他終于爬上了最高點//世間萬物包括山鷹/全都矮在了他的腳下/他站在僅能立一只腳的/梭標一樣的懸崖上。
好了,好了,不說了,說得夠多了,這就是我的第一本書,就是我當時寫的詩。這些詩寫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現在來看,已很老了,老得已經掉了牙了,可在當時,我卻真的:從未想過/歌也會老//以前那么悠揚/如今這樣沙啞//依舊這臺唱機/依舊這張光碟/依舊一個聽歌的人//不依舊的/是這歌聲/是這與歌同老的人(《剪影·日子·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