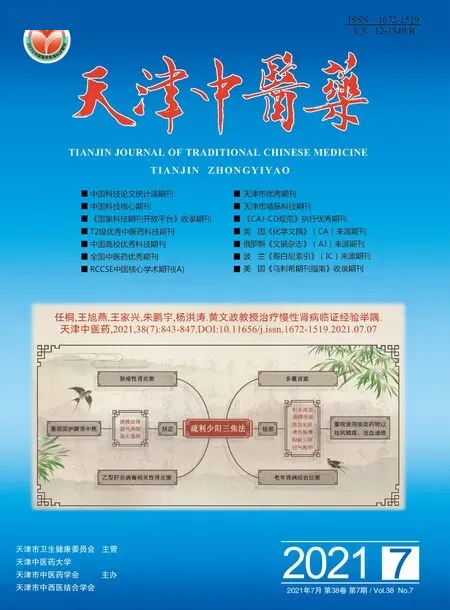安慰針效應對針刺研究影響淺析*
杜蓉,關衛,孟智宏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針灸臨床部,國家中醫針灸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天津 300381)
針刺療法源遠流長,在中國已有數千年的歷史。20世紀以來,針刺療法已傳播到世界各地,被用于治療多種疾病,相關研究也逐漸深入。針刺作為一種復雜的干預手段,其有效性和起效機制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廣泛的實踐和研究均證明了針刺對多種疾病有效[1-2]。針刺也被國外研究者所承認并納入相關指南,如美國過敏性鼻炎指南將針刺療法列為B級證據推薦[3]。
干預治療手段均包含安慰劑效應和特異性效應,而針灸的安慰劑效應一直廣受爭議,近年來國際上發表的一些針刺與安慰針刺方法做對照的臨床研究結論認為,針刺治療能使患者受益,但同時認為針刺治療與安慰針療效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即針刺療效等同于安慰針效應。目前部分研究中顯示針刺效力不優于安慰針對照組[4-6],因此針灸臨床研究得到日益發展的同時也面臨新的問題及困擾。
1 安慰針效應對針刺研究的影響
有研究者對近10年國外針刺隨機對照試驗中安慰針的應用情況進行了系統分析,納入的29篇文獻中,有28篇表明針刺、安慰針均具有臨床療效,占96.55%,針刺的療效優于或不優于安慰針各占37.93%。說明針刺相關研究中針刺組相對于安慰針組的有效性依然需要進一步探索[7]。
1955年Beecher發表經典論著《強大的安慰劑》一文,研究顯示即使患者接受安慰劑治療,仍有35%的患者在接受安慰劑治療后疾病癥狀有效減輕,表明患者獲得的干預手段即使無效,患者相信治療有效時臨床癥狀確實可以緩解,因此安慰劑效應受到國內外研究者廣泛關注[8]。
安慰劑效應廣泛存在于所有醫學干預手段中,國內外研究者為了排除安慰劑效應,采用嚴格的隨機對照實驗進行循證醫學的證據探索。針刺研究也不例外,針刺干預是復雜干預,其治療過程中的反復多次的針刺行為,醫師與患者的互相交流,患者的期望等共同產生安慰針效應。
在針刺研究中應用安慰針相當于在藥物研究中應用安慰劑藥片,由于針刺干預的特殊性,針灸的安慰針效應要強于安慰劑藥品,這可能是由于復雜的干預比藥物的安慰劑效力更強[9]。因此對針刺療法的臨床應用和針刺研究均造成了較大影響,可能產生潛在的偏倚。本研究對針刺的安慰針效應進行相關分析及研究綜述,進一步明確針刺干預的安慰針效應的內涵。
2 針灸的安慰劑效應內涵及相關機制
患者的期望與醫患交流是產生安慰劑效應的重要因素,安慰劑效應也與社會、文化、認知、臨床環境、個體差異及研究設計有關,是心理和生理效應的集合[10-13]。
有研究表明,醫生對患者的溝通程度不同會導致腸易激綜合征患者臨床癥狀改善不同,較好的溝通可使患者的各種臨床癥狀改善率更高。研究結果顯示,在接受治療后,強化溝通組、正常溝通組及空白對照組3組患者的臨床癥狀改善率分別為37%、20%、3%,具有統計學差異[14]。George等[15]發現,在針刺治療腰痛的臨床研究中,患者治療前的期待值越高,疼痛治療的效果越佳,兩者成正相關。
目前對于患者期望對針刺療效影響的評價并無明確固定的測評方法,現階段仍是以心理學量表為主。相關的評價量表也已被應用到研究中。如Mao等[16]應用包含7個問題的問卷,研究期望值大小對針刺減輕肌肉疼痛療效的影響。
目前研究表明,安慰劑效應也具有內在生理機制,安慰劑效應的產生機制包括多個方面,其神經遞質方面的機制可能與多巴胺、阿片受體信號通路、內源性大麻素及血清素等有關[17]。有學者[18]研究了期望對針刺鎮痛的調節作用,通過比較兩個具有不同預期水平的普通針灸組的治療前后變化,發現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上,高期望組的疼痛信號明顯低于低期望組。其內在機制可能是安慰針效應能夠引起內源性阿片遞質釋放。有學者[19]證明了疼痛患者應用阿片受體拮抗劑的情況下,由期望機制引起安慰劑效應受阻,說明安慰劑效應與內源性阿片系統關系密切。
國內相關研究也表明,安慰針刺組可引起內在機制的改變,但同時證明真針刺組和安慰針針刺組相關機制并不相同。
張貴峰等[20]研究安慰針效應與針刺療效的關系及相關機制,研究者將48名健康志愿者,隨機平均分為4組,4組分別為:真針刺外關穴組、不透皮假針刺外關穴組、非穴假針刺組和空白對照組,運用正電子發射型計算機斷層顯像(PET-CT)收集腦中樞激活信號,結果表明真針刺組的激活腦區相對于安慰針刺組均有統計學差異,具有特異性作用。
郭妍等[21]利用PET-CT技術,探尋針刺人迎穴對自發性高血壓(SHR)大鼠腦功能區葡萄糖代謝的影響。研究者將30只SHR大鼠隨機平均分為人迎組、安慰針刺組和模型組,將10只同等體質量的WKY大鼠(選擇性近親交配法培育的Wistar-Kyoto大鼠)作為對照組,其中對人迎組和安慰針刺組各針刺操作30 min,對其他組不進行針刺,通過PET-CT掃描采集大鼠腦功能圖像,結果顯示真針刺組在改善大腦葡萄糖代謝方面比安慰針刺組效果更明顯。
劉波等[22]研究針刺穴區與非穴區對腦功能連接的影響,研究者將21名健康志愿者隨機分為針刺穴位組(真針刺組)和針刺非穴位組(安慰針刺組),并運用功能磁共振掃描技術分別于針刺前、出針后25 min掃描分析兩組的腦功能連接情況。結果顯示兩組均能產生廣泛的腦功能連接,真針刺組與安慰針刺組相比在雙側小腦扁桃體、右側小腦齒狀核、雙側小腦懸雍垂等區域與后扣帶回存在功能連接增強,但在雙側額內側回、右側額下回與后扣帶回的腦功能連接上存在強度減弱。真針刺組志愿者的腦功能連接強度總體上高于安慰針刺組。
由于強大的安慰劑效應對相關研究會造成干擾及導致偏倚,研究者也在探求如何降低對照組干預的安慰劑效應,以明確治療組的有效性。有研究表明,通過減少醫患交流可以減少安慰劑效應,安慰劑效應主要對主觀指標產生影響,對客觀指標影響較小[14]。
3 反安慰劑效應的由來及可能機制
反安慰劑效應,最初由 Walter Kennedy[23]于1961年提出。反安慰劑效應是與安慰劑效應對立存在的,在臨床治療中極為常見。比如試驗中給患者服用惰性藥物并對此藥物給予負面評價,結果顯示患者的病情呈現出惡化趨勢。其原因在于患者對于藥物治療效果的期望是負面消極的,從而產生了反安慰劑效應。現階段,反安慰劑效應獲得的關注較安慰劑效應要少得多,相關研究尚未深入。
雖然目前研究者對反安慰劑效應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見,但其作為一種普遍存在并發揮影響的效應,具有獨特的臨床及研究意義。有關反安慰劑效應的研究已經揭示了負面期望調節人體的神經生理基礎,表明消極態度可能會對生理機制產生負面影響,提示研究者和臨床工作者應在臨床和研究中加以注意,盡可能減少反安慰劑效應,避免對治療效果的影響[24]。心理期望是具有方向性的,可分為正性(積極的)和負性(消極的)期望,并根據其調節方向的不同產生出安慰劑與反安慰劑效應。
目前有研究證明[25],大腦的前島葉皮質(aIC)和喙前扣帶回皮質(rACC)可能在期望引起的疼痛調節中起關鍵作用,當正負期望調節疼痛時,右側aIC和rACC與導水管周圍灰色(PAG)呈現相反的耦合。Kong J等[26]在研究中發現,在反安慰劑效應發生時,與內側疼痛系統相關的腦區優先激活,如島葉、雙邊背側前扣帶回。
鄧瀟斐等[27]研究表明,安慰劑效應與反安慰劑效應分別由阿片肽系統和膽囊收縮素系統所介導;在影像學研究中,疼痛加工系統和脊髓在安慰劑/反安慰劑的調節下呈現相反的激活模式,而海馬的活動在反安慰劑效應發生過程中呈現出特異性。
除上述機制外,在反安慰劑效應發生過程中,個體因素也發揮了一定影響。焦慮情緒是反安慰劑效應發生的關鍵性因素,性別對反安慰效應也有影響,女性更易發生反安慰效應[28]。
4 安慰針設置的科學性
安慰針自1997年在針灸聽證會上被美國國立衛生院提出作為研究針刺療效的對照方法以來[29],逐漸成為針灸領域研究的熱點。
作為為排除針刺的安慰劑效應設置的對照組,安慰針設計的科學性直接決定了該臨床隨機試驗在針灸研究領域中地位。目前,在國內外針刺研究中,安慰針刺對照組的設計并沒有統一的標準。在1項研究針刺對4種慢性疼痛療效的數據分析中[30],納入了近7年研究針刺對非特異性肌肉骨骼疼痛、骨關節炎、慢性頭痛或肩部疼痛療效的隨機對照試驗。分析得出結論,在不同的試驗中,針刺治療效果大小的變化主要是由對照組接受的治療方法的差異而不是針刺治療的特異性差異引起的。明確說明安慰針的設計直接影響針刺治療的療效評估,在針刺研究領域具有重大的臨床意義。
目前,安慰針按有無針灸針,可分為普通治療針、套疊式可滑動鈍頭針、模擬經皮神經電刺激、模擬激光等。安慰針的實施部分可分為穴位點、非穴位點、相關性小或無的穴位點。安慰針的針刺深度可分為皮表非穿透性針刺(多用套疊式可滑動鈍頭針)、皮表穿透性針刺(淺刺、深刺)兩類。
現階段的針灸臨床研究多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設計不同的安慰針刺對照組。其中,把淺針刺非穴位作為安慰針刺對照組,常見于國外研究針刺的隨機對照試驗中。以比較著名的兩項研究為例:近年在德國開展的1項以偏頭痛為觀察病例的大規模針灸隨機對照試驗[31]中,研究者將1 295例偏頭痛患者隨機分為3組,分別進行針刺、非穴位淺針刺和常規藥物治療。其中,針刺組是由醫師依據中醫經絡理論進行辨證取穴,并合并采用阿是穴,針刺進行手法操作以求“得氣”,淺針刺非穴位組選取頭部以外的部位進行淺刺,不做手法操作,最終得出結論,3組治療均有效,且療效無統計學差異。在由德國里根斯堡大學的Michael Haake博士主持的針灸治療慢性腰痛的試驗[32]中,將1 162例慢性腰痛患者隨機分為3組,在真針刺組,研究者依照中國針灸理論選取主穴和輔穴進行針刺,深度達5~40 mm。在假針刺組,研究者在患者腰部選取避開和偏離已知穴位和經絡線的治療點,進行淺刺1~3mm。在常規治療組,患者接受運動鍛煉、物理、藥物等常規治療。3組患者在經過相同療程的治療后,經問卷調查顯示,真針刺組和假針刺組的有效率明顯高于常規治療組,但真假針刺的療效無統計學差異。
除上述兩項試驗外,仍有不少研究在以淺針刺非穴位作為安慰針刺組,并得出類似的結論。因此,國外不少學者對針刺的療效提出了質疑,認為針刺療效等同于安慰劑效應,傳統針灸理論中的穴位選取原則及針刺手法等在臨床中沒有實際意義。由以上研究,不難看出國外針灸研究者對中國經絡系統的理解尚不成熟。
傳統經絡學說認為,穴位不是固定不變的,穴位是空間立體的,是空間結構和功能的復合體,整個經絡系統周而復始、如環無端,“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備急千金要方》曰:“凡孔穴在身,皆是臟腑榮衛血脈流通,表里往來,各有所主。”[33-34]
另外,已有現代研究表明[35-36],穴位處的組織細胞化學成分會受到疾病、刺激、個體機體狀態的影響,而發生動態的變化,導致穴位敏化,引起穴位位置和面積的動態改變,具有功能可塑性。同一腧穴,會在不同的病理狀態呈現出位置、大小、面積及內在生物活性物質的相應改變。這些結論為穴位的定位和功能增加了新的內涵。
此外,隨著針刺研究及臨床的不斷進展,越來越多有特殊治療作用的穴位為人們發現,不斷豐富奇穴、微針系統、阿是穴等內容,同時證明以避開已知穴位或偏離經絡線作為“非穴位”,而認為其沒有療效的認知太過片面。同時,將與治療該疾病無關的穴位設定為“假穴位”,進行針刺的安慰針刺方案是否有足夠的理論證據支持還有待商榷。
淺刺作為一種針刺方法,在中國由來已久。淺刺最早見于《黃帝內經》,指在身體較淺的層次進行針刺的一種方法。《素問·刺要論》論述到:“病有浮沉,刺有淺深,各至其理,無過其道……深淺不得,反為大賊。”說明淺刺和深刺一樣都是根據疾病部位的表里而辨證采用的針刺方法。傳統針灸理論認為,經絡系統中的十二皮部、孫絡、浮絡等均分布在人體的淺表部位。傳統治療手段如火罐、穴位敷貼、艾灸等以及現代常用的皮內針、浮針、腹針、激光針灸等均是通過刺激人體淺表部位以達到治療目的,并都取得較好療效。在國外,淺刺法得到了廣泛應用。例如在日本,針刺技術以針細、針淺為特色,針刺流派中的“銀針淺刺輕針法”派,認為針刺取得的療效與經絡系統中的皮部關系密切。日本制造的“撳針”,針體纖細(直徑 0.2 mm,長度 0.3~1.5 mm),被廣泛應用于國外的針刺治療中,受到普遍認可。淺刺法作為在古代文獻中早有記載的針刺方法,在現代針灸臨床中仍具有重要的治療價值。
在一些現代臨床研究中,同樣證明淺刺法具有其一定的臨床意義。如:在韓國進行的一項研究針灸治療功能性便秘的功效和安全性的隨機對照試驗[37]中,研究者在兩組中均采用同等規格的針灸針(0.25 mm×40 mm),治療組根據針灸理論選取穴位,進行深刺,并行手法使其“得氣”,對照組選取相同數量的非穴位進行淺刺(深度1~2 mm),無手法操作和“得氣”感。結果顯示,兩組患者的癥狀均有改善,且治療組療效優于對照組。但淺針刺組在一些結局指標中顯示出有中等或較大的治療作用,該作用會引起患者一些生理上的變化,說明該治法具有一定的臨床意義。研究者認為,該針刺方案不是理想的安慰對照組。有研究通過fMRI腦成像技術發現,淺刺和深刺均能引起腦功能變化,證實淺刺具有特異性治療作用[38]。
因此,將淺刺法、非穴位作為安慰針刺組進行的隨機對照研究,是脫離傳統針灸理論和現代臨床的,所得出的針灸等同于安慰針效應的理論無法立足于現代針灸領域。
近年來,非穿透性針刺也常被作為安慰針刺方案之一,用于針灸臨床研究中。此類針刺中,尤以套疊式可滑動鈍頭針應用最廣,常出現于國內外針刺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Streitberger針和Park針兩種[39-40]。
如Zotelli等[41]研究針刺治療張口限制及疼痛的療效,治療組使用真正的針灸針在頰車、下關、顴髎、百會、風池、天柱、合谷等穴位上進行針刺,并行一定的手法操作以“得氣”為度。對照組使用德國生產的套疊式可滑動鈍頭針,在與治療組相同的穴位上進行操作,并固定在皮膚上。
另有研究者開展針刺與假針刺對照治療纖維肌痛的臨床隨機對照試驗[42],針刺組采用一次性消毒的0.25 mm×40 mm不銹鋼針刺入穴位,進行手法操作,以“得氣”為度。假針刺組采用Park針,所選穴位與針刺組相同,操作時引起皮膚刺痛感,操作后進行固定。兩組療程相同,結果顯示:總體上,針刺組的療效優于假針刺組,但在緩解疲勞方面沒有統計學差異。
套疊式可滑動鈍頭針在一定程度上減小了對機體的刺激量,但其短暫刺激人體皮膚,造成針刺入皮膚的假象,并依靠裝置進行固定,仍然會同淺刺一樣引起皮膚傳入神經活動。這種傳入神經活動對大腦的功能連接具有明顯影響,從而導致“邊緣接觸反應”,引起生理效應。因此,該類針刺不宜作為惰性安慰劑對照使用[43-44]。
目前,國內外公認的理想的安慰針刺對照組應該遵循3個原則:1)對研究的疾病沒有或幾乎沒有特定治療作用。2)針刺部位對研究的疾病沒有治療作用。3)受試者不能區分安慰針刺與治療針刺。
若根據以上原則來判定,可以說目前安慰針的設計都不能完全符合標準,均有各自的缺陷,這種結果與針刺療法的特殊治療機制有緊密聯系。針刺療法治療人體的過程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療效受針具、手法操作、穴位、醫患交流、個體體質等共同影響。因此,通過改變個別針灸影響因素來設置安慰針刺進行對照的研究方法是不全面的,具有科學局限性。
5 問題及展望
綜上所述,在針刺臨床及研究中,安慰針效應及反安慰針效應對針刺效力均有較大影響,應引起針刺臨床工作者和研究者的關注。目前國內對此開展的大型RCT研究及機制內涵研究依然極少,在中國人群中的安慰針效應是否會對針刺效力具有特異性的影響依然缺少高級別證據支持。綜上國內外研究表明,在臨床實踐中,應當引導患者建立合理的期望,以提高臨床療效。而在針刺研究中應采取減少醫患交流,應用多種主觀、客觀評價測量指標的方式來減少安慰針效應對針刺研究的影響。另外,如何設計符合標準的安慰針對照組,仍是需要探索和討論的問題,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因此,對安慰針效應的研究,明確安慰針效應內涵必將對臨床及科學研究產生深遠意義,進一步影響針刺療法的有效性之辨,推動針刺療法的國際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