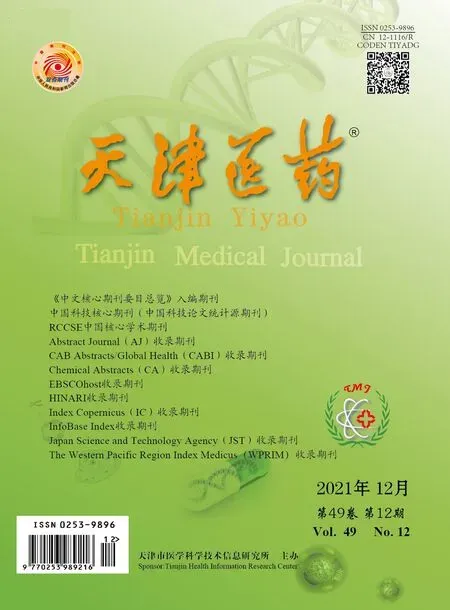神經膠質細胞與突觸可塑性關系的研究進展
張寧,謝璐霜,劉奇,呂沛然△
神經膠質細胞是神經組織的重要組分,其數量為神經元的10~50倍。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的神經膠質細胞最初被認為是將神經細胞聚集在一起的“膠水”,并參與多種調控功能。CNS中的神經膠質細胞主要包括星形膠質細胞、小膠質細胞以及少突膠質細胞等。不同類型的神經膠質細胞與神經元以及周圍的血管等相互聯系,彼此交聯,形成復雜的信息交換網絡[1]。神經膠質細胞在支持神經傳遞、維持細胞外離子平衡、絕緣軸突加速電信號傳導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2]。
突觸是神經元間信息傳遞的樞紐,突觸可塑性與神經系統的發育、損傷后修復等密切相關,是神經科學研究的熱點之一。大腦發育早期,突觸的可塑性很高,成年后可塑性下降;突觸可塑性受到損害可能是諸多發育性、獲得性以及神經退行性腦病的發病原因[3]。神經膠質細胞與突觸可塑性的發揮密切相關[4]。神經膠質細胞與神經元建立雙向通信,一方面對突觸釋放的神經遞質做出反應,反過來又釋放影響神經元和突觸活動的膠質遞質[5]。神經膠質細胞-突觸的相互作用極大地增強了神經環路的自由度,提高了大腦的計算能力。本文就星形膠質細胞、小膠質細胞以及少突膠質細胞與突觸可塑性相互關系的最新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星形膠質細胞
星形膠質細胞是哺乳動物大腦中數量最多、體積最大、分布最廣的神經膠質細胞,占神經膠質細胞總數的20%~40%,是神經元突觸數量、形態、功能的重要調節者[6]。星形膠質細胞是神經上皮來源的特殊膠質細胞,其可參與調控突觸的形成、成熟、刪除或修剪,調節神經遞質釋放,維持鈣穩態和血腦屏障功能,并為大腦提供營養支持[4,7]。研究報道,星形膠質細胞至少通過2種方式參與突觸局部信息傳遞和可塑性:一是與突觸前和突觸后的元件協同進行可塑性重排(形態可塑性);二是通過與神經元元件交換調節信號進而調控突觸功能(雙向交流)[8]。
1.1 形態方面 成熟大腦中的星形膠質細胞通常包圍著神經元和突觸,形成“三聯突觸”結構。這種形態排列為星形膠質細胞與神經元間相互作用提供了結構基礎。大腦灰質中的原生質星形膠質細胞與神經元胞體和突觸緊密聯系,白質中的纖維性星形膠質細胞則與神經元軸突緊密聯系[9]。星形膠質細胞整合和處理突觸信息,控制突觸的傳遞和可塑性,也是參與神經系統信息處理、傳遞和存儲的細胞。
1.2 功能方面 星形膠質細胞與突觸相互作用,是參與突觸可塑性的重要組分。星形膠質細胞可分泌多種受體、轉運體以及其他分子,它們與神經元釋放的突觸遞質、細胞因子等相互作用,進而參與調控突觸可塑性。星形膠質細胞可通過多途徑調控突觸的可塑性來保證突觸正常傳遞[4,10],并影響其行為學表型[11-12]。星形膠質細胞產生多種膠質遞質作用于突觸,如谷氨酸和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Nmethyl-D-aspartic acid receptor,NMDAR)共激動劑D-絲氨酸、腺苷三磷酸(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及其分解代謝產物腺苷以及其他參與突觸連接形成、穩定和刪除的可溶性或接觸性因子[13]。Lee等[14]研究發現,星形膠質細胞可選擇性吞噬成年小鼠海馬CA1區興奮性突觸,這一作用可能是通過星形膠質細胞上的MEGF10基因介導的,并且MEGF10基因對于維持大腦可塑性以及認知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從而證實了星形膠質細胞是突觸刪除的主要參與者。Ackerman等[15]發現,星形膠質細胞可能參與果蠅運動神經環路發育關鍵期的正常閉合過程;隨著發育關鍵期的結束,運動神經元突觸逐漸被星形膠質細胞包裹,若使用遺傳學工具,即采用lexA-lexAop二元表達系統驅動細胞死亡reaper,以誘導果蠅星形膠質細胞凋亡,則會引起發育關鍵期閉合后運動神經元功能損害。該研究通過單細胞測序發現,gat、chpf、Neuroligins(Nlg)4、Nlg2等4個基因是運動神經環路發育關鍵期的正常閉合所必需的;進一步研究發現,星形膠質細胞通過Nlg2-Nrx-1信號調控樹突的微管結構,從而實現運動神經環路在發育關鍵期的正常閉合[15]。此外,星形膠質細胞并不是簡單地跟隨突觸活動,而是將突觸信息處理并整合到不同的可塑性反應中。在這種整合的下游,星形膠質細胞可通過釋放多種膠質遞質對神經元功能活動和通信產生重要影響[5]。
突觸周圍的星形膠質細胞突起在星形膠質細胞對突觸結構和功能的重塑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星形膠質細胞與突觸的通信主要體現在星形膠質細胞通過釋放直接改變突觸功能的遞質來促進突觸可塑性[16]。例如:(1)星形膠質細胞分泌的D-絲氨酸在海馬CA1區突觸經典的NMDAR依賴性長時程增強(long-term potentiation,LTP)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7]。其可能機制為D-絲氨酸可增加NMDAR共激動劑結合位點占有率,達到激活閾值,觸發下游信號通路,進而誘導產生LTP[18]。(2)星形膠質細胞分泌的L-乳酸在海馬CA1區突觸的LTP中也起著關鍵作用[19]。大腦在高能量需求時,儲存在星形膠質細胞中的糖原被代謝成L-乳酸并運輸到神經元,為神經元提供能量支持。外源性L-乳酸的干預可以緩解因星形膠質細胞糖原分解障礙而引起的LTP損害[19]。(3)星形膠質細胞還可通過大麻素1型受體(cannabinoid receptor type-1,CB1R)信號通路影響突觸可塑性[20]。CB1R在CNS中高表達,并且已有證據表明其天然配體內源性大麻素(endocannabinoids,eCB)通 過 抑 制γ-氨基丁酸(gamma-aminobutyric acid,GABA)能和谷氨酸能遞質的釋放,進而調節突觸的興奮性[21]。研究報道,CB1R在星形膠質細胞中也有表達,海馬CA1區錐體神經元釋放的eCB可激活星形膠質細胞CB1R,誘導星形膠質細胞Ca2+升高和谷氨酸分泌,進而引起NMDAR依賴性突觸后慢興奮性電流以及mGluR1依賴性突觸前谷氨酸釋放的異源性突觸易化[22]。另外,星形膠質細胞CB1R信號參與了長時程突觸的可塑性。海馬CA1區突觸的NMDAR依賴性LTP除需要D-絲氨酸外,還需要星形膠質細胞CB1Rs48[22]。(4)星形膠質細胞也有助于突觸調節膽堿能和去甲腎上腺素能纖維活性相關的可塑性。總之,星形膠質細胞通過分泌多種表面受體或釋放遞質傳遞信號,進而在與記憶相關的突觸可塑性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 小膠質細胞
小膠質細胞是CNS的常駐免疫細胞和吞噬細胞。其通過吞噬或產生趨化因子來調節細胞穩態,發揮抵御損傷和預警疾病發生的作用[23]。除調節免疫功能外,小膠質細胞還參與調節突觸傳遞和突觸發生,促進神經回路的成熟[24]。全基因組關聯研究表明,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精神分裂癥、自閉癥和多發性硬化癥等多種CNS疾病的風險基因都與小膠質細胞有關;在CNS中,小膠質細胞動態監視周圍環境,并且與神經元、星形膠質細胞和少突膠質細胞等進行信息交互[25]。
2.1 小膠質細胞通過突觸修剪機制保護和促進大腦的正常發育 小膠質細胞在神經元突觸重塑過程中發揮關鍵調節作用。神經元突觸重塑伴隨機體的整個生命過程。在發育期,神經元必須正確地連接在一起以促進中樞神經系統回路的建立,故而需要一個突觸修剪的過程。成人CNS的突觸連接也是高度動態的,小膠質細胞通過不斷延伸、收縮,進而與突觸相互作用,不斷發生強度和連接的變化[26]。這種動態的運動促使小膠質細胞能夠監測周圍的突觸并做出相應的反應,進而促進突觸可塑性。小膠質細胞-突觸修剪機制對于發育和成年突觸可塑性具有重要作用。雙光子成像研究表明,即使在未受損的大腦中,小膠質細胞的突起也是高度活躍的,它們與突觸的接觸頻繁但短暫[27]。小膠質細胞可能在清除非功能性突觸以及重塑突觸回路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在生理條件下,小膠質細胞吞噬異常的突觸,對神經元的存活起到保護作用。Paolicelli等[28]報道,在發育過程中,小膠質細胞吞噬突觸碎片,在突觸修剪中發揮重要作用。在缺乏Cx3cr1(一種由大腦小膠質細胞表達的趨化因子受體)的條件下,大腦小膠質細胞數量短暫減少,突觸修剪功能受損,進而導致與突觸數量改變相關的發育障礙的發生。
2.2 小膠質細胞通過與突觸進行雙向信息交流調控突觸可塑性 小膠質細胞與神經元相互作用、影響。一方面,小膠質細胞與神經元通過嘌呤信號傳導、細胞因子、神經遞質等多種途徑進行信息交流,突觸釋放的神經遞質可通過膜電位、細胞內鈣和細胞因子釋放等多種途徑影響小膠質細胞的功能[29]。ATP是重要的嘌呤能信號分子,在神經元興奮性增高時釋放,促進小膠質細胞增強免疫監視功能[30]。谷氨酸受體激動劑可觸發ATP介導的小膠質細胞生長[31]。另一方面,在與突觸動態地相互作用中,小膠質細胞充當“突觸傳感器”,對神經活動和神經遞質釋放的變化做出反應。小膠質細胞表達受體或相關信號分子作用于突觸,并對突觸前釋放的神經遞質,如乙酰膽堿、γ-氨基丁酸、谷氨酸和嘌呤能信號做出反應[32]。
此外,病理狀態下的小膠質細胞可能導致神經元損傷。在阿爾茨海默病等疾病的病理過程中,神經元突觸存在的多種神經免疫信號通路的失調,包括經典補體級聯通路、髓樣細胞觸發受體2(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d on myeloid cells 2,TREM2)、磷脂酰絲氨酸及載脂蛋白E相關信號通路等,進而影響小膠質狀態,最終導致神經元損傷[33]。例如,補體C1q參與可溶性β淀粉樣蛋白(amyloidβ,Aβ)寡聚物對突觸和海馬LTP的毒性作用,積聚在突觸上的病理性Aβ或tau可以上調小膠質細胞中的C1q表達,并促進突觸中的補體激活和吞噬性小膠質細胞增多;若利用補體C1q阻斷劑或敲除補體C3的方法阻斷阿爾茨海默病小鼠模型中經典補體級聯通路的激活,則可以避免突觸丟失或突觸功能障礙,提高記憶力[34]。Nguyen等[35]報道,神經元釋放的白細胞介素(IL)-33可促使小膠質細胞吞噬細胞外基質,進而促進突觸可塑性。細胞外基質的清除和外源性IL-33的補充有助于阿爾茨海默病的治療,對小膠質細胞調控突觸功能的分子機制的探索有助于認知修復新策略的開發。
3 少突膠質細胞
少突膠質細胞是CNS的髓鞘形成細胞,可以形成髓鞘以包裹神經元軸突,從而保證軸突傳導的正常進行,是維持CNS的神經沖動和軸突快速傳遞的重要組分。髓鞘的厚度、長度以及軸突覆蓋形式可影響動作電位的傳導速度[36]。髓鞘的缺失可導致中樞神經系統信息傳遞的減慢,并影響軸突的生存,引起多發性硬化癥、視神經脊髓炎等疾病[37]。越來越多的研究報道,神經元活動可通過少突膠質細胞影響髓鞘的形成和成熟,這種貫穿CNS的動態髓鞘形成過程可能在維持神經元正常功能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而為神經可塑性提供一種新機制[38]。
除了形成髓鞘外,少突膠質細胞還可發揮其他支持神經元功能的作用,如在持續的動作電位激發期間向軸突提供代謝底物[39]。谷氨酸是大腦中主要的興奮性神經遞質[40]。目前,星形膠質細胞被認為是唯一有助于CNS攝取和降解谷氨酸的膠質細胞類型[41]。星形膠質細胞可以吸收神經元釋放的谷氨酸,并通過谷氨酰胺合成酶將其轉化為谷氨酰胺,進而谷氨酰胺再循環到神經元,作為再合成谷氨酸的前體。這一過程對于維持神經元谷氨酸信號和防止谷氨酸所致興奮性毒性至關重要。Xin等[39]研究發現,成熟的少突膠質細胞可表達谷氨酰胺合成酶。少突膠質細胞特異性谷氨酰胺合成酶缺失不會損害髓鞘形成,但會顯著降低組織中谷氨酸和谷氨酰胺的水平,使中腦谷氨酸突觸傳遞受損。此外,少突膠質細胞表面單羧酸轉運體1(monocarboxylate transporters 1,MCT1)介導的髓鞘向神經元軸突的乳酸轉運對維持神經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動至關重要[42]。MCT1參與的乳酸代謝改變是導致神經元損害的重要因素。糖酵解途徑產生的乳酸對維持腦部活動有重要作用,尤其在葡萄糖不足的時候,乳酸成為大腦主要的能量來源。CNS神經元的乳酸主要來源于少突膠質細胞和星形膠質細胞內葡萄糖的分解代謝。兩者產生的乳酸在MCTs的協助下轉運入神經元。目前已知的表達于CNS的MCTs包括MCT1、MCT2以及MCT4,其中MCT1主要分布于少突膠質細胞,參與少突膠質細胞或髓鞘內乳酸的轉運。張茂[42]發現,MCT1表達下調及髓鞘結構破壞可導致少突膠質細胞內乳酸向神經元轉運障礙,進而導致神經元內乳酸等能量底物不足,加重神經元的損害。Li等[43]報道,小鼠出生早期接觸異氟烷可能導致海馬中少突膠質細胞發育障礙和髓鞘的實質性破壞,異氟烷的早期暴露可持續性損害少突膠質細胞前體細胞的增殖和分化,以及少突膠質細胞前體細胞與軸突之間的突觸連接,進而導致髓鞘形成減少,并且可能引起心理和認知障礙。總之,除髓鞘形成外,少突膠質細胞為軸突提供代謝支持的作用可能在軸突信息傳遞以及突觸可塑性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4 小結與展望
神經膠質細胞不僅支持神經元活動,而且參與調節神經網絡可塑性。星形膠質細胞、小膠質細胞以及少突膠質細胞分別在突觸可塑性的發揮中扮演著復雜的而又重要的角色。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其與多種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發生密切相關,如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多發性硬化癥等[33,44-45]。近年來,單細胞組學已成為研究熱點,被運用于多種神經系統相關疾病的研究[46]。該技術的出現可以在單細胞分辨率下幫助研究人員揭示新的細胞類型或細胞亞簇,以及分析出新的與阿爾茨海默病進展密切相關的星形膠質細胞[45]、小膠質細胞[47]等。借助新的研究手段與分析策略,進一步深化細胞狀態與功能之間的聯系,深入了解神經膠質細胞如何在健康和疾病的狀態下根據功能的變化而發生相應改變,對于在神經膠質細胞中明確特定的靶點以保持突觸和神經元功能至關重要,也有助于促進對神經系統疾病治療靶點和生物標志物的識別和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