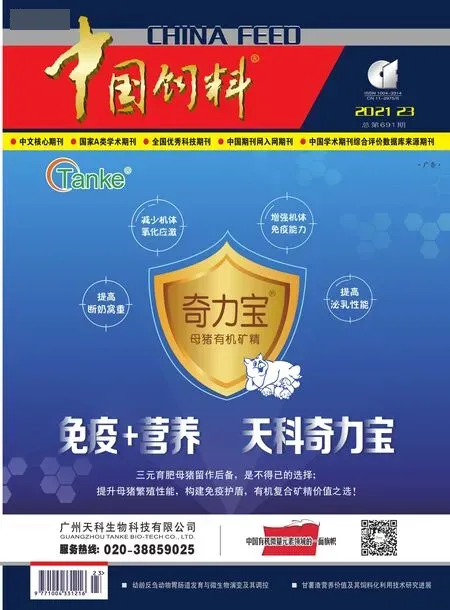幼齡反芻動物胃腸道發育與微生物演變及其調控
郭蕓芳, 徐曉鋒, 張力莉
(寧夏大學農學院,寧夏銀川 750021)
瘤胃是反芻動物最重要的消化器官, 飼料營養物質在瘤胃內消化通過瘤胃上皮吸收, 未被瘤胃消化的營養物質在小腸內進一步被消化吸收。因此,胃腸道發育對反芻動物的生長、生產性能和健康起著關鍵作用; 胃腸道微生物對營養物質消化吸收、 代謝和胃腸道發育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由于幼犢牛免疫力差,消化系統發育不完全, 任何外部環境的干擾或營養水平的變化都會影響犢牛的發育(Diao,2017)和微生物區系的建立;同時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胃腸道微生物群在黏膜免疫系統的發育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Malmuthuge,2015),而幼齡是反芻動物胃腸道發育及微生物區系建立的關鍵時期, 因此了解并根據幼齡反芻動物年齡階段來采取相關調控策略對生產實踐有重要意義。
1 幼齡反芻動物胃腸道發育的規律
反芻動物與單胃動物的主要區別在于具有龐大的復胃消化系統,瘤胃在出生時尚未發育,隨著日齡的增長和飼糧及飼養管理的影響, 使胃腸道的發育呈現一定規律;因此,深入了解胃腸道的發育狀態對于動物營養物質消化吸收、 健康和生產性能都尤為重要。
1.1 瘤胃容積發育變化 犢牛出生時, 網胃、瓣胃和皺胃的重量分別占整個胃重量的38%、13%和49%,隨著日齡的增長,瘤胃重量占比增加,并成為消化營養物質的主要場所(Davis,1998)。 瘤胃發育一般為3 個階段:0 ~ 3 周齡為非反芻階段;3 ~ 8 周齡為過渡階段;8 周齡時瘤胃發育完全,進入反芻階段(Lane,2002)。研究表明,犢牛早在胚胎時期胃腸道開始發育,瘤胃、網胃、瓣胃和皺胃在母畜妊娠56 日齡時已經基本成形 (鄧由飛,2017); 犢牛消化功能在胎兒時期發育, 出生48 h 內,由于與母體分離以及飼喂初乳,使胃腸道形態和菌群變化較大, 哺乳期幼畜的消化功能從消化鮮奶或流體飼料向固體飼料過渡, 這期間瘤胃和網胃快速發育,重量占比增加(Guilloteau,2009)。 羔羊瘤胃重量、肌層厚度和乳頭長度隨日齡的增長而增加,在70 日齡時趨于穩定,而瘤胃乳頭數量在14 ~ 28 日齡時顯著降低,在0 ~ 70日齡, 放牧山羊的瘤胃乳頭面積比補飼山羊的瘤胃乳頭面積增長速度更快(Jiao,2015)。 王佳堃等(2020)研究表明,瘤胃發育成熟的標志是丙酸等生酮物質含量增加; 常用血漿中β–羥丁酸含量來說明瘤胃發育的狀態。研究表明,犢牛皺胃重量相對于體重變化不大, 但皺胃黏膜重量在妊娠最后一個月增加25%, 在出生2 ~ 7 日齡顯著增加20% ~ 30%(Guilloteau,1984)。
1.2 瘤胃上皮與肌肉層的發育 瘤胃上皮的發育是由瘤胃微生物群和宿主之間相互作用引起的, 并隨著飼糧而發展變化(Malmuthuge,2017);研究表明,10 周齡內羔羊瘤胃乳頭長度和乳頭表面發生了顯著變化,1 ~ 4 周齡羔羊瘤胃乳頭表面較光滑,瘤胃上皮細胞發育程度較低,6 ~ 10 周齡羔羊瘤胃乳頭長度增加, 瘤胃上皮明顯增厚且粗糙(Zitnan,1993)。 張科等(2017)研究發現,羔羊采食粗飼料后, 瘤胃背囊乳頭高度和寬度隨著日齡的增加均呈現出增高或增寬的趨勢, 瘤胃肌層逐步增厚;角化層從42 日齡開始出現,皺胃黏膜層厚和皺胃肌層厚沒有明顯變化規律。 值得注意的是, 羔羊采食開食料顯著提高了瘤胃乳頭的長度和寬度,改變了瘤胃發酵參數,可能是由于飼料進入瘤胃后,刺激生酮能力和丁酸代謝,從而促進了瘤胃乳頭的發育 (Wang,2016)。 盧勁曄等(2018) 給90 ~ 120 日齡波爾山羊每天飼喂精料400 g,持續42 d,結果表明,飼糧添加精料可加速瘤胃上皮細胞增殖,促進瘤胃上皮細胞生長,阻滯瓣胃上皮細胞增殖,抑制瓣胃上皮細胞生長。飼糧中添加苜蓿干草或起始料, 促進了牦牛犢牛的胃腸道發育, 原因可能是干物質采食改變了瘤胃發酵狀態,使得瘤胃丁酸濃度升高,瘤胃產丁酸菌的數量增加,因此,可進一步促進瘤胃上皮的發育,但因兩種飼糧成分不同, 其瘤胃丁酸產量也有差異(Wu,2021)。 犢牛出生 5 周齡內無限量或限量飼喂代乳品, 兩組瘤胃上皮的表面積無明顯差異,瘤胃pH 和揮發性脂肪酸濃度不受代乳品飼喂量的影響代乳品與起始料配合飼喂,可以增加犢牛瘤胃上皮重量,瘤胃乳頭表面積也顯著增加, 同時增加腸道基底細胞的增殖率(Yohe,2019)。 斷奶前舍飼有利于牦牛的胃腸發育及消化吸收, 瘤胃上皮乳頭的長度和寬度均顯著升高, 而瘤胃基底層厚度未受影響(Jonova,2021)。 研究表明,長期飼喂高谷物飼糧會改變奶牛和綿羊的瘤胃發酵以及瘤胃和瘤胃上皮相關的微生物群, 并導致瘤胃損傷和代謝紊亂(Hua,2017)。
1.3 腸道發育 腸黏膜的發育遵循近端-遠端的模式,即隱窩和絨毛首先出現在十二指腸,然后逐漸出現在腸道的更遠端(Toofanian,1976)。張科等(2017) 研究了0 ~ 56 日齡羔羊胃腸道組織形態隨日齡的發育變化規律, 發現小腸和大腸的重量隨著日齡的增長而增加,小腸各段的絨毛高度/隱窩深度隨日齡增長而降低, 結腸在整個階段發育最快。飼料過渡期間,營養物質和物理形態均發生變化,腸道變化表現為微絨毛變短,后腸重量占比降低, 為營養物質的消化吸收做好形態學的準備(Guilloteau,2009)。 14 ~ 21 日齡時羔羊盲腸相對質量增速最快,其次為42 ~ 56 日齡,各階段小腸相對質量增速波動較小,56 日齡時大約增加了1倍(王彩蓮,2010)。 以 30 日齡的牦牛犢牛作為研究對象,發現與放牧方式相比,代乳品+補飼的培育方式更有利于牦牛犢牛小腸上皮組織形態發育, 并增強了小腸部分消化酶的分泌能力, 如α淀粉酶和胰蛋白酶(崔占鴻,2020)。 研究發現,舍飼更有利于牦牛犢牛腸道發育, 顯著增加了牦牛犢牛十二指腸、 空腸、 回腸的絨毛高度和隱窩深度,但十二指腸脂肪酶、空腸脂肪酶和回腸脂肪酶顯著降低(Hua,2017)。
幼齡反芻動物的胃腸道發育隨日齡呈現一定的規律,是由胃腸道微生物及其代謝產物、飼糧和宿主之間共同作用的結果, 幼齡反芻動物胃腸道發育程度直接影響成年動物的生產性能和營養物質的利用率。
2 幼齡反芻動物胃腸道微生物區系的演變
胃腸道微生物定植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分娩時與母體分離以及出生后與外界環境接觸都為微生物定植提供了一定條件; 幼齡反芻動物胃腸道微生物區系的豐富度和多樣性處于不斷變化的狀態,這些微生物與宿主相互作用,有利于營養物質的消化吸收和生產性能的發揮; 所以了解幼齡動物胃腸道微生物區系的演變規律, 為幼齡動物生產潛力的挖掘有重要意義。
2.1 瘤胃微生物區系的變化 有研究表明,反芻動物的胃腸道,包括前胃復合體,在出生時是無菌的,但在最初的24 h 內迅速定植,厭氧菌在出生后第二天開始占優勢(Fonty,1989)。 但也有研究表明,在產前羔羊腸道中檢測到一個低多樣性、低生物量的微生物組,主要由變形菌門、放線菌門和厚壁菌門組成,產前胎兒腸道中大腸桿菌的數量最多,說明產前腸道含有微生物,并且胎兒腸道的微生物定植開始于子宮(Bi,2021)。Rey(2014)和 Jimi(2013)等研究表明,犢牛瘤胃細菌群落在出生后迅速形成,瘤胃內群落由成熟瘤胃中發現的許多細菌組成,在門水平上,1 ~ 3 日齡犢牛瘤胃中最豐富的菌門是變形菌門;在屬水平上,3 ~ 12 日齡時瘤胃優勢菌屬為擬桿菌屬、普雷沃氏菌屬、梭桿菌屬和鏈球菌屬,當固體攝食量迅速增加時, 普雷沃氏菌屬占有主導地位,許多屬急劇減少或不再被檢測到(Rey,2014)。研究發現,瘤胃微生物的多樣性和總物種的豐度隨年齡的增長而增加,所有年齡階段的優勢菌門主要由擬桿菌門、厚壁菌門和變形菌門組成,厚壁菌門在所有年齡階段中都穩定存在,而擬桿菌門和變形菌門的相對豐度發生了變化(Wang,2016;Koenig,2011)。 Li 等(2011)研究表明,大多數瘤胃細菌如蛋白質分解菌、纖維素分解菌和其他種類細菌在4 ~ 10 日齡羔羊的瘤胃微生物區系中即定植。
瘤胃微生物群落在不同年齡階段會發生一定變化, 其中細菌和古菌比其他微生物群對年齡的變化更敏感;細菌、古菌、原蟲和真菌在牦牛生長過程中都有相對應的成熟軌跡, 其中瘤胃古菌大約在牦牛5 歲時完全成熟, 而其他微生物群在5~ 8 歲成熟(Wei,2020) 。
以上研究結果表明, 幼齡反芻動物出生前腸道內已經有微生物存在, 在出生幾天內便可以檢測到成熟瘤胃中的細菌、古菌和真菌分類群;可以看出,細菌為各個年齡階段的優勢類群,主要由擬桿菌門、厚壁菌門和變形菌門組成,但在不同年齡階段所占比例不同;在屬水平上,普雷沃氏菌屬豐度隨著日齡增長而增加。
2.2 腸道微生物區系的變化 腸道細菌多樣性從出生到2.5 歲逐漸增加,與群落多樣性的逐漸變化有關(Jiao,2015);新生犢牛出生一周的小腸腔內微生物群由細菌、古菌、真菌、原生動物和病毒組成,在犢牛的所有腸區都可以觀察到厚壁菌門、 擬桿菌門、 變形菌門和放線菌門(Malmuthuge,2019)。
Li 等(2019)對 0 ~ 56 日齡山羊的胃腸道細菌群落動態進行研究,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大腸中的變形菌門被厚壁菌門取代, 而變形菌門主要存在于日齡較大的山羊小腸中,乳桿菌屬在14 日齡山羊空腸和回腸中急劇增加; 年齡較大的山羊十二指腸和空腸中, 乳桿菌屬和擬桿菌屬的比例較低,而Christensenellaceae_R_7 和反芻球菌屬的比例較高。 Song 等(2018) 研究表明,后腸微生物群在出生時具有多樣性, 黏膜附著微生物群比消化相關微生物群具有更高的個體差異, 共鑒定出16 個門,厚壁菌門、擬桿菌門和變形菌門是后腸的優勢菌群;PCR 分析結果顯示, 年齡對黏膜附著大腸桿菌、雙歧桿菌、糞腸球菌的比例有顯著影響; 尤其在出生后第一周檢測到大量的黏膜相關埃希氏菌,表明在此階段致病感染的可能性更高。新生犢牛后腸的優勢菌科包括擬桿菌科、 毛螺菌科、乳桿菌科和腸桿菌科(Frese,2015)。 Kimberly等(2017)研究了犢牛糞便微生物群落,發現斷奶前犢牛糞便細菌群落在OTU 水平上有很高的β多樣性;隨著犢牛年齡的增長,糞便中的許多細菌OTUs 數量逐漸減少,并在成年后消失,這些OTU大多是糖溶性屬,包括乳桿菌(Lactobacillu)和產丁酸的糞便桿菌(Faecalibacterium),這些細菌可能有助于胃腸發育。可以看出,腸道微生物群與瘤胃內菌群相似,隨年齡而變化,不同年齡階段優勢菌門的豐度存在差異, 不同腸段的菌屬豐度也存在差異。
3 幼齡反芻動物胃腸道發育與菌群調控
促進反芻動物胃腸道發育與微生物定植的方法有很多,比如飼糧形態及營養水平、添加劑、飼養管理方式以及微生物移植等, 通過這些調控措施可以改變胃腸道發育程度并改善動物的健康狀態;近年來,有許多關于營養、管理以及微生物移植等方式來直接調控幼齡動物胃腸道發育及微生物區系的相關研究,并具有一定的效果。
3.1 飼糧形態及營養水平 有報道稱,無論飼糧如何,7 日齡犢牛瘤胃中已經建立了成熟瘤胃中常見的古細菌、細菌和真菌分類群,液體飼糧飼喂的犢牛瘤胃中乳桿菌、 擬桿菌和Parabacteroides等菌屬的豐度較高(Dias,2017)。有學者研究了飼喂代乳粉對羔羊的微生物區系建立的影響, 發現代乳粉組羔羊瘤胃微生物區系的變化明顯, 其中擬桿菌門成為優勢菌門,琥珀酸菌屬、瘤胃桿菌屬等在25 日齡后相對豐度高于哺乳組, 乳酸桿菌屬相對豐度在 45 日齡后逐漸升高, 相反, 在25日齡后韋榮氏球菌屬(Veillonella)相對豐度明顯下降(李永洙,2019)。
羔羊補飼開食料,增加了瘤胃揮發性脂肪酸產量,改變了瘤胃發酵和瘤胃微生物群落,表現為普雷沃氏菌屬和毛螺菌科相對豐度顯著升高, 以上兩者可能是添加開食料而引起瘤胃功能變化的主要微生物(Lv,2019)。 研究表明,飼糧脂肪水平會影響瘤胃發酵參數,羔羊60 日齡時飼喂高脂肪飼糧, 瘤胃中變形菌門和纖維桿菌門豐度升高;屬水平上,琥珀酸弧菌屬、擬普雷沃氏菌屬等細菌豐度顯著升高,但羅氏菌屬、梭菌屬、 小類桿菌屬和丁酸弧菌等菌屬豐度顯著降低(李文娟,2018)。 因此,飼糧形態及營養水平會改變瘤胃菌群豐度, 飼糧代謝產物也會改變瘤胃發酵參數, 以上兩者因素共同作用來影響瘤胃菌群的建立和瘤胃發育。
3.2 添加劑 犢牛飼糧中添加鼠李糖乳桿菌GG(GG,ATCC 53013)提高了新生犢牛的主動采食量和生長性能,調節了瘤胃發酵模式,使丙酸鹽和丁酸鹽的濃度增加, 提高了瘤胃液中淀粉酶、蛋白酶活性和微生物蛋白濃度,還使瘤胃內的細菌群落組成多樣化, 并調節瘤胃和腸道微生物的平衡(Zhang,2019)。犢牛飼糧補充釀酒酵母及培養物增加了瘤胃乳頭長度, 空腸隱窩深度降低,小腸絨毛高度與隱窩深度的比率增加,并提高丁酸弧菌的相對豐度, 降低普雷沃氏菌相對豐度(Xiao,2016)。 補飼丁酸鈉可以提高羔羊瘤胃液中乙酸、 丁酸和總揮發性脂肪酸的濃度,增加瘤胃乳頭長度、寬度以及角質層和總上皮的厚度(Liu,2019)。
以上研究說明,在幼齡動物飼糧中添加一些微生態制劑、 發酵劑或酸化劑可以改變瘤胃發酵模式,從而改變瘤胃代謝,促進瘤胃發育和微生物的定植,還能改變部分微生物區系的豐度。
3.3 飼養管理方式 Abecia 等(2014)選擇了懷雙羔的妊娠母羊,羔羊出生后,分別用母乳和人工代乳品喂養,發現母乳喂養的羔羊瘤胃重量更高,而兩組的瘤胃內容物體積則沒有差異, 兩組羔羊均在出生第一天瘤胃內檢測到細菌、 古菌和原蟲的存在;原蟲和螺旋菌門(Spirulina)在母乳喂養的羔羊瘤胃中逐漸增加,而在另一組中沒有變化,說明飼養管理(自然和人工)對微生物定植和瘤胃發育有影響。有學者研究了不同飼養方式對12 月齡蘇尼特羊胃腸道菌群結構的差異,結果表明,放牧組蘇尼特羊胃腸道菌群的α 多樣性顯著高于舍飼組, 放牧組胃腸道菌群中厚壁菌門的相對豐度高于舍飼組, 而變形菌門的相對豐度低于舍飼組。放牧組瘤胃中普氏菌屬、RC9-gut-group、擬桿菌屬、 丁酸弧菌屬和Quinella 屬的相對豐度高于舍飼組;而舍飼組中琥珀酸弧菌屬的數量最多。 放牧組腸道中擬桿菌屬、RC9-gut-group 和Alisties的相對豐度高于舍飼組(王柏輝,2019)。上述研究表明, 不同飼喂方式和管理條件會影響胃腸道發育和微生物區系的建立以及菌群的相對豐度。
3.4 微生物移植 目前關于微生物移植相關報道有瘤胃微生物移植(RMT)和糞菌移植(FMT),是指將健康供體的瘤胃微生物或糞便微生物移植到受體牛胃腸道內,來調節腸道菌群平衡,促進胃腸發育并幫助治療胃腸道疾病。
研究表明, 通過給新生犢牛灌服健康成年牛的瘤胃液,改變了瘤胃和盲腸乙酸與丙酸的比例,十二指腸的絨毛高度增加, 并改善了犢牛早期腹瀉的發病率(張鑫,2017)。有學者給幼齡山羊重復接種成年山羊的新鮮瘤胃液, 發現接種瘤胃液加速了瘤胃微生物的定植, 與未接種的山羊相比觀察到更高的細菌多樣性(+ 234 OTUs)、產甲烷菌(+6 OTUs)和原蟲群落(+25 OTUs);該研究還發現高壓滅菌瘤胃液的接種也促進了瘤胃功能的發育,但使用效果不如新鮮瘤胃液明顯(Palma-hidalgo,2021),可能是高壓滅菌過程中影響了部分有益菌的活性。 Kim 等(2021)研究發現,FMT 之后犢牛腸道微生物群落結構逐漸類似于供體小牛的結構,相關分析表明,腸桿菌科細菌豐度異常增加所表現的腸道菌群失調極有可能引發幼犢腹瀉,腸桿菌科與卟啉單胞菌科相對豐度呈負相關,而FMT 后腸道微生物區系成熟,以卟啉單胞菌科的豐度增加為特征,限制了腸桿菌科種群的擴張,所以FMT 可以改變微生物群落并降低犢牛腹瀉的發病率。
可以看出RMT 或FMT 能夠促進胃腸道發育和微生物區系的變化, 并改善幼齡動物的腹瀉發病率, 但目前關于FMT 在反芻動物上的研究較少;此外,關于這兩種移植技術的樣品前處理、移植劑量、移植細節,對動物身體機能的影響,以及這種移植可能在改善動物生長性能方面發揮的潛在作用還值得進一步研究。
4 小結
幼齡被認為是微生物調控的“窗口期”,進一步研究胃腸道微生物群演替及其功能作用, 了解不同的管理條件下胃腸道菌群的變化趨勢, 瘤胃微生物和代謝產物在調節胃腸道發育過程中的深層次機制, 對于調控胃腸道健康和研究疾病的潛在機制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