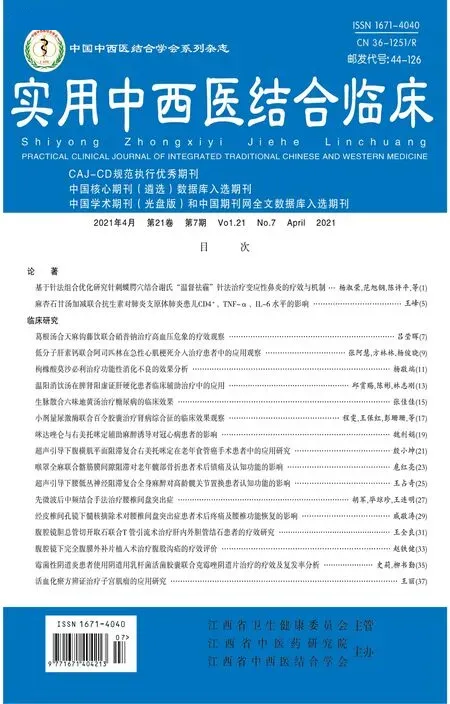何曉暉教授“衡”法辨治賁門失弛緩癥驗案舉隅*
彭秋霞 徐文強 曾學玲 揭智媛 徐春娟
(1江西中醫(yī)藥大學2018級碩士研究生 南昌330004;2江西中醫(yī)藥大學2019級碩士研究生 南昌330004;3江西中醫(yī)藥大學 南昌330004)
賁門失弛緩癥是食管罕見的運動功能障礙性疾病之一,主要特點表現(xiàn)為:食管下括約肌松弛障礙,吞咽時食管蠕動停止。臨床癥狀為吞咽困難、食物反流、胸痛、體質(zhì)量減輕以及因食物反流所致的刺激性干咳、肺炎等病癥[1]。目前,發(fā)病機制還未明確是診治困難的主要原因,臨床治療以緩解癥狀為主,藥物治療、內(nèi)鏡治療及手術(shù)治療是主要治療方式,不管哪種治療方式,都是設法降低食管括約肌的壓力,目的就是緩解癥狀。與此同時,還要預防術(shù)后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的出現(xiàn)[2]。西醫(yī)診治大多只治標,無法治本,且不良反應較多。然而通過有效的中醫(yī)藥治療,既可以避免手術(shù)傷害,又可以極大緩解患者的經(jīng)濟壓力,減輕患者身心負擔。何曉暉教授為江西省名中醫(yī),全國第三、四、五批名老中醫(yī)學術(shù)繼承工作指導老師,擅長運用中醫(yī)藥治療消化系統(tǒng)疾病。現(xiàn)將其治療賁門失弛緩癥經(jīng)驗介紹如下:
1 病因病機
賁門失弛緩癥歸屬于中醫(yī)學“噎膈、反胃、吐酸”等病癥范疇。本病病位在胃和食管,與肝脾關(guān)系密切,亦與腎關(guān)聯(lián)。其發(fā)病機理為飲食不節(jié)、情志不調(diào)、憂思易怒、肝郁氣結(jié)、痰氣交阻,或因其他因素導致食管損傷等[3]。《素問》有言:“膈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說明痞塞不通,氣機不暢乃是此病的發(fā)生根本。故何師認為,氣機之難當首先責之于脾胃,蓋脾胃為氣機升降之樞紐。脾胃一傷,就會影響氣機上下運行,則胃中濁陰難降,脾中之清氣難升。濁氣在陽,清氣在陰,清濁相干,亂于胸中,久則氣結(jié),津液不得輸布,聚而成痰,氣痰交阻,閉塞胸膈,食道不利。其次,氣機想要正常運行,需要通過肝膽的調(diào)節(jié)。如《內(nèi)經(jīng)》所云:“凡十一臟取決于膽。”膽乃“陽升陰降”之腑,少陽膽氣之升發(fā),以助肝之疏泄,從而調(diào)節(jié)胃腸氣機[4]。結(jié)合臨床亦不難發(fā)現(xiàn),賁門失弛緩癥多與情志不遂相關(guān),蓋因肝失疏泄,膽失通降,則濁陰上逆,橫逆犯胃,上擾清道。最后,食管是一富有彈性的肌性器官,其括約肌正常的松弛功能及食物順暢的傳送皆需要陰液的滋養(yǎng),如《醫(yī)學心悟·噎膈》指出:“凡噎膈癥,不出胃脘干槁四字。”說明胃脘陰虧液涸,則食道干澀,松弛無度,飲食難下,則發(fā)為噎膈。然而治病求本,腎為諸陰之本,故亦為食管陰液之本,食管的柔潤有賴于腎陰的滋養(yǎng),故何師認為,噎膈之機與腎亦相關(guān)聯(lián)。總之,噎膈的病位在食管,屬胃氣所主,與肝(膽)、脾、腎密切相關(guān)。基本病機是脾(胃)、肝、腎功能失調(diào),氣、痰、瘀互結(jié),阻隔于食道、胃脘,其中肝脾不調(diào)、痰氣阻膈、脘管狹窄是關(guān)鍵病機[5]。
2 論治與用藥
根據(jù)多年的學習與臨床觀察總結(jié),何師把食管的生理功能歸納為以降為順、以柔為喜、以空為用、以衡為健四個特點。進而提出治療食管病應當順從食管的生理特性,基于“衡”法,著力于恢復食管的運動、升降、弛張等協(xié)調(diào)平衡功能[6],此有四個治療要點。
2.1 整體論治,以平為期 賁門失遲緩癥的發(fā)生與脾(胃)、肝、腎等多個臟腑生理相關(guān),病理相連,故而治療之際當堅持整體觀念,辨證論治。同時此病的表現(xiàn)多為氣郁、痰阻,津枯血燥互相搏結(jié),故此病多為氣血同病、虛實夾雜之證,故而治療常氣血同治、虛實兼顧、納運共理、寒熱并調(diào),以疏其血氣,令其條達,而致和平。
2.2 宣通氣機,升降相宜 食管位于胸中清曠之地,作為腑器,傳化物而不藏,亦當以“空”為生理,“滿”為病理,故只能空,不能滿,古人稱之為“清道”。故而其“清”“空”之性是完成吞咽和傳送食物的生理基礎(chǔ)。宣可寬胸,以行滯氣;通可降濁,以防上逆,有“擴張食管”和“增強食管蠕動”之功[7]。臨床上何師常用的宣通食管藥,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大類:一是理氣宣通藥,如枳殼、厚樸、蘇梗、佛手之輩,以開郁降氣為先;二是化痰宣通藥,如瓜蔞、陳皮、竹茹、桔梗之品,以清熱化痰為要;三是祛瘀宣通藥,如威靈仙、通草、王不留行等,以祛瘀通絡為主。同時在具體配伍之際要注意到脾胃氣機運動是脾升胃降、納運相助、升降相宜,所以治療之際既要注重于降,又要權(quán)衡升降,升降相伍。
2.3 剛?cè)嵯酀瑵欚B(yǎng)為要 食管與胃相連,受胃氣所主,稟胃陰所滋潤,如《醫(yī)學指要》說:“胃管柔空,腑之系也。”說明食管為陽明胃腑所系,位于胸中陽位,下傳食物,然“陽明胃土,得陰自安”,故而要注重潤養(yǎng)食道,保護陰津,即潤津養(yǎng)血。潤津常用藥有麥冬、沙參、玄參、蘆根;養(yǎng)血常用當歸、白芍、枸杞子、桑葚子等藥物。具體運用之際,蓋因養(yǎng)陰滋膩之品,有礙氣機之嫌,故與宣通理氣之辛燥之品相伍,既防溫燥傷陰,運藥和中,又剛?cè)嵯酀罍鈾C[7]。
2.4 病證結(jié)合,內(nèi)外同治 中醫(yī)擅于著眼全局,立足整體,對于局部的病變觀察力有不逮,然而現(xiàn)代醫(yī)學檢查手段極大地彌補了中醫(yī)的不足,為局部病變病理性質(zhì)和預后轉(zhuǎn)歸的明確提供了參考,有利于食管病的早期診斷與根治。故而治療食管病要結(jié)合中西醫(yī)之長,做到辨證與辨病相結(jié)合,采用整體與局部相結(jié)合的治療方法,才能提高臨床療效。同時食管上連口腔,為外治藥物直達病所提供了可能,口服錫類散、云南白藥、三七粉等對于食管糜爛、食管潰瘍具有獨特的作用,同時服藥后平臥一段時間,禁食,使得藥物在病所處停留時間延長,有利于提高藥物治療效果。
3 病案舉隅
3.1 驗案一
3.1.1 病例資料 患者陳某,男,63歲,初診2019年6月28日。主訴:反復吞咽困難1年半。患者自訴1年半前無明顯誘因出現(xiàn)進食和飲水困難,吞咽困難,情志舒暢時減輕,進食生冷食物后出現(xiàn)嘔吐,嘔吐少量黃水,咽干不癢,無胸骨后疼痛或明顯食物反流,癥狀時作時止。于當?shù)蒯t(yī)院做胃鏡檢查示:非萎縮性胃炎;十二指腸球炎。食管造影示:鋇劑通過食管時,食管下端變狹窄,呈鳥嘴樣,食管上端稍有擴張,診斷為“賁門失遲緩癥”,服用西藥后(具體不詳)癥狀一直未見緩解,遂來江西省中醫(yī)院就診。刻下癥見:患者感咽喉梗阻不適,進食和飲水后吞咽困難,情志舒則減,食后噯氣,心下痞悶,咽干口苦,二便正常,寐可,發(fā)病以來體重未見明顯減輕。舌質(zhì)偏紅,苔薄膩;脈緩長,寸浮,按之略滑。西醫(yī)診斷:(1)賁門失遲緩癥;(2)慢性淺表性胃炎。中醫(yī)診斷:噎膈,辨證屬肝胃不和、濁氣上逆。治以疏肝健脾、和胃降逆為法。處方:柴胡10 g、白芍12 g、枳殼15 g、姜半夏10 g、黃芩10 g、旋覆花12 g(包煎)、黨參15 g、白術(shù)15 g、竹茹12 g、茯苓20 g、海螵蛸20 g、萊菔子10 g、煅牡蠣20 g(包煎)、當歸10 g,連服14劑,每日1劑,早晚溫服。2019年7月12日二診:患者服藥后吞咽情況較前好轉(zhuǎn),進食和飲水較前順暢,納寐尚可,今進食油條后感胃脘部疼痛不適,大便正常,舌質(zhì)淡紅,苔薄黃,脈弦緩。秉持效方不變原則,予守方加減,上方基礎(chǔ)上將萊菔子改為12 g,煅牡蠣改為30 g,14劑。2019年7月31日三診:患者吞咽困難明顯減輕,飲食不節(jié)仍稍感吞咽不暢,時有噯氣,寐可,大便稍干,舌質(zhì)淡紅,苔白稍膩,脈緩按略弦。于上方基礎(chǔ)上去枳殼,加枳實15 g,大黃3 g,白芍改15 g,黨參改12 g,再服14劑。2019年8月16日四診:患者進食吞咽基本正常,無反酸噯氣,納寐佳,二便正常,其余未訴明顯不適,病漸愈,繼續(xù)服藥14劑鞏固治療,囑患者保持心情舒暢,調(diào)整生活習慣,不適隨診。2020年1月8日隨訪,患者訴吞咽正常,飲食不節(jié)偶有噯氣,無其他明顯不適。
3.1.2 討論 本案例中,患者的主要癥狀為咽干口苦、吞咽困難、梗阻噯氣,此乃由肝胃不和、濁氣上逆所致。肝失疏泄,氣機郁滯而化熱,熏蒸膽汁,熬傷陰液,煉津成痰,橫逆犯胃,胃氣失和,濁氣上犯而成噎膈之癥。治以疏肝健脾、和胃降逆之法。方中柴胡可升陽,可疏肝,配以芍藥補肝血、斂肝陰,合以枳殼酸苦降氣,三藥合用以達“氣血同調(diào)”“斂泄共用”之效,亦符合肝體陰而用陽之特性。然脾胃本虛,又當明了見肝之病,知肝傳脾之理,故方中黨參、茯苓健脾益氣,與白術(shù)相伍,實為四君子之意,健脾和胃以固其本。半夏、白術(shù)燥濕化痰,黃芩、竹茹清熱生津,寒溫相伍以治其標。此六藥相配,則虛實兼顧。輔以旋覆花、萊菔子降氣通腑,升降同理,以復脾胃之升降功能,同時病證結(jié)合,衷中參西。由于賁門失弛緩癥容易引發(fā)反流癥狀,長期的胃酸反流容易灼傷食管黏膜,造成黏膜的充血、水腫、糜爛等,甚至成為食管癌的發(fā)病誘因。故可予海螵蛸、煅牡蠣制酸和胃降逆,當歸活血養(yǎng)血、潤腸通腑,既可加快消除臨床癥狀,又與白芍相伍,潤津養(yǎng)血護陰;另外有既病防變,阻斷病勢之意[8~10]。二診患者情況好轉(zhuǎn),故效不更方,加大和胃降逆之效;三診患者癥狀明顯改善,但大便稍干,苔白稍膩,故加強通腑降濁、健脾斂陰之效。全方以疏肝健脾、和胃降逆為主,佐以甘溫,配以升降,斡旋脾胃、協(xié)調(diào)肝膽,以達和胃降逆之功。
3.2 驗案二
3.2.1 病例資料 患者,女,40歲,2019年3月29日初診。主訴:吐酸、燒心3個月余。現(xiàn)病史:患者3個月前無明顯誘因出現(xiàn)吐酸、燒心、咽喉梗阻、飽脹感,未予重視,服“艾普拉唑、莫沙比利”等初期稍有緩解,停藥反復。于外院行胃鏡檢查示非萎縮性胃炎伴胃竇糜爛,病理示中度非萎縮性胃炎,診斷為賁門失弛緩癥。刻下癥見:胃脘脹悶,反酸、燒心,噯氣頻作,飲流食則反酸加重,夜間易饑,右肋疼痛,口干口苦,喜冷飲,納可,大便干結(jié),4~5 d一行,先干后稀,小便黃,寐安,舌質(zhì)淡紅,苔薄黃,脈細弦。西醫(yī)診斷:賁門失弛緩癥。中醫(yī)診斷:吐酸,辨證為肝(膽)胃不和、脾虛氣滯、胃氣上逆。治法:疏肝瀉熱、健脾理氣、和胃降逆。選以降逆調(diào)胃湯加減:柴胡10 g、白芍15 g、枳實15 g、姜半夏10 g、黃連4 g、黃芩10 g、吳茱萸4 g、蒲公英20 g、厚樸15 g、大黃4 g、黨參15 g、茯苓30 g、海螵蛸30 g、煅牡蠣30 g、萊菔子10 g,服藥7劑,且配合艾司奧美拉唑(國藥準字H20046380)40 mg/次,1次/d,清晨空腹服用,持續(xù)7 d。二診:服藥后,諸癥見緩,不灼熱,吐酸少,噯氣時作,納可,但因貪食辛辣,癥狀有所反復,舌質(zhì)淡紅,苔微剝,脈沉細。原方加北沙參15 g,大黃改5 g,萊菔子改12 g,再服14劑,繼續(xù)聯(lián)合艾司奧美拉唑治療。三診:服藥后,胃無不適,飲食不節(jié)時,噯氣少作,大便干結(jié),3 d一行,舌質(zhì)淡紅,苔剝薄白,脈沉細。原方去黨參,加生地30 g,大黃改3 g,萊菔子改10 g,白芍改炒白芍15 g,再服14劑。告知節(jié)制飲食,隨訪效良。
3.2.2 討論 本例賁門失弛緩癥患者長期服用西藥,控制效果不佳,故而尋求中醫(yī)。初診時病癥繁多,吐酸嚴重,熱象突出,然火性上炎,當緊抓“逆”之病機,明確其吐酸為標,胃失和降,下之不和為本。此患者乃由于肝膽蘊熱,橫逆中焦,因而升降失調(diào),氣機郁滯,胃失和降,酸濁上犯清道。其治法為:疏肝瀉熱、健脾理氣、和胃降逆,選用降逆調(diào)胃湯加減。首重其標,故于原方中去干姜、桔梗等辛熱上逆之品,加牡蠣,制酸降逆,平肝潛陽;黨參、茯苓以健脾行氣,既可恢復中焦氣機之升降,又有“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之意。待標實得緩,但當謹守病機,再隨證加減用藥。此案有以下幾點體會:一是在治療初期,當快速減輕患者吐酸的臨床癥狀,使得患者對于后續(xù)的治療充滿信心,故而選用艾司奧美拉唑聯(lián)合治療,寓意身心同調(diào),正所謂“善醫(yī)者,必先醫(yī)其心,而后醫(yī)其身”,良好的情緒會加速疾病康復。二是“食邪”在本病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既可加重病情,又可阻礙恢復,必須嚴格控制,不可貪食。三是基于患者病情,當逐步減少降逆藥的使用,既可鞏固療效,防止復發(fā),又可防止降逆太過,傷及正氣。
4 體會
賁門失弛緩癥屬于食管胃動力障礙性疾病,雖非惡疾,但臨證之際,亦頗為難治。首先通過現(xiàn)代醫(yī)學檢查輔助確診,為后續(xù)的辨證論治提供病因、病理機制、預后和轉(zhuǎn)歸理論基礎(chǔ)。從病因病機上看,此病多由脾(胃)、肝、腎功能失調(diào)所致。治療上基于“衡”法,一方面著手以整體論治,以平為期;宣通氣機,升降相宜;剛?cè)嵯酀瑵欚B(yǎng)為要;病證結(jié)合,內(nèi)外同治。治以疏肝健脾、和胃降逆之法,使得氣血、虛實、陰陽、升降、寒熱、納運等多個方面功能得以恢復,同時結(jié)合現(xiàn)代藥理知識,做到病證結(jié)合。另一方面注重疏導患者的心理,共奏身心同調(diào)之效果,故而可取得良好的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