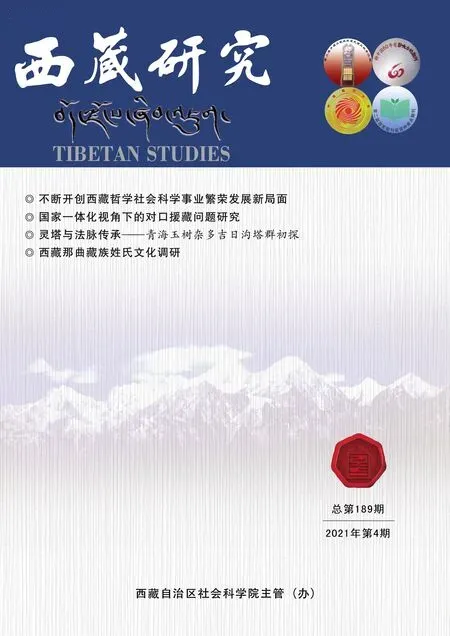明代治理西藏的特點及其作用
楊潔 周潤年
(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北京 100081)
明朝(1368—1644)承元啟清,終明之世,對于西藏關系的審慎處理頗有成效。明朝與元朝、清朝相比,特殊之處是未在西藏駐軍,卻依然對西藏實現了有效統轄,而且在明代,漢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得到空前的加強。
一、實行“懷柔羈縻”改革
羈縻政策最初源于秦漢時期,盛行于唐宋,鼎盛期則到了明朝,一直到清改土歸流結束,前后一千多年的時間里,總的來看,“懷柔遠人,義在羈縻”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國家統一。
(一)制定了治藏政策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年號為洪武。在洪武三年(1370)的詔諭中,雖說朱元璋稱蒙古“虜遁沙漠”(1)《明太祖實錄》卷51·頁5下,洪武三年四月乙丑條。,但事實上對于明朝最大的威脅仍是殘元勢力。以史為鑒古今有之,漢唐興亡之史實是明代統治者的重要借鑒。漢武帝通西域而斷匈奴之右臂,從而開創大一統盛世,而唐朝時期的衰落與吐蕃政權對其進行的打擊有著很大的關系,因此《明史·西域傳》稱:“洪武初,太祖懲唐世之亂,思制御之。”[1]8572因此可以說朱元璋對于西藏的戰略規劃是在吸取漢、唐經驗與歷史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為了徹底消滅殘元勢力,必須阻斷蒙藏聯盟,在西藏重構統治體系。明太祖朱元璋用“懷柔羈縻”及“多封眾建”的和平方式治理西藏的戰略構想逐漸開始形成并付諸實施。
基于明代初期與西南諸涉藏地區以及北方蒙古等勢力之政治關系出發,恢復和加強明朝同西藏等地的聯系,關系到邊疆安全和政治穩定。明太祖朱元璋充分意識到這些地區的復雜性,采取了“招諭為主,軍事為輔”的政策,一方面派大將軍徐達率所部向北和西方向追擊元軍殘余勢力,另一方面迅速著手招撫這些地區的僧俗首領歸附明朝。洪武元年即派人到相關地區宣布明朝建立的消息,同時也派遣許允德入藏與藏族上層的故元官吏聯絡,并頒發詔諭于西藏及青甘川等地區,詔曰:“惟爾吐蕃邦居西土,今中國一統,恐尚未聞,故茲詔示使者至吐蕃。”(2)《明太祖實錄》卷42·頁1上,洪武二年五月甲午條。詔書向西藏等地區政教首領昭示了大明王朝的正式建立以及期望西藏歸順明朝統治的意愿,但由于古代信息的閉塞,西藏還沒有對新生的強大的大明政權有全面的認識,明太祖的此次詔諭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因此,第二年明太祖又另派左副將軍鄧愈自臨洮進克河州,遣人招諭(3)《明太祖實錄》卷52·頁9上,洪武三年五月辛亥條。。之后明朝不斷派遣使者前往西藏,積極尋求與西藏之間的聯系。明廷以招撫甘青涉藏地區的成就為基礎,最終打開了與西藏互派使者友好往來的局面。最早與西藏取得聯系是在洪武五年(1372)四月,中書省“詔章陽沙加仍灌頂國師之號,遣使賜玉印彩段表里,俾居報恩寺化導其民。”(4)《明太祖實錄》卷73·頁4下,洪武五年四月丁酉條。此次封賞賜印,是明王朝第一次冊封西藏地方首領。由于漢藏使者的多方斡旋,西藏地方政教首領也派出使者前往明京,此次漢藏使者的友好往來標志著明王朝與帕木竹巴西藏地方政權隸屬關系的正式確立。
(二)增強了漢藏民族之間的政治認同
明神宗說:“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地都是祖宗開拓的封疆。”(5)《明神宗實錄》卷225·頁5下19上,萬歷十八年七月乙丑條。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朝是中國歷史上十分重要的階段,在古代信息、交通各方面皆不發達的時代,西藏地方與明朝中央的聯系和交流是通過使者往來形式實現的,使者的往來既是西藏地方與中央友好關系的媒介,也是漢藏民族友好交流的有效方式。因此,使者往來不僅增進了漢藏民族友好關系,而且密切了西藏地方與明朝中央的關系,促進了漢藏民族的政治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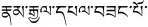

西藏政教首領按期朝貢以示效忠,不僅是政治上的畏于大明王朝之威勢,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心悅誠服與認同,明朝中央對政教首領禮遇有加,給予政教首領以無上榮譽,感化了西藏政教首領及僧俗眾人。有學者認為西藏高僧不遠萬里來到明帝都朝貢,主要是為了追逐經濟利益,我們覺得這樣的說法未必符合當時的實際。西藏到京城的路程來往大約需要兩年左右的時間,在驛站體系尚未完善之前,道路艱險,有時甚至還有性命之憂,只為了貢品三倍的利益,恐怕是解釋不通的。西藏入明使者可獲朝廷的禮遇、朝廷的封號及誥印,從而獲得號令僧俗民眾的資本,中央王朝的支持。如期朝貢,才能鞏固在本地區的統治地位,而且有利于繼續擴大影響,壯大勢力,因此說應該是強烈的政治因素與民族認同所起作用的結果。
(三)穩定了明朝對西藏的統治

二、發展“貢賜貿易”
明代西藏與祖國內地在政治經濟方面關系非常密切,朝貢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西藏將當地的一些土特產、手工藝品、馬匹等以貢品形式帶到祖國內地,而朝廷則將祖國內地的絲綢、彩緞、茶葉等以賜賞形式賜予西藏使者。貢和賜拉近了西藏地方與中央王朝之間的密切關系,同時也加強了西藏與祖國內地的經濟往來,促進了西藏的經濟發展。
(一)朝貢刺激西藏地方經濟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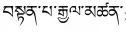
在這種貢賜數量懸殊的貿易中,大規模的物品以及錢幣流入西藏,刺激了西藏經濟的發展。祖國內地的先進技術和工藝也先后進入西藏,例如制革、淘金、建筑、金銀加工、農業種植等技術和技術人員大量輸入,推動了西藏社會經濟的發展。還有制瓷技術的傳入,促成了西藏的第一個瓷窯(普布瓷窯)正式投入生產。湯東杰布在經濟發展及冶鐵技術提高的基礎上,率領漢藏兩族工匠藝人共建鐵索橋58座,方便了人們的通行。西藏僧俗首領通過不定期的朝貢,得到豐厚的收益,在豐厚的物質利益驅動下,貢使隊伍也出現了屢違定制,以假朝貢之名從事商業的活動。實際上,明代空前的朝貢貿易是有史以來對西藏經濟的最大的一次外部撞擊,對于整個西藏的僧俗上層人士經濟思想的成熟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力量也無法替代的。
(二)發展了西藏與祖國內地的經濟貿易
明朝與西藏地方經濟貿易最主要的形式即是茶馬貿易。據《明會典》記載:“貢馬每匹纻絲一匹,鈔三百錠,上等馬加絹一匹”[10],在這樣巨大經濟利益的驅動下,西藏發展畜牧業的積極性大大提高。《明實錄》中有關西藏來貢信息幾乎都包含有貢馬,西藏朝貢使者不僅因之得到明廷賜予的大量茶葉,而且在其返回西藏的沿途以貢使的特殊身份公開申請購茶返藏,朝貢使者得到了最大的經濟效益,同時也繁榮了茶馬貿易的市場,推動了西藏畜牧業和內地種茶業的發展。伴隨著茶馬貿易,促進了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交流,對推動邊疆地區的開發和社會進步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明朝中央除賞賜西藏大量茶葉等物品外,還賞賜一定數量的流通錢幣。洪武二十四年(1391)詔賜“必力公尚師輦卜闍搠思吉結卜使者堅敦真文綺各一襲、鈔二十五錠……”(9)《明太祖實錄》卷27·頁1上,洪武二十四年正月己丑條。這樣賜予流通貨幣及金銀的記載在《明實錄》中隨處可見。與此同時,西藏的物品如皮毛、藥材、藏香、佛像、刀劍等土特產品和手工藝品等作為貢品也源源不斷流入祖國內地,很多物品頗受祖國內地人民的喜愛,比如西藏的氆氌,在大寶法王使者的貢物中即有“紅氆氌一百副、紫氆氌五十副、黃氆氌五十副、紅鐵哩麻五十副、白鐵哩麻五十副”[11]。通過漢藏使者的相互往來,西藏與祖國內地的物品得到空前的交流,也使西藏與祖國各地、藏族和漢族在經濟貿易方面互通有無,相互支持、相互繁榮,促進了整個社會的共同發展。
(三)促進了驛站沿線經濟的興盛

驛站在護送往來使者和朝貢人員方面也擔負著重要作用,有時甚至派員伴隨前往明都。關于驛站護送往來使者和朝貢人員之事,《明實錄》中更是不乏其例。明初對各驛站所設有驛卒以及所應用的馬、驢、牛和差役都有具體規定。依據規定,一般大驛站需馬八十至六十匹;小驛站則為三十至二十匹,并且各個驛站還要儲備充足的糧食,以供應往來使者和朝貢官員。從這些資料來看,明代中央對驛站的管理十分重視,驛站管理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明朝中央政府對西藏的安撫和統治。
明朝中央政府繼元朝對西藏的施政,重視發展中原地區與西藏的交通。經過多次調整、修復,使驛路交通更加暢通無阻,往來使者絡繹不絕,因而出現了“道路畢通,使者往還數萬里,無虞寇盜”[1]8580的太平景象。驛站的暢通以及往來使者的頻繁出入,對驛站和城市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同時也為各族人民生產技術和文化知識的交流、傳播提供了條件,從而也就促進了各民族經濟、文化事業的共同發展,對鞏固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三、采取“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
明代在文化政策上采取了包容多元的態度。明朝前期國力雄厚,經濟繁榮,對不同宗教兼容并蓄,民間宗教信仰、習俗多樣而活躍,這一時期文化、宗教、藝術都有了空前發展。
(一)豐富了西藏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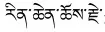

(二)傳播了漢藏典籍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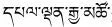
明朝皇帝及大臣對藏傳佛教也十分尊崇。明成祖即位之初就與噶瑪噶舉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得銀協巴交往甚密,永樂八年(1410),永樂皇帝派遣使者侯顯到西藏迎請《甘珠爾》,并以此手抄本為底本在南京首次刻版印刷全套藏文大藏經《甘珠爾》,這套《甘珠爾》共有108軼,每一函皆有大明永樂皇帝所作的《御制藏經贊》及《御制后序》。明廷將印制好的《甘珠爾》贈送給三大法王每人一套,現保存在拉薩色拉寺的《甘珠爾》就是當年永樂皇帝賜給色拉寺的創建者大慈法王釋迦也失的。隨著永樂版《甘珠爾》的雕刻,印刷技術傳入西藏,從而使西藏的雕版印刷業逐步趨向完善。此后,雕版印經院在西藏發展興盛起來,大大小小的印經院不僅印刷出數以萬計“大小五明”的典籍,而且亦為藏文文獻的保存以及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促進了工藝美術及建筑等方面的交流
明朝使臣與西藏使者的往來,使工藝、美術及建筑等方面的交流也成為必然,在長期的交往中,不同的文化兼容并蓄,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現復合、交融的情況。《明實錄》多處記載有“貢馬及方物”,這個“方物”應該就是帶有西藏特色的物品。此外,見于文獻記載的朝貢“方物”的品種還有佛像、銅佛、銅塔、佛經、珊瑚、犀角、刀劍、甲胄、舍利等。隨著西藏到朝廷朝貢的人數不斷增多,中原地區的工藝品大規模流入西藏,使得西藏名不見經傳的寺院都有機會得到產自大明宮廷的工藝珍品[8]30。同時,西藏藝術品也源源不斷地傳入各地,這就使帶有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特色的工藝品得到廣泛交流,客觀上也帶來了漢藏文化交流的空前盛況。
明朝中央政府多次派遣工匠藝人到西藏,漢藏能工巧匠在建筑工程技術方面彼此互相吸收,取長補短,形成了具有漢藏特色的建筑。永樂年間建造的三大寺(即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就是典型的代表,這些建筑既離不開不遠萬里赴藏的漢族工匠,更離不開西藏勞動人民的勤勞智慧。還有像大慈法王釋迦也失、大寶法王得銀協巴等宗教首領,他們既是明代冊封的法王,也是溝通漢藏友好關系的使者,更是促進漢藏文化友好交流的功臣。此外,北京的五塔寺、興教寺、法海寺及五臺山的圓照寺等也是漢藏文化交流的產物。宣德五年(1430)四月,闡教王朵令遣使鎖扎失思奏請“愿居京自效”,宣德五年六月、宣德五年九月,一些高僧大德紛紛要求“居京自效”,“據統計,明代北京的藏傳佛教寺廟約有十余座,較為著名的有大隆善護國寺、大能仁寺、大慈恩寺等,在京的藏傳佛教僧人總人數不低于2000人。如此眾多的喇嘛寺院及藏傳佛教僧人,構成了明代京城文化內容的組成部分。”[17]具有漢藏融合風格的建筑藝術依然保存至今,成為漢藏友好關系的歷史符號。
(四)弘揚了藏傳佛教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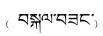
正是因為明朝中央王朝對藏傳佛教的認同與喜好,故西藏入貢的物品大多與藏傳佛教有關,明朝中央也會回賜藏經及法器之類的宗教物品。《明實錄》記載,這樣類似的物品交流貫穿于整個明代,其中有一部分藏傳佛教藝術品也有機會在宮廷及京城民眾中流傳。被皇帝召請入朝的三大法王和其他藏傳佛教高僧隨身也都帶來了較之例行朝貢更為豐富的宗教物品,加之他們在南京、北京、五臺山等地舉行了多種聲勢浩大的宗教活動,在將藏傳佛教于祖國內地的影響逐漸擴大的同時,客觀上也起到了更加廣泛地傳播藏族藝術的歷史作用[8]34。
隨著西藏與祖國內地僧俗使者的頻繁往來,祖國內地的民眾對藏傳佛教了解日益加深,從而使藏傳佛教廣泛流傳。元代時期藏傳佛教開始傳入北京,隨著漢藏使者的頻繁往來,明朝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逐漸水乳交融,并且在北京落地生根,逐漸成為北京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19]。至今北京明代的建筑物上藏傳佛教元素也是隨處可見,例如北京的五塔寺、嵩祝寺、興教寺、法海寺和居庸關等建筑物上雕刻有藏文頌詞、法輪、海螺、傘蓋、木魚等藏傳佛教的吉祥圖形;也有的在廟宇殿堂頂上裝飾有銅質鎦金經幡、法輪、龍、鹿等雕塑。所有這些皆是漢族吸收藏傳佛教文化的最好見證。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明代各民族經過接觸、交流、聯結和融合,形成一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統一體。明代漢藏之間的交往、交流達到了十分寬廣的程度,不僅是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經濟、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很深入的交流與融通。明代是漢蒙藏一體意識形成的關鍵時期,明代比起其他朝代,雖然未在西藏駐軍,但是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政策和措施,仍然達到了統轄的效果。在當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大歷史背景下,分析、研究明代治理西藏的方略及意義,對當今如何繼承漢藏民族友好情誼、處理好共同性與差異性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11)2019年9月,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見https://zujuan.21cnjy.com/question/detail/37294296。。明代治理西藏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特點顯著、作用重大,經過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逐漸發展成為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中華民族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