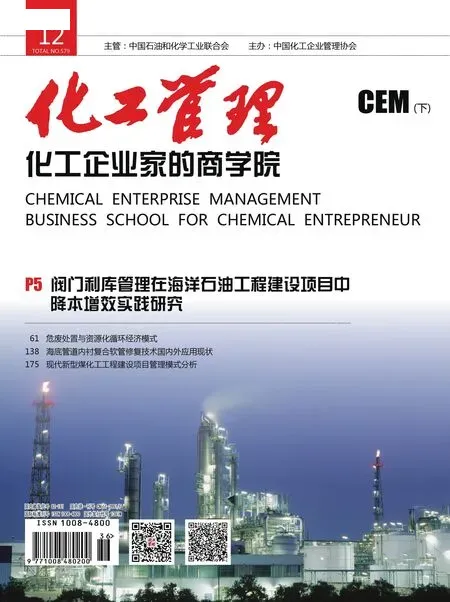蒸發式冷凝器在氨冷凍系統的應用
徐劍虹(大唐呼倫貝爾化肥有限公司,內蒙古 呼倫貝爾 021012 )
0 引言
大唐呼倫貝爾化肥有限公司以褐煤為原料生產合成氨,產能為18萬噸/年。空分采用深冷法空氣分離工藝,氣化采用水煤漿加壓氣化工藝,氣體凈化采用低溫甲醇洗聯合液氮洗工藝,氨合成采用低壓氨合成工藝。氨冷凍系統由氨壓縮機及其附屬設備及一些輔助設備所組成,主要任務是為空分單元、低溫甲醇洗單元、氨合成單元提供低溫冷量。氨冷凍制冷工藝由阿特拉斯及煙臺冰輪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完成。制冷壓縮機采用6級壓縮,其中每兩級均構成一段,分別對應一級冷量,相對應的制冷溫度:一段-38℃、二段-15℃、三段3℃。
1 氨冷凍工藝流程
來自氨合成單元的液氨(10℃)送入氨冷凍系統氨接收罐冷氨區,來自氨冷凍系統經氨冷凝器冷凝的液氨(35℃)進入熱氨區,冷熱氨區的液氨混合后溫度變為25℃,分別送至氨合成單元一級氨冷器和空分單元氨冷器換熱,返回的氣氨(3℃、0.37MPaG),進三段入口分離罐分離液體后,進入氨壓縮機三段;三段入口分離罐中的液氨(3℃、0.37MPaG)送至氨合成單元二級氨冷器換熱,返回的氣氨(-15℃、0.131MPaG)在二段入口分離罐中分離液體后,入氨壓縮機二段;二段入口分離罐中液氨(-15℃、0.137MPaG)送至低溫甲醇洗單元氨冷器換熱,返回的氣氨(-38℃、0.078MPaA)在一段入口分離罐中分離液體后,入氨壓縮機一段。氨接收罐中的液氨大部分作為制冷劑參與制冷循環,另一部分液氨(25t/h、35℃)由液氨泵加壓后送至尿素裝置。氨壓縮機為6級三段壓縮,三段出口的氣氨(145℃、1.48MPaG、33956kg/h),在氨冷凝器中冷凝為液氨返回氨接收罐中。
2 問題的提出
氨冷凍系統自投用以來,存在的主要問題為氨壓縮機出口壓力高于設計值,合成氨系統100%負荷運行時氨壓縮機出口氣氨壓力為1.70MPaG(設計值1.48MPaG),冷凝溫度為44℃(設計值35℃)。由于壓力偏高導致需要開大不凝性氣排放閥放氨火炬以降低氨壓縮機出口壓力,造成了氨的浪費。另一方面當冷凍負荷升高或汽輪機主蒸汽壓力輕微波動時,汽輪機轉速會很快降低,易造成氨壓縮機跳車,氨冷凍系統運行穩定性差,高溫季節時系統經常減負荷運行。氨壓縮機出口壓力高于設計值成為影響生產經濟穩定運行的瓶頸問題。
通過對比各項工藝參數,發現與設計值偏差較大的是氨壓縮機出口流量,氨壓縮機出口流量達到了39000kg/h,為設計負荷的114.8%。由于制冷系統屬于閉式系統,流量超出設計值,造成氨冷凝器的熱負荷超出設計值較多,從而使氨冷凝器出口達不到要求。經分析,氨壓縮機超負荷主要原因為氨合成單元冷量需求超過了設計負荷,因此要降低氨壓縮機出口壓力,需對氨冷凝器進行改造,通過考察比較,考慮到經濟性,決定新增1臺蒸發式冷凝器,以降低氨壓縮機出口壓力。
3 蒸發式冷凝器技術特性
蒸發冷也是冷凝器的一個種類,從結構上來講蒸發冷是集普通水冷冷凝器、冷卻塔、水泵、水系統的管道連接組合成一體,具有節電、節水、安裝方便、占地面積小、維修方便等特點。但在換熱原理存在本質上的差別。水冷式冷凝器是利用水的顯熱吸收制冷劑的熱量達到冷卻的目的,而蒸發冷是利用水的潛熱也就是水在常溫下的蒸發吸收熱量達到冷卻的目的,同樣質量的水蒸發所吸收的熱量是水溫升高5℃時熱量的116倍,所以在帶走同樣熱量時蒸發冷比水冷式冷凝器用水量低得多,這也就是蒸發冷之所以節電節水的根本原因。
冷凝盤管特點。冷凝盤管是閉式冷卻塔換熱最關鍵的部件,材質采用不銹鋼波節管,相對圓管有以下四個特點:
(1)設備結構更加緊湊:相比圓管與橢圓管,波節管單位長度面積更大,相同面積占地最小;
(2)提高換熱系數:管內介質流動時,增加了介質擾動,介質與管壁碰撞次數增大,提高了換熱系數,在目前的不銹鋼異型管內換熱系數最高;
(3)增強自身除垢能力:波節管表面的彎曲結構,在受到溫度變化時,彎曲的地方會發生一定的型變,迫使垢層脫落或松動,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除垢能力;
(4)冷凝盤管在設計時為了使制冷劑更好的流出,盤管的每層管道均沿流向設計一定坡度。另外為提高冷凝盤管的使用壽命,在冷凝盤管共進行四次2.5MPa的壓力試驗。
4 蒸發冷式凝器選型
原設計氨冷凝器為2臺固定管板式循環水冷卻器并聯,新增1臺蒸發式冷凝器,使氨壓縮機出口壓力降至設計值以下。濕球溫度按20℃計。經核算,選用1臺標準排熱量為8000kW的蒸發式冷凝器,主要設備參數見表1。
箱體外護板采用鍍鋁鋅版,防腐蝕能力較高。上下箱采用槽鋼、型鋼等高強度全框架結構,整體高溫熱浸鋅。浸鋅厚度大于0.05mm,耐酸堿腐蝕且結構堅固。
收水器是為了防止噴淋水裝置噴出的水霧被空氣帶出蒸發冷,采用獨特的多孔曲面結構設計,能有效收集濕空氣中的水分,使水的飄逸率小于0.001%,收水器采用高品質PVC材質,具有抗老化、重量輕、便于清洗保養的特點。
軸流風機采用頂吸式,使冷凝盤管處于負壓區,因為水在負壓時更容易蒸發,頂吸式可增強水膜蒸發以提高換熱。軸流風機采用中空鋁合金風機,采用直聯式,減少了傳動部件,提高運行可靠性。
5 使用效果和注意事項
5.1 使用效果
蒸發式冷凝器自2017年6月投用,運行3年以來,氨壓縮機出口壓力降至1.48MPaG以下,冷凝溫度降至34℃以下,氨壓縮機汽輪機主蒸汽閥門開度降至80%左右(改造之前100%),蒸發冷凝器冷凝效果明顯。同時原氨冷凝器可以切出1臺,節省循環水用量。蒸發式冷凝器冬季干運行,即不投冷卻水,用空氣進行冷卻,充分利用低溫空氣冷量,節省用電量和水量。
5.2 注意事項
為了保證蒸發冷凝器使用效果和經濟性,使用注意事項如下:
(1)不凝性氣體存在會造成氨壓縮機出口壓力高,若越積越多,冷凝壓力將會不斷升高。處理方法是開高點排放閥將不凝性氣排至氨火炬,同時要查明不凝性氣體的來源。氨壓縮機不凝氣主要為H2及N2,來源為氨合成單元氨冷器泄漏或不凝性氣排放不及時,需針對實際問題進行處理[1]。
(2)由于蒸發式冷凝器的蛇形盤管內介質為氣液混合物,對管道的沖刷嚴重,因此,應定期對高壓換熱盤管進行測厚,尤其是彎頭處有無明顯的減薄現象。特別注意的是,在進行測厚之后,要立即對破壞的鍍鋅層進行防腐處理[2]。
(3)在日常運行中,要經常檢查噴淋水是否均勻,噴頭有無堵塞等現象。在短期停車時,對收水器及噴淋系統進行檢查,檢查收水器有無塌陷,噴頭有無脫落等現象。
(4)在設備運行過程中,應定期對蒸發式冷凝器循環水質進行檢測,確保循環水水質滿足要求。如循環水無法滿足要求時使用脫鹽水作為噴淋水。
(5)由于噴淋水的蒸發,含在水中的礦物質及其他雜質會遺留下來,因此,需要定期排污,防止上述物質的積聚,否則水的酸度或礦物質含量會增高,產生腐蝕和水垢。
(6)定期清理蒸發式冷凝器,將積留在水箱底部或過濾器、盤管上的雜物及時清理干凈,以避免雜物進入循環系統,堵塞噴頭。由于空氣中沙塵含量較高,導致了循環水中的濁度較高,所以,利用每次停車機會,徹底清理水箱底部的淤泥、雜物等。
(7)蒸發式冷凝器在日常運行過程中,需每小時檢查水箱水位、自動上水浮球閥、溢流閥是否正常工作,以及水泵的運行情況等。
(8)入冬前停噴淋水泵,打開水槽排污閥,排凈水槽水。排凈水泵泵體中水。用氮氣將泵體吹干,防止冬季凍壞設備。冬季每小時巡檢風機運行情況,及時清理換熱器、風機四周積雪。
6 結語
從實際使用情況可以看出,蒸發式冷凝器的投用,降低了氨壓縮機出口壓力,保證了氨壓縮機的安全運行,同時氨壓縮機運行穩定性提高,為合成氨系統安全穩定運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蒸發式冷凝器是高效節能的環保設備,具有穩定可靠的性能,能夠節省循環水用量和用電量,結構緊湊,占地面積小,建議新建裝置使用蒸發式冷凝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