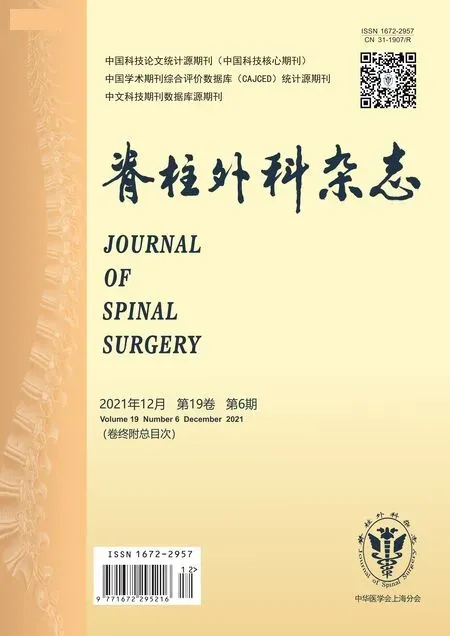脊柱結(jié)核病灶清除并椎間支撐植骨術(shù)后并發(fā)癥的防治
宋向偉,侯文根,郭 鑫,王自立
1.新鄉(xiāng)醫(yī)學(xué)院第一附屬醫(yī)院骨科,新鄉(xiāng) 453100
2.寧夏醫(yī)科大學(xué)總醫(yī)院脊柱骨科,銀川 750004
脊柱結(jié)核病灶清除術(shù)后椎體往往遺留較大的骨缺損,使脊柱失去穩(wěn)定性,不利于結(jié)核病灶愈合,并且易繼發(fā)脊柱畸形[1]。脊柱結(jié)核病灶徹底清除后植骨融合內(nèi)固定在維持和重建脊柱穩(wěn)定性中具有重要意義[2],其能夠穩(wěn)定脊柱結(jié)核病變部位,促進(jìn)脊柱結(jié)核病灶靜止并最終愈合[3-4]。患椎椎間結(jié)構(gòu)性植骨與非結(jié)構(gòu)性植骨治療脊柱結(jié)核均能取得良好臨床療效[5],但并不是所有的植骨都能順利融合,植骨融合期間植骨材料可能出現(xiàn)傾斜、骨折、吸收、下沉、移位、假關(guān)節(jié)形成或脫落等并發(fā)癥[6-8]。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326例脊柱結(jié)核患者椎間結(jié)構(gòu)性植骨的融合情況,旨在對脊柱結(jié)核病灶清除并椎間植骨術(shù)后的并發(fā)癥及其防治進(jìn)行初步探討。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納入標(biāo)準(zhǔn):①根據(jù)臨床表現(xiàn)、實驗室檢查及組織病理學(xué)檢查、結(jié)核分枝桿菌培養(yǎng)明確診斷為脊柱結(jié)核;②采用病灶清除并椎間植骨術(shù)治療。排除標(biāo)準(zhǔn):①椎體附件結(jié)核;②臨床資料不全。根據(jù)上述標(biāo)準(zhǔn),納入2000年1月—2015年12月寧夏醫(yī)科大學(xué)總醫(yī)院收治的脊柱結(jié)核患者326例,其中男157例、女169例,年齡為10~82(42.30±16.54)歲。臨床表現(xiàn):低熱136例(41.7%),盜汗125例(38.3%),乏力132例(40.5%),消瘦82例(25.2%),病變節(jié)段局部疼痛316例(96.9%),神經(jīng)功能障礙119例(36.5%);伴胸腰椎后凸畸形62例(19.0%)。病灶部位:頸椎5例(1.5%),頸胸段1例(0.3%),胸椎93例(28.5%),胸腰段44例(13.5%),腰椎142例(43.6%),腰骶段41例(12.6%)。病變累及單節(jié)段239例(73.3%),雙節(jié)段43例(13.2%),3個節(jié)段及以上44例(13.5%)。本研究通過寧夏醫(yī)科大學(xué)總醫(y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zhǔn)(批準(zhǔn)號:2018168)。
1.2 手術(shù)方法
患者術(shù)前臥床休息,營養(yǎng)支持治療,采用異煙肼、利福平、吡嗪酰胺、鏈霉素四聯(lián)抗結(jié)核藥物治療2 ~ 4周。當(dāng)患者結(jié)核中毒癥狀改善、一般情況好轉(zhuǎn)能夠耐受手術(shù)時進(jìn)行手術(shù)。對所有患者實施徹底病灶清除并椎間植骨,視患者具體病情給予椎管減壓、畸形矯正或內(nèi)固定。徹底病灶清除后,所遺留的缺損為規(guī)則的長方形或正方形,用生理鹽水反復(fù)沖洗創(chuàng)面,再利用腰橋使椎體間隙略開大,將植骨材料鑲嵌植入缺損正中央,再次利用腰橋減小椎間隙,使植骨塊緊緊鑲嵌于椎體之間。植骨手術(shù)入路:前路77例(23.6%),后前路236例(72.4%),后路13例(4.0%)。311例患者行內(nèi)固定,其中66例(21.2%)行前路內(nèi)固定,235例(75.6%)行后前路內(nèi)固定,10例(3.2%)行后路內(nèi)固定。15例患者行外固定,其中11例(73.3%)前路術(shù)后行外固定,3例(20.0%)后路術(shù)后行外固定,1例(6.7%)后前路術(shù)后行外固定。
術(shù)后繼續(xù)抗結(jié)核治療,鏈霉素、異煙肼、利福平、吡嗪酰胺4種藥物聯(lián)合應(yīng)用2個月(強(qiáng)化期);鞏固期視病灶治愈情況而定,異煙肼、利福平、吡嗪酰胺3種藥物聯(lián)合應(yīng)用。服藥期間監(jiān)測肝腎功能及血常規(guī),發(fā)生藥物不良反應(yīng)后及時對癥處理,必要時暫停抗結(jié)核藥物。術(shù)后1個月視復(fù)查情況逐步下床活動。
1.3 植骨融合評價指標(biāo)
使用自行設(shè)計的病例資料收集系統(tǒng),建立脊柱結(jié)核病例資料信息庫,重點觀察患者術(shù)前、術(shù)后融合過程中及停藥時的X線、CT、MRI影像學(xué)資料。記錄植骨材料、位置、跨越節(jié)段及融合情況等。依據(jù)CT三維重建確定植骨是否融合。融合標(biāo)準(zhǔn):患椎骨與植骨塊融合,植骨界面間隙消失,骨小梁貫通形成連接骨橋。根據(jù)MRI及CT了解有無膿腫和死骨,進(jìn)而確定病灶是否治愈。
2 結(jié) 果
2.1 一般情況
所有患者術(shù)后抗結(jié)核化療時間為3 ~ 36(7.89±5.92)個月。停藥時,CT三維重建示植骨均融合,CT和MRI示結(jié)核病灶均治愈且無新的結(jié)核病灶形成。術(shù)后隨訪2 ~ 3年89例,>3 ~ 5年98例,>5 ~ 10年128例,>10年11例,病灶治愈后植骨融合處均無異常改變。術(shù)中共使用348個植骨材料,其中髂骨290個,多根肋骨捆綁20個,肋髂骨捆綁26個,鈦網(wǎng)12個;植骨跨越單節(jié)段276個,雙節(jié)段72個。
2.2 術(shù)后植骨融合并發(fā)癥
術(shù)后植骨融合過程中出現(xiàn)植骨傾斜9例(2.8%),其中2例為胸椎結(jié)核采用肋髂骨捆綁植骨,7例腰椎結(jié)核采用髂骨植骨,均為后路內(nèi)固定并前路單節(jié)段植骨。術(shù)后CT示植骨塊均前后傾斜,給予延長制動時間至植骨塊出現(xiàn)融合跡象,然后開始逐步負(fù)重活動。術(shù)后化療3.5 ~ 10.0個月,最終植骨融合、病灶治愈。
植骨骨折8例(2.5%),均為腰椎結(jié)核采用后路內(nèi)固定并后外側(cè)髂骨植骨,其中3例為跨雙節(jié)段植骨、5例為單節(jié)段植骨,分別于術(shù)后3、4、4、4、5、6、7、7個月發(fā)現(xiàn)髂骨植骨塊骨折。植骨塊骨折端無明顯移位,輔以胸腰支具外固定,植骨塊骨折2 ~ 3個月愈合。術(shù)后化療3.0 ~ 9.5個月,最終植骨融合、病灶治愈。
植骨吸收4例(1.2%),其中2例為腰椎結(jié)核,1例為胸腰椎結(jié)核,1例為胸椎結(jié)核。胸椎和胸腰椎病灶為肋髂骨捆綁植骨,腰椎病灶為髂骨植骨,均為后路內(nèi)固定并前路植骨。胸腰椎病灶跨雙節(jié)段植骨,胸椎和腰椎病灶為單節(jié)段植骨。4例患者術(shù)后CT、MRI檢查示有死骨、硬化壁或病變性骨橋等殘留。分別于術(shù)后8、9、10、12個月復(fù)查示植骨塊末端萎縮吸收,病灶未愈。給予再次手術(shù)徹底清除病灶植骨治療,輔助胸腰支具外固定,繼續(xù)抗結(jié)核治療5 ~ 16個月,最終植骨融合、病灶治愈。
植骨下沉3例(0.9%),2例胸椎結(jié)核行多根肋骨捆綁植骨,1例腰椎結(jié)核行髂骨植骨,均為后路內(nèi)固定并前路單節(jié)段植骨。分別于術(shù)后2、3、3個月發(fā)現(xiàn)植骨下沉,給予輔助胸腰支具外固定,避免過多負(fù)重,患者植骨融合,未再進(jìn)一步下沉。術(shù)后化療6 ~ 12個月,最終植骨融合、病灶治愈。
植骨移位1例(0.3%),為腰椎結(jié)核,行后路內(nèi)固定并前路單節(jié)段髂骨植骨。術(shù)后CT示植骨塊明顯傾斜,囑臥床制動。術(shù)后3個月復(fù)查示植骨塊上端未融合,植骨塊移位,嚴(yán)格限制活動,植骨塊未再進(jìn)一步移位。術(shù)后化療10個月,最終植骨融合、病灶治愈。
假關(guān)節(jié)形成1例(0.3%),為L4~ S1結(jié)核,行后路內(nèi)固定并前路單節(jié)段髂骨植骨,植骨節(jié)段為L5~ S1。術(shù)后化療8個月(自行停藥),術(shù)后2年復(fù)查示L5~ S1植骨塊上端假關(guān)節(jié)形成。再次手術(shù)清除硬化骨后植骨,化療9個月,最終植骨融合、病灶治愈(圖1)。
3 討 論
脊柱結(jié)核主要累及前中柱,病灶清除后嚴(yán)重影響脊柱穩(wěn)定性,常需要椎間植骨來維持和重建脊柱穩(wěn)定性。理想的植骨材料應(yīng)具有穩(wěn)定的生物相容性并能承擔(dān)脊柱載荷,還應(yīng)具有骨形成、骨誘導(dǎo)及骨傳導(dǎo)的特性[9]。目前椎間植骨材料主要有自體骨(髂骨、肋骨等)、同種異體骨、人工骨及填充自體松質(zhì)骨粒的鈦籠等[10-11]。
對于植骨材料的選擇,首選自體髂骨,自體髂骨具有足夠的支撐強(qiáng)度和寬闊的植骨接觸面,植骨效果可靠,植骨融合率高,晚期植骨吸收、內(nèi)固定失敗發(fā)生率較低,是骨移植的金標(biāo)準(zhǔn)[12]。一般截取具有三面皮質(zhì)骨的骼骨塊[4],其有足夠的支撐強(qiáng)度,富含松質(zhì)骨,有利于骨形成、骨誘導(dǎo)。其次是自體肋骨、填充自體松質(zhì)骨粒的鈦網(wǎng),最后才考慮選用同種異體骨及其他人工骨材[3]。楊智賢等[13]綜合分析了27篇文獻(xiàn)中脊柱結(jié)核病灶清除術(shù)后的修復(fù)材料,認(rèn)為自體骨(髂骨、肋骨)是目前修復(fù)脊柱結(jié)核骨缺損的主要來源,其次是鈦網(wǎng),人工骨及人工椎體少量用于臨床治療。本研究326例的348個植骨材料主要采用自體髂骨及肋骨,視具體情況應(yīng)用鈦網(wǎng),與上述文獻(xiàn)中植骨材料選擇相一致。
椎間植骨融合率達(dá)95% ~ 100%[5,14-15]。但在植骨融合過程中仍有可能出現(xiàn)一些并發(fā)癥,如植骨塊傾斜、骨折、吸收、下沉、移位、假關(guān)節(jié)形成或脫落等,需要注意預(yù)防并給予相應(yīng)處理,促進(jìn)病灶治愈和植骨融合。
植骨傾斜一般因術(shù)中視野受限制引起。病灶清除多從椎體側(cè)方進(jìn)入,椎體前方有大動脈,椎體后方為脊髓或神經(jīng)。椎體前后方均不宜過多暴露,否則可能引起災(zāi)難性后果,故術(shù)中椎體暴露往往不充分,植骨時容易出現(xiàn)傾斜。術(shù)中用探針明確椎體前后緣或透視,可很大程度上預(yù)防植骨傾斜。術(shù)后復(fù)查X線片及時評估植骨塊位置,如有明顯傾斜,則延長脊柱制動時間,盡量避免植骨移位和脫落。本研究中出現(xiàn)9例植骨傾斜,均為前后傾斜,給予延長制動時間,均恢復(fù)良好,未發(fā)生植骨移位和脫落。
植骨骨折一般發(fā)生于植骨塊未增粗重塑之前,本研究中8例植骨塊骨折發(fā)生在術(shù)后3 ~ 7個月。為預(yù)防植骨骨折,術(shù)中應(yīng)使用堅強(qiáng)的前路或后路內(nèi)固定,并行后外側(cè)植骨融合。由于后路植骨是植于正常受骨區(qū),因而植骨愈合更為快捷。當(dāng)發(fā)生椎體結(jié)核病灶未治愈、植骨不愈合、延遲愈合、植骨骨折或歪斜時,椎體間依然不穩(wěn)定,后外側(cè)植骨可形成360°融合,使脊柱穩(wěn)定性增加[16-17]。后路融合還可防止因前路病灶未愈、植骨失效而引起的畸形、斷釘、斷棒等嚴(yán)重并發(fā)癥的發(fā)生[3]。加用橫連可增加局部的穩(wěn)定性,有生物力學(xué)研究[18]表明,橫連桿可增強(qiáng)脊柱單節(jié)段椎弓根釘-棒系統(tǒng)固定后的抗扭轉(zhuǎn)能力,降低后方關(guān)節(jié)突應(yīng)力,增強(qiáng)脊柱軸向穩(wěn)定性。在植骨塊未增粗塑形之前,脊柱避免過多負(fù)重,必要時術(shù)后輔助外固定。本研究8例植骨塊骨折患者均在行后路內(nèi)固定的同時行后外側(cè)植骨,并且應(yīng)用橫連連接椎弓根釘-棒系統(tǒng),因此,當(dāng)發(fā)生植骨塊骨折時,脊柱有相對穩(wěn)定的后方,植骨塊骨折端并無明顯移位,發(fā)現(xiàn)骨折后輔以外固定,植骨塊骨折逐步愈合。
植骨吸收一般與病灶未徹底清除有關(guān),術(shù)后植骨區(qū)感染是導(dǎo)致植骨吸收的重要因素之一,感染會使術(shù)后骨吸收明顯增多,一旦發(fā)生嚴(yán)重感染,必然導(dǎo)致植骨失敗[19]。術(shù)前應(yīng)仔細(xì)閱讀三維重建CT、普通或增強(qiáng)MRI資料,充分了解病灶的位置和性質(zhì)。術(shù)中病灶必須徹底清除干凈,否則植骨不易成活,隨后成為死骨,成為新的病灶和感染源。相同條件下,局部的穩(wěn)定和能否徹底清除病灶是影響療效的關(guān)鍵因素,也是預(yù)防植骨吸收的關(guān)鍵。本研究中共發(fā)生4例植骨吸收,術(shù)后CT、MRI檢查示病灶殘留,給予再次手術(shù),并輔助外固定,繼續(xù)抗結(jié)核治療,最終植骨融合、病灶治愈。
植骨下沉多因骨性終板缺損、植骨接觸面積小、骨質(zhì)疏松等造成[20]。椎體由中央的松質(zhì)骨和外周的皮質(zhì)骨組成,終板是位于其上、下面的皮質(zhì)外層。終板并非真正意義上的骨皮質(zhì),而是融合骨小梁組成的層狀多孔結(jié)構(gòu),這一特殊結(jié)構(gòu)使終板中央?yún)^(qū)有較豐富的微血管通道,能給植骨區(qū)提供較充足的血液循環(huán)。尤其是將終板修磨至點狀滲血后,既保留了終板結(jié)構(gòu)的完整,又為植骨塊提供了再血管化的最大可能[21]。植骨接觸面積小時,局部應(yīng)力集中,尤其患者存在骨質(zhì)疏松時,植骨塊容易下沉。Srivastava等[22]認(rèn)為,使用肋骨作為植骨材料時需要2根以上,以增大植骨接觸面積。本研究中共發(fā)生植骨下沉3例,其中2例為多根肋骨捆綁植骨,1例為髂骨植骨,下沉原因為徹底清除病灶后終板缺損,植骨塊與松質(zhì)骨接觸面積小,局部壓強(qiáng)大。給予輔助外固定、避免過多負(fù)重后,患者植骨融合,未再進(jìn)一步下沉。
植骨移位多因植骨塊未緊緊鑲于椎體之間,如植骨塊一端接觸不緊密或植骨明顯傾斜,內(nèi)固定不夠堅固,隨著脊柱的活動,植骨塊會逐漸移位,嚴(yán)重時發(fā)生植骨脫落[11]。欲使植骨塊穩(wěn)固,最好于上下椎體間開槽,嵌插植骨,同時一期內(nèi)固定,為局部穩(wěn)定創(chuàng)造好的條件。還可以利用腰橋增大椎間隙后植入骨塊,然后再用腰橋恢復(fù)椎間隙擠壓植骨塊,這樣植骨塊就嵌插牢固,不易移位。本研究中發(fā)生植骨移位1例,由于植骨塊傾斜并且嵌插不牢固,限制活動后植骨塊未進(jìn)一步移位,最終植骨融合、病灶治愈。
假關(guān)節(jié)形成一般因植骨塊與植骨床未融合,逐漸萎縮硬化,加上局部不穩(wěn),進(jìn)而形成假關(guān)節(jié)。為預(yù)防植骨未融合的發(fā)生,須認(rèn)真制備植骨床,不能有殘留病灶,并使之與植骨塊緊密接觸,植骨面必須與上、下終板垂直,不可歪斜;植骨接觸面要充分,盡量居中,以免載荷不均產(chǎn)生矯正角度的丟失或植骨愈合障礙。在保證病灶徹底清除后,需將植骨床修整成平面,為植骨塊提供一個平整、面積盡量大、骨面盡量優(yōu)良的受區(qū),為植骨的成活創(chuàng)造條件[3]。前路植骨時盡量清除軟骨終板,保留骨性終板;后路椎間小關(guān)節(jié)加強(qiáng)植骨時植骨量要足。另外植骨床必須清除軟組織,必要時對其去皮質(zhì),如后路植骨時需清除小關(guān)節(jié)突的關(guān)節(jié)囊、關(guān)節(jié)軟骨面和橫突上的軟組織,進(jìn)行關(guān)節(jié)突關(guān)節(jié)和橫突間融合。本研究中假關(guān)節(jié)形成1例,由于L5植骨床病灶殘留,逐漸骨質(zhì)硬化,植骨塊上端未融合,形成假關(guān)節(jié),再次手術(shù)清除硬化骨后植骨融合。
綜上所述,為了使植骨早期融合,盡可能避免植骨并發(fā)癥的發(fā)生,需要注意以下幾點。①盡可能選擇支撐作用強(qiáng)、融合率高的大塊髂骨作為植骨材料,并在植入前給予良好的保護(hù),避免不良理化因素的損傷;②盡可能徹底清除病灶,避免植骨塊吸收;③盡可能為植骨塊提供一個平整、面積大、血供良好的植骨床,為植骨融合創(chuàng)造良好的條件;④盡可能將植骨塊緊緊嵌入植骨床中央,必須與上、下終板垂直,植骨接觸面要充分;⑤合理應(yīng)用內(nèi)固定(后路釘棒系統(tǒng)需加橫聯(lián))及后外側(cè)植骨保持局部穩(wěn)定;⑥局部適當(dāng)應(yīng)力負(fù)荷刺激和無不利植骨融合因素(如骨質(zhì)疏松、長期應(yīng)用激素等)亦很重要。植骨融合過程中出現(xiàn)植骨并發(fā)癥時,應(yīng)針對不同原因采取相應(yīng)措施,最終大多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