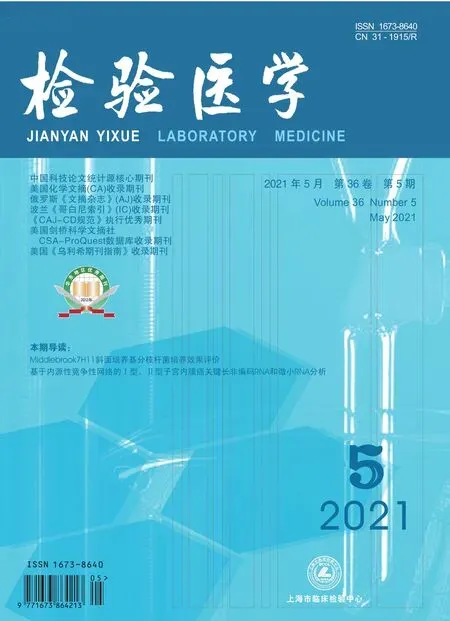腸道菌群與IL-6/gp130信號通路在急性胰腺炎發病機制中的研究進展
肖櫻艷, 崔 艷, 李 艷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檢驗醫學中心,湖北 武漢 430060)
人類的胃腸道中定植著含量豐富的微生物,由超過1014種微生物和超過500萬個基因組成一個豐富的微生物群落,被稱為腸道菌群[1]。正常情況下,腸道菌群的種類和數量是相對穩定的,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是最常見的細菌,占腸道菌群的80%~90%[2]。腸道菌群通過影響新陳代謝、調節黏膜免疫系統、促進消化以及調節腸道結構等在人體生理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腸道菌群、免疫系統和腸道屏障之間的相互作用維持著腸道菌群的穩定,并限制致病菌的生長[3],當這種平衡被打破時,將導致腸道菌群失衡[4]。腸道菌群失衡會引起多種胃腸道疾病,包括炎癥性腸病、腸易激綜合癥[5]、胰腺疾病[6]等。既往認為,胰腺是一個無菌的器官,與腸道菌群無密切關系。最新研究發現,腸道菌群能夠遷移進入胰腺并影響胰腺微環境[7]。腸道菌群的改變可能在急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和胰腺癌等多種胰腺疾病的發病機制中發揮作用[6]。除此之外,炎性細胞因子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作為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上游的炎癥因子參與炎癥和免疫反應,在急性胰腺炎和慢性胰腺炎、胰腺癌的發生和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IL-6通過其信號轉導因子糖蛋白130(glycoprotein 130,gp130)發揮功能,進而激活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啟動酪氨酸激酶(janus tyrosine kinase,JAK)/信號轉導及轉錄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信號通路,促進急性胰腺炎的發生[8]。本文參考近年來相關的人類和動物實驗,著重討論腸道菌群與IL-6/gp130信號通路在急性胰腺炎發病機制中的研究進展。
1 腸道菌群與炎癥反應
腸道菌群穩態是機體免疫-炎癥反應的重要調節因子,腸道菌群數量和結構的改變參與調控免疫屏障,與炎癥反應關系密切。大量研究結果表明,腸道菌群失衡可產生以下效應:(1)可降低腸上皮細胞的緊密連接,增加腸黏膜的通透性,導致菌群和毒素物質入侵,誘導炎癥發生[9];(2)降解腸黏膜中的黏蛋白(Mucin蛋白)和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抗體,使腸道黏膜屏障作用減弱,對炎癥的發生有促進作用[10];(3)導致免疫功能紊亂,誘導腸道黏膜T淋巴細胞數量增多,T淋巴細胞活化并分泌炎癥因子,加重炎癥反應[11];(4)促進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和類脂等細菌成分進入血液循環,作用于單核細胞和巨噬細胞,進一步調節炎癥因子[IL-6、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白細胞介素1(interleukin-1,IL-1)等]的釋放[12];(5)產生對機體有害的代謝產物,如腸道中產H2S的細菌增多,H2S對腸道黏膜有破壞作用,可誘導機體產生炎癥因子,促進炎癥發展[13]。由此可見,腸道菌群可以通過刺激腸上皮細胞、降解相關腸黏膜蛋白、促進內毒素等細菌成分入血而誘導機體的炎癥反應。
2 IL-6/gp130信號通路在急性胰腺炎中的作用
大多數急性胰腺炎患者表現為輕度自限性胰腺炎癥和水腫,病死率低,經保守治療可自行恢復。但20%~30%的患者會出現胰腺出血性壞死病變,病死率高達50%,這種形式的急性胰腺炎被稱為重癥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14]。胰腺腺泡細胞內胰蛋白酶原及相關蛋白酶的過早激活是急性胰腺炎發病的主要分子機制之一。腺泡細胞內IL-6等炎癥因子的釋放是急性胰腺炎發病的決定性環節,并最終影響急性胰腺炎的嚴重程度[15]。IL-6是機體免疫調節網絡的重要成員之一,在炎癥反應中起核心調節作用。IL-6通過其信號轉導受體gp130激活下游trans信號通路,在急性胰腺炎疾病發生和進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8]。動物實驗結果顯示,胰腺腺泡細胞IL-6的釋放能夠激活消化酶,并引起細胞質空泡化,從而促進急性胰腺炎的發生[16]。同時,IL-6通過聚集大量白細胞導致胰腺腺泡細胞水腫和壞死,嚴重時可引發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17]。進一步的研究發現,攜帶人類IL-6轉基因的小鼠更容易在蛙皮素誘導下發生急性胰腺炎,說明IL-6在急性胰腺炎的發生中起重要促進作用[18]。有研究通過在小鼠肝臟中過表達IL-6的受體蛋白gp130發現,IL-6 trans信號通路能夠在胰腺中激活信號轉導及轉錄激活因子3,引起胰腺局部炎癥和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19]。因此,IL-6/gp130炎癥信號轉導通路的激活是急性胰腺炎發病的重要環節之一,其作用機制包括通過促進胰蛋白酶原的激活和炎性細胞浸潤誘導胰腺腺泡細胞水腫和壞死,促進急性胰腺炎的發生和進展。
3 腸道菌群失衡與急性胰腺炎的關系
急性胰腺炎是臨床常見的急腹癥之一,發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20]。其發病原因主要為膽道疾病、高脂血癥和乙醇(習慣性飲酒或短期內大量飲酒)等[21]。但無論病因如何,其發病機制都離不開胰蛋白酶原和其他蛋白水解酶在胰腺腺泡內的過早激活、胰腺腺泡損傷、促炎介質上調、細胞因子釋放、全身炎癥反應和微循環的損傷[22]。
既往認為,正常的胰腺與腸道菌群沒有直接接觸,胰腺也沒有自己的微生物群。但近年來的研究結果表明,腸道菌群能遷移進入胰腺并影響胰腺微環境,進而參與急性胰腺炎的發病過程[23]。在急性胰腺炎中,微循環損傷和低血容量可導致腸黏膜缺血再灌注損傷,導致腸屏障完整性喪失和腸道菌群移位,引起局部和全身感染[24]。多項研究均發現,急性胰腺炎患者存在腸道菌群失衡,絕大多數優勢菌的豐度和多樣性降低,腸桿菌與腸球菌等潛在致病菌豐度明顯增加[25]。致病菌的增多可破壞腸黏膜屏障,導致腸道菌群移位,遷移進入胰腺,最終引發急性胰腺炎[7,22,26]。有學者發現,59%的急性胰腺炎患者存在腸道屏障功能障礙[26]。除此之外,腸道菌群失衡還可使腸黏膜通透性增加,導致內毒素等入血,從而加重急性胰腺炎,并引發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LI等[27]發現,68.8%的急性胰腺炎患者的循環血中具有腸道菌群代表性細菌的DNA。進一步研究發現,在胰腺腺泡細胞中,病原菌識別受體如Toll樣受體和核苷酸結合寡聚域(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NOD)樣受體對細菌抗原的感知是胰腺炎發病機制的一部分[28]。
由此可見,腸道菌群失衡是急性胰腺炎發病的重要危險因素,腸道菌群可以遷移進入胰腺并引發胰腺局部炎癥;同時,在急性胰腺炎患者中,某些致病菌,如腸桿菌、腸球菌豐度的升高會導致腸黏膜屏障功能受損,使腸黏膜通透性增加,內毒素等此時便可進入血液,引起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增加急性胰腺炎患者的死亡率。
4 腸道菌群-脂質代謝-IL-6-急性胰腺炎
近年來,多項研究發現腸道菌群是機體代謝和免疫表型的重要參與者,對人類健康有重要影響[29]。腸道菌群具有調節脂質組成,影響脂質消化和吸收的能力,并參與脂質代謝[30]。腸道菌群α-多樣性與血三酰甘油水平呈負相關[31-32]。脂肪因子是脂肪細胞分泌的一系列向大腦、肝臟、胰腺、免疫系統、血液系統、肌肉和其他組織反映脂肪組織功能狀態信號的多肽,脂肪細胞產生和分泌的脂肪因子主要包括瘦素、脂聯素、促酰化蛋白以及細胞因子(IL-6、TNF-α、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等)[33]。脂肪因子能夠對機體包括免疫反應、葡萄糖代謝、血管內皮細胞功能、炎癥反應在內的多種生物學進程產生特定的影響[34]。脂肪細胞堆積過多,將導致IL-6等促炎因子的釋放增加,在急性胰腺炎的發病進程中起促進作用[35]。
腸道菌群豐度和多樣性的改變能影響機體的脂質代謝過程,脂質代謝紊亂對于促炎因子IL-6的釋放有促進作用,IL-6水平異常對于胰腺炎的發生有促進意義,IL-6/gp130炎癥信號通路激活在急性胰腺炎的發病進程中可能是重要的一環。
5 總結
腸道菌群失衡是急性胰腺炎的發病機制之一,IL-6在急性胰腺炎中的異常表達和大量釋放使其成為與急性胰腺炎發病機制直接相關的重要細胞因子。腸道菌群豐度和多樣性的改變對于脂質代謝紊亂、IL-6水平異常增高和IL-6/gp130信號通路的激活有著促進作用。因此,識別腸道菌群失衡、特定腸道定植菌豐度和多樣性的改變、機體脂質代謝水平的改變和IL-6在急性胰腺炎發病時上調的機制可能對設計新的預防措施和治療方案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