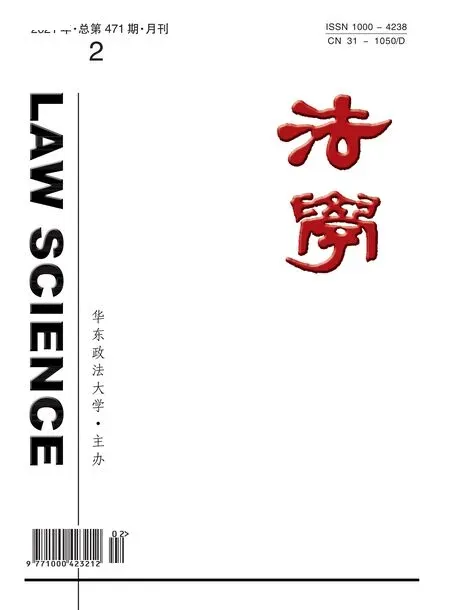論社會補償權
婁 宇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我國社會法學界廣泛關注社會補償制度及相關的社會補償權,并在相關領域展開了初步研究,但是概念的規范結構仍欠清晰,尚難形成令人信服的邏輯體系,由此導致社會補償權的制度設計缺乏統一的權利理論支撐,實施的機制較為隨意。
試舉幾例說明。例1: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國,財政部與國家醫保局要求對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發生的醫療費用,按規定在基本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助等支付后,個人負擔部分由地方財政給予補助,實現全免費。由此引發爭議:醫保基金支付而后由財政補貼的法律依據何在?補貼的主體為什么是地方財政,而不是中央財政?〔1〕參見《兩部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患者個人負擔的醫療費由財政補助》,載中國網,http://newS. china.com.cn/txt/2020-01/26/content_75649856.htm。而武漢市為了打好防疫攻堅戰,將各發熱門診留觀病人的門診費也由政府負擔,基本醫保基金的支付項目甚至也由地方財政埋單,這是否存在法律依據?〔2〕參見《國家醫保局:對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等患者采取特殊報銷政策》,載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 com/gn/2020/01-21/9066608.shtml。
例2: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的災后重建資金高達1 萬多億元。財政部分別將重建資金的支出形式規定為恢復重建、異地安置、就業援助等。基于此,有學者認為,我國應當值此契機發展和完善社會補償制度。社會補償權系“自然、社會、政策等風險產生的社會弱勢群體向國家和社會追償的權利”,被追償的對象并無“侵害權利的行為”,僅是由于社會主體間對共生系統的維護責任而產生的補償義務。〔3〕參見白小平:《社會補償的社會法證成——以災后房屋修復重建社會補償為視角》,載《前沿》2015 年第8 期,第76 頁。但是,如此界定社會補償權是否無限擴大了國家責任?公共財政資金如何負擔如此巨大的經濟補償責任?
例3: 獨生子女政策的長期實施造成了兩個獨特的社會現象:獨生子女家庭和失獨家庭。社會各界一直呼吁建立社會補償制度,賦予兩類家庭必要的利益損害補償權。前一類家庭中的子女無暇照顧父母,于是多地出臺了“獨生子女護理假”,后一類家庭中的父母可以按照當地政策領取特別扶助金,包括精神慰藉金與生活補助金。這些舉措也引發了較多的社會爭議,“獨生子女護理假”難以被企業所接受,認為國家政策造成的家庭損失不應由企業承擔,國家責任不應當在此處缺位;〔4〕參見《獨生子女護理假,只能看上去很美?》,載中國新聞網,https://view.inewS. qq.com/a/20190228A00S5200。而“失獨”并非計劃生育政策的直接后果,由財政負擔扶助金的法理依據是什么?全國統一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失獨”,特別扶助金由地方政策規定并由地方財政負擔的法理何在?
例4: 2018 年年中,國家食藥監總局發布通告確認,長春長生公司和武漢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生產的多種疫苗不合格,引發社會恐慌。數月后,長春長生公司在承擔相關的行政處罰責任后,設立了專項賠償金,對接種造成的關聯損害后果予以賠償。聯系到近年來發生的多起疫苗接種致害事件,學者提出了摒棄社會保險制度,由國家無過錯補償計劃先行支付,而后向承擔民事責任的疫苗企業追償的建議。〔5〕參見馮玨:《民事責任體系與無過錯補償計劃的互動——以我國疫苗接種損害救濟體系建設為中心》,載《中外法學》2016年第6 期,第1746 頁。但是,補償計劃的范圍是什么?與民事責任的關系又是什么?補償計劃的主體是哪一級政府財政?與社會保險制度的職能分工又當如何界定?
上述四個案例涉及不同的社會政策領域,問題也形形色色,但都與國家積極的財政給付義務密切關聯,大致包含如下要素:(1)在損失原因與形式方面,主要表現為突發自然災害或政治原因造成的人身和經濟損失、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為個人造成的機會成本損失、個人為促進公共利益受到的人身損失和經濟損失幾種類型;(2)在歸責原則方面,在利益被侵害過程中,國家并無過錯或過失,損害結果與原因之間的關系呈現出客觀的表征;(3)在補償義務主體方面,受害人都要求共同體給予利益補償,即使造成損失的主體有明確的指向,受害人也不向其主張權利;(4)在債權發生的形式方面,即使存在社會保險或商業保險,受害人一般也不會通過合同途徑去主張權利,而是直接責難于國家。這些要素使得該領域的權利異于傳統的社會保障權利,與行政法領域的國家補償權和國家賠償權亦有區別,成為現代社會中的一類新型權利。
如前述案例所示,我國目前的單行立法中已隱約可見社會補償權的要素,但是,一方面,實定法中沒有反映出統一的社會補償權內容,該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尚不清晰,頂層規劃的缺失導致后續立法的隨意與無序;另一方面,現有的立法對該權利維權方式和內容的規定不一,引發諸多社會質疑,影響了權利的實施效果。如果再考慮到學界對這個概念的無序使用,無法在同一語境下開展理論研討,那么實務界被誤導的可能性將會更高。〔6〕我國法學、社會學、經濟學各類文獻都可見“社會補償”的概念,但都不是社會保障法意義上的“社會補償”,其權利的形成機理和實現方式與社會補償權大相迥異,概括起來主要集中于以下四個領域:侵權責任中民法不可期待性的國家補償(如環境污染、生態失衡)、個人負擔的社會成本的補償(如生育成本、女性單身家庭的養育成本、留守兒童)、軍人的安置補償、技術進步之后對經濟利益受損者的補償(如應用新技術造成失業,對失業者的補償)、政府征收征用對利益受損者的補償(如土地征收補償)。相關文獻可參見金蓉等:《黑河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及效益評估研究》,載《人民黃河》2005 年第7 期,第4-6 頁;王愛麗等:《女性單親家庭經濟資源的受損與社會補償》,載《黑龍江社會科學》2009 年第10 期,第163-167 頁;袁寅生:《社會補償:優撫安置的一種理論闡釋》,載《中國民政》2001 年第4 期,第26-27 頁;高奇琦等:《社會補償與個人適應:人工智能時代失業問題的兩種解決》,載《江西社會科學》2017年第10 期,第25-34 頁;王華華等:《中國土地征收政策:“社會補償”還是“社會賠償”》,載《理論參考》2013 年第6 期,第36-39 頁;等等。基于此,本文嘗試探討社會補償權的功能地位、規范構造與規范領域,以求匡正學理,指導實踐。
二、社會補償權的生成、正當性依據與功能
對社會補償權的分析不能局限于法律規范本身,還需從歷史和社會發展的角度進行探討。社會補償制度源自對在戰爭中犧牲的軍人以及家屬的撫恤,隨后拓展至對所有戰爭被害人的補償,最終發展成在戰爭、特別的政治事件、犯罪、瘟疫等情況下,國家即使合法行使了公權力或無違法行為,但是未盡職責致使公民健康利益受損,公民可基于“共同體權利”要求政府財政予以補償的法律制度。
(一)社會補償權的發展史
對戰爭或執行軍事任務中傷亡的軍人進行醫治和后事料理,并撫恤家屬的做法早已有之。我國春秋時期征戰頻繁,各諸侯國都為軍人頒布了救治傷病、獎勵軍功、減免家庭賦稅的措施,〔7〕參見群峰:《古代軍人的撫恤與優待》,載《天津社會保險》2015 年第4 期,第69 頁。古羅馬《民法大全》中更是全面建立了維護軍人經濟利益的法律制度,〔8〕參見[意]桑德羅·斯奇巴尼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年版,第270 頁。但是這些撫恤待遇僅能由軍人及其家屬享有,相關權利的主體很有限,現代戰爭造成的人員傷亡遠大于冷兵器時代,類似于軍人撫恤的待遇逐步延伸至戰爭造成的所有傷亡人員,進而類推擴展至為國家遭受特別犧牲的公民身上。
1.魏瑪共和國的社會補償立法
社會補償法律制度與社會補償權的概念均源自德國社會法實務與理論界,后被日本所引介,近年來在我國臺灣地區也有研討,并付諸了一定的實踐。
德國社會補償制度源自第二帝國時期的軍人保障立法。19 世紀60—70 年代,普魯士王國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但是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軍隊傷亡慘重、人心不穩,歐陸列強對德國仍存戒心,戰事隨時可能再起,必須及時通過優撫策略穩定軍心。1871 年,德國頒布《軍隊優撫法》(Gesetze zur Milit?rversorgung),決定為統一征戰中受難的陸軍和海軍軍人提供補償。此次獲得補償的群體龐大,待遇優厚,讓人們首次看到了德國政府的決心和能力。〔9〕Vgl. Muckl/Ogerek/Rixen, Sozialrecht, München: C. H. Beck, 2019, S. 391あ.“一戰”之后,魏瑪政府上臺,為了安撫傷亡慘重的德國軍隊,并踐行《魏瑪帝國憲法》中確定的社會權利,這個左翼政權加大了優撫的力度。1920 年,德國頒布《帝國優撫法》(Reichsversorgungsverordnung),由國家財政為“一戰”中傷亡的軍人提供醫療、就業優待及養老金,并貫徹職業軍人與其他軍人待遇平等原則,由此引發普羅大眾的不滿,他們認為平民的傷亡系戰爭引發的客觀結果,難以歸責于自身,因此醫療救治待遇也應當延伸至平民,而各類軍人因參軍喪失了就業機會和參加社保的機會,可給予就業和養老金優待,這些待遇不適用于平民即可。〔10〕Vgl. Achterberg/Püttner/Würtenberger (Hrsg.), 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 Bd. II, Heidelberg: C. F. Müller, 2000,§27 Rn. 7 あ.隨即德國又頒布了《戰爭受害者補償法》(Kriegspersonensch?dengesetz),將《帝國優撫法》中的醫療救治待遇照搬到了普通公民群體,這標志著社會補償制度正式建立。雖然魏瑪政權僅存在了15 年,而且“二戰”前的政府財政狀況非常糟糕,社會補償制度的實施效果難以令人滿意,但是這兩部法律確立的社會補償理念卻深入了人心。
2.基本權利時代的社會補償權理念與立法
與“一戰”相比,“二戰”帶來的傷亡更加慘重,恢復魏瑪政權時期社會補償制度的提議幾乎在沒有遇到阻力的情況下就被立法者所接受。1950 年,成立僅1 年的聯邦德國就頒布了《聯邦優撫法》(Bundesversorgungsgesetz),1957 年又頒布了《軍人優撫法》(Soldatenversorgungsgesetz),這兩部法律以魏瑪時期的兩部法律為藍本,在借鑒其合理制度設計的同時,也摒棄了其中不現實的立法理念。加上“二戰”后《基本法》構建的基本權利體系日益成了憲法法院和各類法院普遍認可的客觀秩序,所有權利都要在基本權利的框架下獲得教義學內容,所以社會補償權可被視為基本權利時代的產物。
通說認為,社會國家原則入憲肇始于《魏瑪憲法》,該法采用了權利條款型立法方式,即將公民基本權利條款作為社會國家原則的具體表現形式,授權司法創設社會權利類型,但是如此做法僅是社會權利保障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且不論社會權利需要財政支出來實現,司法機關缺乏民主正當性,即使將這種權利作為主觀權利,由于其涉及的領域過于寬泛,亦難獲得明確的教義學內容。〔11〕參見[德]V.諾依曼:《社會國家原則與基本權利教條學》,婁宇譯,載《比較法研究》2010 年第1 期,第146 頁。《魏瑪憲法》規定的社會權利條款非常翔實,且可以由司法機關隨時增補,迫于政府財力和所處的經濟社會財力,能夠真正實現者寥寥無幾,尤其是到了魏瑪政權后期,憲政實踐的效果幾近于無,〔12〕Vgl. Stolleis, Geschichte des Sozialrechts in Deutschland, lucius & lucius, 2003, S. 240あ.社會補償權落實的狀況可想而知。
“二戰”后,德國立法者對社會補償權采用了“憲法模糊處理+社會保障統一立法描述+單行法特別規定”的立法模式,在將該權利作為社會權利法定類型的同時,又避免了其外延的無限泛化。〔13〕同前注〔11〕,V.諾依曼文,第150 頁。首先,在《基本法》中將社會國家原則作為憲法基本原則,承認了社會權利的憲法地位,但并不賦予其獨立的教義學內容,至多只把該權利與平等權結合起來,實現某特別法賦予某群體具體的社會權利,那么另一相似的群體也可主張的效果。其次,德國《社會法典第一冊——總則》中將該權利定義為“相關人員基于國家共同體由法定原因造成的健康損害的補償權”,另據《社會法典》其他分冊的規定,該權利只能在現實的危害發生后,由權利人向國家提出給付請求權來主張,給付的內容包括保持、改善、恢復健康狀況以及合理的經濟補償,權利人的遺屬也可以提出經濟補償請求權。最后,嚴格遵循特別法規定的原則,社會補償權是立法確定的權利,為了限制司法創設,德國《社會法典》未單設“社會補償”分冊,而是把這項制度分別規定在《聯邦優撫法》《軍人優撫法》《民役法》《傳染病法》等特別法中,權利的規范要件清晰,避免了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減少了法官造法的可能性。〔14〕Vgl. Schulin, Einführung, Sozialgesetzbuch, München: Beck-Texte im dtv, 2009, S. LVII.如果考慮到《社會法典》采用了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社會保障制度設獨立分冊的立法體例,唯獨社會補償由特別單行法規定,那么社會補償權受到的立法限制可見一斑。〔15〕Vgl. Reinhard, Neuregelung des Sozialen Entsch?digungsrechts im SGB XIV in ZRP 2019, S. 221f.
3.當代社會補償權理念與立法
基本權利意義上的社會權利往往通過平等權獲得新的教義學內容,這實際上與社會補償權的產生路徑十分相似。如前所述,軍人的健康利益可能在戰爭中受損,普通民眾同樣面臨這種風險,因此軍人優撫的權利民眾也應當享有,而普通民眾不會發生軍人就業機會成本喪失的危機,所以不享有安置的優撫權利,這種安排是公平的。由此不難發現,社會補償權天生帶有一種“平等的基因”,這在客觀上導致了該權利關注的是損害的結果,而非損害的原因,于是便產生了這樣的立法理念:某一群體因為戰爭、政策、災害等原因而利益受損,享有了向國家主張補償的權利,另一個類似的群體也可以作此主張。
當代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未知的、意圖之外的后果成了歷史和社會的主宰力量,所有的生命形態都處于工業社會制造的危險中,〔16〕參見[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張文杰、何博聞譯,譯林出版社2018 年版,第74 頁。而社會國家原則影響下的立法不斷賦予政府新的職能,“全能主義”政府的趨勢愈演愈烈,層出不窮的社會立法導致了社會國家原則不斷地“基本權利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以人權保障為基石的國家制度的當然組成內容”。〔17〕[德]艾伯哈爾特·艾希浩佛:《社會基本權利——肇因于魏瑪,成就于統一后之德國!》,胡川寧譯,載《中德法學論壇》2017 年第2 期,第269 頁。在此背景下,社會補償權也難以獨善其身,雖然該權利被德國立法者相對合理地控制在了有限的領域,但是由于政府職能的頻繁擴張,加之該權利具備豐富的規范內容,所以一旦被其他國家所移植,很難不發生新的變種。
事實上,在一些借鑒德國社會補償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已經發展出了一些新的內容,有的甚至突破了社會補償權原有的內容。這方面較為突出的例子是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立法實踐。日本將社會補償權拓展至對環境食品公害的損失補償領域,理由是國家應當擴大生產者責任來落實社會國家原則,因為污染者付費原則僅針對有害環境的行為,潛在的污染風險仍難以克服,所以國家可以對潛在污染者課以費用,當損害發生時,受害人可據此提出補償請求權,國家以此費用來支付。〔18〕參見徐良雄:《建構公害健康被害補償法制之可行性》,載《軍法專刊》2018 年第64 卷第3 期,第142-169 頁。筆者以為,此種補償制度的實質是環境保險,或者破壞環境生態罪的被害人補償制度,并不能構成獨立的社會補償權。社會補償權產生于無侵權人或者即便存在侵權人,國家也疏于履行維護社會共同體成員健康權的義務而實施的無過錯平衡補償制度,其資金來源是政府財政,而環境侵權可能是民事侵權,可通過建立強制環境保險制度來規避,這種補償權基于契約產生,亦可能是環境犯罪的被害人補償,那即是社會補償的一種具體類型。這種通過國家單獨收費來支付利益受損者的制度已經構成了額外征稅,對此已有日本學者指出,該制度難以歸于社會補償之列,而應當受到法律保留、合憲性和合理性(比例原則)的約束。〔19〕中原茂樹「誘導手法行政法體系」小早川光郎、宇賀克也主編『行政法發展變革上卷』(有斐閣,2001 年) 568 頁參照。轉引自上注,徐良雄文。這就需要結合本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況來綜合考量,僅有權利分析并不充分。我國臺灣地區將對“二二八”事件中的補償金制度作為社會補償權的具體類型,旨在當無其他社會保障制度予以救濟時,對該事件中生命、健康受到侵害者予以補償,這被認為將源自德國社會補償法中政治事件受害者的補償權進行移植的成功案例,起到了“使人民了解真相、撫平歷史創傷、促進族群融合”的效果。〔20〕參見林谷燕:《社會補償》,載《師友月刊》2009 年第9 期,第57-59 頁。
綜上,筆者主張可結合現實國情,對當代域外的立法理念進行辯證地認識和有選擇地揚棄。
(二)社會補償權的正當性依據
權利的正當性依據是法律文化的核心觀念,意即人作為一種理性的存在,對其利益有合理的需求和主張,相應地,國家制定的簡單形式的法就構成了權利的合法性基礎。〔21〕參見[德]卡爾·施密特:《合法性與正當性》,劉小楓等編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108 頁。可以說,理性主義主張的正當性催生了權利,而經驗論層面上的國家法落實了權利,因此,正當性需從法理層面上去解讀,而功能要在實定法框架下去探討。德國社會法學者曾指出,“社會平衡的觀點”(Billigkeitsgesichtspunkt)是指導立法者安排社會補償法律制度的法理依據,〔22〕Vgl. Rüfner, Einführung in das Sozialrecht, München: C.H.Beck, 1991, S. 119あ.相應地,社會平衡的涵義也就構成了該權利的正當性基礎。當然,因社會補償權發揮了填補傳統社會保障權功能漏洞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說,一國既有的社會保障立法的結構性制度也限定了社會補償權的正當性范圍,從此角度觀察,完全脫離開現行立法去理解社會補償權并非理性做法。
結合德國社會法通說及我國的社會立法實踐,筆者認為,社會權利的正當性可以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社會補償權旨在平衡社會共同體成員的利益正是作為基本權利的平等權衍生出來的正當性內容
平等權是一種具有豐富教義學內容的基本權利。在德國《基本法》規定的基本權利類型中,排位僅在人的尊嚴和自由權之后,具有重要的地位。雖然該法將平等界定為“法律面前的平等”(Gleich vor dem Gesetz),最初僅旨在抵御公權力對人們要求平等對待的權利的侵害,并僅指向法律適用的平等,但是聯邦憲法法院在多年的司法實踐中已將其拓展至參與權的平等,平等地獲得國家福利制度的給付,包括使用公共設施和政府財政等,“法律面前的平等”發展成了“法律背后的平等”。
政治(政策)的或自然的突發事件導致了某些社會成員的利益受到損害,而某些社會成員投身于公益事業使其他不特定多數成員獲利,如果將平等權拓展為結果的平等,且現有立法準許某些利益受損者提起補償請求權,那么平等權的理性主義內涵就要求與之處于相同境地的其他社會成員也當然享有此權利。同理,結果平等的原則也可以推導出,當大多數社會成員獲利時,也應當為利益受損者分攤負擔。由此與具體的社會福利制度相結合,平等權便蛻變成一種具體的社會權利請求權,社會補償權就此“呱呱落地”。前述原理可以作為構建戰爭受害人補償制度的法理依據,后者則是軍人優撫制度的法理淵源。當然,社會補償權的義務主體只能是社會共同體的代表——國家,因為只有在公共預算和財政支出的權力保障下,這項制度才能得到有效落實。〔23〕即便是在社會保障給付領域奉行自行政(Selbstveraltung)原則的德國,社會補償的承擔者(Tr?ger)也是擁有公權力的行政機關。Vgl. Hase, Soziales Entsch?digungsrecht, in: von Maydell/Ruland (Hrsg.), Sozialrechtshandbuch, Baden-Baden: Nomos, 2003, S. 1380 あ.
2.社會補償權指向的平衡產生于國家策動的作為或不作為的擔保義務
現代國家承擔著通過積極作為推進公共福祉之職能,那么未盡此職能時就負擔著平衡利益受損公民的義務,而國家積極策動的行為也可能為社會共同體成員招致利益的損害,所以也負擔著對不利后果的補償擔保義務。〔24〕Vgl. Eichenhofer, Sozialrech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3, Rz. 418あ.德國社會法學者Zacher 指出,由于社會保障項目類型化很容易引發對邊緣人群的忽略,并且可能與微觀社會的考量因素相互矛盾,所以社會國家原則還應當謀求一種“宏觀社會的延伸”。只是這種延伸是有限的,肆意擴大社會權利相當于賦予了社會國家原則無限的適用空間,國家財政必然不堪重負。聯邦憲法法院的意見是,平等原則是限定社會國家原則的重要工具,而平等的含義是肆意禁止(Willkurverbot),如果一項理智的、表明事物本身性質的或者以任何其他實質上顯而易見的理由都無法為這種差異找到存在借口時,那么這種不同等的待遇就是肆意的,此際國家權力就需要發揮作用。
若將這些理念應用到社會補償權領域,可以得到這樣的論證:國家負有創設和平、健康的環境和氛圍的“社會塑造”義務,在其未盡此義務時就需以財政手段對既有利益損失者施以補償。因平等原則是一種無法開脫之理由,故這種補償責任不應當附加條件,應以利益未受損者或未受損時的狀態為補償目標。社會補償權在產生的同時也被限制在了社會國家原則的合理范圍內,由此產生的對甲類傳染病感染者和疫苗接種受害者的補償制度,以及政治事件或國家政策間接受害者的補償制度,表明國家在負擔某些義務時,才產生未盡義務的平衡責任,如果社會共識未將某項義務作為國家平衡義務,那么即便出現了損害結果,也不會產生社會補償權,如地震等自然災害導致的流離失所不應當通過社會補償制度來解決,而應訴諸于相應的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制度。
3.社會補償權體現了國家對待社會保障事務的保守態度,因此具備正當性的補償實現的“平衡”必須存在參照物
在某種程度上,社會補償權沒有獨立的內容,這與其他社會保障權利有著本質區別,立法者設置社會補償的目的在于,在窮盡所有的社會保障給付后,比照現有社會成員的生活狀態,發現仍然存在難以“平衡”之處時,而采用的“兜底性”給付。當然,“兜底”并不等于給付水平“墊底”,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指出,生存權實現的是“讓人能過上人那樣的生活”,這就是“人的尊嚴”(Menschenwürde)的含義,而國家的義務在于“扶助生活貧困者和社會經濟上的弱者”過上“有尊嚴的生活”。〔25〕BVerfGE 30, 173 (194); 88, 203 (251 f.).對此,有學者指出,這種論證實際上是比較的結果,“尊嚴”應當理解為特定歷史時期和社會環境下的具體產物,不存在抽象的尊嚴標準。該水平應以社會共同體成員的一般水平和損失的機會成本利益來確定,也就是說,在這些情形下,社會醫療保險的待遇水平和利益受損者之前的生活和就業能力將發揮“參照物”的功能。〔26〕同前注〔15〕,Reinhard 文,S. 220。
4.社會補償權基于深化的“社會整體連帶責任”衍生,其平衡的利益只能產生于本國立法
一般性的社會保障權利(如社會保險權)產生于“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理念(亦稱“社會團結”),由于人們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形成了合作共濟,而基于共同的生存需要產生了相互服務的機制,這是一種初級的社會連帶,〔27〕參見[法]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敬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年版,第91 頁。其關注的是合作和服務的過程。隨著對風險社會認識的加深,人們愈加意識到作為結果的利益平衡同樣重要,社會成員需要為自己和他人謀幸福和減少痛苦,因為在連帶關系中,一個人的不幸會影響到他人,一個人的幸福也會使他人受惠,所以國家應當建立一套機制來平衡不幸與幸福的結果。〔28〕參見沈宗靈:《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版,第252 頁。
基于前述的國家保守態度,這套機制需要建立在狹義的立法上,當然,也不一定以法律特別明確規定為前提,在現有法律確定的框架下發展相關權利的實現機制亦無不可,下文所述的將“不真正工傷”制度拓展到居民即是在社會補償權正當性考量下提出的修法建議。
(三)社會補償權的功能
社會補償權的功能應當在作為實定法的憲法和社會法的層面上去解讀,憲法層面主要聚焦于該權利實現的平等權以及對社會國家原則的拓展,社會法層面則主要關注該權利與其他社會保障權利的分工與銜接。
1.實現作為基本權利的平等權
平等不僅僅指向過程,在接近基本權利核心保障內容時,其更加關注的是結果的平等。現代工業社會中引發身心健康損害的風險無處不在,多數都是個人無法預料且難以承受的,如突發疫情、政治事件與政策導向等,在已有國家立法對某個群體予以實物給付和服務給付(主要是醫療救治)的前提下,與之類似的群體遭受的損害也會因此而產生社會補償的效果。在此意義上言,社會補償權是一種由現有立法規定的補償權發展出來的新型權利,由于其實現的是作為基本權利的平等權,所以一般并不具備獨立的規范內容。
當然,在特殊情況下,社會補償權也要根據受侵害利益的特征做出一些變通性調整,如政治事件中恢復名譽、政策導致經濟利益受損時發放救濟金等,但是這些調整皆不具普遍意義,而且社會補償權的給付不能超越原權利,否則將會造成新的不平等與“逆向歧視”。〔29〕BVerfGE 12, 354(367).例如,因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失獨家庭”現象,是政策導致的客觀損害結果,若為這些家庭發放補助金,一般不能高于無子女家庭(即城鄉居民的“五保戶”)的待遇標準。
2.有限拓展社會國家原則
社會國家原則是國家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憲法依據。盡管德國《基本法》中的社會國家原則教義學內容匱乏,多以平等權來支撐,但是社會保障立法必須將該原則作為支撐,與公共利益立法及相關的高權行政區分開來。公共利益立法旨在增進整體福利,而社會國家原則旨在保障個人的自由和充分發展。〔30〕BVerfGE 33, 303(333).就此,社會補償權拓展了社會國家原則指向的社會權利,同時又與國家補償權相區別。
社會補償旨在補償國家未盡積極義務,或者無違法行為下造成的人身利益損失,這種損失具備“無因性”。一方面,損失是一種客觀結果,在多數情形下,國家呈現出不作為的態勢,即使作為,損失與國家行為之間也無直接的聯系;另一方面,不需要刻意對損失進行價值考量,尤其是不以實現公共利益為前提。〔31〕不可否認的是,某些社會補償權也基于權利人維護公共利益的前提而產生,如職工在搶險救災中受到的傷害,軍人優撫措施也可視為國家對軍人為實現公共利益而受到損失的一種補償,這里只是說社會補償權不需要刻意關注是否實現公共利益。就此,社會補償權區分于國家補償權,前者是社會法上的權利,踐行的是社會國家原則;后者是行政法上的權利,指向的是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目標,合法積極行使職權給公民造成的經濟損失。兩者產生的機理不同,故而補償的內容亦不同,社會補償多為實物給付(例外情況下為貨幣給付),國家補償多為貨幣給付或返還財產。〔32〕參見[日] 宇賀克也:《國家補償法》,肖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394 頁。此外,在我國很多文獻中,國家對土地征用的補償與社會補償混淆使用,〔33〕同前注〔6〕,王華華等文,第37 頁。這極易引發爭議,為了共同的學術話語體系,有必要作出明確的區分。〔34〕國家賠償權是基于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給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造成的損害產生的法律權利,與社會補償權產生的機理與功能有著明顯差異,我國各類文獻中一般也不會混淆國家賠償與社會補償,故不再贅述。
3.衡平生命權與健康權
生存和健康是維持正常生活的前提,但是這種權利的實現程度千差萬別,最低的生活保障可以實現生存和健康,優厚的生活保障可以保持良好的健康狀態。當社會國家原則被確立為憲法基本原則后,國家就作為了自然人基本生活權利保障的主體,社會立法不得不考慮將積極義務界定到何種程度才屬合理。〔35〕參見[日]菊池馨實:《社會保障法制的將來構想》,韓君玲譯,商務印書館2018 年版,第15 頁。
基于前述原因若將生存和健康提高到最低標準之上,實現有尊嚴的生存和健康,就必須將同一社會共同體、同一時期的公民群體的一般水平作為標桿,使因自然、社會事件承受不利益者恢復到這一標桿的水平,更確切地說,社會保障法律體系中需要設置一種權利類型,用于修復權利主體受損的健康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所有社會成員都能過上具有尊嚴的生活。為了實現這種衡平功能,社會補償制度應運而生。
4.填補傳統社會權利的漏洞
從傳統社會權利給付的前提條件看,社會保險制度以參保資格和繳費為給付前提,社會救助制度以現實需求為給付前提,社會福利雖然給付項目廣泛,但是以全部社會成員和特殊弱勢群體為給付主體。〔36〕參見尚曉援:《“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再認識》,載《中國社會科學》2001 年第3 期,第115 頁。在功能上,社會保險旨在預防風險,在風險產生時通過給付來保障個人生活水平不會急劇下降,因此設置社會保險權的目的是保障社會安全;社會救助旨在幫助個人擺脫困頓的生活狀況,因此設置社會救助權的目的是保障基本生存;社會福利旨在改善個人、家庭或社會群體內部的社會狀況,促進全體國民,尤其是弱勢群體共享發展成果,因此設置社會福利權的目的是實現機會平等。〔37〕Vgl. Zacher, Entwicklung einer dogmatik des Sozialrechts, in Abhandlung zum Sozialrecht II, 2008, Baden-Baden: Nomos, S.339.那么,當一些利益受損主體的社會權利仍然難以實現時,社會保障制度就需要增加一項新的功能,為了實現社會團結,有必要賦予受害者一項新的社會權利——社會補償權。
在自然變遷和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共同體對某項損失負有責任并且依據立法必須承擔責任的先期史(Vorgeschichte),〔38〕Vgl. Bogs, Grundfrage des Rechts der Sozialen Sicherheit und seiner Reform, 1955, S. 117.雖然不存在能夠明確歸責于國家共同體的原因,但是受害者的生命權和健康權被嚴重地侵犯,原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在這里出現了“失靈”。首先,損害系突發的人為或自然事件所致,無法呈現出“大數法則”的特征,難以通過保險機制來補償,此際社會保險權難以奏效。其次,受害者并非一定呈現出生活困頓的狀態,現實需求與受害者的自我保障能力有關,但是共同體享有征稅權,同時也就產生了為成員創設和平安定的生活環境的義務,未盡義務時產生的損害應由稅收支付,由于受害是一種客觀事實,所以權利主體的貧富狀況與自我保障能力不作為考量因素,此時社會救助權也無能為力。最后,先期史是“宏觀事件”〔39〕同前注〔37〕,Zacher 文,S. 339。,其造成的損害具有隨機性,一般不會危及全體社會成員,受害群體也未必是特殊弱勢群體,因為弱勢群體往往基于個體的微觀差異產生(如性別差異、生命差異、家庭狀況等),所以社會福利權也無法企及。如果將社會成員理解為一個共同體內無差別的主體的話,那么社會權利體系中即應當產生一種客觀補償的類型,當相關共同體成員受到立法中規定的特別犧牲,導致生存權和健康權受害結果時,國家財政就有義務補償這種損害。
三、社會補償權的規范構造
社會補償權系社會國家原則發展出來的具體的社會權利,基于平等的理念產生,因此應當在這兩個基本概念的框架中解讀該權利的規范構造。
(一)社會補償權的性質
社會補償權具有復雜的權利構造,表面上其呈現出積極權利的特征,實質上卻發揮了消極權利的功能,意在恢復至權利未受侵害時之狀態。
1.表面上的積極權利
社會補償權要求國家補償由自然、政治、政策原因導致的個人人身利益損害,系典型的要求國家給付的積極權利。與其他積極權利相比,產生社會補償的原因有三大特點:(1)原因的影響范圍廣,并不局限于一時一地,如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適用于全國;(2)即使產生于一地,但是擴散的速度快、范圍廣,如甲類傳染病、疫苗接種等;(3)某些侵害雖然表面上僅及于受害人個人,但是已經構成了刑事犯罪,而犯罪系“社會不斷進步導致的復雜化與個人自由發展下無法避免的結果”,于是遭受犯罪侵害之人成了“社會進步所衍生的副作用的影響者”,此副作用的影響范圍同樣廣泛,所以需要對“與未受侵害之社會成員相比較的特別犧牲者”予以補償。〔40〕趙義德:《檢舉人被害人及證人保護之研究》,載《司法研究年報》第19 輯,“司法院”秘書處1999 年版,第71 頁。相比之下,其他積極權利產生的原因只限于一方主體,如社會保險權僅為參保人享有、社會救助權僅為有生活需求者享有等。
社會補償權的內容是疾病和意外事故的救治,國家除了提供藥品和診療服務外,還需要在公共醫療衛生設施方面進行投入,與某些以貨幣給付為內容的社會保障權利,如養老保險權、失業保險權等相比,國家積極作為的程度更高。如果一國中各地區的醫療設施和醫療服務水平存在差異,那么即便社會補償制度的資金主要源于中央財政,該權利的實現程度也會存在地區性差異;對于例外情況下的貨幣給付而言,由于地區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水平存在差異,此法則同樣適用。也就是說,作為積極權利的定位,社會補償權雖然給付資金擁有基本統一的來源,但是無法保證實現全國統一的標準,這與典型的消極權利存在明顯差別(例如,國家對自由權的保障措施和保障水平在一國范圍內至少是統一的)。
2.實質上的消極權利
目前的憲法學通說認為,現代權利具有復合的性質,這一性質在社會法權利中表現得更甚,〔41〕參見陳云良:《健康權的規范構造》,載《中國法學》2019 年第5 期,第66 頁。雖然建構積極權利是現代福利社會的主要任務,但是積極權利往往產生于消極權利,〔42〕參見張翔:《基本權利的規范建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第38 頁。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甚至指出,設置基本權利的目的在于保障個人自由免受公權力的干擾,設置積極權利的核心目的是為了實現消極權利。〔43〕Vgl. BVerfGE7, 198あ.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至少是在目的論層面上,積極權利都體現為消極權利的實現工具。作為積極權利的社會補償權實質上也是服務于消極權利的實現,這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理解。
首先,社會補償權產生于形式意義上的平等權。如前所述,雖然社會補償權指向的待遇給付種類多樣,包括對軍人與戰爭受害者的優撫、大型傳染病與疫苗接種損害的診治、國家政策間接造成利益損害的補償、刑事犯罪受害人的補償等,但是從權利人的范圍與補償的內容看,平等權自始至終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一則,社會補償的權利人并非基于社會國家原則的積極拓展而產生。這個群體在原始狀態下都享有與其他社會群體相同的自由權、生命健康權等權利,只是因人為或自然事件的干擾,這種原始權利被剝奪或削減,這與狹義上的社會福利權不同:在作為社會保障子項目的社會福利制度中,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觀念的變遷,原本不享有福利權的人群也會被納入,比如近年來自閉癥患者也可以享有殘疾人福利。〔44〕參見韓君玲:《關于我國殘疾人福利法律制度構建之思考》,載《河北法學》2012 年第4 期,第97 頁。
二則,社會補償權的內容和標準是參照當前社會群體普遍的權利狀態確定的。社會補償的給付方式以實物給付為主,例外情況下可包括金錢給付,此二類給付的內容并非憑空產生,也不能超越現有社會成員平均的權利實現程度。比如,對大型疫情感染者和疫苗接種健康受損者的診治應當按照社會醫療保險的待遇標準來實施,蓋因社會保險的水平是與一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又如,軍人優撫制度中的就業安置以彌補服役期間喪失的就業機會成本為目標,故而應以當地的社會平均收入水平為參照標準,不可一味地追求所謂的“好單位”和“高待遇”。
上述兩方面的特征表明,社會補償權的實質還是實現平等權,而平等權本身并不是一項積極權利,只是“其他實體權利在形式上的應有屬性”,〔45〕Stern, Staatsrecht III/2, München: C. H. Beck, 2006, S. 1828f, 1839f.因此社會補償權的實質也是一項消極權利,這是該權利與其他社會保障權最大的區別,因為后者幾乎都是立法創設的積極權利,在權利主體與待遇給付方面沒有比照的對象。
其次,社會補償權的目標是恢復作為消極權利的原權利。社會補償權利人只能請求國家恢復原本的權利狀態,人為或自然事件發生之前的個人情況是補償目標重要的參照標準,由此,前述“當前社會群體普遍的權利狀態”應當被修正為權利人個體狀態為上限的“普遍狀態”,因為普遍狀態可能優于個人狀態,如果要求補償達到社會普遍狀態,就會出現權利人“因禍得福”的可能性,這將是不公正的,也容易產生道德風險。比如,重大疫情感染者不能要求提供感染病毒加重的原有慢性病的治療,相關費用可由社會保險或商業保險負擔,社會補償制度只能提供治愈病毒直接造成的器官組織的損傷。又如,退伍軍人只能要求與自身學歷和能力相適應的工作安置,應當避免20 世紀80 年代大量復轉軍人進法院,不能適應法官職業化和專業化的現象。〔46〕參見賀衛方:《復轉軍人進法院》,載《南方周末》1998 年1 月2 日“人與法”專欄。當然,參軍入伍導致的就業機會成本損失程度只能以具備相同資質社會群體的就業狀態作為參照標準,因為權利人個人的職業發展狀況無法假設,純粹的積極就業損失也就無法作為退伍安置的目標。
就此,社會補償權可以界定為以積極的國家給付措施實現的,以權利人在人為或自然事件發生之前的個人權利狀況為上限的,以社會群體的普遍狀態為參照物的社會保障權。
(二)權利主體與義務主體
1.權利主體
我國《憲法》將社會保障權利界定為“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所以具有我國國籍并依法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公民是所有社會保障權的主體。當然,社會保障制度保障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是全人類共同擁有的權利,出于人道主義的考慮,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我國不應當把外國人排除在這兩類權利指向的社保項目之外。這方面的實例一是在我國與其他國家簽署的社保免除協定中,在華務工的外國人一般都免除在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中參保的義務,但是基本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是不能免除的,主要原因就是各險種保障的基本權利類型不同;〔47〕參見婁宇:《平臺經濟從業者社會保險法律制度的構建》,載《法學研究》2020 年第2 期,第201 頁。另一是社會救助中的臨時救助項目也會向外籍人士開放,如《杭州市城鄉居民臨時救助辦法》規定,持有效護照居住在杭州市且困難發生在本市的外籍人員也可以申領臨時救助。
社會補償制度旨在補償社會共同體成員因影響范圍廣泛的人為或自然事件造成的利益損害,公民似乎是毫無爭議的社會共同體成員,一般都理所應當地視為社會補償權的主體,那么,對居住在外國的中國公民于所在國發生的意外事件造成的損害,是否也能申領社會補償待遇?居住在中國的外籍人士因在中國發生的意外事件造成的損害,是否能基于人道主義和基本權利保障的考量申領社會補償?回答這兩個問題取決于社會共同體的范圍界定以及社會補償制度的資金來源:(1)社會共同體首先應當局限于一國范圍之內,發生在國外的意外事件是難以預料和控制的,一國無義務亦無能力去掌控他國的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因此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應當是否定的;(2)社會共同體系社會中存在的、基于主觀和客觀上的共同特征而組成的團體,社會公眾的價值觀念至少是決定因素之一,而法律則是這個因素的集中反映,〔48〕See Taekema & van de Burg, Towards a Fruitful Cooperation Between Legal Philosophie, Legal Sociology and Doctrinal Research: How Legal Interactionism May Bridge Unproductive Oppositions,in Nobles & Schiff (ed.), Law, Society and Community, Ashgate, 2014, p. 129-130.因此非法居留滯留的外國人應當被排除在社會共同體成員的范圍之外,至于是否應當出于人道主義的考慮,在緊急情況下給予他們臨時救助,則是另外一個問題;(3)社會補償制度的資金來源于國家財政預算,而稅收是財政資金的主要來源,因此納稅人獲得社會補償待遇給付實質上是納稅義務的一項對價權利,按照權利義務一致的基本法律原則,具有合法身份的外籍納稅人也應當作為社會補償制度的權利主體。綜上,一國的社會共同體成員(主要是公民)與法律認可的外籍納稅人系社會補償權的權利主體。
值得反思的是,在去年年初的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表示,北京等地有關防控規定適用于來自或去過境外疫情嚴重地區的所有入境人員,對中國公民和外國公民一視同仁。〔49〕參見《中方:防控規定對中國公民和外國公民完全一視同仁》,載中新網,http://www.chinanewS. com/gn/2020/02-28/9107987.shtml。由國家財政支付相關診療費用的制度是社會補償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從外交部的發言看,確實沒有明確外國人在中國確診病例的治療費用屬于自費還是由我國政府負擔,但是“一視同仁”的用詞似乎意味著全部免費治療。筆者認為,為所有在華或來華的外籍人士免費提供診斷和治療展現了中國的大國風范和人道主義考量,但并不妥適,應當將人群范圍限定于中國公民與法律認可的外籍納稅人。當然,為了控制疫情傳播,除了嚴守國門、限制無關的外國人來華外,也應當為臨時來華的外籍人士提供必要的隔離和診治措施,由此產生的相關費用應當知會外國在華代表機構,由外籍人士自行負擔或者其國家(政府)按照該國法律規定的方式承擔。同理,作為刑事犯罪受害者的外籍人士及在搶險救災中受傷的外籍人士原則上也不能請求社會補償,除非他們系受害地所在國的合法納稅人,否則相應的生命與健康損失只能要求民事侵權賠償。
2.義務主體
我國《憲法》將社會保障權利對應的義務主體確定為國家和社會,那么作為國家代表的政府有關部門和作為社會代表的集體經濟組織、人民團體、群眾自治組織皆涵攝其中,〔50〕參見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注解與配套》(第2 版),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97 頁。但就社會補償權而言,只有國家才是社會補償權的義務主體,因為只有國家才負有為共同體成員提供和平安定的生活環境與生活條件的義務。
一方面,在行政執法層面,人們為了結束自然狀態下的混亂與無序,將自己的權利讓渡給了政治國家,與之達成“社會契約”,只有國家才可以合法動用公權力(主要是征稅權與預算權)去開展“社會塑造”,在未達到此目標時,承擔責任的主體也只能是國家;另一方面,在司法層面,人們放棄了自然狀態下防衛的權利,而國家獨占了懲戒違法犯罪行為的權力,隨著社會秩序的規范化,犯罪突破了侵害個體利益的范圍,演化成了對制度、體制、秩序的侵犯,于是犯罪人與受害人的力量均衡被嚴重打破,國家在懲戒犯罪的同時,也負有恢復被侵犯的利益的義務。換言之,國家基于社會共同體的連帶責任而給付,在實質上實現社會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利益平衡,而社會組織無法合法擁有這些權力,也就不負有補償之義務。
實現社會補償權需要財政資金的支持。在我國,某些社會保障支出由中央財政負擔,如養老保險建立中央調劑金制度,主要考慮的是勞動力在全國范圍內流動,地區分割的格局會造成地區之間不合理的博弈,而某些社會保障支出由地方財政負擔,如社會救助資金等,主要考慮的是生活需求的標準和生活方式存在較大的地區間差異,統一的中央規劃不利于進行精準的待遇發放。那么問題來了:社會補償權的義務主體究竟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綜合考慮意外事件的性質與補償的方式。
社會補償指向的人為和自然事件具有影響人群與地域范圍廣和侵害利益的層級高的特征,因此,補償的主體應當是中央財政,而非地方財政。以2020 年年初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救治為例,由于人口流動不利于疫情防控,異地就醫的患者一般都會被要求在病情查出地就醫,這在實質上起到了抑制疫情擴散的作用,最終受益的將是全國所有地區的公民(不僅是參保地的公民,返回參保地沿途及乘坐同列交通工具的公民都將獲益),獲益主體呈現出公共物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即不影響和排斥他人享有),單單指定某一地區的政府承擔財政責任并不合理,最恰當的補償義務主體應當是中央政府。〔51〕參見婁宇:《對新型冠狀病毒防控中的醫保責任與財政責任的思考》,載中國醫療網2020 年2 月26 日,http://med.china.com.cn/content/pid/161933/tid/1026/iswap/1。類似的理由還體現在政治事件造成的社會成員利益損害、疫苗接種造成的損害、搶險救災等維護公共利益的活動中造成的損害等社會補償類型中。刑事犯罪侵犯的法益層級高,因犯罪的認定標準、預防措施與刑事程序在一國范圍內具有統一性,故由中央財政資金補償受害人損失合乎情理。
需指出的是,慮及地域差異和屬地管理之需,某些社會補償項目也可以由地方財政適度分擔,用以作為中央財政責任的有益補充。這主要表現在生活補助性質的補償項目中,如我國的軍人退伍補助金、失獨家庭扶助金等由中央、省級和地市級財政共同負擔,中央財政負擔最高的份額。
(三)權利的內容
1.實物給付
如前所述,社會補償的對象是政治事件或自然事件損害的社會共同體成員的生命權與健康權,提供恰當的物品與服務有利于恢復或彌補受損的權利,因此實物給付是社會補償權的基本內容。而為了避免權利人不合目的地使用補償資金,以及為了獲得補償故意欺詐或額外獲利的道德風險,原則上應避免采用貨幣給付的方式。補償的實物通常表現為與滿足生活需要和保健需要的物品和服務,這就與社會保險中的基本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及社會救助的給付內容發生了重合,此際我們需要解決下面兩個問題。
第一,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補償三類項目給付的標準如何確定?
社會救助滿足的是社會成員最低的生活需要,給付水平按照所在地居民生活必需的費用確定,具有客觀的標準,如市場菜籃子法、恩格爾系數法、馬丁法等,一般由滿足人體最低熱量的支出為基礎,將支出轉化為食品,再加上非食品必需品的支出,如住房、取暖等,社會救助在健康權保障方面多體現為臨時救助,即以控制突發的急性病情為標準。社會保險的給付水平按照“以收定支”的原則確定,參保人數、繳費基數、繳費率、政府補貼的份額等因素確定后,實際的基金收入決定了給付的水平,這個水平沒有統一標準,與一國的社保立法理念、傳統、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水平密切關聯,〔52〕參見婁宇:《論作為社會保險法基本原則的“精算平衡”與“預算平衡”》,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8 年第5 期,第180 頁。體現了社會共同體成員平均的生活水平,因此必然高于該國社會救助的標準,在一般的健康權保障方面,即使領取社會救助者也往往被要求加入社會醫療保險,享受與普通參保人同樣的醫療保障待遇,所需資金由各級財政補貼。〔53〕例如,我國各地出臺的“新農合”地方法規和規章中都將農村“五保戶”“低保戶”、在縣為單位的扶貧機制中識別和登記的貧困人群、殘疾人、“獨生子女戶”“雙女戶”中的一種或幾種人群作為免繳費的參保人,參合資金由各級民政部門負擔。社會補償的目的是恢復因政治和社會事件損害的生命和健康權利,原則上也無確定水平的客觀標準,但在實物給付方面,當以恢復社會共同體成員一般的健康水平為標準,以社會醫療保險的待遇為參照。
第二,當三類項目發生重合時,應由哪一類給付?
在人為的、自然的突發事件中,社會成員可能同時滿足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補償三類項目給付的條件,此時三種權利的實現需要設計合理的位階關系。
首先,社會救助的最低標準已經被社會保險所涵蓋,除了在極端特殊的情形下,如自然災害中無法保障正常的醫療條件,需要提供臨時應急的措施外,沒有必要再啟動社會救助的申領程序。
其次,在社會補償項目中,當社會保險權與社會補償權發生重合時,可由社會保險先行支付,而后由社保基金向國家財政行使代位求償權。此次新冠疫情中,中央和各級醫保部門臨時擴大了醫保基金的支付范圍,采取了先救治后結算、提前預撥總額基金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緩解了罹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的燃眉之急,化解了各級醫療機構收治患者的后顧之憂。但是,新冠疫情與巨災相差無異(依據《傳染病防治法》,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按照最高等級的甲類傳染病防控),覆蓋面廣,人均醫療費用高,保險的風險分散機制基本是失靈的,慮及社保基金貫徹“以收定支”原則,大型傳染病的診療費用又難以作為精算考慮的支出范圍,本預算年度的基本醫保基金可能會因此吃緊,〔54〕同前注〔52〕,婁宇文,第182 頁。然而,社會補償資金來源于國家財政,如此大規模的應急救助費用也難以提前納入政府預算,考慮到醫保基金支付的現實性,可由其先行支付,而后納入下一年度的中央財政預算中,用以彌補基金缺口。此一做法契合我國《社會保險法》第30 條規定的醫保先行支付的法律框架,可視為學者所主張的“妥善解決社會保障制度穩定性與靈活性”的一種解決方案。〔55〕《疫情大考,社會保障效果如何?專訪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載《南方都市報》2020 年4 月15 日“國內版”。
最后,在自然災害和特別政治事件中,社會救助權和社會補償權可能發生重合,如第一部分中列舉的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異地安置、就業援助措施涉及的社會保障權利。按照前述的社會補償權優先拓展社會國家原則和填補傳統社會權利漏洞的兩項功能,社會補償的措施不能無限擴展政府的財政支出,并且當存在其他傳統社會權利時,應當優先行使傳統權利,恢復重建是一個大型的、系統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涉及的權利類型復雜多樣,需要龐大的財政支出,已經遠遠超出了社會權利的范疇;而安置和援助措施有可能是臨時性的,此時實現的是社會救助權,無需啟動社會補償權的申領程序,也有可能是較長期性的,此時實現的是社會福利權,也不涉及社會補償權。
2.貨幣給付
人為事件或自然事件可能打亂社會共同體原本的生活和工作計劃,改變人生軌跡,由此產生經濟學意義上的機會成本損失,因此在例外情況下,社會補償權的內容也體現為貨幣化的補助。〔56〕德國社會法學者Eichenhofer 持偏離性意見,認為社會補償的目的主要在填補“個人的損害”(Personensch?den),而非“財產的損害”(Verm?genssch?den),但是,德國軍人撫恤法中也存在服役補助金制度,在搶險救災中為實現公共利益(?あentliches Interesse)而受害者也可領取務工補助,因此采用實物給付為原則,貨幣給付為補充的方式更為符合社會補償實踐。同前注〔24〕,Eichenhofer書,Rz.416あ.只是發放此類補助應當遵循三個基本原則:(1)應當存在機會成本損失的參照對象,社會成員普遍的損失不能以貨幣的方式補償。例如,前述的汶川地震案例中的恢復重建費用和就業安置費用就不應當由社會補償項目發放貨幣化補助,因為地震影響區域內所有成員都有財產損失與就業損失,無法確定補償的參照對象。事實上,所有突發事件類的社會補償項目中都不應當包含貨幣給付,因為此類事件造成的機會成本損失在所在區域內是一種普遍現象。(2)相關權利人機會成本的損失對應了其他人群的受益,產生了社會補償的合理性。參軍入伍者損失了正常工作的機會,卻換來了社會的和平安定,所有社會共同體成員都將獲益,因此應由全體成員共同負擔軍人群體的就業成本損失。相反地,公民在戰爭或政治事件中受害是一個客觀事件,不會產生增益的社會效果,因此相關受害人群不能申領貨幣補助(社會補償制度不向刑事犯罪受害人發放貨幣補助同理)。(3)應當以機會成本的損失額度為考量依據,采用屬地化和個性化的確定方法。例如,在軍人優撫制度中,應當以為復員軍人安置工作為主要補償方式,即使發放貨幣化的退伍補助,也應當以補償入伍期間的工資機會成本損失為主要參考依據,如退伍安置地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可盲目追求高待遇,防止社會補償演變成社會福利,同時也不適宜對來自同一地區的所有義務兵都執行同樣的標準,入伍前的個人情況也應當作為補助標準確定的因素。〔57〕我國《軍人撫恤優待條例》第3 條將“撫恤優待標準與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確定為基本原則,保障撫恤優待對象的生活不低于當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但是,入伍服役之前的學歷、工作狀態并沒有作為考慮的因素,未來修法時應當考慮這一點。當然,軍人優撫制度是一個包含了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補償等多種項目的綜合性社會保障制度,其中社會補償與社會福利的邊界有待進一步框定。又如,失獨家庭可認定為國家政策導致的生存利益間接損害,扶助金應當以必要及家庭收入狀況為依據,同時以精神慰藉為主要目標,生活困難的失獨家庭滿足城鎮“三無人員”或農村“五保戶”條件的,可以申領社會救助性質的供養待遇。
四、我國社會補償權的規范領域
作為一項法律制度,社會補償應當存在權利的規范領域,才能產生權責義的內容,進而當義務主體違反客觀法秩序時,權利人可以請求司法的保護,而綜觀前述國家和地區的立法例,社會補償權的規范領域雖然大致框架類似,但是具體表現并不相同,即便在德國,社會補償也是唯一未規定在《社會法典》中的社會保障制度,且受到最嚴格的單行法立法限制。〔58〕同前注〔15〕,Reinhard 文,S. 220。德國社會法學者將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歸結為社會補償是一個不足以成型的、開放性的領域,雖然其產生于實現公共利益的特殊犧牲(Aufopferung),但是在現代社會中,人民基于義務而“被迫”做出公益犧牲的情形已經不能涵蓋所有的社會補償類型,“自愿”乃至客觀上為社會整體利益做出犧牲者也有必要納入補償的范圍,所以很難在法理上總結出一般性的概括條款,只能依據個案的共同特征(Fallgruppe)來探究。〔59〕同前注〔22〕,Rüfner 書,S. 122。
結合“社會平衡”的一般性法理以及現實國情和立法,筆者認為,我國的社會補償權應當存在于以下六個領域。
1.軍人及家屬優撫權
我國的軍人優撫制度包括對軍人(包括現役與退役的義務兵、志愿兵、軍官)及其家屬的優待和撫恤,相關群體享有的權利按照社會補償權的規范構造設計安排。我國傳統社會法理論認為,軍人的社會保障針對軍人群體的職業特點設置,內容多元化,每個項目還可以再細分為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但是軍人保障有著自身的特點,似乎又不能完全歸于一般的社會保障項目,〔60〕參見鄭尚元、李海明、扈春海:《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588 頁。而這種特點是什么,現有文獻鮮見分析。基于本文對該補償權制度的正當性剖析可知,軍人優撫權源于維護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給軍人群體造成的利益損害,所有獲益的成員都有義務平衡這種損害結果,由于“國防公共安全產品”惠及全民,因此相關開支主要部分由中央財政負擔;同時也可得知,軍人優撫權的本質是社會補償權,只要達到平衡的效果,即實現平等權即可,過度的待遇給付將使軍人優撫演變成軍人福利,當然,這也不是不被允許的,只是需要通過社會福利權的法理去論證。例如,我國《軍人撫恤優待條例》規定,現役軍人憑有效證件乘坐市內公共汽車、電車和軌道交通工具享受優待,殘疾軍人憑有效證件免費乘坐市內公共汽車、電車和軌道交通工具,這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平衡服役導致的損害結果的范疇,需要論證該立法的合理性。〔61〕囿于篇幅,本文在此不探討該立法作為社會補償權實現方式的合理性,只是拋出問題作為例證。
德國和我國臺灣地區都建立了戰爭及軍事勤務事件對平民造成損害的補償制度。〔62〕參見鐘秉正:《從社會補償法理看藥害救濟——兼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零四年度訴更二字第三十號判決》,載《月旦法學雜志》2017 年第6 期,第219-233 頁。除了立法沿革史(德國的戰爭受害者補償是較早的社會補償制度)、制度移植(如臺灣地區的相關立法)等方面的考慮外,一國政府和社會公眾對戰爭危害性的認識也是重要的決定因素,如德國社會法理論即認為,國家負有保障和平環境的義務,對生命權和健康權的損害是戰爭極為負面的因素,需要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反思和撫平,因此德國“二戰”后的立法很自然地將此項社會補償權寫入了立法,〔63〕同前注〔12〕,Stolleis 書,S. 180あ.我國臺灣地區對“二二八”事件的定性也是建立軍事勤務事件損害補償制度的緣起。亞洲各國在這個問題上幾乎全部聚焦于對日本政府侵略戰爭的索賠上,并未建立起一個常態化的戰爭補償制度,這大概與“二戰”后整體的和平環境與本國政府沒有發起過戰爭有關。有鑒于我國立法沒有建立這一制度,社會補償權也就不存在這一規范領域。
2.國家政策間接利益損失補償權
國家政策僅在一國內實施,因此造成的利益損害也僅局限于一國范圍內,應當說,任何政策都是對現有社會格局的重新調整,必然會有獲益者與損益者。各國對國家政策的性質定位不同,因此是否補償以及采取何種形式和標準補償損益者亦無統一的立法例。筆者認為,我國對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失獨家庭的補償可以歸于這一規范領域,計劃生育政策系中央政府實施的基本國策,為我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64〕參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計劃生育白皮書》,載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0908/224683.html。因此全民都是這一國策的受益者,但是因獨生子女死亡給相關家庭成員帶來的老年生活困難不得不視為該政策造成的間接利益損失,按照相關機構的樣本分析,我國15 歲至30 歲的獨生子女總人數約有1.9 億人,這一年齡段的年死亡率為萬分之四,照此計算每年約產生7.6 萬個失獨家庭,目前的失獨家庭已超百萬,〔65〕參見《政協委員:特別扶助金標準應逐年提高》,載人民網,http://politicS. people.com.cn/n/2014/0311/c70731-24604561.html。所以為這一群體建立合理的社會補償法律制度應提上日程。
按照衛計委等部委聯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我國失獨家庭主要的補償方式是發放特別補助金、醫療保險繳費補貼、醫療救助費用等,以貨幣給付為主。按照社會補償權的基本法理,補償以平衡利益受損成員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為主要目的,未來還應當考慮將養老服務和家政服務等家庭幫扶性措施作為給付內容。
前述的獨生子女護理假制度也是這一規范領域熱議的問題,獨生子女職工無暇照管父母當然可以視為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間接利益損害,但是其法理探討的進路應當區別于失獨家庭,計劃生育政策的受益者包括國家和社會,同樣也包括獨生子女家庭,這一類家庭在子女尚幼時負擔輕,相較于多子女家庭,生活條件往往更優越,因此不能簡單地將此類家庭的成員認定為純粹的損益者。因此,獨生子女護理假應更接近于一項社會福利制度,可以鼓勵有條件的企業自行開展,但不宜作為立法強制建立的社會補償制度。
3.不真正的工傷補償權
我國《工傷保險條例》第15 條第(二)項規定,職工在搶險救災等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動中受到傷害的視同工傷。工傷系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傷害,上述情形不滿足工傷認定的要件,因此在法律性質上不是工傷,可以稱為“不真正的工傷”。〔66〕參見李海明:《依“48 小時條款”之病亡的工傷定性》,載《法學》2016 年第10 期,第19 頁。工傷保險費率按照同行業的工作風險確定,實行浮動費率,因此搶險救災時受到的傷害無法作為基金收支精算的要素,相關費用只能依靠財政補貼解決。就法律性質而言,此不真正的工傷補償實為社會補償的一種類型,解決的是為了維護公益搶險救災的受害社會成員與客觀受益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
值得探討的是,為公益而犧牲私益者不僅有職工,未參保工傷保險的城鄉居民亦有之,從社會補償權的一般法理出發,未來也應當為這些群體建立社會補償法律制度,提倡與鼓勵所有成員維護社會共同體利益的行為。
4.甲類傳染病健康受損補償權
我國《傳染病防治法》 依據致病性、傳染速度、波及范圍等因素,將傳染病分為甲、乙、丙三個等級,衛健委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作為乙類傳染病,但是按照最高等級的甲類傳染病進行預防和控制。有鑒于甲類傳染病暴發的可預測性低、防控費用和治療費用高、波及人群范圍廣等特點,社會醫療保險制度難以抵御,應當建立專門的法律制度,作為社會補償權的規范領域。
此外,慮及中央財政預算也不便于納入此類預測難、支出高的突發疫情診療費用,而我國的基本醫療保險基金規模大,年度支出的壓力小,可以適用《社會保險法》確定的基金先行支付和向中央財政代位求償制度,這是本文前述的“無特別法律規定,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發展新的社會補償權與實施機制”原則的一項具體應用。
在正當性基礎上,甲類傳染病健康受損的補償權與前述的三項權利有共性也有差異,共性在于權利都基于平等權產生,因此補償都以權利未受損害的社會成員的一般狀態為標準,差異在于前述三項受損的權利內容不局限于生命和健康,也可能涉及就業、升學、居家生活能力等,這大概與國防、國家政策和維護公共利益造成的間接損害存在于較長的時期內,而傳染病等造成的損害持續的時間較短有關,因此前三者補償的內容也就需要相應拓展到相關領域的優待服務,甚至發放貨幣補助,而傳染病的補償僅限于診斷和治療及疫苗接種。〔67〕2020 年12 月31 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疫苗研發專班負責人曾益新表示,新冠病毒疫苗將為全民免費提供,理由是疫苗是公共產品,這也印證了本文所持的防控和診療甲類傳染病屬于社會補償制度的觀點。參見《衛健委:新冠疫苗為全民免費提供 已獲批上市屬于公共產品》,載和訊網,http://tech.hexun.com/2020-12-31/202737984.html。基于同樣的正當性考量,與本項補償權制度相似的領域還包括以下的疫苗接種健康受損補償權、犯罪受害人補償權兩類。
5.疫苗接種健康受損補償權
疫苗是滅活或者降低毒性的病毒,百萬分之一二的異常反應率導致了每年1000 余例的接種兒童終身殘疾,甚至死亡,對已發生的損害進行救濟的方式主要包括民事賠償和國家無過錯補償。按照《預防接種異常反應鑒定辦法》《全國疑似預防接種異常反應監測方案》等行政法規規定,既非因疫苗生產與流通環節的問題,又非因疫苗接種不規范引起的異常反應,受害人可以請求一定的無過錯補償,以此區別于民事賠償,由此應對和分散由免疫學知識有限而帶來的技術風險。〔68〕我國將疫苗分為兩類,一類是國家納入免疫規劃,免費向公民提供的疫苗,二類是自愿且自費接種的疫苗。國家無過錯補償計劃只針對一類疫苗,疫苗生產企業負擔二類疫苗的異常反應損害賠償。此處的國家補償實質上就是本文所言的社會補償。
回應前述長春長生疫苗案例中提出的問題,首先,社會保險待遇是對參保人群體繳費的對價給付,肯定應當排除在外;其次,社會補償權的功能是恢復健康狀態,因此國家財政補償應當以平衡受害者與一般社會成員的利益為目標,而民事賠償的目的在于恢復受害者原有的生活狀態,前者以基本醫療保險反映的社會成員的一般健康狀態為依據,以基本醫療保險范圍內的診療為主要內容,后者則包含了更多的內容,如康復費、護理費、誤工費、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等,因此二者在醫療服務和藥品提供方面可能發生重合。為了避免受害人額外獲利,應當避免雙賠,為了防止疫苗企業不當免責,應當首先訴之于民事賠償。當然,為了保障受害者能夠獲得及時的救治,可以建立國家先行補償而后代位求償的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疫苗質量監管部門是維護疫苗安全的責任主體,國務院、省級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分別負責全國和各省的疫苗流通和質量監管,相應地,國家財政預算和省級財政預算應當是這類補償計劃的資金來源。
6.犯罪受害人補償權
犯罪受害人的國家補償是世界各國普遍建立的一項社會保障制度,多年來的實踐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法理通說:國家壟斷了懲罰犯罪的公權力,因此負擔預防和制止犯罪的義務,犯罪是未盡此義務時發生(于國家而言)的客觀結果,所以國家負有補償損害結果的責任。〔69〕參見程滔:《刑事被害人的權利及其救濟》,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79 頁。此觀點亦可視為受害人補償權的正當性基礎,即在現代社會,國家擴大了對公民生存保障的職能,對不積極作為(有時甚至是沒盡到積極預防義務)時對受害者履行的一項利益補償責任。因此,與疫苗質量責任相類似,犯罪受害人也享有民事賠償請求權與社會補償請求權,按照相同的法理進行制度安排,當受害人無法從罪犯或其他來源得到充分補償時,可以要求社會補償。
近年來,我國很多刑事訴訟法學者都主張,在目前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下,我國構建相關的補償制度具備必要性和一定的可行性,〔70〕參見孫謙:《構建我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之思考》,載《法學研究》2007 年第2 期,第53-62 頁;孫寶民、李環宇:《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立法構想》,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9 年第1 期,第99-103 頁;等等。但是,西方國家建立的全面的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并不適合我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才是最好的選擇。〔71〕參見李海瀅:《我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來走向——以國家刑事賠償、國家刑事補償與刑事被害人救助關系辨析為進路》,載《齊魯學刊》2012 年第2 期,第88-93 頁。雖然刑事法學界采用了“國家補償”“救助”等術語,但是其論證的該項補償權制度并非行政法意義上的國家補償和社會法意義上的社會救助,因為前者的正當性基礎是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權衡下犧牲個人利益所做的補償,利益損害系國家積極作為所致,以經濟損害為主要表現形式,因此補償也以貨幣補償為主;后者的正當性基礎是現代福利國家對個人的生存照顧,公民依靠個人能力在長期或者短期內無法過上最低標準的生活,因此需要求助于國家的長期或者臨時的給付,救助以提供生活物資為主,此二者與社會補償有著本質區別,由此決定了各自的制度安排也必然有所差異。
綜合來看,我國確有必要在社會法的話語體系中重新建立犯罪受害人補償權制度。未來的相關補償權制度應當作為犯罪人民事侵權賠償制度的補充,在犯罪行為造成受害人健康權損害時,實施國家財政先行給付和向犯罪人代位求償救治費用的機制,此項社會補償以醫療救治為主,而由于對生命權和健康權的訴求沒有人群的差異,所以不應當區分受害人的財產狀況和經濟承受能力,而給予與社會醫療保險待遇相仿的給付。
五、結語
社會補償權具有規范的權利構造與應用領域,可在法理層面上解讀其正當性依據與功能,進而確定其法律性質、權利主體、義務主體以及給付內容,最終總結和歸納我國立法規定的規范領域。探究社會補償權法理的價值不僅在于解釋和適用現有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更在于發現現有制度的不足和彼此之間的矛盾,為相關領域的立法和司法提供對策建議。當然,通過統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來節約學術研究資源,為社會保障理論界和實務界創建共同的話語體系亦符合本文的寫作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