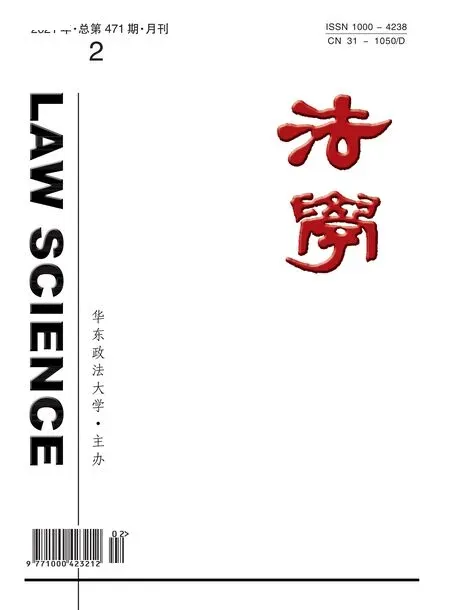勞動關系從屬性認定標準的理論解釋與體系構成
肖 竹
一、問題的提出
雇傭(勞動)關系〔1〕文中對“雇傭關系”一詞的理解和使用需特別說明。在許多國家,雇傭關系(employment relationship)以雇主的“控制”或雇員的“從屬性”為標志,但在一些國家,雇傭關系還包括具有平等性的自治勞動,例如法國法下“雇傭”還包括“包工與承攬”、德國的雇傭合同還包括“獨立”“自主”的雇傭合同。由于雇傭關系在我國立法和學理上并未有明確和一致的界定與理解,因此當本文以“雇傭(勞動)關系”形式使用時,意指與勞動關系同質之雇傭關系。從屬性,是勞動法產生、發展、適用的原點性問題。我國勞動立法對勞動關系成立與認定并未規定明確標準,實踐中以《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勞社部發〔2005〕12 號)作為司法裁量依據,但寥寥數條規定,內在缺乏學術機理,外在缺乏具體適用要素與解釋,使司法者同時面臨依據不明與依據過寬的困境,導致司法實踐異樣頻發,法官釋法造法缺乏約束與預期。而在理論研究上,學界基本承繼大陸法系勞動關系從屬性理論,體系上以人格、經濟、組織從屬性為其展開,〔2〕參見[德]曼弗雷德·魏斯、馬琳·施密特:《德國勞動法與勞資關系》,倪斐譯,商務印書館2012 年版,第41-43 頁;田思路、賈秀芬:《日本勞動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50-51 頁;黃程貫:《勞動法》,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版,第A3-A22 頁。但總體上看,研究仍屬籠統,無論是比較法研究還是案例闡釋,各判斷要素多呈現堆積性、羅列性的研究形態,各從屬性概念映射的內涵不明,三者之間缺乏體系化關聯與邏輯延伸的學理解釋,各自內轄要素不作具象化區分與闡釋,對司法實踐的指引性作用較弱。更為重要的是,“三新”(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背景下的用工實踐已然觸動勞動關系從屬性的根本邏輯,而從擁有成熟理論積累與司法適用的國家(地區)經驗看,在勞動關系的認定上“不存在適用于所有行業和崗位的判斷標準,需在具體個案中綜合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判斷做出總體評價”,〔3〕王倩:《德國法中勞動關系的認定》,載《暨南學報》2017 年第6 期,第42-43 頁。“需考量不同行業和工種的差異,靈活地決定哪些因素將占較多的權重”,〔4〕Ryuichi Yamakawa,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Employee/ Independent Contractor Distinction Under Japanese Labor Law, Comparative Labor Law & Policy Journal, Vol. 21, Issue 1, 1999, p.123-124.而晚近對從屬性的解釋亦以綜合判斷說為主流。〔5〕參見邱駿彥:《勞動基準法上勞工之定義——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986 年度訴字第5026 號判決評釋》,載臺灣勞動法學會編:《勞動法裁判選輯(二)》,元照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98-100頁;楊通軒:《勞動者的概念與勞動法》,載《中原財經法學》 2001年第6期,第277-279 頁;林更盛:《勞動契約之特征[從屬性]——評“最高法院”1992 年臺上字第347 號判決》,載《臺灣本土法學雜志》2002 年第36 期,第76-79 頁。既然如此,應對錯綜復雜的實踐作出綜合性、個案性、權衡性與靈活性之考量,是否意味著從屬性認定標準的體系化構建,及其下轄各要素的權重分析注定是一場屠龍之術呢?
從法學研究的一般范式而言,勞動關系從屬性認定標準的體系化研究不能被直接逾越以致被忽略。“體系的意義在于,其一旦大功告成,就成為一個具備自我發展與再生能力的活體。它不僅保障法律適用完全奉行形式主義與普遍主義,還具有使司法者‘作繭自縛’的功能。”〔6〕謝鴻飛:《民法典與特別民法關系的建構》,載《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2 期,第102 頁。勞動關系從屬性的認定標準需在理論解釋的基礎上,在相互關聯的意義整體下研究“人格”“經濟”“組織”從屬性的體系構成,才有可能對各從屬性的內涵界定,及其對勞動關系認定的意義進行通盤考量,避免因研究對象本身的界定不清而自說自話;才有可能對被缺乏邏輯意義的、各自羅列的微觀判斷要素進行學術上的機理性探討,為司法者的案件甄別與判決展開提供要素選擇與權重賦予上的指引。
二、從屬性作為雇傭(勞動)關系認定標準的理論解釋與現實挑戰
傳統勞動關系的建構是以雇傭身份的確認來定義勞資雙方的權利和義務。英國工業革命塑造了“等級體系”的服務模式,起源于《主仆法》,而后影響到普通法。〔7〕See Deakin and Wilkinson, The Law of the Labour Market: Industrialization, Employment and Legal 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在傳統上,工作關系中的等級權力(hierarchical power)和由此產生的雇員的“從屬性”(subordinate),無論是在成文法國家還是判例法國家,皆被視為雇傭(勞動)關系與自雇傭相區分的顯著要素。勞動法理論一般認為,從屬性導致勞資失衡以及雇員權利受不公正侵害現象的產生,為了矯正民法雇傭契約的平等原則,實現勞資關系的實質平衡,需要將具有從屬性的雇傭關系納入勞動法的保護范圍,這亦與雇傭關系發展至勞動關系的歷史脈絡相一致。
“從屬性→不平等性→矯正自由→勞動法的干預與調整”這一基本邏輯產生于典型工業時代階層化的組織與規訓式的管理模式,傳統勞動法也與該時代工廠的“泰勒式”管理且強調紀律為生產力之本的組織文化相匹配。在垂直與整合的企業中,雇主的法律概念邊界與工作場所的經濟組織邊界相重合,二者的一致性又反過來強化了“雙方”雇傭(勞動)關系的構建,最終在制度呈現上,雇傭(勞動)關系“與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從屬關系有關,無論是通過英國法院設計的‘控制檢驗’,還是法國和其他大陸法律體系的典型‘法律從屬關系’,所有國家對于雇傭合同的定義都有一個前提,即基于內在的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垂直權力關系的工作范式。”〔8〕Countouris, N.,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ational Judicial Approaches, in G.Casale ed.,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 A Comparative Overview, International Labour Oきce, 2011, p. 35-68.雇傭(勞動)關系及雇員的從屬性地位,成為標準雇傭(勞動)關系規則的核心認定標準,以及為雇員提供勞動法保護的基本前提。
然而,從屬性、雇傭(勞動)關系認定、標準勞動關系和勞動法的調整對象,這幾者間的邏輯自洽隨著非標準就業的繁榮導致的雇傭(勞動)關系邊界的模糊而不斷受到挑戰。隨著商業中信息技術的使用和服務業中新的工作形態的擴展,工作中等級管理的減少實質上改變了工作行為的履行方式,特別是當越來越多的工作行為發生在指揮權和科層制組織日益松散的情況下,原有的分類和雇傭(勞動)關系認定標準便會導致嚴重的問題,并隨著零工經濟(gig economy)和平臺用工的日益活躍而陷入白熱化。于是,人們開始反思,傳統勞動關系認定理論與標準對新形態的工作是否喪失了解釋力?以從屬性作為勞動關系法律調整的邏輯起點是否本身已為謬誤,或應為時代的發展所摒棄?
當我們再次回看“從屬性→不平等性→矯正自由→勞動法的干預與調整”這一基本邏輯時便會發現,勞動者對雇主毫無限制的從屬關系是大機器時代雇傭關系的重要特征,正是勞動力的商品化與其人格屬性形成的沖突,成了勞動立法保護的根源。但事實上,雇主對雇員的“控制”和雇員對雇主的“從屬性”,與其說是雇傭關系的特征,倒不如說是雇傭關系的后果。勞動法理論將該后果反過來作為判斷雇傭(勞動)關系成立的標準與依據,并就此認為與雇主控制的權力相對應,需要求其對雇員的勞動條件保障承擔相應的責任。這種一定程度上的“倒果為因”其實并未能解決為何“從屬性”成為雇傭關系認定標準及其制度展開的理論問題,仍需另外的理論解釋。
德國學者辛茨海默曾嘗試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從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角度進行解釋,認為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導致了依附性勞動以及決定依附性的支配權限,并認為所有權是從屬性理論合理性的最終根源。〔9〕參見游進發:《德國民法上勞動契約的特性》,載《財產法暨經濟法》2013 年第35 期,第55 頁。哈特在某種程度上回答了馬克思,認為所有權的意義在于資產的“剩余控制權”,即可以按任何不與先前的法律、合同、慣例相違背的方式決定資產使用的權利。〔10〕See Hart, Oliver, Firm, Contract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9-33.該解釋路徑賦予了資本控制勞動的合理性與效率性,并揭示了以所有權為基礎的控制意義在于“剩余控制權”。科斯則在其《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將“雇傭”作為企業資源配置的方式,認為作為雇傭關系核心特征的“控制”要素,是區別于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典型特征。西蒙承襲了科斯的觀點,認為當有限理性的企業無法締結完全契約的情況下,通過實施控制權而行使“剩余決策權”是節約交易成本的行為。〔11〕See Simon, H. A., A Formal Theory of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Econometrica, 19(3), 1951, p. 293-305.在新制度經濟學的解釋框架下,雇傭被看作是企業資源配置的本質特征,雇傭關系中雇主的等級權力為雇主提供了很大的靈活性,使企業能夠利用等級結構作為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種方式。〔12〕See Giuseppe Casale,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Giuseppe Casale ed.,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 Comparative Overview, International Labour Oきce, 2011, p. 19.此外,雇傭關系下雇主的控制權激勵企業對人力資本進行投資,從而讓工人獲得對本企業有用但對其他公司價值有限的技能,也會讓企業為維持控制權的持續性而選擇建立雇傭關系。總體而言,雇傭關系的存在使企業能夠獲得管理特權和權威,并能保證工人工作的穩定性和連續性,相比使用獨立勞動進行重復性經濟交換的做法,建立雇傭關系的產出效率更高。
上述理論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何等級權力和從屬性構成雇傭關系認定標準的合理性,并就此展開雇主、雇員的權利義務配置。從法律的角度看,等級權力、控制與從屬性是雇傭關系的核心,而對雇員的法律保護傳統上則以減少上述特征所造成的沖突為重點,也即回到最通常的勞動法邏輯——矯正合同自由與實現勞資平等上,如減少工作時間、管制加班、解雇保護等,最明顯的是雇員有權組織起來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勞動法的勞動基準及集體勞權規則體系就此展開。雇傭關系的出現,加上有限責任制釋放出的重要資金資源,推動了垂直整合的現代企業的興起,大規模企業的出現也為雇傭關系內社會保護的擴大提供了機會。同時,國家成了第三方,負責通過社會保險體系調節經濟不安全感給整個勞動力群體帶來的風險,并通過社會保障繳納和征稅收入支持福利服務的公共供給。然而,對雇主等級權力的限制,特別是對雇員集體勞權的保障最終將導致整個企業靈活性的降低,因此雇傭關系的法律規制會給企業帶來組織成本。此際,雇主就會在決定是內部執行還是外包生產階段時,對組織成本和交易成本進行權衡。事實上,雇主也一直在為減少和規避組織成本而改變勞動力使用方式,隱蔽性雇傭、勞務派遣和外包等均為其體現。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進一步方便了平臺供需撮合,極大地降低了企業的交易成本,由此催生零工經濟特別是眾包工作形態的迅速發展,引發對雇傭關系既有認定規則的不斷質疑與挑戰。基于此,本文對雇傭(勞動)關系從屬性認定規則的體系化研究,以學界通說的從屬性范疇構成為展開,將等級權力、控制與從屬性給雇主帶來的“剩余控制(決策)權”納入分析架構,在探究雇主義務來源的思路上,分析各從屬性及其要素組成,以及各要素在雇傭(勞動)關系認定中的意義與權重。同時,在分析從屬性勞動與平等性勞務給付區分規則的基礎上,不斷思考勞動力使用形式變化對雇傭關系認定規則的沖擊,特別是零工經濟、平臺用工背景下雇傭(勞動)關系認定實踐對從屬性標準適用帶來的挑戰,并給予回應。
三、作為從屬性核心認定標準的人格從屬性:雇主與雇員的視角
(一)雇主視角的人格從屬性:基于雇主“控制”的指揮、監督與懲戒權
不同國家和法律傳統中雇傭關系的主要特征表現為雇主對雇員的等級權力(hierarchical power),主要由三個相關因素組成:(1)分配任務并給雇員以命令和指示的權力,即指揮權;(2)對雇員履行任務和對命令和指揮的遵守進行監督的權力,即監督權;(3)對分配任務不適當或疏忽履行,以及為違反給定任務和指示的行為進行懲罰的權力,即懲戒權。〔13〕同前注〔12〕,Giuseppe Casale 文,第3 頁。這三項權力是雇主得以最終實現對雇員的“控制”,從而獲得比一般性的勞務市場交易行為(如承攬、委托)更有效率的收益,因此能成為雇主“控制”與雇員“從屬性”認定的最核心要素。
1.指揮權:分配任務的命令和指示
指揮權為雇主在從屬性勞動中最本源性的權利,是人格從屬性最重要的特征。〔14〕參見黃越欽:《勞動法新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94 頁。日耳曼法以身份法的奉公關系予以規范,繼承日耳曼法思想的英國法,關于勞務契約最初仍然規定于主從間的身份法契約中。傳統上,主人與仆人之法理,不僅指主人有權控制(control)仆人做什么(what),亦包括主人有權控制仆人如何(how)執行職務之方式(manner)。上述法理成為英美法雇傭關系、雇員身份認定的理論依據。〔15〕See ILO,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n Annotated Guide to ILO Recommendation No.198,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dialogue/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72417. pdf , p. 41, last visit on September 1, 2020.德國法上,根據聯邦勞動法院、社會法院、最高法院判決以及主流學說,作為勞動關系和委托人與自由勞動者之間界限的“人格從屬性”最為重要的特征就是雇員在雇主的指揮下工作。〔16〕同前注〔3〕,王倩文,第42 頁。
雇主的指揮權包括由雇主決定雇員從事何種工作、完成工作的手段、工作時間的指定和工作地點的安排。當企業具備相當規模時,指揮權則更多透過管理體系和工作規則,以整體的分工來決定雇員的勞務給付方式。我國《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規定的勞動關系認定標準之一,“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即為從屬性指揮權之體現。
指揮權作為人格從屬性判斷核心要素的理由在于,勞動契約具有繼續性法律關系的特性,在契約存續期間,勞動者的工作義務內容會不斷發生變化,契約對此可能永遠無法詳盡,而雇主的指揮權及雇員的服從義務,則為雇主因資本或企業組織優勢而擁有剩余控制(決策)權的集中體現。在此需要區分雇傭(勞動)關系中具有控制意義的指揮權與委托、承攬關系中委托人與定作人的指示性權利,后者體現為平等主體間明確的合同內容,受托人、承攬人依約履行合同義務,并未因此形成對合同相對人的從屬性。
2.監督權:履行任務的監督
監督權意味著雇員的勞務給付行為受雇主監督,雇員有義務接受雇主的考察與檢查,以確定其是否遵守了工作規則或雇主的指揮。雇主的指揮權與監督權為一體兩面的關系,指揮權是實施監督權的指引,監督權是實現指揮權的保障。南非《勞動關系法實施法典》第39 條規定,雇主的控制權可從雇主對員工的指示及監督該指示的完成中看出。〔17〕See South Africa Code of Good Practice: Who Is an Employee, 2006, https://www.ilo.org/dyn/natlex/docs/SERIAL/74747/77159/F-566381856/ZAF74747.pdf, last visit on September 1, 2020.監督權是雇主對雇員“控制”判斷的核心特質,顯示出雇員對雇主較強烈的個人的、正式的從屬與附屬關系。
其一,對勞動過程的監督。國際勞工組織(ILO)在其第198 號《雇傭關系建議書》中提出的雇傭關系界定指標之一——“對工作和指示的控制”,意指雇主擁有指揮工人適應勞動過程不斷變化所需要的權力,考慮因素主要包括工作的指示、招聘、紀律、培訓、考核等。〔18〕同前注〔15〕,ILO 文,第35 頁。對勞動過程而不僅是對勞動結果的監督與控制,或者說,合同是以勞務給付為目的,還是以勞務所完成的結果為目的,是雇傭(勞動)關系與承攬關系的根本區別。正是雇傭與承攬合同目的的不同,而產生勞務給付人是否應有專屬性,以及合同履行風險承擔人的不同,此亦與下文雇員視角的人格從屬性要素相關。
其二,對工作地點、時間的決定權。與對工作過程的控制即監督權相匹配的,是雇主對雇員工作時間、地點的指定和決定權,并需與基于債之履行方便而在勞務提供地點、時間上的配合(例如,搬運公司承攬搬運貨物須配合托運方的時間和地點要求)相區分。ILO 《雇傭關系建議書》將“該工作是在下達工作的一方指定或同意的特定工作時間內或工作場所完成的”作為雇傭關系判斷的指標之一,并認為“控制的核心方面之一,是雇主有權決定何時何地開展工作,而不是簡單地以何種方式完成工作”。〔19〕同前注〔15〕 ,ILO 文,第27-31 頁。南非《勞動關系法》第200A(1)(b)條規定,除非有相反的證明,當一個人的工作時間受另一個人的控制或指揮,為他人工作或提供服務的人士即被推定為雇員。〔20〕同前注〔17〕 。德國2017 年修訂民法典新立之611a 條,對勞動合同雇主的指揮權依然強調工作的內容、實施方式、時間和地點。〔21〕參見婁宇:《民法典的選擇:勞動合同抑或雇傭合同——〈德國民法典〉第 611a 條修訂的教義學分析與啟示》,載《法律科學》2019 年第5 期,第144 頁。在我國平臺用工司法實踐的典型案例中,〔22〕參見“尤培娥與北京河貍家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其他勞動爭議案”,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2019)滬0106 民初27907 號民事判決書。法官亦以上門服務美容師可以自主選擇工作時間和地點,而認為平臺并未對其實施勞動管理。
需要考慮的是,雇主對雇員工作時間的控制是否需要體現為對工作時間連續性的要求。ILO 《雇傭關系建議書》將“工作有一定的持續時間并有某種連續性”作為雇傭關系認定的指標之一,在一些國家的立法中,工作的連續性被明確作為雇傭關系的認定標志,如智利《勞動法》第8 條規定:“既不間斷也不零星的家庭作業被認為是雇傭。”〔23〕同前注〔15〕,ILO 文,第41 頁。由工作時間的連續性而引申的雇員與雇主“關系的持久性”,也成為一些國家雇傭關系判定規則的要素之一。〔24〕See U. S. Dept. of Labor, Wage and Hour Standards Div., Fact Sheet #13: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Under 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FLSA), www.dol.gov/whd/regs/compliance/whdfs13.pdf, last visit on September 1, 2020.雇傭關系對工作時間連續性的要求通常是為了維持雇主組織的正常運作,雇員需持續為雇主提供勞務且于一定期間內工作相當時數。與雇傭不同,承攬關系中一般只要求工作必須在一定期間內完成,定作人不干涉實際工作的時數,且工作完成承攬合同即終止;而委托合同的委托人,除非依時計酬,否則亦不干涉受托人完成委托事項所需的時間。
與工作時間的控制與連續性要求相關的是雇主是否擁有對雇員“隨叫隨到”的權力,這亦是ILO《雇傭關系建議書》中雇傭關系的認定指標之一。ILO 認為,對一名工人隨叫隨到的要求,可以證明他的雇傭狀況,也可以證明他的實際工作成績。〔25〕同前注〔15〕,ILO 文,第41 頁。“隨叫隨到”意味著雇主對雇員工作時間內充分的指揮權和對勞動力的支配性,這一認定指標也是當前平臺勞動者雇員身份認定的最大障礙,因為此時勞動者對是否必須承擔工作任務享有極大的自主性。
3.懲戒權:對違反雇傭(勞動)合同或工作規則的懲戒處分
懲戒權意味著雇員在違反雇傭(勞動)合同或工作規則時,雇主得予扣減工資、記過、解雇等懲戒處分,而雇員有接受制裁的義務,從而使雇主得以維持企業組織內的秩序。懲戒權使雇主對勞務提供者擁有超過一般契約當事人間單純的違約處罰的權力,與指示權相比,接受懲戒或制裁義務使勞務提供者更具有——或至少擁有相同程度的從屬性;〔26〕同前注〔5〕,林更盛文,第85 頁。更有學者認為,懲戒權使雇主對受雇人之意向等內心活動過程均能達成某種程度之干涉與強制,此點乃人格上從屬性效果最強之處,也是最根本所在。〔27〕同前注〔14〕,黃越欽書,第94 頁。懲戒權允許雇主對違反其命令和指示的行為進行制裁,由于遵守雇主的命令和指示是雇員的合同義務,當雇主必須通過新命令和指示迅速調整其活動以適應不可預測的需要時,通過執行內部規則使合法地制裁違約而非終止合同成為可能,這一機制大大降低了合同的執行成本,從而降低了整個交易成本。
4.雇主“控制”的判斷:控制的現實還是控制的權利與可能
作為標準勞動關系的反映與寫照,雇主視角的指揮、監督與懲戒權是人格從屬性判斷的體系化構成要件,并成為“控制”標準與雇傭(勞動)關系認定的核心要素。從根本上說, 指揮和監督權意味著對工作內容、時間、地點的單邊決定權,使得勞動者在提供勞動的過程中處于弱勢地位,從而為勞動法的保護提供了因由,而懲戒權則執行與進一步強化了指揮與監督的“控制”特征,并成為組織成本優于交易成本的一項制度安排。
然而,對這三項要素的認識與判斷,在平臺用工下變得撲朔迷離。在一些案例中,三者仍被解釋為雇傭關系認定的核心依據,如2015 年美國加州勞動委員會在裁定Uber 平臺與網約車司機存在雇傭關系的理由中,認為Uber 公司對司機在工作量(接單比例)、工作方式和方法(著裝等紀律要求)及監督方式(根據乘客打分決定終止合同)上存在著指揮、監督與懲戒權控制。〔28〕See Berwick v. Uber Technologies, Inc., CGC-15-546378 (Cal. Labor Commissioner, June 3, 2015).然而,Uber 模式中平臺“控制”的弱化與碎片化無法被否認,此時如何認定平臺企業的雇主身份依然未解。在“控制”決定雇傭(勞動)關系的理論路徑下,企業的經營選擇依賴于其對組織成本與交易成本的評估,如果企業不需要從對勞動過程的控制中獲利,那么就不需要控制勞動過程而只需要控制勞動結果,此際企業也無需對控制勞動過程付費,即因“控制”行為被認定為“雇主”而需負擔雇傭成本。在此,對“控制”本身的理解就尤為關鍵:平臺工作者可自主決定是否上線、接單的外在表征,究竟是無法履行“隨叫隨到”義務,從而作為不受平臺控制和不具有從屬性的重要依據,還是平臺控制碎片化的表現?在平臺頗具吸引力和趣味性的計酬機制和實時評分機制的約束下,勞動者接受和完成工作的主動性和選擇性,能否掩蓋和否定其一旦履行任務而同意勞動過程被剝削、被控制的被動性?平臺設計的由客戶、消費者對任務履行的監督、評分和懲戒機制,是普通的商業/服務評價機制,還是平臺以超低成本轉移對勞動過程的監督從而實現了控制的隱蔽性?〔29〕參見吳清軍、李貞:《分享經濟下的勞動控制與工作自主性——關于網約車司機工作的混合研究》,載《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4 期,第145-146 頁。雇主的控制權究竟是實際控制的現實還是可以控制的權利?在技術和組織手段可以使用工方不實際實施對勞動過程的控制亦可獲得勞務使用收益的今天,對“控制”的判斷是否應當加入用工方控制的主觀意圖與實現可能性的考量?
有學者認為,對平臺用工應將主體策略作為聯結行為主體和用工關系之間的紐帶,強調企業的“控制動機”。〔30〕參見王琦、吳清軍、楊偉國:《平臺企業勞動用工性質研究:基于P 網約車平臺的案例》,載《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8 年第8 期,第98 頁。根據南非《勞動關系法實踐法典》第40 條的規定,控制權即使不行使,也可能存在;雇主不行使控制權,允許雇員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工作,并不會改變這種關系的性質。〔31〕同前注〔17〕。在2015 年美國加州Uber 案中,〔32〕See O’Connor v. Uber TechS., Inc., 82 F. Supp. 3d 1133, 1135 (N. D. Cal.2015).地區法庭和委員會認為,在判斷對于一個人的控制是否充分并足以認定存在雇傭關系時,“控制的權利”不需要延伸至工作中所有可能的細節,問題不是雇主能施加多少控制,而是雇主保留了多少可以施加控制的權利。〔33〕See Ayala v. Antelope Valley Newspapers Inc., 59 Cal. 4th 522, 531 (2014).2018 年11 月28 日,法國最高法院就網絡送餐平臺“Take Eat Easy”與送餐人的法律關系作出從屬性認定,認為平臺公司通過定位系統實時追蹤送餐者構成了對其的監督,而有關取消送餐者在網約平臺上的賬戶和切斷網絡鏈接的制度安排則是懲罰權的行使。〔34〕參見法國最高法院社會庭(Cour de cassation, Chambre sociale)2018 年11 月28 日n°17-20.079 判決。2020 年3 月4 日,法國最高法院遵從“Take Eat Easy 案”的裁決要旨,認為Uber 司機雖然沒有連接數字平臺的義務但能夠選擇工作天數和時間的事實本身并不排除雇傭從屬關系。〔35〕參見法國最高法院社會庭(Cour de cassation, Chambre sociale)2020 年3 月4 日n°19-13.316 判決。筆者以為,因互聯網技術的介入而產生的用工方式變化模糊了傳統的“控制”外觀,對“控制”的判斷加入控制權利實現意圖與可能性的考量,更有利于清晰地認識控制權下的“指揮”“監督”與“懲戒”權要素,更清晰地判斷技術介入所改變的究竟是控制的方法還是控制本身,以及真實的控制事實上是更少還是更嚴。
(二)雇員視角的人格從屬性:勞務給付的親自履行性、專屬性與利他性
1.親自履行性
雇傭(勞動)契約以雇員提供自身的體力、智能為勞務給付標的,且雇主需從對雇員的勞務給付過程的控制中收獲“剩余價值”,因此雇傭(勞動)關系的認定需考量雇員給付勞務的親自履行性。我國臺灣地區法院將“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作為從屬性判斷的特征之一,認為若提供勞務者在契約法上可另行聘用他人代服勞務,則顯然可藉此減少受相對人行使指示權的拘束而欠缺從屬性。〔36〕同前注〔5〕,林更盛文,第84 頁。ILO《雇傭關系建議書》將“該工作必須由勞動者親自履行”作為雇傭關系認定的指標之一,并認為如果工人可以提供一個替代的人選來完成這項工作,那么此人通常不是雇員。〔37〕同前注〔15〕,ILO 文,第39 頁。
我國《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并未就勞動關系中勞動者的親自履行問題作出相關規定,臺灣地區“民法債編”第484 條就“勞務之專屬性”在“雇傭”一節中專門予以規定。〔38〕第484 條規定:“受雇人非經雇用人同意,不得使第三人代服勞務;當事人之一方違反前項規定時,他方得終止契約。”在我國臺灣地區,雇傭契約是勞動契約的上位概念,民法對雇傭關系勞務專屬性的要求亦成為雇傭(勞動)、承攬與委任關系的重要區分點。我國《民法典》第772、773、923 條亦對承攬人將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時對定作人所負的不同責任,以及轉委托問題予以規定,說明承攬與委托中的勞務給付并不具有專屬性特征。
2.專屬性:不具有或具有較弱的勞動(創業)自由
雇傭(勞動)契約中雇員應親自為勞務給付,在工作時間內沒有同時為他人提供服務之可能,且基于雇員對雇主所負忠實義務,業余時間亦不宜為雇主商業上的競爭對手工作,此點亦為雇傭(勞動)與委托、承攬關系的重要區別。雇員勞務給付的親自履行性,自然可衍生出工作時間內雇員勞動的專屬性,及其對自身勞動力利用和使用的非自由性。而對工作時間和方式頗具靈活性的職業群體(例如,計程車司機、快遞員、零工經濟工人)而言,其勞動自由及自主決定權被限制的程度,即“雇主對就業者自主利用勞動力的限制程度”與“從業者利用勞動力的自由被喪失的程度”,〔39〕田思路:《工業4.0 時代的從屬勞動論》,載《法學評論》2019 年第1 期,第84 頁。成了雇傭(勞動)關系認定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3.利他性:為雇主之目的而非自己的營業而勞動
與雇傭(勞動)關系中雇員給付勞務的親自履行性和專屬性相關的,是雇員勞務給付的利他性。利他性意味著雇員義務僅限于提供勞務,其勞務給付依附雇主,構成雇主生產、經營的一部分,而非為自己的營業目的而從事獨立的生產事業或商業行為。ILO 《雇傭關系建議書》將“完全或主要為他人的利益而做的工作”作為雇傭關系認定的指標之一,并將其解釋為“工人是否完全限于為委托人提供服務”,〔40〕同前注〔15〕,ILO 文,第41 頁。即可見勞務給付“利他性”與“專屬性”的相通之處。勞務利他性是雇傭(勞動)合同與承攬、委托合同的重要區別之一,承攬人對于承攬工作的履行為其自己獨立的商業行為,受托人亦同,并由此導致承攬、委托合同皆有工作成果所有權轉移的問題,并有定作人在受領前不負擔工作毀損、滅失危險的相關規則。而在雇傭(勞動)契約下,并無勞動成果所有權的轉移,及雇方受領遲延應續付工資等問題的判斷問題,這意味著雇員不直接投入市場競爭,而是僅獲得固定薪資,其勞動成果歸由雇主,由后者投入市場,經營獲利。
4.專屬性、利他性作為核心要素的現實意義與問題
雇員勞務給付的親自履行性、專屬性與利他性與雇主的指揮、監督與懲戒權共同構成了“控制”與“從屬性”認定核心要素的一體兩面。在平臺用工的雇傭(勞動)關系認定上,勞務給付專屬性、創業自由因素占有重要地位。在美國NLRB v.Friendly Cab Co.一案中,〔41〕See NLRB v.Friendly Cab Co., 512 F.3d at 1098.法院認為,出租車公司明確禁止出租車司機尋求任何外部商業機會,強調該身份的認定要考慮是否擁有創業自由,即可以像真正的獨立承包人一樣發展自己的商業利益,以此強烈支持認定司機的法定雇員身份。在FedEx Home Delivery v.NLRB 一案中,〔42〕See FedEx Home Delivery v. NLRB, 563 F. 3d 492 (D. C. Cir. 2009).聯邦快遞確實以各種方式對司機進行了控制,但公司也允許司機雇傭自己的員工承擔多條路線合并,甚至在沒有聯邦快遞許可的情況下將自己的路線賣給其他人,因此被法院認為構成獨立承包人的重要特征。而在2019 年,NLRB 的總法律顧問辦公室在其發布的針對Uber 公司的建議備忘錄中同樣強調,公司對司機是否具有創業機會的實際控制才是雇員身份認定的決定性因素。〔43〕See Uber Drivers Are not Employees According to the NLRB,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uber-drivers-are-notemployees-94262/ (Last visit on September 1, 2020).而在法國,巴黎勞動法院曾在2016 年12 月基于網約平臺VOXTUR 與司機簽訂的合同中有排他條款——禁止網約車司機接運散客及與其他公司合作,而將司機界定為平臺公司的雇員,〔44〕參見巴黎勞動法院(Conseil des prud’hommes)2016 年12 月20 日n°14/16389 判決。并直接導致法國議會于2016 年12 月29 日通過《格朗吉約姆法律》,禁止網約平臺公司在格式合同中規定不允許網約工從事任何其他相似業務的絕對排他條款。〔45〕參見《格朗吉約姆法》(Loi Grandguillaume)2016 年12 月29 日n°2016-1920,第3 條。而我國2016 年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再審的“叢某與某報社勞動爭議糾紛案”中,〔46〕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48 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將“報社對叢某不具有勞動力專屬性”作為否定勞動關系的理由之一,說明此要素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亦為勞動關系認定的核心要素。
雇員的勞動力專屬性和創業自由的喪失意味著雇主對勞動力的實質性控制,哪怕勞務給付的履行在時間、地點和方式上仍存在較大的靈活性,依然能構成雇主承擔雇傭關系組織成本的合理化依據,也應成為平臺用工勞動關系屬性判斷的核心要素。勞務專屬性強調雇主控制的組織屬性并容易使得“控制”特征顯性化,而勞務給付的“利他性”因涉及雇主與雇員的利益分配方式而更為復雜。在2018 年北京市海淀區法院認定“‘閃送員’勞動關系案”中,法院對“勞務利他性”因素予以考量,認為同城必應科技公司從李某提供的勞動中獲益,則其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及企業社會責任。〔47〕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稱“閃送途中發生事故,閃送員起訴平臺經營者要求確認勞動關系獲支持”。參見http://bjhd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5470,2018 年6 月6 日訪問。雇主對勞動力剩余價值的攫取,與平臺從其工作者勞務履行中的獲益方式相去甚遠,背后更關涉工資給付風險負擔與企業風險理論對該要素判斷的影響,即應厘清“從中獲益”的經營組織者,與得實施“控制”而需承擔經營風險并履行工資給付義務的雇主之間的差別,由此“利他性”則不應成為獨立的核心判定要素。申言之,勞務給付“利他性”又與“經濟從屬性”相關,我國臺灣地區相關法院在對勞工從屬性的界定中,將“受雇人并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于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歸納為經濟從屬性,并作為從屬性判斷的必備要素之一。〔48〕同前注〔5〕,林更盛文,第80 頁。但亦有臺灣學者認為,“勞動力之純粹利他性”是人格從屬性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將其作為經濟從屬性的內容,會推論出經濟從屬性與人格從屬性同為勞工判斷標準的錯誤結論。〔49〕參見魏千峰:《勞動基準法上之勞工——評釋臺灣“高等法院”1994 年勞上字第三十七號判決》,載臺灣勞動法學會編:《勞動法裁判選輯(一)》,元照出版公司1999 年版,第348 頁。由此可知具體判斷要素的從屬性類別歸屬及體系性解釋的必要與重要性。
總之,人格從屬性包含的上述構成要素均根源于對初始狀態雇傭(勞動)關系的描述與總結,將其作為雇傭(勞動)關系認定的核心標準,符合對雇傭關系法律規制的內在邏輯機理,也成為目前各國雇傭(勞動)關系判定規則的核心要素。在歷史發展的脈絡上,淵源于主仆關系,被簡單地理解為雇主對雇員所做工作的直接“控制”標準,隨著技術和組織的變化而逐漸出現與實踐的脫節,如強求整個生產過程中的任何事情皆須由雇主掌控才算具有雇傭(勞動)契約性質,實與社會分工與專業化趨勢相違背,且事事指示與管制于專業化工作中亦難產生良好的工作成果。因此,純粹的“控制”標準在實踐中逐漸改弦易張,而改變的路徑就是“控制”的實際指示性要素被其他一些指標所補充,包括“業務”指標(工人是否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和“整合化”指標(工人完成的工作是否是企業的業務組成部分)等,〔50〕同前注〔12〕,Giuseppe Casale 書,第24 頁。即后文所涉人格從屬性標準向經濟從屬性與組織從屬性的擴張,并進而產生對經濟從屬性與組織從屬性認定標準的認識與權衡問題。
四、能否作為從屬性核心認定標準的經濟從屬性——涵義、作用與意義
(一)經濟從屬性與人格從屬性之關系及對雇傭(勞動)關系認定的意義
將人格從屬性作為勞動關系的標志,在等級結構的時代可以很好地處理出現的案件形態,為勞動法的特別保護提供理論基礎并構成與社會保障的連接點。但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在歐洲范圍內法律上從屬(指示權)的案件和經濟上依附的案件分別發展,經濟上的從屬性被置于勞動關系之外,而這兩種案件以前被認為在根本上是重合的。〔51〕參見[德]雷蒙德·瓦爾特曼:《德國勞動法》,沈建峰譯,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52 頁。在一些法律體系中,“從屬性”(subordination)和“依賴性”(dependency)可能是同義詞而被替代使用,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含義并伴隨不同的限定詞,如“法律從屬性”和“經濟依賴性”。前者被理解為雇主或其代表直接或可能直接指揮工作的執行,后者存在于工人所得的款項構成其唯一或主要收入來源,以及勞動者沒有經濟自主權,在經濟上與被視為用人單位的人或者企業的經營活動范圍相聯系的情形。〔52〕同前注〔12〕, Giuseppe Casale 書,第26 頁。
經濟從屬性(依賴性)與人格從屬性歷經了從重合到分離的演化過程,當二者在用工實踐中呈現分離狀態時,經濟從屬性對于雇傭(勞動)關系的認定就存在兩個層面的判斷問題:一是在依據人格從屬性無法認定時,經濟從屬性是否可作為確定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核心要素?日本勞動法理論認為,僅僅根據雇傭從屬關系來判斷個人是否是“勞動者”非常困難,因此還需要輔以一些補充因素,如生產資料以及工具的所有、報酬的多少以及損害責任的負擔等。〔53〕同前注〔4〕,Ryuichi Yamakawa 書,第104-106 頁。我國有學者認為:“即使從業者沒有人的從屬性,但被認為存在經濟的從屬性時,可以較為廣泛的對符合勞動契約目的的法律規定加以適用,并提供與該從屬性程度相對應的一定的法律保護。”〔54〕同前注〔39〕,田思路文,第84-85 頁。二是經濟從屬性是否應為雇傭(勞動)關系認定的必要因素,即該因素的缺失將導致雇傭關系認定的否定性結果?我國有學者認為,經濟從屬性是人格從屬性的基礎和前提,是判斷勞動關系存在與否的重要因素。〔55〕參見謝增毅:《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關系認定》,載《中外法學》2018 年第6 期,第1560 頁。我國臺灣地區司法實踐認為,受雇人不僅必須人身上從屬于雇傭人,尚須經濟上與組織上從屬雇傭人才是勞動契約中的勞工。在技術發展與組織經營形態不斷更新與變化、人格從屬性認定不斷遭遇挑戰的今天,經濟從屬性在雇傭(勞動)關系認定中的作用問題就顯得更為突出。
(二)經濟從屬性的具體界定及其在雇傭(勞動)關系認定中的作用
與人格從屬性不同,學理上學者對“經濟從屬性(依賴性)”具體涵義的理解并不一致,包括經濟資源上的依賴性、雇員無需承擔經營風險、經濟來源上的依賴性及經濟地位上的弱勢性等,而不同解釋之下的經濟從屬性,在雇傭(勞動)關系認定中發揮的作用也不盡相同。
1.經濟資源上的依賴性
將經濟從屬性作經濟資源上的依賴性的解讀,符合勞動關系產生之初大工業化工廠生產的現實。雇員對雇主經濟資源的依賴,皆因生產組織體系、生產原料、生產工具屬于雇主所有而產生。〔56〕同前注〔14〕,黃越欽書,第95 頁。雇主因掌控生產組織體系而導致的依賴性,可單獨衍生出雇員的“組織從屬性”;對生產原料擁有所有權,意味著在雇傭(勞動)關系中,雇員付出勞動在原料上加工,即使加工價值遠超原料價值,也并不影響工作成果所有權的歸屬;對生產工具或機械的所有權而產生的經濟從屬性,則具有更大的研討價值,并成為當今平臺用工勞動關系認定問題的焦點之一。
與雇傭勞動不同,承攬人、受委托人一般自行擁有及提供生產工具以完成工作任務。在美國,在雇傭關系認定的Borello 多因素標準,〔57〕See S. G. Borello & Sons, Inc. v. Dep’t of InduS. Relations (Borello), 48 Cal. 3d 341, 350 (1989).以及國家勞動關系委員會(NLRB)區分雇員和獨立承包人而采用的普通法的代理檢驗中,〔58〕e. g. Associated Indep. Owner-Operators, Inc. v. NLRB, 407 F. 2d 1383, 1385 (9th Cir. 1969).都將是雇主還是工人提供工具、設備作為考量要素。在2019 年針對Uber 公司的建議備忘錄中,NLRB 總法律顧問辦公室就將司機本人提供了主要的勞動工具(汽車)并承擔了自己車輛的維護成本作為否定司機雇員身份的理由之一。對于這一問題,ILO 《雇傭關系建議書》雖將“下達工作要求方提供工具、物料和機器等事實”作為雇傭關系界定的指標之一,但其亦認為工具和設備的所有權本身并非決定性因素,因為許多雇員擁有自己的工具。〔59〕同前注〔15〕,ILO 文,第41 頁。芬蘭《雇傭合同法》(2001)第1 條規定,該法的適用并不能僅僅因為工作是使用雇員的工具或機器進行的而被排除。〔60〕See Finland Employment Contracts Act (No.55 of 2001), https://www.ilo.org/dyn/natlex/natlex4.detail?p_lang=en&p_isn=58905, last visit on September 1, 2020.但ILO 同時認為,如果工人個人進行了大量的資本投資,比如購買自己的汽車,那么通常會顯示出獨立承包商的身份。〔61〕同前注〔15〕,ILO 文,第41 頁。日本勞動基準法研究會1985 年就勞動者的判斷基準和勞動者性質發表的研究報告認為,如果工人花費很大的投資來購買生產工具,將會增強其被判斷為自雇傭的可能,因為工人承擔較多的風險。〔62〕同前注〔4〕,Ryuichi Yamakawa 文, 第106 頁。在當今司機以自有車輛提供網約車服務的勞動關系爭論中,“司機自有車輛”往往成為否定雇傭(勞動)關系的重要要素。此時出現了勞動者自備生產工具的一個悖論:經典邏輯之下雇員不擁有生產工具,而雇主投資購買生產工具并承擔風險,因而雇主可在工作過程中對雇員施加控制,從而承擔雇主責任。而平臺用工等情形中若生產工具為勞動者自備,但若控制過程并沒有減弱,反而因其自備工具而否定其雇員地位,實質上既讓其承擔投資生產工具的經營性風險,又接受平臺的控制,其不利地位是否比大工業時代更甚?因此,不能一概以生產工具為勞動者自有而否定其從屬性,仍需結合人格從屬性各判斷要素考察其被控制的程度。
2.雇員無需承擔經營風險
雇傭關系中由雇主而非雇員承擔企業經營風險,意味著雇員對雇主的義務限于忠實的提供勞動力,只要其依據勞動契約或雇主指示給付勞務,雇主即有給付報酬之義務,當危險發生時,由雇主承擔經營風險。此點與承攬人需以約定的工作成果領取酬勞,以及受托人以完成委托事務而由委托人支付報酬存在明顯的不同。
在ILO 《雇傭關系建議書》中,“勞動者沒有財務風險”亦為雇傭關系認定的指標之一,如果雇主的業務利潤下降,雇員不會承擔直接的財務后果,但傭金或獎金等激勵結構不應被視為財務風險的指標。〔63〕同前注〔15〕,ILO 文, 第45 頁。在愛爾蘭,其勞動法也以此指標作為立法上區分雇員與自雇傭者的重要標準,認為雇員沒有機會從項目的有效管理及任務的執行中獲益,而自雇傭者則須承擔合約之下不合格工作的成本而有財務風險,但也有機會在項目和任務的調度和執行方面獲益。〔64〕See Ireland, The Code of Practice for Determining Employment or Self-employment Status of Individuals of 2001, https://www.revenue.ie/en/self-assessment-and-self-employment/documents/code-of-practice-on-employment-statuS. pdf, last visit on September 1, 2020.在我國,審理“王志杰訴上海溫石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勞動合同糾紛案”〔65〕參見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18)滬0115 民初61915 號民事判決書。該案獲評全國法院系統2019 年度優秀案例分析評選活動一等獎。的法院認為,原被告簽訂的協議中約定的雙方對營收收入的分成方式以及管理費的規定,不同于一般勞動關系項下基本工資、提成工資或績效獎金的約定,因此雙方之間財產關系中的從屬性并不明顯,從而否定了勞動關系。因此,工人承擔經營風險,特別是可從任務執行中獲得非績效獎金類的收益,往往會成為否定雙方雇傭(勞動)關系而被認定為合作關系的考量要素;而雇員無需承擔經營風險既是雇傭(勞動)關系的典型表征,亦可反之作為雇傭(勞動)關系認定的核心考量要素之一。
3.經濟來源上的依賴性與經濟地位上的弱勢性
該意義上的經濟從屬性強調雇員在經濟現實所造成的與雇主不平等的談判地位中,欠缺對勞動條件的決定權,且必須依賴于對雇主提供勞務賺得工資以求生存。人格從屬性下,雇員對于雇主必然存在經濟來源上的依賴性與經濟地位上的弱勢性。ILO 《雇傭關系建議書》將“向勞動者定期支付的報酬構成勞動者唯一或主要收入來源這一事實”作為雇傭關系認定的指標之一,并進一步指出如果自稱為“獨立承包商”的人在法律上有權向全世界出售服務,但實際上完全或實質上為一個雇主工作,這表明該人實際上是一名雇員。因此,一個人為多個雇主工作的事實并不一定表明其是獨立的承包商而不是雇員。〔66〕同前注〔15〕,ILO 文,第43 頁。雇員對雇主經濟來源上的依賴性必然導致經濟地位上的弱勢性,但在經濟來源上不具有完全的依賴性時,也可能在經濟地位上具有弱勢地位性。例如,對已累積相當財富而不必受雇于人,或不必依靠工資薪金來維持生計的勞動者群體來說,即便擁有財產,勞動者對雇主提供的工作要約同樣只能選擇接受或拒絕,不愿接受者只能退出勞動市場或自行創業,也因此具有經濟地位上的弱勢性。
若對經濟從屬性作經濟來源上之依賴性的理解,并將其作為雇傭(勞動)關系的認定要素,已經逐漸脫離了人格從屬性的等級權力和控制邏輯;而將其擴展至經濟地位上的弱勢性,則已體現出從屬性認定的另一邏輯線索——雇傭(勞動)合同的擴展適用。例如,葡萄牙《勞動法典》第10/13 條規定,履行合同的工作雖然不具有法律從屬性,但是應當遵守該法規定的原則,尤其是涉及人的權利、平等、不歧視和安全衛生工作,在不違背任何特殊立法的規定下,如果工人被認為對他行為的受益人存在經濟依賴性,該法將這些合同視為雇傭合同,并使其符合該法所訂明的原則。〔67〕同上注。德國學說上對從屬性的判斷標準亦存在經濟上從屬性(經濟生活的來源大部分來自他方當事人)的觀點,但有學者認為,此類從屬性導致的法律保護若非直接或間接出于契約約款拘束的結果,首先當由其他法律(如社會保險法)加以適當解決,而非一味地將之轉嫁勞務受領人負擔。〔68〕同前注〔5〕,林更盛文,第86 頁。德國勞動法針對雖不具有人格從屬性,而具有“經濟依賴性”和“與雇員有類似社會保護的需求”的“類雇員人”,提供區別于雇員的特別法律保護,〔69〕BAG July 6, 1995, NZA 12, p. 33 (1996); BAG Nov. 4, 1998, BB 54, p.11 (1999); Wolfgang D?ubler, Working People in Germany, Comparative Labor Law & Policy Journal, Vol.21, Issue 1, 1999, p. 88.即為一例。因此,單純經濟來源上的依賴性與經濟地位上的弱勢性是否能成為雇傭(勞動)關系認定的核心要素,不能從經典的雇傭(勞動)關系從屬性理論中尋找到依據和答案,而有賴于國家的立法政策考量與勞資利益衡量。
(三)經濟從屬性的概念涵攝與認定意義
在依據人格從屬性無法認定時,經濟從屬性是否可作為確認雇傭(勞動)關系的核心要素,及其是否應為雇傭(勞動)關系認定的必要要素,實則與其概念涵攝與解釋直接相關。對經濟從屬性作“經濟資源上的依賴性”的理解,將雇主擁有生產資料作為雇傭(勞動)關系認定的重要因素,根源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討論:勞動者一無所有只能為生計所迫出賣勞動,生產資料由資本家所有并由此控制勞動過程,以確保對剩余勞動的榨取。〔70〕See Michael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 30.此時,資本家(雇主)對生產資料的擁有與其對勞動過程的組織具有同質性,對工人勞動過程的控制而形成的人身從屬性與經濟從屬性得以重合。辛茨海默正是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從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來解釋控制權力的合理性,并認為其是決定依附性(從屬性)的支配力。我國有學者也明確將生產資料為勞動者本人還是他人所有,作為自營、獨立勞動與受雇、從屬勞動的區分因素。〔71〕參見王全興:《互聯網+背景下勞動用工形式和勞動關系問題的初步思考》,載《中國勞動》2017 年第8 期,第7 頁。隨著生產方式和組織形式的變化,大型資合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以及股權的分散化,使得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與勞動過程的控制者首先在形式上發生了分離,而在很多企業運營極少需要實物資本的行業中,雇主對雇員的支配權也并不必然源于其對生產工具、設備的所有權,“生產資料”的內涵被逐漸擴大。在2017 年的“閃送”案中,北京市海淀區法院認為,在互聯網經濟下新的用工模式中,交通工具并不是主要的生產資料,由“閃送App”平臺運營方同城公司通過互聯網技術所掌握的信息才是更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并借助對其的掌控權而在與李某的用工關系中處于強勢支配地位。〔72〕參見“‘閃送APP’平臺確認勞動關系案”,https://www.pkulaw.com/pfnl/a6bdb3332ec0adc4cb0b52b95e2f0210227a4dafce7c 1051bdfb.html?keyword=%E9%97%AA%E9%80%81,2020 年9 月1 日訪問。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數據”納入生產要素范疇,〔73〕《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并在《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中進一步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的要求,正式將“數據”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納入市場化配置與分配機制。筆者認為,審判實踐中將平臺企業掌握的市場供需等“信息”納入生產資料的范疇,為理解平臺企業的“控制權”及工人的經濟從屬性提供了符合勞動法傳統理論路徑的解釋方法,也揭示了平臺用工中控制權的根源并對其予以約束和責任負擔的合理性。
作為經濟資源依賴性的自然衍生,雇員無需承擔經營風險符合其提供勞務給付而收獲工資,而非參與資產性、管理性、經營性收益分配的雇傭關系的描述,更發展出勞務給付不能時雇主需依“企業風險理論”承擔工資給付風險,凸顯了對雇員的社會保護義務,這與平等勞務給付交換關系下的風險分配規則相異。在近期的典型案例中,法院將雇員申請報銷或審批報銷的行為認定系使用公司資源,為其向公司提供勞動形成便利并由公司承擔其行為的成本,而認定雙方之間符合勞動關系的經濟從屬性特征;〔74〕參見“普瑞森能源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與介智華勞動爭議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9)京01 民終3931 號民事判決書。而將公司僅從患者繳納的護理費中提取中介服務費,將近76%的護理費作為工資支付給勞動者的報酬計算方式理解為雙方對護理費的分成,而作出異于勞動關系中一般工資支付的認定,〔75〕參見“呂曉楊與常州枝秀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勞動爭議案”,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蘇04 民終2987 號民事判決書。均顯示了收益分配與風險負擔方式作為勞動關系認定核心要素的重要性。
因此,將經濟從屬性作“經濟資源上的依賴性”與“雇員無需承擔經營風險”的理解,與人格從屬性下雇員視角的“專屬性”“利他性”具有邏輯上的一致與自洽,并仍能為雇傭(勞動)關系“剩余控制權”與組織、交易成本理論所解釋與涵蓋,而成為雇傭(勞動)關系認定的核心要素。美國Borello 判斷規則中,“是否由用工方提供設備工具和工作場所”“雇員依賴于其管理技能而獲得收益或遭受的損失”,以及“雇員是否為了完成其工作任務而在設備和材料上進行的投資”即為上述兩項核心要素的體現。〔76〕See S. G. Borello & Sons, Inc. v. Dep’t of InduS. Relations (Borello), 48 Cal. 3d 341, 350 (1989).但在平臺用工的Razak v. Uber Technologies Inc.案,〔77〕See Razak v. Uber Technologies Inc. 2:16-cv-00573.和Lawsom v. Grubhub, Inc.案中,〔78〕See Lawson v. Grubhub, Inc., 302 F. Supp. 3d 1071 (N. D. Cal. 2018).美國賓州東區法院和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均基于“平臺并未對員工提供勞動工具”“員工對工作所需設備予以投資”的事實而作出否定雇員身份的認定,意味著上述經濟從屬性雖仍為雇傭關系認定的核心要素,但在新的用工形態和生產組織方式下,對原本與控制權一一對應的要素特征(典型如生產工具為雇主所有)的理解,以及是否將平臺提供的信息撮合數據作為生產資料的認識,將直接決定對雇傭(勞動)關系的認定。而案件的爭議與認知的模糊,并非主要來自經濟從屬性自身解釋力的匱乏,而是源于數字經濟和平臺用工中,組織者與勞動者對勞動過程的參與方式對傳統垂直權力關系工作范式的又一次突破,給理論與實踐帶來的陌生與不適感。在經歷最初的懵懂期后,司法實踐在現實逼迫下已愈發自信,控制權、從屬性認定規則依然具有強大的解釋力,在新業態下的勞動關系從屬性判斷中,冠以“經濟從屬性”之名的“經濟資源上的依賴性”與“雇員無需承擔經營風險”仍然得為雇傭(勞動)關系認定的核心要素。
而如前述,若以經濟來源上的依賴性與經濟地位上的弱勢性來界定經濟從屬性,則已脫離人格從屬性的等級權力和控制邏輯,在缺乏人格從屬性要素特征時,以二者的存在為由認定雇傭(勞動)關系或提供勞動法保護,則或是基于立法政策而對雇傭合同予以擴展適用(如葡萄牙勞動立法),或是基于對特定勞動者群體的特殊制度安排(如德國的“類雇員”制度)。二者雖為人格從屬性的必然結果,卻不必然能成為人格從屬性與雇傭(勞動)關系的認定要素,然而其在雇傭(勞動)關系認定日益模糊化的今天有別處之意義,即以其強弱為標準作為法律為所有對社會福利有需求的工作者提供合理保障的入口與依據。〔79〕參見婁宇:《平臺經濟從業者社會保險法律制度的構建》,載《法學研究》2020 年第2 期,第195 頁。
五、作為從屬性補充認定標準的組織從屬性——同質性與依賴性
組織從屬性一般被理解為雇員在雇主企業組織內部,雇員給付的勞動為雇主組織生產、經營過程中不可欠缺的一環。《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中,“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的規定即將組織從屬性作為勞動關系認定的必要要素之一,美國Borello 判斷規則亦存在“提供的服務是否是雇主業務的組成部分”這一判定要素。與經濟從屬性不同,組織從屬性的涵攝清晰,但在體系歸屬上則存在差異。我國臺灣地區的司法實踐將“受雇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配合“服從雇主權威,并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一同納入人格從屬性項下;大陸有學者將“雇員的工作是雇主業務的組成部分”作為經濟從屬性的體現,將其與“何方享受利潤和承擔風險,以及雇員收入的來源”作為并列邏輯項。〔80〕同前注〔55〕,謝增毅文,第1560 頁。在上述認識下,組織從屬性已與前文所述人格與經濟從屬性出現重合,這在一些國家的立法中亦有體現。葡萄牙《勞動法典》第12 條對雇傭關系的判定指標中,包含“工人是受益人活動的組織結構的一部分,并在受益人的指導下提供服務”,〔81〕同前注〔15〕,ILO 文,第37-38 頁。即將其歸在人格從屬性下;而南非《勞動關系法實踐法典》第18(C)條雇傭關系的推定規則認為,“如果申請人的服務是雇主組織或業務的組成部分”可被推定為雇員,但若一個人在經營自己的企業且承擔風險,則不構成雇員,因為雇主通常會承擔這類風險,〔82〕同前注〔17〕。即將其與經濟從屬性中的風險負擔相關聯。
ILO 《雇傭關系建議書》將“工人對企業的融入(企業對工人的整合)”作為雇傭關系認定的指標之一,并解釋組織從屬性所體現的“整合”的重要性:在新的工作組織形式中,控制越來越少,但整合越來越多。由于雇傭關系的多樣化,在確定雇主對時間、地點和方式上是否存在控制頗有難度,因此“融入組織結構”的概念在許多國家得到了更多的注意。在一些國家(法國、南非和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一體化”(integration)的概念越來越多地被用來作為存在雇傭關系的一個決定性指標。〔83〕同前注〔15〕,ILO 文,第37-38 頁。組織從屬性強調雇員對組織的融入即“一體化”或“整合”,基于此,需要進一步思考和討論的問題是,組織從屬性在雇傭(勞動)關系的認定中究竟是否擁有獨立的地位與價值?
(一)組織從屬性與人格從屬性的同質性
與雇傭勞動不同,承攬人的義務為一定工作的完成,其工作不必然融入定作人的事業,且獨立于定作人人事管理制度;受托人亦獨立處理委托人事物,且非屬于委任人組織編制的一員。而雇傭(勞動)契約下的雇員非僅受制于雇主個人的指揮命令,在現代企業組織形態之下,更需日常遵從雇主經營生產團隊的意愿、生產秩序及組織規則,其勞務給付行為構成雇主組織生產過程中的必要環節與整體事業經營的一部分。從此意義上言,組織從屬性為人格從屬性在現代企業生產經營下的形態呈現,故而與人格從屬性具有同質性。
(二)組織從屬性的特別意義
組織從屬性在雇傭(勞動)關系認定中的意義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變化。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組織從屬性成為區分產業雇傭與農業雇傭、家庭消費雇傭等非組織雇傭的區分點,并分化出由民法調整的傳統雇傭和由勞動法調整的產業雇傭關系。〔84〕參見鄭尚元:《雇傭關系調整的法律分界——民法與勞動法調整雇傭類合同關系的制度與理念》,載《中國法學》2005 年第3 期,第80 頁。時至今日,雖然《民法典》在其第七編“侵權責任”第三章第1191、1192 條對用人單位和個人勞務接受一方的“用人者責任”予以區分規定,但對于不具有組織從屬性的自然人雇傭關系的法律調整模式,在我國無論是立法還是學理均未有定論。與自然人、家庭雇傭不同,組織體系下的雇傭勞動大多非單獨即能達成雇傭(勞動)合同目的,雇員之間往往需相互配合并共同構成組織有機體,以使雇主因此有機體的存在而從雇傭(勞動)關系中收獲大于單個市場交易的利益,即組織收益大于組織成本與交易成本,從而為雇主建立企業、與雇員建立雇傭(勞動)關系,以及組織從屬性作為雇傭(勞動)關系的認定要素提供合理性解釋與正當性基礎。依此邏輯推演,產業雇傭與非組織性雇傭自應適用不同的雇主義務與勞動法保護制度。
隨著技術發展和專業分工精細化,工作對受雇人技術需求提高而導致其工作專業性與自由度亦大幅提高時,控制理論在決定該受雇人是否處于雇傭關系時將變得越發薄弱。〔85〕See Beloあ v. Pressdram Ltd. [1973] 1A11 ER 241, 250.正是在此背景下,英國隨后出現了組織標準(organization test,又稱為整體標準test of integration),以此說明在大規模等級組織內工作,但對工作方法、時間等有很大自主權并擁有專門技術的勞動者,被認定為雇員的理由,組織從屬性即成為對人格從屬性與控制標準的必要補充。
然而,組織形態和生產經營方式的進一步變化對組織從屬性的要素地位與權重產生了極大影響,這在目前平臺用工的爭議中尤甚。在前述Razak v. Uber Technologies Inc.案和Lawsom v. Grubhub, Inc.案中,法院雖均認為原告提供的服務為被告整體業務的一部分,但亦認為該要素屬于雇傭關系認定的次要要素,證明力度本身較弱。此外,平臺用工中勞動者的工作是否為平臺業務的組成部分本身也存在爭議,美國勞工部在前述2019 年針對網約工的意見中,將其僅僅只是通過平臺獲得工作機會,而其工作并不是平臺業務的組成部分作為否定其雇員身份的理由之一,而背后更深層的原因是,勞工部認為虛擬市場交易公司的主要業務不是為終端市場的消費者提供服務,而是提供一項連接網約工和消費者的網絡平臺指引業務。而在我國江蘇蘇州美團騎手勞動關系確認案中,〔86〕參見“寧波捷順食品配送有限公司與秦雅靜、秦某等確認勞動關系糾紛案”,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蘇05 民終212 號民事判決書。兩審法院均不認為平臺公司僅扮演市場供需信息撮合者的角色,認為外賣派送服務屬于配送公司的主要經營范圍,而勞動者的外賣配送是配送公司業務的組成部分,從而成為判決存在勞動關系的重要支持理由。我國2016 年實施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將網約車經營服務的界定最終落腳在“提供非巡游的預約出租汽車服務的經營活動”,規定網約車平臺公司要承擔承運人責任,對網約車平臺“信息撮合者”身份予以否定,從而為網約車司機勞動給付的組織從屬性提供重要指引。而在外賣騎手、閃送等其他平臺業務領域,平臺身份與法律地位則仍未有規范予以明確界定,此不僅關涉平臺企業性質是信息中介、服務公司,還是從事具體服務業經營企業的組織從屬性的判斷,還關涉平臺對任務的系統自動派單,是市場供需信息的撮合行為還是對處于接單狀態的勞動者工作任務的指派這一人格從屬性,以及平臺收益是平臺市場信息的服務費,還是對勞動者勞動創造價值的分享這一經濟從屬性的判斷,此時對平臺本身的認識與判斷,就經由“組織從屬性”繼而與人格和經濟從屬性相互關聯與呼應。在“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旗幟下,對上述問題所謂“讓子彈飛一會兒”的應對策略,既是給理論觀察與實踐發展以時間,更是讓就業與企業在政策模糊中得以保持與生存,其意旨遠超學理探討,以組織性質與行為判斷為基石的組織從屬性的要素權重權衡,便具有了濃重的政策色彩,而個案裁判則就更依賴于人格與特定意義經濟從屬性的要素判斷,才能獲得充分的說服力。
六、結語
雇傭(勞動)關系從屬性認定標準的體系構成,以人格、經濟和組織從屬性三者間的邏輯關聯與內涵區分為基礎,并需對“從屬性”成為雇傭(勞動)關系認定標準的內在機理予以解釋。在以“剩余控制權”與組織、交易成本理論解釋從屬性的等級權力和控制邏輯的基本路徑下,人格從屬性下的各項判斷要素作為雇傭(勞動)關系認定的核心要素能夠被證成,并能與“經濟資源之依賴性”與“雇員不承擔經營風險”之經濟從屬性獲得理論自洽與實踐一致。若將經濟從屬性作“經濟來源上的依賴性與經濟地位上的弱勢性”之解所具有的權重與意義,則應取決于特殊立法考量與制度安排。作為本與人格從屬性具有同質性的組織從屬性,其獨立價值隨企業經營組織發展與變遷而不斷變化,現今則體現出對人格與經濟從屬性更強的依附性。
正如前文所述,從屬性認定標準當前面臨空前的質疑與挑戰,在平臺用工中完全相同的案例背景下,同一微觀判斷要素會基于不同的認識而被賦予不同的權重,并導致相異的裁判結果。這些差異究竟是司法理性主義的結果,還是司法實用主義的需要?由于平臺用工這一新興事物的方興未艾、撲朔迷離和知之尚淺,至今還尚無答案,且使勞動法的法政策屬性日益彰顯。但是,理性與邏輯是法學研究與司法適用的根本,作為勞動法立論與展開的原點性問題,雇傭(勞動)關系從屬性認定標準的體系性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才能以強大的理論解釋力應對紛繁復雜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