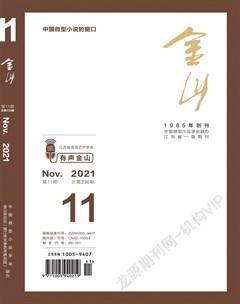破碎、圓滿以及“愛”的生成
錢暉
張潔寫就于1984年的《祖母綠》,現在讀來依舊引人深思。不難想象,在上世紀80年代男性作家熱衷于建構男性雄強形象的潮流中(如張承志《北方的河》中的“我”、路遙《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蔣子龍筆下的改革者形象、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等),《祖母綠》這個異數的出現多少令人感到訝異。張潔的《祖母綠》以婚姻愛情生活為主線,剖析了女性對愛的理解,演變及生成過程,簡單地說,這篇小說講述了兩女一男之間的愛情故事,情節雖略顯俗套,但文本中充滿了對女性情感和愛的意義的思考,加深了這篇小說的分量。小說寫到左葳在大學期間同時被盧北河和曾令兒愛慕著,當時曾令兒是以確定的身份陪伴在左葳身邊,并在幾次危難時刻拯救了他的生命。然而在黑板報事件上,曾令兒為了替左葳承擔“右派”罪責而被發配邊疆,盧北河成為一個替補如愿嫁入了左家,并努力協助左葳的事業。盧北河為了維護左葳現實利益和工作上的體面形象,幫助他挽回最后的尊嚴,主動策劃活動并邀請左葳的昔日戀人曾令兒擔任副組長。在小說敘述的過程中,張潔借助盧北河和曾令兒這兩個主要人物深入探討和思考了女性之愛的哲學意義。對于愛情的理解,每個時代的人都有迥然不同的看法,女性如何獲得愛,什么是真正的愛,也是這篇小說所思考的重大問題。張潔的高明之處在于她將女人兩種不同的情感觀念編織進一個故事里,又帶著女性意識進行抽絲剝繭的描摹,給讀者得出一個具有深度的關于愛的總結。
小說中書寫的幾乎是愛的殘片,如何將這些破碎的殘片拼湊成一個整體的愛之形狀,曾令兒這一女性形象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解讀的方向。曾令兒通過自身的經歷和體現,在懂得什么是愛這一過程中,不斷地建構又打碎關于愛的鏡像,她在鏡像的想象中建構,又在鏡像的破裂和粉碎后,逐漸理解和找回了愛的能力,最終獲得了個體生命的重生和情感的完滿。小說在處理這個問題時,首先從盧北河和左葳看似相敬如賓實則同床異夢的婚姻生活開始寫起,通過盧北河這個人物,來證明曾令兒的寬恕與博大。盧北河作為左葳的妻子,在愛面前戴著面具,在疲憊中又帶著提防。她當初為愛爭奪一切,如今看著與左葳的結婚照,卻感覺他們倆的脾氣、秉性、氣質、品位都不相同。但她了解左葳的心,她在承擔和滿足他所需要的一切,努力作為幕后幫手,在潛移默化中成了左葳的替補和工具,失去了作為女人的主體身份。我們能夠通過盧北河與左家婆婆之間的微妙關系中看出左葳是一個怎樣的男性。左葳對盧北河言聽計從,不過是一個空洞的能指,是徒有其表的男性符號,他看似忠誠、孝順、聰明,但事實上都只是幻象而已,他沒有個人才能更不愛任何人。老母親是左葳生命的給予者,是家族中的至高無上者,左葳在她的威嚴庇佑下并未實現真正的成長。在某種程度上,老母親是盛氣凌人的統治者,她保護左葳,排除他身邊所有不利的因素,并動用權力將左葳犯下的錯誤轉移到曾令兒的身上。在這一層面上,盧北河扮演著跟婆婆一樣的“母性”角色,雖然婆婆一輩子都未正視過盧北河的身份,但她早透過兒子的表象了解自己兒子的無能和卑瑣,所以她為了左葳的事業與人生,成全了盧北河這個對左葳十分有利的愛人。婆婆與盧北河都深知左葳“他是一個自信的男人,可要是沒有盧北河暗中的支持和斡旋,他又干得了什么?” 在這里,盧北河與婆婆都承擔著“母性”功能。在她們母腹般的溫暖的懷抱里,左葳這類男性既是情人又是兒子,享受到從食色到生活的全面滋養,左葳一直處于“母子同體”的階段,尚未重新整合起殘缺的自我。左葳只是一個意識到自己與女性身體差異的男性,他還未形成關于“自我”的認識,也未確認自己的主體地位。左葳在家里的兩個女人之間游移,心思總在情人曾令兒身上,他在午夜思考曾令兒的私生子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一直做著關于美人的幻夢,卻從未勇敢地承擔責任,而是反復強調“不會那么巧”以逃脫責任,他對曾令兒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種無比真誠的偽善。這種偽善可以在他去領與曾令兒的結婚介紹信時得到證明,“確知它已使自己道德完美、英勇無比的時候,左葳卻感到心里空空如也,步履飄浮。他不斷對自己說,曾令兒是他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可偏偏——偏偏不是他的情人了。”
我們在左葳的猶疑中逐漸了解了曾令兒的過往,因為“自我只有在他者”之中才能把自己確立為一個自我有意義的主體。讀大學時,因左葳生病,曾令兒為他補了一學期的課,那時的曾令兒是一個不完整的匱乏的形象,她頭發發油,皮膚干燥,她的不完美以此成就左葳精心打造的完整的“自我”形象,左葳在這種生活上的差異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優越感,使得自己的病癥得到了修復,也使得這種虛榮的愛得以膨脹。這種膨脹打著道德的名義逼向曾令兒,曾令兒和左葳在一起用了一個晚上,完成了一個婦人的一生。這種危險關系的發生,以及關系發生后陶陶的出現和死去,最終導致了曾令兒對和諧美滿愛情想象的徹底破裂。曾令兒也認識到“她只是愿意為一個她愛的人,做她所能做的一切。她實實在在希望聽到的是愛的回聲,而不是一種交換。而她也錯了,錯把那種交換,當作了愛的回應。” 曾令兒在回城的火車上,從新婚夫婦那里借來一本消遣讀物,翻到《星座運程》時出于好奇心,找到自己的生辰年月,看到上面寫著“祖母綠,無窮思愛”。在火車上遇見的新婚夫妻是曾令兒渴望的愛情長相廝守的鏡像,但這個鏡像因為曾得知左葳的生活之后,在和盧北河的對談后,在海浪無情的沖擊下變得破碎不堪。結局部分她要對新娘說“無窮思愛”時,就是對愛情的歌唱,她在整個愛的覺醒和覺悟后,尋回了自己的主體。由第三人稱的他即新娘支撐著曾令兒對情感的深刻理解,新婚夫婦夫人的悲劇讓她在愛的思索與建構中形成了一個模糊的印象,也就是對愛的一種堅定的信仰,這種信仰超越時代帶給她創傷與苦難,但這個“理想自我”畢竟只是幻象、心象,還不是真正的主體。要想成為主體,必須打碎之前對所有愛的幻想,真正領悟到愛時,才能真正地找回女性主體。
曾令兒后來在“無窮思愛”四個字中理解和完成了超越時空的愛戀,她的奉獻和寬恕,以及重獲愛的能力也成為她找回主體的標志。“我終于清楚了,在我心中恢復的不過是愛的感覺罷了。愛海灣、愛礁石、愛記憶、愛逝去的年華、愛我年輕時愛左葳的那顆心、愛微型電子計算機、愛微碼編制組,愛一切……卻偏偏不是愛左葳。我真高興,我重又變成一個可以充分感知的人。” 而在盧北河看來,一個人只要不再愛,他就勝利了,曾令兒對于她這句回復了一句“愛就談不上犧牲”。我們不難看到盧北河羨慕曾令兒,原因也許是她知道左葳誰也不愛,只愛他自己,但她無法脫離對方,她的悲傷源自“我”無法成為一個真正女人的遺憾。在某種程度上,她存在于左葳的世界里只是承擔著和婆婆一樣的“母性”功能。盧北河是傳統的,在傳統的家庭關系中承擔著丈夫的妻子這一附庸身份。而曾令兒已經完成覺醒,從失敗中完成獨立,與盧北河的見面相遇也是對過去的和解。同時她曾令兒還重新具有愛的能力,可以與服務生談笑風生,從卑微變得自信,從小愛到大愛,曾令兒已越過了內心的障礙走向人生的另一個高度。她將與左葳合作,既不是因為對左葳的愛或恨,也不是因為對盧北河的憐憫,而是為這個世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左葳對她,已成過去。她已在海邊的窗前得到了愛的呼應,正如她自己所說,“這種可以呼應的愛情,哪怕只有一天,已經足夠。因為還有那么多人,過完了沒有被呼應的人生。還要告訴她,‘無窮思愛那句話。” 至此,在幸福、破裂以及重新理解愛的坎坷進程中,在新婚夫婦這一鏡像的破碎后,曾令兒已經完全確立了自我的主體性。“無窮思愛”既是使曾令兒脫胎換骨的愛情箴言,也是小說努力做出的對完美之愛的一種闡釋,她在愛的鏡像破碎后重新獲得一個人的圓滿,那個真正的“愛”的意義也正是在這一刻悄然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