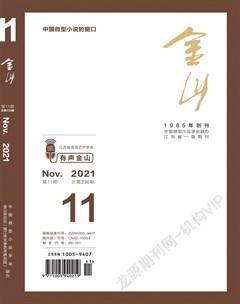傾聽是一種態(tài)度,更是一種美德
徐習軍
《金山》嚴主編轉(zhuǎn)來相裕亭的《 傾聽“海外”之聲》,要我談點看法,這也是“相峙南徐”欄目一以貫之的風格,要體現(xiàn)出“不同”的聲音,否則何“峙”之有。況且,我讀了《 傾聽“海外”之聲》確實讀出了與文題字面意義相反的“異樣”的聲音,為此,我也來發(fā)出點“雜音”,如有得罪,請裕亭兄見諒。
《傾聽“海外”之聲》寫的是在常德舉行的“第七屆武陵國際微小說節(jié)”的事,我沒有參加會議,但關(guān)注朋友圈和媒體報道,幾乎所有朋友在群里、圈里所發(fā)的都是溢美和贊賞。裕亭文中也說“邀請的領(lǐng)導、嘉賓,好多都是國外來的”,據(jù)裕亭文中描述:“中午,已過了午飯時間,我們會場那邊的發(fā)言,還在‘傳遞話筒之中。各地來的作家(應(yīng)該說是各個國家來的作家、文學評論家們),還在激情高漲的發(fā)言中。”看來會議安排非常好,按理說這是和海外華文作家交流的一次好機會,可是相裕亭文中讀不出絲毫的“滿意”。
盡管裕亭說我“長期”與他作“懟”,我還得就此說道說道,如果還以為是作“懟”,那也是善意“懟”你。
每個活動都有特定的活動宗旨,本次微型小說節(jié)兩天的活動中,分別舉行了“‘善德武陵杯·全國微小說精品”“‘田工杯·廉潔(勤廉)微小說全國征文”頒獎大會、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創(chuàng)作研討會等系列活動,主打是“頒獎會”,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創(chuàng)作研討這個環(huán)節(jié)的安排,恰恰是海內(nèi)外作家、評論家交流信息的很好機會,裕亭因為留給他(作者)的發(fā)言機會太少而心存不滿。
這就涉及到一個對自己定位的問題。本次活動海內(nèi)外的,中國作協(xié)、中國微型小說學會等各方面的領(lǐng)導、評論家、作家來的很多,難道高層次的領(lǐng)導、評論家以及不遠萬里海外來的作家不安排先發(fā)言只“聽”你裕亭及國內(nèi)作者先“發(fā)言”就對了嗎?這是一個世界華文微型小說交流盛會,當然應(yīng)該盡可能多讓海外作家、學者交流信息,這一點裕亭定位沒有搞準,長期以來裕亭自以為“國內(nèi)一流”了,別人就應(yīng)該聽他這個“名家”發(fā)言才對的。其實,每個活動都有主旨,活動主辦者對參會者邀請或不邀請都是周密籌劃的。更何況這么好的機會你不珍惜,這是不求上進的表現(xiàn)。
裕亭在文中對“外宣工作”也不無“抹黑”之意。武陵國際微小說節(jié)就是一個外宣活動,經(jīng)過努力武陵微小說已經(jīng)成為了常德獨特的城市文化名片。“搞過外宣”的裕亭怎能不知道活動主旨呢?還要為他這樣有名氣的作家沒能發(fā)言而感覺“不關(guān)自己的事”,這理解就錯了。
裕亭在文中寫道:“話題再回到我們微小說(小小說)的各種‘節(jié)日‘研討等活動,每一次活動的‘話語權(quán),可能都不在創(chuàng)作者這邊,多數(shù)是領(lǐng)導給我們指明方向,批評家指出我們存在的問題。”扯到“話語權(quán)”的高度,對于真正善于“傾聽”的作者,“領(lǐng)導給我們指明方向,批評家指出我們存在的問題”這是何等的好事啊,不吸收“方向性”的意見,你能搞好創(chuàng)作?
作為一個微型小說作家,裕亭的“名氣”是響當當?shù)模@在業(yè)界人所共知……裕亭如果覺得自己的微型小說已經(jīng)“爐火純青”了,那么多寫一篇、多出一本也就沒有什么意義了,是不是可以開拓自己,去搞搞批評、搞搞理論研究,甚至搞搞文史、搞搞經(jīng)濟或文化產(chǎn)業(yè)呢?
傾聽不是簡單地用“耳朵”來聽,而是要用“心”領(lǐng)悟。傾聽還是一種“態(tài)度”,善于傾聽是與人為善、心平氣和、虛懷若谷的表現(xiàn);“傾聽”可以汲取知識信息,提升自己;“傾聽”更是一種營造團結(jié)、友愛、和睦氛圍所必須的處世哲學。
不知裕亭兄是否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