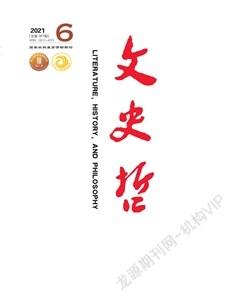傳統話語背景下近代維新派的民權觀
孫曉春
摘 要:維新派的民權觀是近代中國思想界向西方學習過程的重要環節,維新派有關民權的討論始于中日“甲午戰爭”以后,維新派闡釋民權的過程與其理解和接受西方近代價值理念的過程是基本相應的。權利與權力是維新派理解民權的兩個維度。把近代的自由、平等理念置于傳統話語背景下加以解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近代中國思想界的進步,但傳統話語也導致了維新派民權觀的理論局限。
關鍵詞:維新派;民權;權利;權力;傳統話語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1.06.15
毛澤東同志在論及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歷史時說:“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①民權觀念引入中國并且日益為人們所接受,便是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重要環節。自1879年郭嵩燾首次使用“民權”概念之后,到了“戊戌維新”時期,民權逐漸成為思想界所關注的主題。以汪康年、梁啟超、何啟、胡禮垣為代表的維新派,在認識和理解西方近代價值理念的基礎上,把這一概念放在中國傳統話語下加以闡釋,從而使“民權”成為中國近代思想界可以理解的術語。由于自身的知識背景和對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理解水平所致,維新派的民權觀不可避免地帶有理論的局限。解讀近代維新派的民權觀,對于認識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革與觀念變革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權力與權利:維新派民權觀的兩個維度
關于中國近代民權觀的來源和路徑,有人認為,“民權”概念是通過日本輸入的,是“民主”(democracy)一詞的日本譯法。近代日本人把democracy譯為“民權”,其用意是強調人民的權力②。不過一些新近的研究表明,“民權”并不是democracy的日譯,democracy在日語中更多的是被譯為“民主”③。實際上,“民權”不僅不是democracy的日本譯法,甚至最初也不是由日本引入。
“民權”一語最早見于清駐英公使郭嵩燾的旅歐日記。在述及英國布雷福德織布機廠工人罷工事件時,郭嵩燾說:“西洋政教以民為重,故一切取順民意。即諸君主之國,大政一出自議紳,民權常重于君……亦西洋之一敝俗也。”④郭嵩燾這篇日記寫于光緒四年(1879),當時,郭嵩燾所以提出“民權”的概念,主要是基于對近代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觀察,而不是由于日本學界的影響。不過,郭嵩
作者簡介:孫曉春,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天津 300350)。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政治倫理思想通史”(16ZDA104)的階段性成果。
①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358頁。
② 較有代表性的說法可參見韋杰廷、陳先初:《孫中山民權主義探微》,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4頁。
③ 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見溝口雄三:《中國民權思想的特色》,孫歌譯校,夏勇編:《公法》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頁;王人博:《中國的民權話語》,《二十一世紀》總第6期,2002年。
④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84年,第575576頁。
燾在提出“民權”概念的時候,并沒有對這一概念作出說明,于是,“民權”便成了一個缺少定義的概念,這一概念的內涵只能由人們在后續的討論中去賦予。
郭嵩燾以后,“民權”的概念也見于黃遵憲編撰的《日本國志》,書載明治八年(1887)年板垣退助復歸元老院,“遂倡民權自由之說”黃遵憲:《日本國志·國統志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4頁。。由此可知,當時日本人是把民權與自由聯系在一起考慮的。不過,在甲午戰爭以前,民權尚未成為中國思想界討論的主題,日本學界的民權觀念對中國思想界也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
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促使人們把注意力從經濟、技術轉移到了政治方面。梁啟超在論及這一時期思想界的變化時說:“自從和日本打了一個敗仗下來,國內有心人,真像睡夢中著了一個霹靂,因想道堂堂中國為什么衰敗到這田地,都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變法維新做一面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44頁。當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政治方面的時候,“民權”逐漸成為思想界關注的話題。
近代維新派最初是用權力的觀點理解“民權”的,這種認識最早見于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余嘗閱萬國史鑒,考究各國得失盛衰而深思其故,蓋五大洲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君主者,權偏于上,民主者,權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北京:朝華出版社,2017年,第9495頁。《盛世危言》成書于1894年,鄭觀應的這段話代表了當時思想界對于民權的基本理解。到了1896年,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等人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同年刊發了汪康年《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一文,汪康年認為,在中國君權漸失的情況下,“參用民權”是君權得以行使的必要條件,“必民權復,而君權始能行”,“夫民無權,則不知國為民所共有,而與上相睽;民有權,則民知以國為事,而與上相親。蓋人所以相親者,事相謀、情相接、志相通也”汪康年:《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汪林茂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汪康年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2、13頁。。次年,《時務報》又刊發了梁啟超《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梁啟超依據康有為的“公羊三世說”對民權問題作了解釋:“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為政之世,二曰一君為政之世,三曰民為政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梁啟超:《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飲冰室合集·文集》第2冊,第7頁。梁啟超斷言,“君政”必然為“民政”所取代,但“民政”又是有條件的,“必其民之智甚開,其民之力甚厚”。一旦實行“民政”,“既舉一國之民而智焉、而力焉,則無復退而為君權主治之治”梁啟超:《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飲冰室合集·文集》第2冊,第10頁。。與鄭觀應一樣,汪康年、梁啟超這一時期所理解到的“民權”也是一個權力的概念。
1902年,康有為在辯白其君主立憲主張時說:“仆在中國實首創言公理,首創言民權者。”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76頁。實際上,戊戌維新時期的康有為并沒有直接討論民權問題,能與民權問題扯上關系的只有代內閣學士闊普通武撰寫的《請定立憲開國會折》。康有為在這篇奏折中說:“竊聞東西各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康有為:《請定立憲開國會折》,《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338頁。折子交付廷議時,遭到了孫家鼐等人的反對,其理由便是“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康有為:《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折》,《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340頁。。可見,在戊戌維新時期,變法的推動者和反對變法的保守勢力都把民權理解為權力,所不同的是,在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那里,“民權”是君權得以強固的輔助物,保守派則把民權看作是與君主權力截然對立的東西。如此看來,當民權被理解為權力的時候,它既可以是維新派變法的理由,也可以成為保守勢力反對變法的理由。
盡管把民權理解為權力是甲午戰爭至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的主流認識,但在當時,一些對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有所了解的思想家,傾向于用近代的自由觀念來闡釋民權,進而把民權理解為權利的概念。在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是嚴復和香港的何啟、胡禮垣。1895年2月,嚴復在天津《直報》發表了《論世變之亟》一文,在介紹西方近代的自由觀念時,嚴復說:“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毋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為逆天理,賊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皆侵人自由之極致也。故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為此設耳。”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頁。嚴復的這段話雖然不是對西方近代自由思想的準確表達,但“唯天生民,各具賦畀”一語,所表述的卻是近代天賦權利的觀念,“人人各得自由”便是每個人的天賦權利。
在戊戌維新時期的民權話語中,“人人各得自由”也被表述為“人人有自主之權”。1898年,也就是戊戌變法的同一年,張之洞的《勸學篇》刊行,書中對當時業已流傳的“人人有自主之權”觀念進行了駁難:“考外洋民權之說所由來,其意不過曰國有議院,民間可以發公論、達眾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攬其權。譯者變其文曰‘民權,誤矣。近日摭拾西說者,甚至謂人人有自主之權,益為怪妄。此語出于彼教之書,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靈,人人各有智慮聰明,皆可有為耳。譯者竟釋為‘人人有自主之權,尤大誤矣。”張之洞撰,馮天瑜、姜海龍譯注:《勸學篇·正權》,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11頁。張之洞的這段話表明,“人人有自主之權”的觀念在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已經開始流行。
生活在香港的何啟、胡禮垣,對于“人人有自主之權”的民權觀念作了較為系統的闡述。兩人自幼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何啟曾經留學英國,對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何啟回到香港以后,兩人合寫了許多政論文章,宣傳變法維新的思想主張。就在張之洞的《勸學篇》刊行的第二年,何啟、胡禮垣作《〈正權篇〉書后》,系統反駁了張之洞有關民權的觀點。
關于“人人有自主之權”的民權觀念,何啟、胡禮垣作了正本清源的解釋:“‘里勃而特(liberty——作者注)譯為自由者,自日本始。雖未能盡西語之意,然以二字包括之,亦可謂能舉其大由。自由二字而譯為民權者,此必中國學士大夫讀日本所譯書者為之,其以民權二字譯里勃而一語,吾無間然,獨惜譯之者于中外之理未能參究,其同閱之者,或至誤猜其意。”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二)》,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影印本,第670671頁。按照何啟、胡禮垣的說法,當時人們所說的“民權”,實際上是英文liberty的中國譯法,而這個詞在日本是被譯為“自由”的,只是中國學者從日文轉譯時譯成了“民權”。維新派思想家把“自由”轉譯為“民權”的同時,也就把“權利”的內涵賦予了“民權”概念。
戊戌維新之后,康、梁等人流亡日本,這使得他們有機會接觸到日本明治以來流行的民權觀念,他們對民權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1900年,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寫了一篇題為《地球第一守舊黨》的短文,就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實行的文化閉鎖政策指斥道:“禁斷外國的學問”,就是要“禁精神上之學問”,而“精神上之學問”就是“民權自由”。“民權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也”,壅塞自由的結果只能是“壅之愈甚,則決之愈烈”梁啟超:《自由書·地球第一守舊黨》,《飲冰室合集·專集》第2冊,第6頁。。梁啟超這里所說的民權自由,與黃遵憲《日本國志》中記述的板垣退助的民權觀念已無二致,這意味著梁啟超也已經對權利的民權觀有所了解。
戊戌變法以后,康有為也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權利的民權觀。論及民權與憲政問題,康有為說:“今歐美各國,所以致富強,人民所以得自主,窮其治法,不過行立憲法、定君民之權而止,為治法之極則矣。”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475頁。這里,“人民得以自主”,強調的就是近代自由主義思想家所說個人權利,而“定君民之權”雖然還不是西方近代思想家所說在權力與權利之間劃定一個邊界,但也不再是他在變法時期所主張的“君民共治”。
戊戌維新時期,以汪康年、梁啟超為代表的內地維新派人士在最初之所以把民權簡單地理解為權力,主要是因為他們當時對西學所知不多,如梁啟超所說,“吾既未克讀西籍,事事仰給于舌人”梁啟超:《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飲冰室合集·文集》第2冊,第10頁。。許多年后,梁啟超在追述戊戌變法的情形時還說:當年康有為、梁啟超這一班人,“中國學問是有底子的,外國文卻一字不懂,他們不能告訴人‘外國學問是什么,應該怎么學法,只會日日天天大聲疾呼說‘中國舊東西是不夠的,外國人許多好處是要學的”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冊,第44頁。。再由于維新派思想家自身的知識背景,他們起初只能用權力的觀點理解民權,即使在后來接受了權利的民權觀,他們也仍然沒有放棄權力的觀點。例如,梁啟超在解釋強權的概念時便曾說:“強權云者,強者之權利之義也。英語云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此語未經出現于東方,加藤氏譯為今名。何云乎強者之權利?謂強者對于弱者而所施之權力也。自吾輩人類及一切生物世界乃至無機物世界,皆此強權之所行,故得以一言蔽之曰:天下無所謂權利,只有權力而已。權力即利也。”梁啟超:《自由書·論強權》,《飲冰室合集·專集》第2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9頁。按照梁啟超的說法,權力就是統治者的“權利”,“強權”也是權利,只不過是統治者的權力,“故謂自由權與強權同一物,驟聞之似甚可駭,細思之實無可疑也”梁啟超:《自由書·論強權》,《飲冰室合集·專集》第2冊,第31頁。。這表明,梁啟超對民權的理解一直是在權力與權利這兩個維度之間搖擺不定。思想家在理論上的搖擺必然影響到他們對于民權的深入理解。
二、維新派對近代價值理念的本土闡釋
在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民權觀念的傳播是一個過程,這與近代中國人學習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過程基本相應。可以說,人們在怎樣的程度上理解了西方近代的價值理念,也就在怎樣的程度上理解了民權。
如前所述,戊戌變法失敗以后,隨著康、梁等人流亡海外,他們對于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逐漸接受了權利的民權觀,而不是像以往那樣把民權單純地理解為權力的概念。這樣,以康、梁為代表的內地維新派對民權的認識,便與香港的何啟、胡禮垣愈益接近,這一思想變化是在近代思想文化的影響下發生的。因此,維新派闡釋民權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闡釋近代自由、平等觀念的過程。
維新派的民權觀首先體現了對西方近代自然權利觀念的理解。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是17世紀以笛卡爾、斯賓諾莎、洛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所倡導的價值理念,這一理念的核心便是認為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生存、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權利,斯賓諾莎說:“所謂天然的權利與法令……這是自然的最高的律法與權利。所以每個個體都有這樣的最高的律法與權利。”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溫錫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12頁。此后,洛克在《政府論》中也闡述了這一思想,洛克認為,“人類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權利”約翰·洛克:《政府論》(下),葉啟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3頁。;并且認為,人類曾經有過一個自然狀態,在這個狀態下,“人具有處理他的人身或財產的無限自由”,任何人都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約翰·洛克:《政府論》(下),第6頁。。維新派接受了這一觀念,這在何啟、胡禮垣的民權觀中體現得尤為明確。
維新派把西方近代思想家所說的自然權利解釋為“天賦之權”,亦即后來學界習用的“天賦人權”。何啟、胡禮垣說:“以大經大法之至正至中者而論,則權者乃天之所為,非人之所立也。天既賦人以性命,則必畀以顧此性命之權,天既備人以百物,則必與以保其身家之權,是故有以至正至中而行其大經大法者,民則眾志成城以為之衛,有不以至正至中而失其大經大法者,民則眾怒莫壓而為之摧,此非民之善惡不同也,民蓋自顧性命自保身家,以無負上天所托之權然后為是已。”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后·正權篇辯》,《新政真詮》,第644645頁。何啟、胡禮垣所說的“大經大法”,應該就是西方近代思想家所謂的自然法。在西方近代思想家那里,自然法至高無上,每個人的自然權利都是由自然法所賦,“自然狀態有一種為人人所應遵守的自然法對它起著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導著有意遵從理性的全人類”約翰·洛克:《政府論》(下),第6頁。。或許因為“自然法”在中國傳統話語中是難于理解的概念,何啟、胡禮垣將其轉換為“大經大法”,他們雖然沒有說明“大經大法”究竟是什么,卻認為,大經大法是“至中至正”的,受這個大經大法保護的天賦之權也是至高無上的。維新派不僅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家的自然權利觀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家的論證邏輯。
在接受自然權利觀念的同時,維新派也接受了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觀念。近代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把人假定為自由平等的主體——人的自由與生俱來。用盧梭的話說,就是“人是生而自由的”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8頁。,因為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和獨立的”約翰·洛克:《政府論》(下),第6頁。,人的生命、財產和自由便是不可剝奪的。在英國留學期間學習法律的何啟,對近代的自由理念有著較為深刻的理解,在《正權篇辯》中,何啟、胡禮垣援用《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一語,表達了人生而自由的觀念:“夫里勃而特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義如一。性曰天命,則其為善可知矣。道曰率性,則其為自由可知矣。是故凡為善者,純任自然之謂也。”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后·正權篇辯》,《新政真詮》,第670671頁。何啟、胡禮垣認為,西方人所說的人生而自由與傳統儒家的“天命”“率性”具有相同的意義,“天命之謂性”,就是人類之善本于天,“率性”就是自由。這一表述雖然并不準確,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說法卻使自由成為中國思想界可以接受的觀念。
何啟、胡禮垣之外,沒有受過西式教育的梁啟超,也認識到了自由是民權的根本問題。他在《自由書》中說:“自由者,精神發生之原力也。”梁啟超:《自由書·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飲冰室專集》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36頁。在論及中國軍隊何以孱弱的原因時,梁啟超說:“今中國之有兵也,所以鈐制其民也。奪民之性命財產,私為己有,懼民之知之而復之也。于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視民也如盜賊,民之視政府亦如盜賊,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也亦如芥,似此者,雖日日激厲之,獎榮之,以求成所謂武士道者,必不可得矣。”梁啟超:《自由書·中國魂安在乎》,《飲冰室專集》第2冊,第38頁。因為沒有自由,梁啟超稱中國的軍隊為“無魂之兵”。梁啟超顯然認識到了自由對于社會生活的重要性。
在把民權理解為自由,亦即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的同時,維新派也把民權理解為每個人的平等權利。何啟、胡禮垣在解釋“民權”概念時說:“民權者,以眾得權之謂也……以善善從長,止問可之者否之者人數眾寡,不問其身分之貴賤尊卑也,此民權之大意也。”這是在說,每一個社會成員,無論其社會地位如何,在社會生活中都有同等的權重,“而人人自主之權,則不問其人所居之位何位,所為之事何事,其輕重皆同,不分軒輊故也”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后·正權篇辯》,《新政真詮》,第671672頁。。
戊戌維新時期,內地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很少說到平等,但當他們流亡海外,接受了“自由民權”的觀念以后,對平等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例如,康有為的“公羊三世說”把人類社會的歷史分為據亂、升平、太平三個階段,并且認為太平世的特征就是平等:“(《春秋》)分據亂、升平、太平三世。據亂則內其國,君主專制世也;升平則立憲法,定君民之權之世也;太平則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1902年春),《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476頁。后來,康在為在所著《大同書》中表達了他對“人生而平等”這一命題的理解,“夫人類之生,皆本于天,同為兄弟,實為平等,豈可妄分流品,而有所輕重,有所擯棄哉?”《大同書·丙部·去級界平民族》,錢鐘書主編,朱維錚編校:《康有為大同論二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62頁。《大同書》的主題雖然不是民權,書中討論的問題卻與近代民權觀有著密切關聯。
近代的自由、平等觀念依賴于一個假定的前提,即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存在者,每一個人都有道德判斷的能力,維新派“人人有自主之權”的觀念依賴的便是這一前提。何啟、胡禮垣說:“聰明智慮,賦之于天,而所以用其聰明智慮者,其權則自主于人。視者,人之所能也,而不欲視則不視,聽者,人之所能也,而不欲聽則不聽。上帝予人以性靈,而使之大有可為者,惟其視所當視,聽所當聽,無勉強,無縛束,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耳。此而謂之有為,則真有為也。”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后·正權篇辯》,《新政真詮》,第663頁。雖然視、聽、言、動為傳統儒家習用的術語,何啟、胡禮垣的闡釋卻遠遠超出了傳統儒家思想的界囿。雖然傳統儒家素有重民傳統,但歷代儒家一直把民眾視為愚昧無識的群體,“夫民之為言,瞑也,萌之為言,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賈誼:《新書·大政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66頁。由于對民眾道德理性的悲觀估價,儒家把民眾設計為教化、提防的對象,“大為之坊,民猶逾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禮記·坊記》,《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618頁。。何啟、胡禮垣顛覆了傳統儒家的這一認識,在何、胡二人看來,視、聽為“人之所能”,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理性能力,都能做到“視所當視,聽所當聽”,而不需受制于人,“無勉強,無縛束”是他們應該擁有的生活狀態。
在維新派有關民權的認識中,還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西方權力制衡觀念的影響。就近代中國的社會歷史環境而言,無論民權被理解為“權力”還是“權利”,最終都匯聚到共同的一點:如何約束現實生活中的權力。在這一問題上,維新派不約而同地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權力制衡觀念,通過君主立憲的方式來約束權力是他們的基本共識。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曾經對西方國家的君主立憲政體有過一番描述:“蓋自三權鼎立之說出,以國會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總之,立定憲法,同受治焉。人主尊為神圣,不受責任,而政府代之,東西各國,皆行此政體,故人君與千百萬之國民,合為一體,國安得不強?”康有為:《請定立憲開國會折》(1898年7月),《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338頁。在戊戌維新時期,中國思想家對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所知不多,康有為對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能夠描述如此已屬不易。如果說這一時期的康有為還沒有弄清開國會、定憲法與民權之間的關系,何啟、胡禮垣則對此作了明確的說明:“是故中國之不能富強者,由不明民權之故,然則立強中御外之策,而欲以忠義號召天下之心,以朝廷威靈合九洲之力,以成天經地義之道,而行古今中外不易之理者,其為設議院立議員而復民權矣。”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后·正權篇辯》,《新政真詮》,第674頁。何啟、胡禮垣立憲主張的主旨也是約束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權力。
維新派的民權觀包含的諸多近代思想元素表明,維新派對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特別是受過西式教育的何啟、胡禮垣等人,對于自由、平等的認識已經很接近近代思想家的原意。然而,當他們援用這些觀念闡釋民權的時候,又必須借用中國傳統話語把近代思想觀念表達出來,即盡可能地把自由、平等這樣一些概念還原到中國思想傳統話語中加以解釋,這樣,維新派民權觀中所包含的近代觀念,便不再是原原本本的近代觀念,而是近代價值觀念與中國傳統觀念的混合體。傳統話語背景下的民權觀,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了中國傳統思想的印痕。在這里,姑且不論維新派對近代價值理念的闡釋是否準確,我們需要追問的是,近代維新派為什么會用這種方式來闡釋民權觀念?
在文化傳播的意義上說,維新派把西方近代的價值理念放在中國傳統話語中加以闡釋的做法有其合理性。中日甲午戰爭以后,維新派接觸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渠道有兩條,其一是日本學界的轉介,如梁啟超等人的民權觀便在流亡日本時發生了改變;另一渠道是如何啟、胡禮垣等人與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直接接觸,相比于日本學界的轉介,這條渠道顯然更為簡捷。兩人所受的新式教育,特別是何啟留學英國的經歷,使得他們對近代自由、平等的價值理念的解讀也比康有為、梁啟超更為準確。但是,對于維新派來說,無論他們是通過什么渠道獲得的近代價值觀念,這些觀念都是舶來品,他們所面對的共同問題就是如何使這些觀念成為人們能夠理解和接受的知識。做到這一切的前提,就是把他們理解到的近代價值理念用人們熟悉的話語表達出來,而傳統的儒家思想便是當時的中國思想界最為熟悉的話語,對于維新派來說,這是使他們所認可的價值觀念能夠為人們接受的唯一可靠的途徑。
維新派在闡釋其民權觀念的過程中,無法擺脫的是中國傳統價值觀念的影響。在任何歷史時代,人們樂于接受的總是與其固有的價值觀念相去不遠的東西。當維新派表達西方近代的價值理念的時候,亟須向當時中國思想界乃至整個中國社會證明,他們所倡導的民權、自由、平等,在道德意義上是對的。在他們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人們普遍接受的是傳統儒家的倫理政治學說,這就決定了維新派只能把他們所肯認的東西放在傳統的儒家話語背景下去印證,此外別無選擇。
三、維新派民權觀的意義與局限
維新派是中國近代最早倡導民權的思想家群體。按照梁啟超的說法,中國近代向西方學習的過程,經歷了器物、制度、觀念三個階段,一般以為,近代中國人在思想層面上學習西方始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實際上,維新派對民權的理論闡釋,才是近代中國觀念變革的開端。
維新派對于民權的認識是近代中國思想界具有重要意義的進步。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素有重民傳統,傳統儒家強調民眾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把民眾看作是國家成敗興亡的決定性力量,甚至有些時候還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諸子集成》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573頁。。但是,在傳統儒家的觀念中,民眾從來不是權利的主體,而只是統治階級的治理對象關于傳統儒家的民本思想,可參見拙作《儒家民本思想發微》,《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年第5期。。近代維新派有關民權的認識,無論把民權理解為“權力”還是“權利”,都在根本上顛覆了儒家的傳統觀念。維新派民權觀的理論價值,就在于以近代的方式理解“民眾”,認識到了以往思想家不曾意識到的民眾的價值。
維新派對于民權的理論闡釋,開啟了近代中國社會觀念變革的歷史進程,雖然維新派主導的變法運動失敗了,在戊戌變法失敗到辛亥革命爆發這一段時間里,由于滿清貴族集團的倒行逆施和清末新政的破產,改良變法的出路被徹底堵死了,維新派的君主立憲主張愈發不合時宜,這決定了維新派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在辛亥革命前夕,維新派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之間在立憲還是共和,改良還是革命等問題上有著嚴重的分歧,但在倡導民權這一點上,他們卻是一致的。這意味著,維新派的民權觀,作為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思想元素,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但是,維新派的民權觀畢竟是在近代中國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在他們所生活的歷史時代,人們對近代文明所知尚少,加之語言、知識背景等方面的原因,對于西方近代的先進思想文化的理解也十分有限,當他們刻意把近代的價值觀念放在中國傳統話語背景下來表達的時候,便不可避免地帶有理論局限。維新派民權觀的理論局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維新派對西方近代價值理念與中國傳統思想存在著雙重誤讀。
維新派在闡釋其民權主張的時候,無論是內地的康有為、梁啟超、汪康年,還是香港的何啟、胡禮垣,都把他們所理解到的西方近代思想觀念,轉換到傳統儒家的話語體系中來,試圖在儒家思想傳統與近代價值觀念之間找到通約之處。他們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要說明,西方近代思想家所倡導之價值觀念,中國古已有之;另一方面則是要說明,他們所倡導的民權、自由、立憲主張在道德的意義上是正當的。對于生活在19世紀末葉的維新派來說,這或許是把近代價值理念引入中國的可靠方式。然而,維新派并沒有意識到,傳統儒家的政治思想與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在價值層面上并不可通約,當他們著意尋求這兩種思想之間的融通之點的時候,他們也在有意無意間曲解了傳統儒家思想和西方近代政治思想。
戊戌維新期間,康有為在寫給光緒帝的奏折中說:“吾國行專制政體,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蓋千百萬之人,勝于數人者,自然數矣。其在吾國之義,則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故黃帝清問下民,則有合宮;堯舜詢于芻蕘,則有總章;盤庚命眾至庭,《周禮》詢國危疑,《洪范》稱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孟子稱大夫皆曰,國人皆曰,蓋皆為國會之前型,而分上下議院之意焉。”康有為:《請定立憲開國會折》,《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338頁。康有為“吾國行專制政體”的說法雖然是對的,可是,他轉而認為,開國會、立憲法、行民權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本來就有的,傳說中的“黃帝清問下民”、《周禮》中的“三詢”、《尚書·洪范》的“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就是君主立憲的本原形態,這顯然是一種牽強附會的解釋。康有為既誤讀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思想與文化,也曲解了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香港的何啟、胡禮垣身上。在論證民權就是“人人有自主之權”這一命題時,何啟、胡禮垣說:“一切之權皆本于天,然天不自為也,以其權付之于民,而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天聰自民聰,天明自民明,加以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天下之權惟民是主,然民亦不自為也,選立君上以行其權,是謂長民。”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后·正權篇辯》,《新政真詮》,第645頁。何啟、胡禮垣的本意是要闡述近代的自然權利觀念,他們把與生俱來的權利表述為“一切之權本于天”或可理解,但下文“天不自為也,以其權付之于民”,“民亦不自為也,選立君上以行其權,是謂長民”,卻是地地道道的儒家話語,循著這一邏輯推導出的結果依然是“天生民而立之君”。再如,為了說明民權的重要性,何啟、胡禮垣說,“天子之權得諸庶民,故曰得乎邱民而為天子也”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后·正權篇辯》,《新政真詮》,第645頁。。這樣,一個有關民眾權利的論題,最終回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傳統話語。
其次,維新派對近代民主政治缺乏準確理解,使得他們過度沉迷于君主立憲政體。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民權是與民主政治緊密聯系的議題,思想家對于民權的認識,必然歸結于對民主政治的理解。按照一般的邏輯,在中國近代史上極力倡導民權的維新派,一定會贊同民主政治。可是,維新派的民權觀卻有一個反乎常識的傾向,在有關國家政治制度的認識方面,他們大都反對民主而主張君主立憲。如前面引述的那樣,早期維新派代表人物鄭觀應在闡述其立憲主張時,把東西方各國的政治體制分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種類型,并且認為三者之中,君民共主的立憲體制為最好:“凡事雖由上下院議定,仍奏其君裁奪,君謂然即簽名準行,君謂否則發下再議。其立法之善,思慮之密,無愈于此。”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第95頁。鄭觀應所說的“民主”是指共和政體,而“君民共主”則是君主立憲政體。他不知道,二者都是近代民主的政體形式。鄭觀應如此說,說明其對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了解十分有限。遺憾的是,數年以后,維新派對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了解還是停留在這一水平上,康有為寫給光緒皇帝的上書說:“竊考之地球,富樂莫如美,而民主之制與中國不同;強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與中國少異。惟俄國其君權最尊,體制崇嚴,與中國同……故中國變法莫如法俄,以君權變法,莫如采法彼得。”康有為:《上清帝第七書》,《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218頁。康有為認為,民主只是適用于美國,中國則應效法俄國走君主立憲的道路。直到1902年,康有為仍然說:“蓋今日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正當過渡之世,孔子所謂升平之世也,萬無一躍超飛之理。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法國其已然者矣。”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476頁。在表面上看,專制、立憲、民主循序漸進的主張似乎有些道理,其實質卻是把君主立憲與民主對立起來。
如果說內地維新派主張君主立憲而反對實行民主是由于對近代民主政治的無知,香港的何啟、胡禮垣則由于其所受的英式教育而對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更是深信不疑。在他們看來,保障民權的關鍵就是設立議院,“夫民權之復,首在設議院,立議員”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后·正權篇辯》,《新政真詮》,第646頁。,只要設議院、定憲法,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議院之法一行,外國定當刮目,挽回中國在此一舉”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后·正權篇辯》,《新政真詮》,第648頁。。在某種意義上說,何啟、胡禮垣對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
維新派之所以反對被他們稱之為“民主”的共和政體,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對“法國大革命”的消極認識。維新派認為,共和政體只能通過革命來實現,而立憲是比革命更為溫和的方式,整個社會也無須付出更多的代價。在回答時人中國為什么只可立憲而不可革命這一問題時,康有為說,凡是主張共和的人們,都只是看到了美國的強盛,卻沒有看到法國革命導致的社會動蕩,“徒見美國獨立之盛,但聞法國革命之風而慕之行之,妄言輕舉,徒致敗亂,此仆之愚所未敢從也”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477頁。。從社會代價方面考慮,維新派的改良主張或許無可厚非,但是,當維新派主張立憲、反對共和的時候,他們顯然忽略了至關重要的一點:君主立憲政治得以實現,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統治者必須愿意與社會分享權力,可是,這對于把國家視為私產的清王朝來說卻是萬萬不能的。正是由于對清王朝不切實際的期望,使得維新派最終成為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看客。
再次,維新派的民權觀帶有濃重的功利主義傾向,在維新派的觀念中,民權不是最高的價值,而是求富求強的手段。
求富求強是近代中國人揮之不去的情節。“甲午戰爭”之后,這種情節在中國思想界變得尤為強烈,這也成為維新派倡導變法的理由。在維新派看來,西方列強所以強大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船堅炮利,而是因為在憲政體制下,君民共治一國。因此,只要“上師堯、舜、三代,外采東西強國,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制,則中國之治強,可計日待也”康有為:《請定立憲開國會折》,《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339頁。。或許,康有為如此說有策略方面的考慮,因為富強是最有可能為專制政治的統治者接受的理由。和內地的康、梁一樣,香港的何啟、胡禮垣也把民權與富強聯系在了一起,“夫中國之所以不能雄強,華民之所以無業可安”,“皆惟中國之民失其權之故”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后·正權篇辯》,《新政真詮》,第657頁。。可見,戊戌維新時期,用功利主義的態度對待民權,是維新派一致的思想傾向。在維新派看來,開國會、定憲法、興民權,是比洋務派的自強新政更為有效的求富求強的手段。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說得甚為直白,“世之所謂溫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張矣”,然而,李鴻章、張之洞不過是建了海軍,練了洋操,設了學堂,“然則再假以五十年,使如李、張者,出其溫和之手段,以從容布置,到光緒四十年,亦不過多得此等學堂洋操數個而已。一旦有事,則亦不過如甲午之役,望風而潰,于國之亡能稍有救乎?”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戊戌政變答客難》,《飲冰室合集》專集第1冊,第84頁。總之,富強是維新派立憲法、興民權的理由。然而,維新派不知道,當他們用功利主義的態度理解民權的時候,他們所倡導的自由、民權便已經不再是最高的價值。當人們在觀念上認為,自由、民權是從屬于某種目的的手段的時候,它便不再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必需品。用工具主義的態度對待民權,使得近代維新派在根本上誤解了民權的意義。
綜上所述,近代中國思想界的覺醒始于維新派對于民權問題的討論,在對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理解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維新派把近代價值理念放在傳統話語背景下加以闡釋,使自由、民權成為中國思想界能夠理解的話語,維新派的民權觀事實上開啟了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先聲。在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傳統話語的影響,導致了維新派民權觀的諸多局限。在某種意義上說,維新派所闡釋的自由、民權,已經不再是近代價值觀念的本來面貌,這又在根本上阻礙了從傳統向近代轉變的思想進程。
[責任編輯 劉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