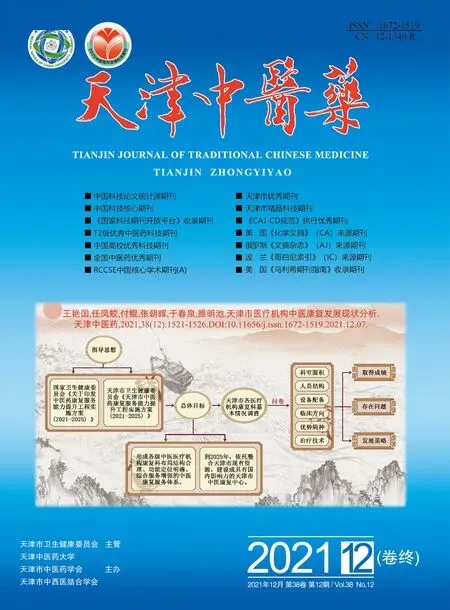袁紅霞教授從少陽辨治慢性萎縮性胃炎經驗*
張月林,袁紅霞
(1.天津中醫藥大學研究生院,天津 301617;2.天津中醫藥大學管理學院,天津 301617)
慢性萎縮性胃炎(CAG)是慢性胃炎的一種類型,指胃黏膜上皮遭受反復損害導致固有腺體的減少,伴或不伴腸腺化生(或)假幽門腺化生的一種慢性胃部疾病,伴有腸上皮化生及異型增生(上皮內瘤變)屬于胃癌前病變(PLGC),相關研究顯示,1/85的慢性胃炎、1/50的CAG、1/39的腸上皮化生和1/19的胃黏膜異型增生在20年內將發展為胃癌[1]。中醫中并無“慢性萎縮性胃炎”這一病名,根據患者的臨床主癥,可歸為“痞滿”“胃脘痛”“嘈雜”等范疇。
袁紅霞教授是全國首批優秀中醫臨床人才,天津市名中醫,從事中醫藥防治脾胃病工作30余年,擅長用經方治療CAG或伴腸上皮化生及增生,形成了自己的治療體系,在改善胃黏膜萎縮、逆轉腸上皮化生及增生療效甚佳。現將其經驗整理如下,以饗同道。
1 中醫對CAG病因病機的認識——視其所以
CAG的病因主要為外感六淫、飲食不節、情志不暢、素體脾虛,其病位主要在胃,與肝、脾密切相關,因膽附于肝,與肝同主疏泄,與膽也有著密切聯系。CAG病程較長、反復發作,久病多虛多瘀,往往表現為本虛標實、虛實夾雜。袁紅霞教授認為,本病病機系脾胃本虛,少陽樞機不利,而致脾胃升降紊亂,長期失于調攝,此疾由生。
2 CAG從少陽論治的理論依據——觀其所由
《傷寒論》中提出六經辨證法,開辟了中醫辨證論治的先河,對中醫治療各類疾病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傷寒論》治療疾病的描述中,字里行間無不有六經,六經之中無不有脾胃。袁教授臨證以六經辨證為基礎,多從少陽論治CAG,常取得滿意療效。
2.1 少陽的生理 少陽主樞,《素問·陰陽離合》云:“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在人體的氣機生化理論當中,少陽為三陽之樞,處于半表半里。少陽包含手少陽三焦和足少陽膽腑而言,三焦乃人體三元之氣,中清之腑,統領人體五臟六腑、經絡、內外和上下左右之氣。“三焦”為人體內多處能量代謝之處,其病位涉及全身,是人體氣機升降、水液代謝的樞紐[2]。膽附于肝,藏精汁,為肝之余氣所化,名“中精之府”,主疏泄、決斷,為“中正之官”。《素問·六節臟象論》云:“凡十一臟,取決于膽也。”脾胃的升清降濁,肺的宣發肅降,腎陽的溫煦皆離不開膽的疏泄,且足少陽膽經“循于頭身兩側,絡肝屬膽,入季肋,散胸脅,過心臟”,故心與膽也有關聯。由此可見,少陽在六經的氣機運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樞紐作用,故少陽樞機通利,則人體陰陽氣機調暢,五臟安定,因而脾胃方無賊邪之患。
2.2 少陽之氣與脾胃發病 《素問·血氣形志》曰:“夫人之常數,太陰常多氣少血,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氣血作為三陰三陽最基本的物質基礎,其根本在脾胃,乃因脾胃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與六經的發病皆有密切關系。少陽包含膽和三焦,是人體周身氣機與水液代謝的通路,為三陽之樞,同時在三焦中,脾胃乃是上、中、下三焦之樞,主臟腑氣機的升降出入[3]。張志聰《侶山堂類辨·平脈篇》有云:“上焦不歸者,噫而酢谷;中焦不歸者,不能消谷飲食;下焦不歸則遺溲,中氣不足者溲便為之變也。”邪氣傳入少陽三焦影響脾胃的功能,致使胃氣上逆,脾氣下陷,則致胃脘填塞,濁氣翻涌,心煩喜嘔;或可致腸道內結燥熱,不大便而嘔,若少陽邪氣內傳,致胃實而腸虛,脅下滿而便溏,此時也可能會出現熱結旁流之證;亦或邪氣侵犯少陽,膽火上炎,致少陽樞機不利,少陽屬木,木盛制土而影響脾胃功能,出現如氣郁、火郁、濕熱、痰飲,或寒、熱、虛、實等多種病理因素錯雜相兼的病證[4]。少陽病還可以作為判斷邪入脾胃的標志[3]。《黃帝內經》有云:“人之飲食入胃,英氣上行,即少陽甲膽之氣也;其手少陽三焦經,人之元氣也,手足經同法,便是少陽元氣生發也。胃氣、谷氣、元氣、甲膽上升之氣,一也,異名雖多,止是胃氣上升者也。”由此可見,少陽之氣與脾胃發病具有密切聯系。
2.3 少陽病CAG疾病表現和病情演變規律 CAG發病緩慢,病程日久,纏綿不愈,多因脾胃虛弱,生化乏源,致氣血虛弱,讓外感邪氣有機可乘,從太陽之表傳入少陽之半表半里,其臨床表現有胃脘痞滿,可兼有胃脹、胃痛、食欲不振、惡心嘔吐、口干苦、脅肋脹痛、乏力等癥狀,與小柴胡湯中的“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等相吻合。少陽病涉及膽經、膽腑及三焦腑,常會出現經腑同病。所以,少陽病CAG,多在少陽病的基礎之上,出現膽熱犯胃、三焦功能失司,脾胃停飲、停水等病變,這與膽腑三焦受邪后氣機失調有著密切聯系,同時還易伴有太陰、陽明之氣升降失常等。肝膽疏泄功能失調,膽汁分泌異常,則脾胃消化飲食不佳,易引發脘腹脹滿等癥;橫逆犯胃而形成慢性胃炎,長期失于調攝而逐漸發展成為CAG甚至胃癌前病變[5]。
3 從少陽論治CAG——察其所安
3.1 和解少陽之經,調理脾胃升降 袁教授臨證針對少陽病CAG多以此為大法,用柴胡類方加減化裁。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6],柴胡類方中柴胡-黃芩藥對的主要化學成分具有抗炎抗氧化、保肝利膽、促胃腸動力及抗抑郁等作用。但針對每位患者的兼證及病理階段,袁教授亦有不同側重,個體化加減藥味或合方化裁運用。少陽居半表半里,受寒邪侵襲時,不能往外與寒邪抗爭,郁里而發熱,此時與外寒抗爭,則表現為往來寒熱,且發無定時。少陽經脈循胸絡脅,邪氣侵入,則胸脅苦滿;滿而致肝膽之氣不舒,谷氣不化,故默默不欲飲食;相火熾熱,正邪斗爭,故心煩喜嘔。臨床中,CAG患者常伴有乍寒乍熱、胸脅脹滿不適、納呆,情緒煩躁等類似癥狀,袁教授強調此時需準確判斷是否為少陽樞機不利而致,方可運用小柴胡湯加減施治。小柴胡湯見證有七,但臨床上不必強求每一個癥狀在患者身上都有體現,只要辨證正確,都可以采用和解少陽的治法,方用小柴胡湯加減[7],以和解肝膽脾胃。
3.2 和解少陽之腑,兼調他經他邪 邪氣侵犯少陽所致CAG,非獨少陽氣火郁滯而致病,或可兼挾他經、他邪同時致病。少陽脾胃病易伴有陽明、太陰之氣不利,或可伴陽明里實,或可見太陰脾虛,亦或兼挾痰飲、水濕、瘀血等病理產物。兼陽明里實者,出現胃脘脹滿、疼痛、惡心嘔吐、便秘、欲矢氣而不得出等癥,此為少陽陽明合病,方用大柴胡湯加減,以內瀉熱結,利膽和胃;有大柴胡湯證而體虛者,袁教授則用小劑量小柴胡湯加小劑量芒硝之輕劑以清膽和胃通腑,避免體虛不受大柴胡湯之藥力而再傷正;兼太陰脾虛者,若出現納呆、脅痛、善太息、口苦口渴、便溏等癥狀,可予柴胡桂枝干姜湯,以和解散寒,生津斂陰;出現食后胃脘脹悶不舒,心下支結,惡心欲吐,納呆等癥,以柴胡桂枝湯和解表里,調和脾胃。若出現胃脘脹痛、心急易驚、心中悸動、寐差、口干苦、納呆等癥,予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以調肝膽、和榮衛,化痰飲、助升降。CAG患者,以胃脘痞悶、脹滿、疼痛為主要表現,多伴有焦慮抑郁、急躁、失眠多夢、恐懼等精神心理障礙,相關研究表明柴胡加龍牡湯可明確改善患者的抑郁狀態,還可很好地緩解抑郁共病的軀體疾病[8]。
3.3 健脾補虛,祛瘀散結 針對CAG病理腸化、增生,袁教授亦有兼顧,根據病情所需隨癥加入薏苡仁、仙鶴草、三棱、莪術、蜂房、山慈菇等健脾祛濕、補虛祛瘀、解毒散結之品。現代藥理學研究[9-13]表明它們均具有一定的抗腫瘤、抗菌、抗炎等作用,可有效逆轉腸化、增生以及改善胃部血液循環,重建胃黏膜。它們對CAG中幽門螺桿菌(Hp)陽性患者,亦具有一定作用,減緩腸上皮化生、增生向胃癌方向的演化進程,早遏其路,降低癌變率。
4 典型病案
4.1 少陽陽明合病 患者女性,45歲,2019年9月4日初診。主訴:胃脘疼痛1個月余。刻診:胃脘部疼痛,按之亦痛,連及右肋。無燒心反酸;口中不和,納差,不知饑。大便干結,每4~5日1行,寐可,畏寒肢冷,舌暗紅,苔白略厚,邊齒痕,脈弦細。2019年7月6日胃鏡示:中度萎縮性胃炎(胃竇),腺體灶性腸化,伴輕度非典型增生,胃竇黏膜欠光滑。中醫診斷:胃痛,證屬少陽樞機不利,橫逆犯胃。袁教授緊守本案之關鍵病機,治以和解少陽,清膽和胃并兼顧腸化、增生。予方藥:小柴胡湯+黃連湯+四逆散加減化裁,柴胡 15 g,黃芩 10 g,半夏 10 g,黨參 10 g,炙甘草 10 g,黃連 10 g,干姜 6 g,桂枝 10 g,酒大黃10 g,枳實 10 g,白芍 20 g,莪術 20 g,丹參 20 g,薏苡仁30 g,生姜4片,大棗5枚,7劑,水煎服,每日1劑。
2診(2019年9月11日):患者述胃脘疼痛緩解,納食稍轉佳,大便每1~2日1行,近日出現咽喉疼痛,效不更方,前方加桔梗6 g,炙甘草改生甘草10 g,以利咽止痛,續服14劑。
3診(2019年10月7日):期間約號未成,遂照上方續服10劑,現胃脘疼痛幾無,但因飲食大意或因情緒問題稍有陣發隱痛,食欲正常,余無特殊不適,余劑后諸癥幾無,停湯藥,續服丸藥以鞏固。2020年5月復查胃鏡示:CAG。病理:部分腺體腸上皮化生。但不適癥狀無幾,囑患者飲食調理;保持情志舒暢,起居有常,防止癥狀反復和疾病演化。
按語:此案患者胃脘疼痛、牽及脅肋,納差不知饑,脈弦,為小柴胡湯證之“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大便干結,因胃熱腸燥,屬陽明病。故本案為少陽陽明合病,確因少陽疏泄失調,致津液不得下于腸道所致。《傷寒論》第230條:“陽明病,脅下硬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苔者,可與小柴胡湯。”胃痛牽及兩脅,畏寒肢冷,加四逆散疏肝理脾;加酒大黃蕩滌腸胃,并能與莪術、丹參奏“破癥瘕積聚”之功,薏苡仁健脾祛濕,消腫散結,諸藥合用,少陽樞機得利,脾胃升降得復,則諸病自除。
4.2 少陽挾瘀 患者女性,60歲,2020年11月2日初診。主訴:胃脘疼痛間斷發作20余年,加重1個月。刻診:胃脘刺痛,夜間甚,情志不暢亦痛;胃脹滿,噯氣則舒;偶反酸燒心,胸骨后燒灼感,惡心欲吐;口干口苦;后背沉重。情志不暢,兩脅脹痛,納一般,寐入睡難,多夢,大便每日1~2次,不成形,小便可。舌紫黯,苔薄白根部黃微膩,左脈弦細,右脈沉弱。2020年10月27日胃鏡示:慢性胃炎。病理顯示:CAG,腸上皮化生,淋巴組織增生,Masson染色顯示黏膜肌。中醫診斷:胃痛,證屬少陽樞機不利,郁而化火;中土受灼,胃不和則臥不安;火灼津耗血,津血虧虛,血行不暢則為瘀。當治以和解少陽,疏肝瀉熱,鎮靜安神兼活血化瘀。予方藥: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四逆散+桂枝茯苓丸加減,柴胡15 g,白芍 10 g,枳實 10 g,炙甘草 10 g,黃芩 10 g,半夏10 g,黨參 10 g,龍骨(先煎)30 g,牡蠣(先煎)30 g,桂枝 3 g,茯神 30 g,桃仁 10 g,牡丹皮 10 g,大黃炭 3 g,莪術15 g,薏苡仁30 g,仙鶴草30 g,生姜4片,大棗5枚,7劑,水煎服,每日1劑。
2診(2020年11月9日):患者述服上方諸癥均減,近日腰膝酸痛,雙下肢無力,上方加四味健步湯,續服2周。
3診(2020年11月23日):患者述胃痛未反復,納寐尚可,心情甚是愉悅,袁教授隨癥處以他方,繼續鞏固,防癥狀再作。
按語:柴胡加龍骨牡蠣湯癥見“煩”“滿”“驚”“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等,與CAG伴寐差患者癥見胃脘滿悶、消化欠佳、大便不通、煩躁易怒、焦慮抑郁、失眠等癥狀相吻合。本案患者胃痛多因情志不暢,以夜間為甚,兼見胃脘部其他不適及寐差等癥狀,故用柴胡加龍牡湯調節少陽樞機以促進脾胃樞紐轉運,脾胃和則臥得安。四逆散調和肝脾;桂枝茯苓丸活血化瘀;加薏苡仁、莪術、仙鶴草健脾祛濕,行氣祛瘀,促進胃部血流,扭轉腸化增生,從而抑制CAG癌變。諸藥合用則瘀血去,胃痛止,情緒調。
5 小結
CAG是臨床中較為常見的慢性難治性脾胃系疾病,其治療周期較長且療效欠佳,西醫一般運用質子泵抑制劑(PPI)、促胃動力藥、消化酶制劑等,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臨床上應大力施展中醫中藥的優勢,運用不同視角辨析、探索CAG的治療。六經辨證作為中醫辨證論治的先導,對中醫治療疾病有普遍的指導意義。袁教授臨證治療CAG,以六經辨證為基礎,從少陽入手,結合兼證及病理加減,往往取效良好。少陽膽與三焦經,皆為少陽樞機,少陽膽從橫向主疏泄膽汁,參與水谷運化,以促脾胃吸收;少陽三焦從縱向將陽氣、水液疏布全身。然脾胃為全身氣機升降之樞紐,使五臟六腑之氣機順暢,則病無所生。少陽、脾胃均為樞紐,用和解少陽樞機治療CAG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六經發病皆可導致脾胃病的發生,臨床中應仔細辨析,精準辨證,用藥精當,方可著手成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