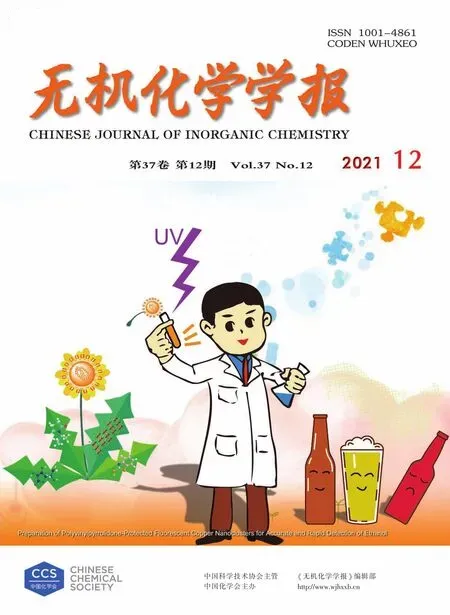一種高容量的層狀Co-MOF基超級電容器電極材料
戎紅仁 王先梅 魏英華 陳曉娟 賴梨芳 劉 琦
(常州大學石油化工學院,江蘇省精細石油化工重點實驗室,常州 213164)
0 引言
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清潔能源需求,發展具有良好能量儲存和轉換的技術是不可或缺的[1-2]。近年來,多孔金屬-有機框架(MOFs)及其衍生物已經逐漸應用于電化學能量存儲領域,例如鋰離子電池和超級電容器[3-5]。超級電容器憑借其高功率密度、長循環壽命和快速充電能力,已經在計算機、軍事和工業設備等方面獲得了廣泛的應用[6-9]。然而,超級電容器相對較差的能量輸出阻礙了它們的進一步應用[10]。為了在不放棄其高功率密度的情況下改善超級電容器的能量密度,研究人員專注開發電極材料,這些材料被認為是決定電化學存儲能力的關鍵因素[11-12]。如今,研究人員大力開發了諸如碳材料、導電聚合物和過渡金屬氧化物等超級電容器電極材料[13-14]。然而,它們無法滿足對具有更高電容、電化學穩定性和高倍率能力的超級電容器不斷增長的需求。因此,開發能夠改善超級電容器電化學性能的先進材料至關重要。
MOFs具有特殊的結構和可調的性質,作為一類新材料,直接使用MOFs作為超級電容器電極材料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15-32]。到目前為止,已經報道多種三維和二維MOFs作為超級電容器的電極材料,尤其是針對二維層狀MOFs的報道[16-26]。考慮到層狀的過渡金屬MOFs不僅能提供具有氧化還原活性的金屬陽離子,而且其結構中層與層之間的空隙還可以用于電解液的存放和擴散,因此,從理論上講,層狀MOFs材料也可以作為超級電容器的電極材料。Yang課題組報道了作為電極材料的一系列層狀MOFs且其展現出良好的電化學性能[20-22]。我們課題組在層狀MOFs基超級電容器電極材料方面也進行了一些研究,例如,以層狀Co-LMOF[16]作為電極材料,在電流密度為1 A·g-1時,材料比電容高達2 474 F·g-1,2 000次循環后比電容的保持率為94.3%。隨后,我們課題組還研究了層狀銅基配合物(Cu-MOF)[23]和錳基配合物(Mn-LMOF)[17]。總的來說,雖然這些MOFs材料具有良好的電化學性能,但是,目前為止,有關層狀MOFs基電極材料的研究仍然有限。目前的研究表明,這些材料的超級電容性能與其自身結構特征直接相關[25]。因此,很有必要探索并設計出更多新穎的層狀MOFs電極材料。
考慮到金屬鈷離子具有可變的化合價,可以參與氧化還原反應,以及上述的二維層狀MOFs的結構特點,我們設計、合成了層狀鈷基配合物[Co(4,4′-bpy)(tfbdc)(H2O)2](Co-BTH,4,4′-bpy=4,4′-聯吡啶,H2tfbdc=四氟對苯二甲酸),并首次考察了其作為超級電容器電極材料的性能。Co-BTH電極展現了較高的比電容和較好的倍率性能,在1 A·g-1電流密度下和1 mol·L-1KOH溶液中的比電容最大可達2 316 F·g-1。
1 實驗部分
1.1 實驗試劑
試劑包括氫氧化鉀(江蘇強盛功能化學股份有限公司,AR)、去離子水(自制)、四氟對苯二甲酸(阿拉丁,97%)、Co(OAc)2·4H2O(Co(CH3COO)2·4H2O,百靈威科技有限公司,AR)、4,4′-聯吡啶(阿拉丁,98%)、丙酮(國藥集團化學試劑有限公司,AR)、乙炔黑(國藥集團化學試劑有限公司,AR)、聚四氟乙烯(PTFE,國藥集團化學試劑有限公司,60%)、無水乙醇(南京化學試劑廠,AR)、泡沫鎳(國藥集團化學試劑有限公司,含鎳99.8%,1.0 mm厚)。
1.2 Co-BTH的合成
將Co(OAc)2·4H2O(0.049 8 g,0.20 mmol)、四氟對苯二甲酸(0.047 6 g,0.2 mmol)、4,4′-聯吡啶(0.038 4 g,0.2 mmol)和6 mL H2O混合,超聲1 h至分散,放入15 mL聚四氟乙烯內襯的高壓釜中,隨后將反應釜放入烘箱中,在100℃下保持24 h,然后自然冷卻至常溫。通過過濾分離得到固體后,分別用水和丙酮洗滌2次,并在常溫下自然干燥,最后得到0.076 g Co-BTH[33]。
1.3 材料表征
采用Nicolet 460型紅外光譜儀測試合成的配合物樣品的FT-IR譜圖。利用X射線衍射儀(XRD,D/max、2500 PC,Rigaku)對樣品結構進行分析,采用Cu Kα輻射(λ=0.154 06 nm),管電流為300 mA,管電壓為60 kV,掃描范圍2θ=10°~80°。樣品的形貌和微觀結構通過日立S-4800場發射掃描電子顯微鏡(FESEM,加速電壓20 kV)和JEM-2100型透射電子顯微鏡(TEM,加速電壓200 kV)測試。使用ASAP2010C全自動程序升溫比表面積及孔徑分析儀,以氮氣為吸附質,在液氮溫度為77 K的條件下得到樣品的N2吸附-脫附等溫線,由Brunauer-Emmett-Teller(BET)、Barrett-Joyner-Halenda(BJH)法分析可以確定樣品的比表面積、孔徑大小和孔體積。熱重(TG)曲線是在美國TA公司Q600-TGA/DSC熱分析儀上測定,N2氣氛,升溫速率10℃·min-1。利用Perkin-Elmer 2400型元素分析儀測試樣品中碳、氫和氮含量。利用Varian Vista-AX型等離子體發射光譜儀測試樣品中鈷的含量。
1.4 電極制備和電化學表征
電極材料的制備:將電極材料(Co-BTH)、乙炔黑和聚四氟乙烯(PTFE)三者以質量比為75∶15∶10進行混合,滴入一定量無水乙醇充分攪勻,進行和漿處理。采用輥壓機將其制成1 mm厚的糊狀電極膜,80℃真空干燥1 h。接著用打孔器將糊狀電極膜打孔成圓片狀薄片(直徑1 cm),然后用粉末壓片機壓在集流體泡沫鎳上。在10 MPa下保持30 s,最后將壓好的電極材料置于真空干燥箱內,60℃下恒溫8 h,得到電極材料。實驗中需準確稱量圓形泡沫鎳電極片負載前后的質量,其質量差為電極中活性物質的質量。
電化學性能測試:以下所有的電化學測試均在室溫下采用北京華科普天科技有限公司生產的CHI660D型電化學工作站進行。用常規的三電極體系,以制備的泡沫鎳電極作為工作電極,鉑片為輔助電極(對電極),飽和甘汞(SCE)電極作為參比電極,1 mol·L-1KOH溶液為電解液。在 0.2~0.6 V(vs SCE)電位范圍內,分別以2~200 mV·s-1的掃描速率測試電極的循環伏安(CV)曲線;在0~0.6 V(vs SCE)電位范圍內,分別以1~20 A·g-1的電流密度對電極進行恒流充放電測試,并在2 A·g-1的電流密度下測試電極的循環壽命(循環1 000次);在開路電位條件下進行交流阻抗的測試,振幅為5 mV,頻率為10-2~105Hz。
可以通過式1計算該電極材料的比電容:

其中,C為比電容(F·g-1),I為電極活性材料的放電電流(A),t為恒電流充放電(GCD)的放電時間(s),m為電極活性材料Co-BTH的質量(g),ΔV為電勢窗(V)。
2 結果與討論
2.1 Co-BTH的表征
圖1a是Co-BTH的XRD圖,由圖中可以看出,合成樣品的XRD圖與Co-BTH晶體(CCDC:737133)[33]數據模擬的XRD圖中的峰一一對應,說明成功合成了純度高的Co-BTH。利用元素分析儀和等離子體發射光譜儀分別測定Co-BTH中C、H、N和Co的含量,其質量分數分別為44.35%、2.50%、5.78%和11.91%,這與Co-BTH的理論計算結果基本一致(C 44.37%、H 2.46%、N 5.75%和Co 12.09%),進一步驗證了Co-BTH的高純度。
圖1b是Co-BTH的FT-IR譜圖,從圖中可以看出,在3 441 cm-1處有一個較強的峰,屬于配位水分子中—OH的特征吸收峰(νOH),在1 615和1 388 cm-1處較強的吸收峰是四氟對苯二甲酸中—OCO—的不對稱伸縮振動峰(νas,OCO)和對稱伸縮振動峰(νs,OCO),在812 cm-1處是4,4′-聯吡啶中C—H的彎曲振動吸收峰(νC—H)。圖2是Co-BTH的TG曲線,由圖可知,在80~220℃的溫度范圍內,重量減少了7.68%,與理論計算值7.39%(失去兩分子的水)基本一致[33]。

圖1 (a)合成的Co-BTH和Co-BTH晶體數據模擬的XRD圖;(b)合成的Co-BTH的FT-IR譜圖Fig.1 (a)XRD patterns of as-synthesized Co-BTH and Co-BTH crystal data simulation;(b)FT-IR spectrum of as-synthesized Co-BTH

圖2 Co-BTH的TG曲線Fig.2 TG curve of as-synthesized Co-BTH
為了考察Co-BTH的比表面積、孔體積和孔徑分布,我們測試了Co-BTH的氮氣吸附-脫附等溫線(圖3)。由圖3可以看出,所合成的Co-BTH的氮氣吸附-脫附等溫線屬于Ⅳ型,在p/p0=0.6~1.0范圍內的遲滯環屬于H3型,這表明Co-BTH中存在介孔。從孔徑分布圖(圖3中插圖)可知顆粒之間存在微孔和介孔,根據BJH等溫線方程式計算出平均孔徑為15.39 nm。介孔結構會改善材料作為超級電容器電極材料的電化學性能。在p/p0=0.6~1.0范圍內的遲滯環屬于H3型。Co-BTH材料的BET比表面積和累積孔體積分別為9 m2·g-1和0.023 cm3·g-1·nm-1。

圖3 Co-BTH的氮氣吸附-脫附等溫線圖和孔徑分布(插圖)Fig.3 Nitrogen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of as-synthesized Co-BTH and pore size distribution curve(Inset)
由圖4a可以看出,Co-BTH是一種二維層狀MOFs,這些二維層通過氫鍵之間的相互作用進一步連接,從而形成三維的超分子框架,如圖4b所示。結構中層間的空間將有利于電解質溶液的擴散和儲存。因此,理論上Co-BTH能作為超級電容器中的電極材料。

圖4 Co-BTH的(a)二維和(b)三維結構圖Fig.4 (a)Two-dimensional and(b)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diagrams of Co-BTH
FESEM和TEM也用于表征Co-BTH材料的微結構和形貌。圖5a和5b是Co-BTH的FESEM圖,由圖可知,Co-BTH是由大量的納米片組成,納米片彼此聚集在一起,其厚度為50~100 nm,寬度和長度分別為65~500 nm和200~950 nm。
由Co-BTH的TEM圖(圖5c)可以看出,其由許多納米片構成。圖5d是單個Co-BTH納米片的TEM圖,由圖可以看出,Co-BTH納米片具有多層堆疊結構。圖5d中插圖是Co-BTH的高分辨TEM圖,從圖中可知其晶格條紋間距約為0.25 nm,對應于Co-BTH的(002)晶面。

圖5 Co-BTH的(a、b)FESEM圖;(c)Co-BTH和(d)單個Co-BTH納米片的TEM圖(插圖:高分辨TEM圖)Fig.5 (a,b)FESEM images of Co-BTH;TEM images of(c)Co-BTH and(d)single Co-BTH nanosheet(Inset:high resolution TEM image)
2.2 電化學性質
利用CV、GCD和交流阻抗譜(EIS)等對Co-BTH作為超級電容器電極材料的電化學性能進行了評估。在2 mV·s-1的掃描速率下1 mol·L-1KOH電解質中Co-BTH電極的CV曲線如圖6a所示。由圖可知,曲線上出現了一對氧化還原峰,這揭示了贗電容行為是由于電極表面發生了法拉第氧化還原反應。在0.45 V的氧化峰和0.30 V的還原峰分別對應鈷不同氧化態之間的轉化[16],如式2和3所示,式中的下標s和ad分別表示固態和吸附。已經報道的一些鈷基MOF電極材料,比如Co-LMOF[16]和Co-ip[30],也發生了上述類似的變化。

圖6b是掃描速率從2 mV·s-1增加到200 mV·s-1(2、5、10、20、25、40、60、100、200 mV·s-1)的CV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到,掃描速率增加時,有快速的電流響應,峰電流隨著掃描速率的增加而明顯增加。氧化還原峰電流的增加,表明電極上發生了快速可逆的氧化還原反應。與此同時,還原峰的電位隨著掃描速率不斷地增加而發生負向移動,氧化峰的電位則發生正向移動,這可能與電極內部電阻增加有關。當掃描速率增加到25 mV·s-1時,還原峰消失,這可能是電極的氧化還原過程由擴散控制轉為電荷轉移控制或擴散和電荷轉移的混合控制導致的[17]。
圖6c是Co-BTH在不同電流密度下的充放電曲線,由圖可知,當放電電流密度從1 A·g-1經過2、3、4、5、6、8、10 A·g-1變化到 20 A·g-1時,其仍然保持31.5%的電容,表明Co-BTH具有較好的倍率性能。如圖6d所示,比電容隨電流密度的增加而減小,這種減少可能與大電流密度下電解質離子和電極之間的有效相互作用降低有關[17]。Co-BTH的比電容在1 A·g-1的電流密度下高達2 316 F·g-1。當電流密度增加到20 A·g-1時,其比電容也可達到728 F·g-1,這表明Co-BTH電極具有良好的倍率性能。為了扣除泡沫鎳裸電極的影響,我們測試了其在1 A·g-1電流密度下的充放電性能,比較圖S1(Supporting information)和圖6c可知,泡沫鎳裸電極對Co-BTH電極比電容的貢獻可以忽略不計。

圖6 Co-BTH在1 mol·L-1KOH溶液中的電化學性能:(a)掃描速率為2 mV·s-1下的CV曲線;(b)不同掃描速率下的CV曲線;(c)不同電流密度下的GCD曲線;(d)電流密度與比電容的關系圖Fig.6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Co-BTH electrode in 1 mol·L-1KOH:(a)CV curves at the scan rate of 2 mV·s-1;(b)CV curves at different scanning rates;(c)GCD curves at different current densities;(d)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ent density and specific capacitance
在考慮實際應用的基礎上,有必要研究超級電容器的循環穩定性。圖7a是Co-BTH電極在1 mol·L-1KOH溶液中、2 A·g-1的電流密度下進行1 000個循環的GCD曲線。由圖可知,該電極材料的初始放電比電容為2 066 F·g-1,循環1 000次后,Co-BTH電極的比容量維持在41%左右(847 F·g-1),這表明在0~0.5 V的電壓范圍內,Co-BTH材料循環穩定性一般。圖7b是Co-BTH電極在電流密度2 A·g-1下,前3個充放電循環周期的曲線。每條曲線具有類似的時間-電位響應行為,證明Co-BTH電極具有良好的電化學可逆性。

圖7 Co-BTH在電流密度為2 A·g-1下的(a)循環壽命圖和(b)前3個GCD曲線Fig.7 (a)Cycle life diagram and(b)first three GCD curves at current density of 2 A·g-1of Co-BTH
為了進一步了解Co-BTH電極的穩定性,將循環前和循環1 000次后的電極進行FT-IR譜圖測試。圖8是包含Co-BTH、乙炔黑、黏合劑(PTFE)的Co-BTH電極(裸電極)和循環1 000次后的Co-BTH電極的FT-IR譜圖。由圖可知,在3 457 cm-1附近的強峰,對應于配位H2O分子的νOH伸縮振動,在1 625和1 385 cm-1處的強峰歸屬于配位的tfbdc2-的νas,OCO和νs,OCO伸縮振動,這2處峰均出現在裸電極和1 000次循環后電極的FT-IR譜圖中,表明tfbdc2-陰離子在每個循環過程中是可逆的。裸電極的FT-IR譜圖中出現在1 187~1 112 cm-1處的吸收峰歸屬于C—F鍵的伸縮振動或彎曲振動,而1 000次循環后電極的FT-IR譜圖中沒有觀察到1 112 cm-1處的吸收峰,這可能與部分電解質離子(OH-)與C—F鍵之間形成了氫鍵有關。此外,歸屬于C—H鍵彎曲振動的吸收峰從裸電極的846 cm-1移動到1 000次循環后電極的823 cm-1處,這也可能跟OH-離子與C—H鍵之間的作用有關。

圖8 裸電極和循環1 000次后的Co-BTH電極的FT-IR譜圖Fig.8 FT-IR spectra of bare electrode and Co-BTH electrode after 1 000 cycles
電阻是超級電容器電極的重要參數,可以通過EIS譜圖進行定量評估。圖9是Co-BTH電極在開路電位和10-2~105Hz的頻率范圍內得到的EIS譜圖。根據曲線在高頻區域與真實阻抗(Z′)軸相交的點,可得到Co-BTH電極的內阻(Rs)為3.3 Ω,其由電解質的離子電阻、活性材料(Co-BTH)的內阻以及集流體與活性材料(Co-BTH)的接觸電阻組成,該值稍微高于文獻報道的Co-ip MOF的內阻值[5]。由于曲線在高頻區存在一個半圓,阻抗可歸因于電荷轉移和表面電阻的組合(Rct+Rs),Rct+Rs值約為20 Ω。在低頻區域,EIS譜圖的相位角大于45°,表明離子遷移率較好,這是因為Co-BTH的層間空間和Co-BTH納米片堆積形成的微介孔有利于離子的遷移。

圖9 Co-BTH電極的EIS譜圖Fig.9 EIS spectrum of Co-BTH electrode
3 結論
我們通過簡單的溶劑熱反應成功制備了二維層狀鈷基MOF(Co-BTH)。Co-BTH的層狀結構和納米片結構使Co-BTH電極具有良好的贗電容性能,包含高比電容、較好的倍率性能和較好的循環穩定性。在 1 mol·L-1KOH 中,電流密度為 1 A·g-1時,Co-BTH電極的最大比電容為2 316 F·g-1,同時在2 A·g-1的電流密度下循環1 000次后的比電容仍然能保持847 F·g-1,這些特征使其在高性能超級電容器中具有潛在的應用前景。該研究為二維MOFs作為超級電容器電極材料提供了新的例證。
Supporting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t http://www.wjhxxb.cn
- 無機化學學報的其它文章
- Synthesis of Quasi-MIL-53(Fe)Photocatalysts for Enhanced Visible Light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Organic Dyes
- Synthesis,Structures,Luminescence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Co(Ⅱ) and Ni(Ⅱ)Coordination Compounds Based on Dibenzoyl-Tartaric Acid
- Synthesis,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Three Copper(Ⅱ)Complexes Based on a Bifunctional Ligand 2,2′∶6′2″-Terpyridine-4′-carboxylic Acid
- Visible Light-Assisted Synthesis of Platinum Nanoparticles for Catalytic Reduction Reaction of p-Nitrophenol
- Synthesis of Porous CuO Based on an Etching Strategy and Application in Electrochemical Glucose Sensing
- 超快速turn-on型ClO-熒光探針的合成及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