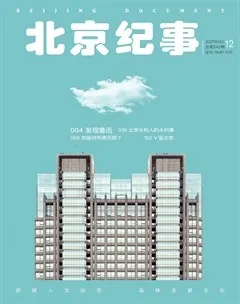王一川:電影的符號

本期嘉賓
王一川,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主任、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是國內文藝美學和藝術理論領域有影響力的學者。著有《意義的瞬間生成》《語言烏托邦》《修辭論美學》《中國形象詩學》《中國現代性體驗的發生》《文學理論修訂版》《中國現代學引論》《藝術公賞力》等學術著作共28種。在重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200余篇,主編高校教材10余種。
2010年5月8日,第十七屆北京大學電影節圓滿閉幕,又是一年,看著一張張年輕的新面孔閃耀著自信和感恩之光,攜著屬于他們的滿滿收獲和理想站在那里。不僅讓王一川腦中想起開幕時所說的:“我相信,在這個中國電影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特殊時刻,年輕的小飛虎會為能親身參與創造中國電影的新歷史而深感榮幸,并愿意不惜付出自己的全部才智和活力!”
是的,作為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的組織者之一,他最清楚,所有為此平臺的建立發展所付出的各界人士、組織和部門,都是如此渴望讓這只小飛虎為中國電影業中的大學生新生力量助力護航。
到了2020年,十年過去了,王一川親眼見證了以大影節為窗口,在新的起點上向世界展現新時代中國大學生的精神面貌與青春風采的歷程。大學生以電影這一思想藝術媒介,認真地體驗和反思,淋漓盡致展現了自我和時代的價值。他們用他們的作品去為受眾和這個時代做梳理,努力弘揚主流價值,煥發青春活力,淬煉專業品質,提升國際影響。
作為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及北京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王一川的學術之路在他那個年代走得相當艱難,當時對于藝術類大學生的學術理論、學術交流的資源和平臺非常有限,而作為大學生的他們不能退縮。因為時代的責任需要他們堅定開拓,不只是他們,整個中國電影人和國家相關部門負責人也都在砥礪前行,為未來的電影藝術新人創建更好的理論指導、環境和平臺。而對于王一川,能做的也是必須要做的就是尋找更科學的藝術理論。
1988年,牛津大學。如果我們那個時候是王一川的同學,應該會看到他在異國他鄉的頂級學府里躑躅困惑的身影。作為一個來這里深造文藝理論的博士后,它所遇到的完全不同于當時國內學術氛圍的,所謂“語言學轉向”,足以讓他感到難以言喻的震驚。
在來牛津之前,王一川是以脫離中國傳統的過度“經世致用”式的教條主義美學,而轉入強調獨立藝術價值的“體驗美學”而自豪的。不管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當我們說某種文藝形式讓我們感覺到了美,難道不是某種體驗超脫出了形式束縛才體驗出來的嗎?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每一個字我們都認識,可我們能說這些字,就代表了這首詞的意境嗎?這些關于中國古文化的理解,貫穿了王一川在去牛津大學之前,對美學的反思。但由此引發的困境,對于這個敏感而上進的學者來說,也被清晰甚至可以說有些痛苦地感覺到了。
如果我們把美學的所有研究集中于“體驗”,集中于不可言說的“意境”,那么我們怎么進行“文藝批評”?號稱可以脫離形式(文字)的東西,又怎么用文字闡明?
王一川看到了問題,但中國的改革開放畢竟剛剛開始不久,文藝理論的現實環境在教條的形式和不可言說的體驗之間,仍然是缺乏其他理論建樹的。對于那時還是20多歲的、充滿朝氣的年輕人來說,寧選體驗不落教條。恐怕是他的一個合理抉擇。
但這種抉擇的合理性在他進入牛津大學,師從當時西方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家特里·伊格爾頓之后,就遇到了巨大挑戰。這就是所謂的“語言學轉向”。
意境并不在語言(形式)之外,而是在語言符號的諸多象征之中!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當我們去欣賞、評判乃至體驗這句詞所傳達出來的意境時,我們不應該把“意境”剝離出“語境”。
春花、秋月、往事以及與其他詞匯的排列……詞語的分析,讓我們尋找到了不同的符號以及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概念排列組合延展出了不同的意境……語言在可以清晰分析的結構中將意境的內容“限定”了出來。藝術的價值不再是某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而成了實實在在可以被語言分析的對象!
純粹的體驗美學在這種語言學轉向的文藝理論面前驟然間變得極度暗淡……這應該是王一川在牛津時所有困惑的來源。形式和體驗這種顯然的兩分突然間被嶄新的視角打破了。當上進的中國學者們大部分認為在美學研究中,需要擺脫形式桎梏的時候,語言符號學的崛起,卻又從某種程度上徹底將純粹的體驗美學擠到了學術潮流的邊緣。

我相信,這對于一個苦心于這一理論的年輕學者來說,絕不是一個可以輕松擺脫的困惑。該怎么辦?全盤接受這新的理論工具?還是說體驗美學依然有值得堅持的理由?
這樣的疑問并不是幾天、幾個月能解決的。王一川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才完成了這痛苦的反思。這反思對他以后的學術生涯具有著里程碑的意義,作為一個卓絕的學者,王一川沒有亦步亦趨地跟隨任何既定的理論,困惑與躑躅不是停滯不前的理由,也不是全盤接受的借口,一個有作為的學者,都渴望能夠成一家之言!
而對于王一川來說,這一家之言就是他隨后雖多有微調,卻不在根骨上再做變更的——“修辭論美學”。
這不僅是王一川學術上的一個嶄新起點,也是他能卓有成效、獨樹一幟地進入電影評論領域的重大誘因。也就是它在牛津求學的那段時間,張藝謀的紅高粱登陸了英倫。
“中國人怎么能夠拍出這樣粗野、野蠻的電影?”王一川在英國的鄰居,一個神學博士這樣質問他。這讓他感到一“激靈”,隨后當它看到日本麻風病人協會號召抵制這部影片的時候,這種一激靈的思想沖蕩激起了他進行電影評論的興趣。
第一次,他嘗試應用自己的修辭論美學來解釋這種文化無意識的“分歧”,也是從這一次嘗試之后,王一川與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
當然,如果說修辭論美學的建立,是王一川能夠游刃有余地進行電影評論的學術基底,那么他在北京師范大學求學期間“飽覽電影”,又是另外一種“物質積累”。
弄到一個可以看電影的“觀摩證”,可能對今天的讀者來說實在有些費解。我們處在一個文化產品高度豐富的時代,電影不是太少了,反而是太多了。可對于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文化市場來說,電影尤其是國外的大量電影,恐怕仍然不是一個“想看就能看”的東西。
而王一川卻沾了電影資料館的那個觀摩證的光,得以在那個年代就看到了許多國外的經典影片。
經驗的充實與理論的完備。我們還能為一個優秀的文藝批評家,一個卓絕的電影評論人提供什么更好的際遇呢?王小川最終深入到電影行業的所有前提都已經再明朗不過了。
不停地寫出優秀的電影評論,有什么理由不會被邀請成為各種電影節的評委呢?當評委的職責履行得極為出色的時候,參與到更為具體、更為深入的籌備與管理中,也成了王一川深入到電影行業順理成章的歸宿。
對于王一川來說,修辭論美學當然不是只為了評論電影而被建立的,但作為一個更為大眾、更為流行,同時在象征符號上也更為具象的文化產品,電影對文化市場的影響是文學等純文字的文藝作品所不能比擬的,它的影響力,對國家文化形象的塑造,以及在公民生活中的重要性,恐怕都是王一川愿意將更多的經歷投入其中的原因。
正如他在十八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的引言里強調的,在一個中國電影的黃金時期,我們需要更有“青春激情、學術品位、文化意識”的電影。
一個在1989年的牛津,就已經奠定了自己將文藝理論回顧與中國文化批評的學者,一個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嚴肅卻又充滿激情的電影評論的青年。在今天,對后輩的殷切,恐怕無非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