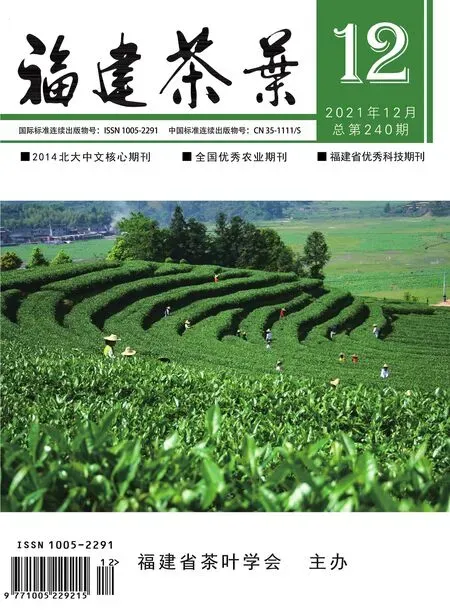音樂美學視角下茶室音樂研究
郭瓊惠
(河南工業貿易職業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1 中國音樂美學的發展
1.1 美學與音樂
人類對美學問題的思考起源較早,美學一詞來源于希臘,但是在中國也有著悠久的歷史。美并不是具象,而是抽象的,美學是以美的事物為載體的抽象規則與理念。美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美的事物,不同審美主體和不同的參照物都會造成對美的不同評判。音樂美學是研究音樂與美學的一門交叉性研究,主要研究音樂本質和音樂內在規律。音樂的研究離不開表演,表演藝術又叫表情藝術,包括音樂和舞蹈,二者都是表演藝術,是作為一種具體演繹過程所帶有表演者自身的創作與發揮,所以音樂和舞蹈又都是表演型的二度創作。音樂是人類藝術發展史上最古老的藝術之一,它是一種表演性的聽覺藝術,是通過樂音在時間中的流動創造音樂形象,表達人的感情與思想。宗白華先生指出:中國民族音樂從古到今都是聲樂占主導地位。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漸近自然也”。并且中國古代的“樂”并非純粹的音樂,而是舞蹈、歌唱、表演的綜合體。“樂”是情感的語言,“悅之故言之”,因為快樂所以情不自禁地說出來,聲調拖長的“長言之”“嗟嘆之”就成為歌唱。
1.2 音樂美學的發展
我國先秦時期的諸多學說已經出現大量的美學思想,雖然沒有成為體系化的建構,但是已經涉及至詩詞書畫、建筑、雕塑與音樂等各個領域。明清時出現“美學”的詞匯,當時的含義類似于“良知”。現代美學意義是在1875年德國傳教士花子安在《教化議》中譯作“美學”,此后美學的研究逐漸進入國人視野。王國維把美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獲得確立,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為中國美學打下基礎,之后宗白華與朱光潛將中國美學系統化并全面展開。中國近現代音樂美學起步于20世紀初,留德歸國的音樂家蕭友梅博士最早撰文介紹“音樂美學”,指出音樂美學乃樂學的一門主課,是普通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對音樂美學的特點和研究對象都做了簡要說明。近年來國內學者對音樂美學的深入研究,主要是從國內和西方兩個方面研究,國內是對儒家、道家、嵇康的音樂美學思想、古琴音樂美學、聲樂演唱美學深入探討,國外則包括古希臘、中世紀的音樂美學觀念,情感論、自律論以及20世紀的西方音樂美學思想等,完整地勾勒音樂美學的演變軌跡。
2 茶室音樂的選擇
2.1 茶室音樂語言的特征
人類的音樂語言自建立之初就是用以表達內心情感,音樂藝術演變至今的形態與樣式,一直反映著人類利用聲音表達和交流自身思想情感的能力和水平,并在表達與交流中傳播了不盡相同的聲音美感體驗。某茜要在《音樂的文化闡釋》中指出,正是最初處于萌芽狀態的音樂形態為后來音樂藝術運用聲音、音響作為音樂語言材料界定了相應的范疇,并在此基礎上著由單純到復雜的發展軌跡使音樂藝術建立起特殊的、獨立的藝術語言系統,音樂語言發展為無限可能的人的精神、情感的呈現物與載體,其美學價值也在應用中被不斷實踐。茶室音樂語言有三個特征,一是作為現場和表演的藝術,它不能存在于空間的所有地方,具有轉瞬即逝的特征。二是音樂不能確切地描寫音響以外的客觀事物,在特定情況下,有時音樂可以表現一些事物和情緒,但是范圍非常有限,與繪畫、雕塑等其它藝術形式相比,表現力也較弱。三是音樂語言的非具象特征,它能展示出其他藝術形式所不能表現的微妙情緒和抽象的精神世界。
2.2 茶室音樂的情感特征
維特要斯坦認為音樂強調與生活日常和時代的聯系,能夠描繪生活狀況、生命奮進、理想失落、憂傷情感等,是直覺和感性的藝術。人的意志和意識是人類最早的心理活動形式,在此基礎上發生的一切音樂形式,是人生命精神的直觀外顯,被賦予了人對于情感的邏輯性彰顯,以觀看、聽賞、知覺這個世界,成為獨立于自然的個體。在音樂的表達中,對自然的敬畏、對生命的惜嘆、對勞動節奏的體驗、對生命節律的共鳴、對災難的戰斗、對死亡的恐懼等,都成為激發音樂生命力量向意識對象進行投射的契機,可以說,音樂創造之始就因豐富活潑的生命體驗,充實著原始本能的情感特征。茶室的音樂選擇分為聲樂和器樂,音樂自身可表達復雜的情緒,其中包含了對審美的認識與追求。每一首樂曲都是表演者的復雜心理體現,以茶室中經常播放的樂曲《琵琶語》為例,這是作者林海和朋友在江南水鄉茶館中聽評彈,被琵琶的音色打動,所創作的以古箏“瀝音”和“揉弦”技法的“輕”“淡”潤飾,把江南的秀麗和柔美表現的淋漓盡致。此外,古箏作為最能體現東方氣韻的樂器,被人贊譽彈古箏的人可獨坐自得其樂,可嫻雅如高山流水,可豁達如漁舟唱晚,
2.3 民族音樂在茶室中的適用性
在中國綿延幾千年的民族文化不斷融合相生的過程中,以民間歌曲和民族器樂為主要內容的中國民族音樂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優秀代表,發展至今更是成為中國音樂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音樂文化象是一條璀璨的星河,閃耀著無數光芒,其主要包括充滿濃郁鄉土氣息的民間音樂、古風典雅的宮廷音樂、風韻儒雅的文人音樂、神秘虔誠的宗教音樂等,各自富有不同的音樂美學特征。不同歷史時期中,特定的文化、經濟、歷史環境等不同要素也從觀念和思維方式等方面影響著音樂的形態。首先,茶室音樂的選擇以民族音樂為主,民族音樂體現出統一性和連續性的特征,其中“人文精神”是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征,它全為一個文化系統的時空特征,集中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音樂的發展都是在自我發展的軌道上完善融合。李智萍在《音樂的文化闡釋:中國民族音樂特征及人文色彩》中把民族音樂的美學定義為“韻致”,重天道自然,與儒家平和雅淡中正的修身養性理念相結合,又與道家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的理念同一,注重內心感受,很好發揮了音樂人文教育目的。以茶室經常選擇的樂曲《云水禪心》《琵琶語》《深谷幽蘭》《茶道至簡》《夏雨風荷》等為例,樂曲的名稱即有著豐富的意識聯想,每一首樂曲,都是安撫心靈的良藥。丁立梅在《只因相遇太美》中寫道:初聞《云水禪心》即驚為天曲,滿世界的喧嘩一下退避數千里,魂魄被它一把攥住,人已經完全做不了自己的主了。清爽的古箏,如隔夜雨滴滴落芳草,一扇門洞開,紅塵隔在門外。《樂記》中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于物而后動,故形于色”,其中提到的“物感心動”就是心性對外部世界的“感”,樂曲的客觀世界已經進入人的思維,被符號化,樂曲中聲音的高低,節奏的快慢,旋律的起伏,色彩的濃淡,其所隱喻的含義已經超越了客觀意象達到藝術意象,這是音樂在人心性意象的映射。
3 茶室音樂美學的內涵與深度
3.1 茶室音樂的題材層
題材是指音樂所表現的對象。茶室音樂的題材性所以表達的內涵比較寬泛,音樂可以表達文學性或繪畫性題材,以及純音樂的題材。中國上古時的“樂”就是“詩、歌、舞”三位一體的概念,在之后的發展中藝術形態又有“樂中有畫、樂中有詩”的表現形式,這一藝術境界反應的就是中國藝術在表現形態上,強調各門藝術之間相互融合的審美追求。以隋唐法曲代表作《霓裳羽衣曲》為例,其調式、旋律和套曲結構等樂曲方面,和樂器伴奏演奏方法等形式都與道教音樂的風格相類似,可見在不同領域的音樂相互融合的審美傾向,也是音樂不同題材類型的生命力表現。
3.2 茶室音樂的氣質層
氣質是精、氣、神方面具有的精神氣質,音樂氣質則是音樂家和樂曲自身的主體氣質,如古典、浪漫等。被人們稱為二十世紀最后一個浪漫主義鋼琴家的霍洛維茲認為,任何音樂都是表達人的感情,具有浪漫氣質。他本人也非常尊重聽眾的感受,他詮釋的莫扎特作品充滿戲劇性的力度對比,瞬息萬變、難以捉摸的速度變化,深入挖掘表現隱伏聲部等,均給聽眾帶來強列的震撼。以茶室經常播放的樂曲為例,作曲家在創作時不是希望控制樂思,而是希望樂思可以控制自己,樂曲的風格和豐富的色彩,均是古典主題風格,其音樂氣質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地在《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系》中提到的那樣:“任何事物,我們在那里面看得見依照我們的理解應當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這也是演奏家對樂曲的處理,以及茶室管理者對音樂的選擇,要尊重消費者心理,關注音樂氣質符號闡釋的時代性,關注并尊重當下時代客戶的審美心理。
叔本華曾高度稱贊音樂在各種藝術中占據最高地位,說它是能夠表現意志本身的藝術。音樂與茶文化相結合的探索,主要是研究茶室音樂的美的多樣性和美學美感的特征,這些也將在新的茶室管理中得到更好的繼續延續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