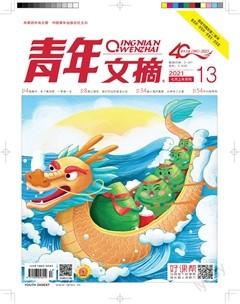超人離開氪星,火神回了火星
朱秋雨

2020 年7 月23 日,長征五號遙四運載火箭搭載“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在海南文昌發射。10 個月后,2021 年5 月15 日,“天問一號”探測器軟著陸于火星烏托邦平原南部預選著陸區,中國成為第二個成功著陸火星的國家。后續“祝融號”火星車將依次開展對著陸點全局成像、自檢、駛離著陸平臺并開展巡視探測。
回顧1960 年以來的火星探測史,人類先后開展了40 多次探測,但成功率并不高——此前只有8 次任務成功著陸并開展火星探測。此次在火星的順利登陸,意味著我國成為唯一一次性完成“繞落巡”的國家。
如今,這顆紅色星球附近已經變得擁擠,有7架飛行軌道器在火星軌道附近繞行,包括美國航天局(NASA)的3 架,歐洲的2 架,以及印度的“曼加利亞號”、阿聯酋的“希望號”。人類為何都將目標朝向這顆紅色星球?登陸火星能給人類帶來什么好處?
清楚這些問題,我們或許才會知曉:“天問一號”探測器的成功登陸,究竟對中國、對世界意味著什么。
一次就好
太陽系的八大行星排列上,地球是離太陽第三近的行星,火星則是第四個。但從地球跨越到火星,并非如科幻電影里表現的一樣——造精密的飛船即能任意飛抵。精密的距離和時間的控制,是現實世界飛抵火星中的一大考量因素。
2020 年7 月23 日出發的“天問一號”,正是選在最適合飛往火星的“窗口期”。彼時,阿聯酋的“希望號”和美國航天局的“毅力號”,都在發起相似計劃。一切的源頭是——火星和地球以不同的速度和距離繞太陽公轉,地球和火星最遠距離大約4 億公里,最近的距離是5600 萬公里。而每隔26 個月,會出現“火星沖日”的天文現象——火星、地球和太陽所處的軌道位置將形成一條直線。此時飛去火星,最節約燃料。
2020 年10 月14 日正是這一天文現象起作用之時,以此推算最佳的發射時間大約為“火星沖日”之前兩個月。“天問一號”在這時出發,被賦予了更重的使命——阿聯酋的“希望號”僅進入火星軌道環繞,探測火星大氣;美國NASA 在發射“毅力號”之前,有過4 次火星車登陸火星表面的成功經驗。而第一次執行火星探測任務的“天問一號”,即要一次性完成環繞火星軌道、登陸表面和巡視著陸地這三大步驟。
而在2021 年2 月10 日,“天問一號”經過200多天的飛行停泊進入火星環繞軌道時,包括《紐約時報》等外媒發表社評稱,“與登陸火星相比,繞火星軌道飛行的挑戰根本不算什么。”
登陸火星的危險之處,首先表現為抵達火星表面附近時,航天器需剎車減速,并以正確的角度切入火星大氣層——角度太陡會起火燃燒。過去,NASA 和歐洲的很多火星探測器都因此起火墜毀。
從穿越火星大氣層到著陸需大約7 分鐘,卻被國際航天界公認為“死亡7 分鐘”。著陸器進入火星大氣的時機、姿態和角度都需要精準的控制。又因為地球單程無線電信號到達火星需要20 分鐘,地面人員亦無法實時指揮——一切都要靠關于航天器的精準設計。
“天問一號”探測任務總設計師張榮橋表示,這短短的7 分多鐘內,“天問一號”需要從每秒4.8公里的速度急剎車到零,同時忍受上千攝氏度的高溫,歷經4 段不同方式的減速:
首先穿過火星大氣層,進行氣動減速,將速度降至460 米/ 秒;第二段,著陸巡視器打開降落傘,用拉拽的方式將速度降至95 米/ 秒;接著是反推發動機點火,速度減少到3.6 米/ 秒,將這個速度維持到最后;離地面100 米左右實現懸停避障,火星車即完成著陸。
偏偏是火星
在中國的“祝融號”發射成功以前,登陸過火星的只有美國、蘇聯。盡管后者在1971 年發射了火星3 號探測器,但僅在火星表面工作約20 秒即與地球失聯。
當前,各國火星探測器主要有三種:繞火星軌道運行,開展遠距離探測的探測器,比如,阿聯酋的“希望號”;降落到火星表面,進行原地探測的著陸器;能在火星上運動的火星車。
據不完全統計,自1960 年以來,世界各國圍繞火星的發射任務共計51 次。進入21 世紀,世界各國朝火星發射了17 個探測器。如今,還在圍繞著火星軌道繞行的探測器共計7 個,壽命最長的是NASA 在2001 年發射的“火星奧德賽號”。在火星表面上,除了“祝融號”火星車外,美國于2012 年、2018 年、2021 年分別成功登陸的“好奇號”“洞察號”“毅力號”火星車也在火星上巡視。
人類為何一窩蜂地探測火星?
就這一點,科學家運用的思路是“排除法”。以從太陽系中尋找生命的維度,與太陽距離的遠近可由此得出“宜居帶”。從八大行星的位置判斷,位于“宜居帶”的是和太陽距離適中的金星、地球和火星。
與地球大小、質量、體積相似的金星成了最早人類探測外空、發現生命的第一選項。20 世紀50年代,美蘇兩大國掌握了航天技術后,同時將金星作為航天競賽的首要目標。但人們很快認識到發射目標的錯誤。10 個在金星著陸的探測器,都來自蘇聯,但它們都“活不長”。最“長壽”的一個也在向地球傳輸了127 分鐘信息后“犧牲”。科學家們發現,這全因為金星的惡劣環境,地表溫度超過460 攝氏度,氣壓是地球的92 倍,還隨時會下硫酸雨。科學家由此下結論,金星的環境孕育出生命的可能性為零。
與此對比的是,火星雖然地表溫差大,平均氣溫為零下55 攝氏度,但一個最令人興奮的行動支撐是,火星上可能有液態水的存在。科學家們普遍推測,火星歷史上有過活躍的地質運動與河流,但由于太陽風的吹拂以及小行星的撞擊等原因,后來逐漸都消失了。
2003 年歐洲航天局發射的“火星快車號”探測器,于2012 ~ 2015 年期間在火星南極冰蓋下進行了29 次探測。2018 年,負責該項目的意大利科學家在《科學》雜志刊登論文宣布,該雷達系統發現了一片至少有數米深、直徑約20 公里的湖泊。一旦該發現進一步得到確認,該湖泊將成為人類在火星發現的首個液態湖,這“讓火星環境中微生物的存在成為可能”。只是,科學界對相關發現反對聲音猶存。他們指出,缺少足夠的熱源將上述湖泊的冰融化成水。而沒有水,生命的存在也就失去可能。
探索火星的本質
赴外星尋找生命,這對于全人類而言都是興奮的命題。“祝融號”官方微博曾解釋其奔赴火星的原因——“我是來火星找答案的:火星上到底有什么?它由什么組成?”
第一個登陸火星的衛星為美國“維京號”計劃的“海盜一號”,時間在1976 年。該著陸器運行了驚人的2245 個火星日,直到1982 年11 月13 日才與地面失聯。而與“祝融號”性質一樣、能在火星表面移動的火星車,是美國最早于1997 年通過發射“火星探路者號”,成功讓名為“旅居者號”的火星車著陸。在千禧年以后,美國共計發送4 個火星車到達火星表面,運行時間最長的“機遇號”——設計壽命最初為92 天,而其實際運行了15 年,創造了地球以外星球的最長徒步旅行紀錄。
有了多次登陸火星的經驗,美國壟斷了對于火星著陸過程中涉及的諸多技術參數,而這些參數,尤其對于“死亡7 分鐘”期間——地面與探測器完全失去聯系時,尤為重要。
中國的火星探測任務在此背景下開啟。國家航天局官網顯示,我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于2016 年正式批復立項,計劃通過一次任務實現火星環繞、著陸和巡視。
對于此刻的動因,中國火星探測首席科學家萬衛星院士在2019 年的一篇文章中談道:“如果說第一次熱潮的主題是探測競賽,比的是誰先跑得最快。
那么第二次熱潮的主題應是科學競賽,比的是誰先看得最深。”“人們已經不滿足于到行星表面看一看,而是看向時間的深處——研究行星的演化歷史,看向空間的深處——研究行星的內部結構,看向人類的深處——研究生命起源和尋找地外生命。”
這次,“祝融號”選擇巡視的烏托邦平原南部,過去美國的“海盜二號”也曾在此著陸,但著陸的方向偏北。該平原位于一個巨大的盆地中,位于古海洋與陸地的交界面,永久凍土層可能正好藏在該平原地表以下。有古代火神寓意的“祝融號”即將在這一寬闊的平原上度過90 個工作日。
這90 天,是中國航天人用過去5 年的日夜,以此點燃中國星際探測的火種。
(摘自“南風窗”微信公眾號,知止圖)